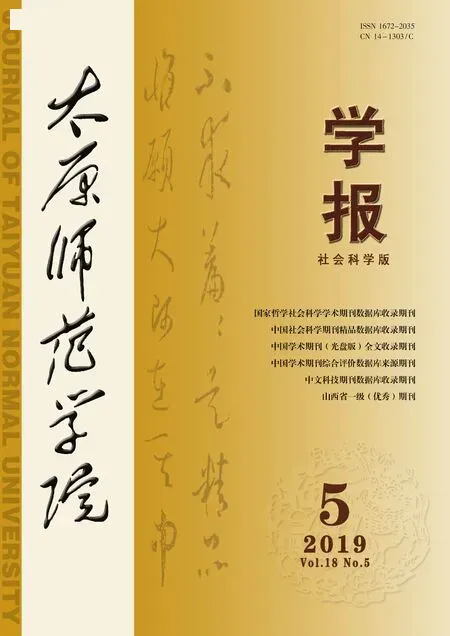性别语言中的语言意识形态研究
2019-01-20刘正霞陈玉秀
刘正霞,陈玉秀
(淮阴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3)
3月8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rking Women’s Day),在中国又称“国际妇女节”“三八节”和“三八妇女节”,是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而设立的节日。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妇女”一词逐渐被年轻人所嫌弃,而用“女生”或者“女神”表示对女性的赞美和欣赏,“三八妇女节”近年来也被广大网友称为“女生节”或者“女神节”。这一有趣的变化可从一个侧面看出语言的性别差异和语言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发展。本文试图从英语中性别语言的差异入手,研究语言意识形态在性别语言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揭示语言的性别差异和语言歧视产生的原因。
从意识形态研究语言的性别差异已成为语言学界的共识,早在1923年,丹麦语言学家Jesperson在《英语的发展与结构》[1]一书中就指出语言的性别现象;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语言学家Lakoff在《语言和妇女的地位》[2]一书中深入研究了语言的性别差异和语言表现;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Rumsey提出要建立一门新的语言学科——性别语言学[3];旅英学者王颖(2017)[4]提出了CHELF(Chinese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概念,从语言意识形态视角分析中国人使用英语的语境和文化,分析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在全球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语言学界多位学者如戴炜栋(1983)[5]、杨永林(1991)[6]、吴亚欣(2002)[7]等纷纷从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视角,运用语言学中的建构主义和语言变异理论,深入考察女性语言的语言变项和语言态度,分析男女对话中话语量、话题转换、话轮转换、话语方式的竞争与合作、会话场合等体现出来的性别差异,跨学科研究语言结构和使用的性别差异。
一、英语中的性别差异
现代研究表明,男女之间在体型和生理上各有特点,心理上也有明显差异,这种性别差异表现在感知能力、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和行为举止等方面。如果男生比较害羞、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行为举止像女生等,会被称为“娘娘腔”,英语中则使用“sissy”表达。 反之,如果一个女生像男生一样高声讲话、动作粗鲁,又会被斥不像个女生,英语中的“tomboy”“hoiden”就是描述这样的女生。社会生活中的这种性别差异反映在语言层面,就是语言的性别差异。
(一)语言材料的选择
对于语言材料的性别差异,国外语言学者早有针对语音或语法层面和性别的关系进行的模拟研究。Jesperson(1923)[1]首次描述了女性语言和男性语言的不同之处:在语言材料上,男女生会分别使用符合自己性别特点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Lakoff(1975)[2]从话语层面研究了美国女性语言的几个特征:在语音层面,女性具有更高的语音敏感度,女性音调高于男性,女性说话经常用升调,男性喜欢用降调,女性通常使用“ing”发音多于男性;在词汇选择上,女性经常使用“Oh,dear!”和“Goodness” 等口头语;由于对颜色的敏感,女性更擅长使用“mauve”“beige”“brownish grey”“aquamarine”等男性不太常用的颜色词;在语法层面上,女性喜欢使用反义疑问句表示商量和礼貌,男性更多使用肯定句。无独有偶,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1928)[8]在现代吴语研究中发现,吴语中同样也是女性声调高于男性,这一研究结果说明语言材料的性别差异在中外语言中都有相似的规律。
(二)言语行为的差异
语言具有社会属性,性别语言不是孤立产生的,而是由女性所处的语言群体决定的。在大多数社会阶层中(如印度或阿拉伯国家等),男性具有话语权,占主导地位,女性属于服从地位,表现在语言行为上,男性语言直接、自信、肯定,女性语言多含蓄、礼貌、委婉。Tannen(1990)[9]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男性多采用公共话题,如政治、 经济、商业等,男性交际的目的是提供信息、表达交流目的和展示话语主导地位;女性话题则局限于家庭、娱乐、时尚,女性语言通常具有个人化和情绪化特征,缺少男性的理性和直白。Lakoff(1975)[2]认为女性在言语行为上表现出的配合和礼貌是为了减弱话语的力度,显示女性的温柔和顺从,避免威胁男性的面子,这一心理符合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可见,言语行为的性别差异不是天生的,而是由男女所处的社会亚文化环境所决定的,性别语言存在于社会约定俗成的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层面,遵循社会通用的语言规范,体现语言的共同规律,符合社会文化对性别的期待。尽管现实社会纷繁复杂,生活交际千变万化,但是语言却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语言的性别差异成因值得深入探讨。
二、 语言意识形态在性别语言中的作用
19世纪初,法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特拉西在《意识形态概论》中首先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Rumsey(1990)[3]认为语言是唯一能将人们所隐藏的情感、认知、观念、信仰表达清楚的媒介,社会群体对语言所持有的共同的思想观念就是语言的意识形态。许多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对语言使用和话语方式产生重大影响,Silverstein (1979)[10]把说话者的语言意识和语言结构看作是影响语言发展的关键因素:“…Speaker’s awareness of language and their rationalization of its structure and use as critical factors that often shape the evolution of a language structure.”王颖(2017)[4]在研究CHELF的语言意识形态中指出,语言交际已经跨越地理边界,具有跨文化和跨语言的特点,语言使用者有权使用合适的表达完成交际目的,语言交际就是不断的话语协商和顺应(negotiation and accommodation)的动态过程。
(一)语言意识的同类化
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这一过程受意识形态不同程度的指导和调控,我们对世界感知不同,表达这些感受的方式也会不同。 Tollefson (2012)[11]认为,个体角色是在群体社会化过程中不断模仿和学习与自己性别相应的行为规范,不可避免地带有群体的性别特征,包括社会环境、语言交际的客体、语境的变化,语言能力绝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社会亚文化对群体不同的期待所致。Blommaert(2005)[12]在深入研究欧洲语言后得出结论:所有语言背后都有两种标准化语言政策的影响,两者折中后形成欧洲社会认可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即语言意识形态的同质化(Language ideological homogenism)。
由于社会特定的观念和对两性的刻板印象,女性在两方面承受着语言意识控制:一方面女性生活的社会环境和女性活动的团体教导女性必须以某种方式说话或者选择某种语言,在语言意识的指导和调控下,女性选择共同的表达模式和语言结构;另一方面媒体和公众利用传播的力量推广女性语言案例,试图创立某种标准化语言,制定性别语言的行为规范,使女性语言逐渐成为男性语言的附属品,失去语言的独立性。Irvine等(1989)[13]指出:性别角色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模仿学习获得的一套与自己性别相应的行为规范,在社会语言习得过程中,女性通过观察和模仿女性群体的理念和语言行为,逐渐将女性语言作为第一语言,如果拒绝这一语言形式,必然会脱离女性社会群体,甚至被孤立和嘲讽。在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女性语言交际的目的就是建立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善于倾听和妥协,所以女性语言表现为消极和顺从,属于语言的被支配地位。
(二)语言的性别歧视
研究性别语言,不可避免地要提及语言的性别歧视。语言性别歧视是指使用不对称、不平等或者侮辱性和歧视性语言来描述和评价女性。比如, 英语经常用“man”指代人类,如“Man can triumph over the nature.”男性语言很有力量(powerful),男士像“lion”,而女性像“chicken”,形容女性也通常使用“cookie”“peach”“honey”“tart” 等词汇。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文词汇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性别不对称,如“家属”“堂客”等词汇只能指女性,“警察”“司机”等词汇多指男性。 女性词汇逐渐贬化,男性词汇呈现褒义的较多,如“manly”指具有男人味, “a financial lord”指金融巨头,而相应的女性词汇“lady”逐渐呈现贬义,如“lady-dog”指母狗,“Ladies”直接表示女性洗手间。“brothers”是指义薄云天的手足,而对应的“sisters”则暗指从事不正当性交易的女性。巧的是,中文中表示女性的词汇,如“妇女”“小姐”“女司机”等近年来也被众人所排斥,贬化为带有特定含义的歧视语言,这也是文章开头提到的近年来“女神节”说法流行的原因。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的发展,女权主义的语言意识形态得到普遍认可,一些中性词被广泛接受,温柔体贴的男士被称为“暖男”;英姿勃勃的女生被称为“女汉子”,如“chairperson”“salesclerk”“police officer”等进入英语;在正式文体(如法律文本)中逐渐倾向使用“they”代替“she”或者“he”这样带有明显性别特点的词汇。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女权意识在性别平等上已经取得很大进步,语言性别差异一直存在,而语言上的歧视将逐渐得到改观。
(三)性别语言的二元论
语言的性别差异的产生具有多种原因,如社会性、心理性和生理性,但是总体而言都离不开语言意识形态的指导和约束。Razfar(2005)[14]指出,学界对于语言意识形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中立主义认为说话者的思想和信念受其所处的文化体系影响,形成女性语言的同类化,语言意识代表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必然具有文化的普遍性。批评主义则认为语言意识形态是主流社会维护权力和地位的策略,具有特定的社会认知和社会根源,是标准化语言意识形态对于理想化的同质语言的偏见和歧视。Tannen(1990)[9]把男性和女性分为不同文化的语言群体,用双重文化模式解释语言的性别差异(dual-culture model)。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反映在性别语言形式上的二元性,一方面女性语言的产生具有文化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女性语言不能独立于主流社会的思想观念之外,必然具有社会的共同性。根据语言的意识形态二元理论重新审视语言的性别差异,可以解释女性语言在词汇使用和语用选择上的社会差异,探讨女性语言形成的原因。
Silverstein(1979)[10]指出,语言意识形态是所有语言使用者对其语言结构和使用合法、合理化的信念。在性别语言形成的过程中,强势语言意识形态支配主流话语权,判定语言使用和语言结构的合理性。这种权力不平等的结果必然会反映在语言的不平衡上,出现男先女后、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等特殊的语言现象。Tannen(1990)[9]用九个词语概括女性语言的共同特点,即亲密、联系、融合、关系、和谐、社团、问题、新手、倾听。在约定俗成的语言表达中,通常遵循男先女后的原则,如在新闻报道中经常听到“某某总统和夫人”到访,中文称呼上有“一对夫妇”“一双子女”“公公婆婆”等。英语同样有男主女次的原则, 如“the farmer and his wife”等于“a farm couple”。在语言特征上,男性话语具有一定的任务倾向性,Tannen(1990)[9]把这种男性语言的特殊性归纳为:独立、排外、地位、信息、报道、比赛、专业、演讲。所以,性别语言在主流意识形态下逐渐发展为辩论与关联、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男性的世界是竞争,女性的世界是合作。Irvine(1989)[13]指出,这种语言结构的二重性涉及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的冲突,反映出不同性别群体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男女在语言中表现出的不同的语言意识倾向,用自身的语言标准衡量对方的语言行为,在主流社会群体中不断复制和肯定,表现出语言的性别自我中心主义,这也是语言差异形成的根本原因。
三、结论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语言也不断国际化。语言的国际化不仅仅局限于语音、语法和文字,还涉及语言群体的其他方面,即语言的意识形态,如文化象征、感情利益、政治权力等社会因素,语言意识形态反映出基本的社会制度,是语言的中介,也是语言使用的结果。从语言意识形态视角分析语言的性别差异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面对全球化的趋势,研究语言的意识形态在性别语言中的作用,推动性别平等,消除语言歧视,加深文化交流,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但是,语言意识在语言选择过程中的调控作用并不是自发的或与生俱来的,而是为了顺应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以及环境等因素而产生的,所以对这些因素的探讨也是很有意义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