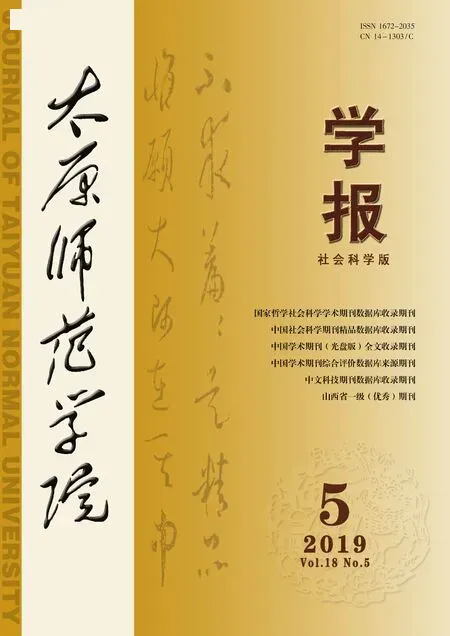郑瑜杂剧研究三题
2019-01-20吴秀明
吴秀明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郑瑜,一名若羲,字玉粟,号夕可,江苏无锡人,据周妙中《清代戏曲史》考证,其生年约为明万历四十年(1612),卒年约为清康熙六年(1667)。(1)周妙中《清代戏曲史》云:“郑瑜,一名羲,字玉粟,一字无瑜,又字伯昆,号夕可,别署正谊、西神。”笔者查方志传记资料,号“伯昆”的郑瑜为山东诸城籍。周先生所载郑瑜生卒年乃为诸城籍之郑瑜,非无锡郑瑜。清顾光旭《梁溪诗钞》所载引《义夫传》曰:“夕可妻周氏没,年止三十,终身不再娶,鳏居二十六年而卒。”郑瑜30岁的时候,妻子去世,后又独自生活26年,由此推算出郑瑜卒时56岁。[1]88郑瑜工诗文,善词曲,诗作存《园楼夜饮》《过采石吊李青莲》两首,清顾光旭收入《梁溪诗钞》卷十八。今知其所作杂剧五种,现存四种,即《鹦鹉洲》《汨罗江》《黄鹤楼》《滕王阁》四剧,总称为“郢中四雪”。另《椽烛修书》一剧,《远山堂剧品》著录,被列入“雅品”,[2]167无传本可见。今收录郑瑜作品的杂剧选集有清初邹式金《杂剧三集》。孙书磊《<杂剧三集>辑刊及版本流变考论》梳理了《杂剧三集》的顺治本、康熙本、诵芬室本三个版本系统。该文还详细列举了《杂剧三集》现存的本子及支藏情况[3]130:(1)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室藏顺治十八年(1661)原刻本,收录明末清初杂剧34种,存26种。郑瑜杂剧《鹦鹉洲》《汨罗江》《黄鹤楼》《滕王阁》分别收录于该书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2)康熙元年(1662)复刻本,这个本子对顺治本所选剧目重新编目,收有剧本33种。这个本子中郑瑜杂剧的收录情况与顺治本同。(3)民国三十年(1941)董康诵芬室重校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两部诵芬室本子,为同一版本。诵芬室本对顺治本、康熙本出现的误字进行了修订和补充,本文所引郑瑜杂剧所用版本为诵芬室本(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影印)。
关于郑瑜杂剧的研究尚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郑瑜杂剧的创作问题,二是郑瑜杂剧的本事来源与主题倾向,三是郑瑜的创作心态。
一、郑瑜杂剧创作考
前人及今人对郑瑜杂剧作品的评价都很高,从杂剧的发展阶段来看,郑瑜杂剧属于明清杂剧。明清杂剧在艺术体制、主题思想等方面别具特色,是继元杂剧之后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创作时间
对于郑瑜杂剧的创作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徐子方《明杂剧研究》一书把郑瑜四部杂剧和《椽烛修书》列入明中后期作家作品。[4]463《远山堂剧品》著录《椽烛修书》云:“南一折,宋子京燃椽烛,拥歌妓,修润《唐书》,是一番极富丽景象,词亦华美称之”。[2]167《远山堂剧品》后来进行了增补,最终成书时间为崇祯辛未年(1631)春夏之际,所以其著录的《椽烛修书》当为明代作品,且从《远山堂剧品》所载该剧的内容来看,此剧也应创作于明代。郑瑜其他四部杂剧的创作时间当为清初,因为从作品所塑造的抒情主体来看,入清“遗民”的形象贯穿于四部杂剧之中。尤侗《<读离骚>自序》:“近见西神郑瑜着《汨罗江》一剧殊佳,但隐括《骚》经入曲,未免聱牙之病。余子廖廖至郐无讥矣。予所作《读离骚》,曾进御览,命教坊内人装演供奉,此自先帝表忠微意,非洞箫玉笛之比也。”[5]934何光涛博士论文《元明清屈原戏考论》对郑瑜《汨罗江》的创作时间进行了推断。作者认为尤侗《悔庵年谱》《读离骚》创作于顺治十三年(1656),由此可知,《汨罗江》至少该在1656年之前就已经完成。[6]87虽然单以“顺治十三年(1656)之前”这个界限并不能确定该剧是作于明末还是清初,但是,从杂剧所塑造的“遗民”来看,对入清之后时局的感慨更契合作者当时的心境。
(二)创作背景
明末清初是一个引人关注的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改朝换代,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一次转型。自明末万历三十年(1602)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百余年中,政治层面的国难、党争、民族矛盾相互交织,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着江南人民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影响着这一地区的戏曲活动。
清卢文弨《常郡八邑艺文志》:“水土之风,情欲之俗,分言之则二,合言之则一。武进之土多丘陵原隰,故曰‘毗陵’,厚也。其民刚柔中,文质半。无锡之土多川原,其民柔,文胜质。宜兴之土多山林,其民刚,质有其文。江阴之土多坟衍,其民刚,质胜文。靖江之土多沙衍,其民刚柔半,质胜文。五土五民,此五邑大略也。”[7]江南地区科举兴盛,推崇文教。从郑瑜家族一脉观之,其二世、四世、五世、六世、九世、十世都是生员,有的被推荐到京师国子监读书,有的赠官至中宪大夫。七世伯兴考中进士,据《郑氏续修大统宗谱》载:“郑伯兴,字子振,号南溟。嘉靖庚子科中式第十三名举人,庚戌会试入贡第二十四名,赐进士及第。原任海宁县知县,丁忧后补商丘县升户部主事,历转员外郎中,出任浙江衢州府知府,升任河南道副使,转湖广按察司副使。”[8]此外《海宁州志稿·人物志·名宦》也有郑伯兴的传记,讲述他任海宁知县期间,恰逢倭寇犯边,布政司想要百姓多缴纳军饷,强征百姓打仗,郑伯兴为保护生民,损己奉给,补贴官兵。为官期间,他政绩卓著,宽厚爱民,深受百姓爱戴,[9]到郑瑜祖父邦傅已是第十代。《郑氏续修大统宗谱》记载郑瑜祖父邦傅“邑庠生,贡入太学”,伯祖邦才“国学生”,叔父似曾“长洲县庠生”,父仪曾“邑庠生举行优”。[8]郑瑜的祖上虽然算不上是达官显贵,但也是世代书香。耕读传家、清廉仁孝的家族环境对郑瑜的性格气质及精神风貌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郢中四雪”本事来源与主题倾向
“郢中四雪”主人公分别是祢衡、屈原、吕洞宾与王勃,这四位人物都是命运多舛、时运不济的古代文人。郑瑜杂剧创作以改编历史人物的际遇为法,达到借古喻今、观照现实的目的。
(一)《鹦鹉洲》
关于祢衡的生平记载主要见于《后汉书·文苑列传·祢衡传》:“祢衡,字正平,东汉末年人,少有才辩,而气高傲物。受之于孔融,终因恃才狂放,为黄祖所杀。”[10]764史书上的祢衡有才情,但常常违背世俗。孔融把他举荐给曹操,祢衡自称有癫狂病不肯去,曹操怀恨在心不肯重用他。祢衡在曹操宴宾客时赤身裸体,曹操受到羞辱,就把他送到江东刘表处,刘表不容他,转送到江夏太守黄祖门下,后因讥讽黄祖被杀,葬在鹦鹉洲上。
《鹦鹉洲》以《后汉书》为依据,写东汉末年名士祢衡被黄祖所杀后,魂魄到处游荡。一日,他乘风而返到了鹦鹉洲,遇到了当年与他同死的鹦鹉鬼魂,欲同去岳阳楼,会见吕洞宾。祢衡在路上与鹦鹉谈起过去的经历,认为自己的结局完全是前生注定,对曹操、刘表、黄祖全然没有责怪之意。此剧的亮点是对历史人物曹操的评价,剧中的祢衡一反历史上击鼓骂曹的史实,说当年骂曹是“昧了心”。他认为曹操是个大功臣,刘备不应该联合孙权对抗曹操,而应该与曹操合作,灭吴兴汉。他还为曹操杀伏后、杀皇子、幽禁汉献帝等行为辩护,认为曹操是不得已而为之。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历来人们对曹操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然而,郑瑜的《鹦鹉洲》认为曹操挟汉献帝之举是“替他藏拙”,曹操杀伏后是为了“保住汉祚”。[11]邹式金在《鹦鹉洲》卷首有眉批:“郢中四雪,才情横溢,舌藻纷披,真可嗣响临川。老瞒翻案,狡狯作戏耳,莫向痴人说前梦”。[11]邹式金认为,郑瑜文辞华美,继承了汤显祖的才情,但是为“老瞒”(曹操)翻案,只是做文字游戏,迷惑后人。郑瑜可能是目击了南明覆灭、异族入侵的真实场景,心中痛恨,借此剧以伐之。弘光帝继位后,南明各势力暂时妥协,但是政权非常不稳定,很快就导致了内部的党争和分化。驻守武昌的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顺势东下争夺南明政权,内阁首府马士英调江北四镇力量迎击左军,致使应对清军的江淮防线空虚,再加上后来政权内部又出现诸藩争立、互相倾轧的局面,不能集中力量对抗满清,导致了失败。曹操是东汉末年割据势力中实力比较强的,汉献帝回洛阳后,他以保护皇帝为由带兵进入洛阳,又以洛阳粮草不足劝汉献帝转移到许昌。许昌是曹操的老窝,汉献帝遂成了傀儡,曹操自封将军,能以皇帝的名义向诸侯发号施令,所以历史上多认为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郑瑜借汉末之事影射南明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腐败不堪的状况。
(二)《汨罗江》
《汨罗江》叙写的是楚大夫屈原才识广博却生不逢时,君主昏庸无能,又遭奸臣混淆视听,终被放逐贬官的事情。剧中混迹波臣的屈原与一渔夫在江边同游,渔夫请屈原将《离骚》编成一套北曲,自己以笛声相和,二人边唱边饮,放舟江中。这里的屈原一改忧国忧民的屈大夫形象,成了一个放浪形骸的作曲家,作者对屈原形象的改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屈原为了自己的“美政”理想九死不悔,面对社会的污浊黑暗,始终坚守自己高标的人格精神,为了与谄媚小人划清界限,甚至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这种不屈的斗争精神受到了司马迁的赞扬。《汨罗江》中屈原投江,混迹波臣,已经不再有当日的忠愤之心。在“时逢浊乱,君主昏庸”的政治背景下,他“自从江上逢渔父,学得餔糟与啜醴”[12],自言“况劫尘弹指,岁月如流。纵当日君明臣良,至今数千里云梦潇湘,未必仍属爽鸠之乐,即在我谏行言听,到今几千年芊昭屈景,未必永分轸蚓之尘”[12]。作者把屈原的执着和渔夫的旷达糅合到了一起。这里的屈原形象,正是郑瑜自身的写照。郑瑜生逢易代之际,早年曾渴望为官,当建功立业的理想无法实现、无法把握人生的时候,他只能通过隐逸来逃避现实,寻找精神寄托。作者借用“追寻”和“放逐”这两种主题形态,作为自己身处历史巨变之际纾解郁闷心境的出路。
(三)《黄鹤楼》
《黄鹤楼》主要写的是吕洞宾与柳树精之间的事情。关于吕洞宾的事迹,《宋史·陈抟传》载“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13]240,其中提及的吕洞宾是“神仙化”了的吕洞宾,不能看作是真实可信的历史。关于吕洞宾的身世,从宋时的野史、笔记、神仙通鉴等记载来看,历史上确有其人。史书载吕洞宾的祖父是唐代礼部尚书吕渭,父亲是海州刺史吕让。吕洞宾生于贞元十四年(798),累举进士不第。后在长安酒肆中遇到钟离权,受其点化得成仙道。[14]8文学作品中的吕洞宾是一个不得志而归隐的隐士,虽出身儒门却仕途无望,又遭逢乱世,所以只得避世隐居,游戏人间。
《黄鹤楼》写吕洞宾度脱柳树精成仙后,厌烦了天上的生活,故带着柳树精重游黄鹤楼。二人在路上把世上怪异的事情细数一番,最后重返蓬莱仙岛。《黄鹤楼》中吕洞宾作为仙人形象,并无元杂剧中仙人畅游天地的志趣。元代神仙道化剧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反映了当时严酷的高压政策下文人士子内心的矛盾和苦闷。马致远剧作中所塑造的神仙道人并非都是无欲无求的宗教使者,有的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失意文人。郑瑜剧作中的吕洞宾则完全是作者的代言人,他认为仙人更苦于世人,“五百年遭一风劫”“再五百年又遭一火劫”。[15]柳树精问及他和何仙姑相好,想必是仙家乐事,吕洞宾澄清:“世人演八仙庆寿,为凑脚数,把我扮作生,把她扮作旦,故有此胡说”[15]。柳树精又问他炼金银、飞剑斩黄龙的事情,吕洞宾说并无这些事。通过与柳树精一问一答,吕洞宾回想当时三醉岳阳楼度人成仙而不成的遭遇,感慨万端:满腹经纶之时,无人赏识;成了神仙之后,也只有老树精认识他。细数前世遭遇的苦事之后,吕洞宾道出心声:“我世间住怕了,天上也不愿去,还到蓬莱山去吧”[15]。此时的吕洞宾表现出强烈的出世精神,不愿为世俗所左右。剧中时刻关注时代更迭的吕洞宾,尽管表面在针砭时弊,骨子里却是对人世的留恋;表面上热衷于遁世,实际上是对现实社会的失望。
(四)《滕王阁》
《滕王阁》写唐代诗人王勃南下省亲,逢滕王阁重阳大宴,群公赋诗,王勃文思泉涌,作《滕王阁诗》一事。最早记录王勃创作《滕王阁序》本事的是宋代委心子撰《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三“异兆门·王勃不贵”中所引录的罗隐《中元传》。[16]43关于此事影响最大的说法是唐末五代王定保撰《唐摭言》卷五“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的记载:“王勃作《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胥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矣!’又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语。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17]60此事的真伪虽无法考证,但是《唐摭言》以纪实著称,加上王定保又是唐代人,相比于《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三“王勃不贵”载“唐王勃方十三,随舅游江左,尝独至一处,遇神叟”“神叟助王勃借清风之力,赶往都督宴会作《滕王阁序》”等情节可信度更大些。署名后晋沈昫所编《旧唐书·文苑上》也记载了王勃的生平,但对王勃作《滕王阁序》只字未提。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的《新唐书·列传·文艺上》则采用故事的形式记录了王勃作《滕王阁序》的事迹。北宋刊行的《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五“幼敏门”有“王勃”条,大致沿袭了《唐摭言》的内容,文字比《唐摭言》要多几十字,内容也更加丰富完整。[18]968北宋时人曾慥编《类说》卷三十四录《摭言》和《摭遗》中,有“滕王阁”“滕王阁记”。前者基本是《唐摭言》的简写,后者则是根据罗隐《中元传》改写。此后,南宋时期祝穆编纂的《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十一“天时部”收录“作滕王阁记”一则。
明末冯梦龙拟话本小说《马当神风送滕王阁》[19]2376在叙事上增加了曲折的情节(王勃坐船突遇风浪,作诗掷入水中,救了船上数人的性命,以及仙娥玉女招王勃至蓬莱赴会,最后落水成仙),使得故事更加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滕王阁》敷陈王勃作序文的全过程而成,诗人在把宴会的盛况铺叙到极致之后,转入对人生仕途的冷静思考。“望长安,日下南溟地势长。横倚着天柱北辰傍。有谁悲失路,关山难越状。”[20]其中“望长安”是希望得到皇帝的重新任用,无奈“关山”阻挡,难以逾越。在王勃不长的政治生涯中,他先因戏为《檄英王鸡》被赶出王府,后因擅杀官奴事件被免官,经历了他人生中的两次重大打击。从序文中王勃对自己仕途坎坷的嗟叹,可以猜测他写此文时心中的感伤:“嗟时命,从来多舛伤。略举那李广与冯唐,他易老难封同肮脏。”[20]王勃虽遭遇仕途的坎坷,但并不甘愿自弃,他相信“老当益壮,白首贪泉,洁青云涸辙汪。海虽赊,扶摇风壮”。剧末“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20],描绘了昔日兴建此阁的滕王在阁上举行豪华宴会的情景,与今日滕王阁的冷落寂寞形成鲜明的对照。
三、郑瑜的创作心态
“遗民”作为朝代更迭时期的一个特殊文化群体,其生存状态和文学思想历来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清初有七种流传很广的“明人遗民录”秘本:邵廷寀《明遗民所知传》、黄容《明遗民录》、朝鲜佚名氏《皇明遗民传》、陈去病《明遗民传》、孙静庵《明遗民录》、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秦光玉《明季滇南遗民录》。此后,又有谢正光和范金民合编的《明遗民录汇辑》,共收入遗民两千多人。关于遗民戏曲家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周妙中《清代戏曲史》、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郭英德《明清传奇史》、陈芳《清初杂剧研究》、曾影靖《清人杂剧略论》等。孙书磊《明末清初戏剧研究》从“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层面将郑瑜看作是由明入清的遗民作家。[21]88杜桂萍《遗民心态与遗民杂剧创作》从“遗民杂剧作家是一个将自己的政治身份乃至灵魂归属定位于明朝却生活、创作于清初的文人群体”入手,把郑瑜等14位清初杂剧作家划归“明遗民”。[22]359从郑瑜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四种杂剧都有明显的“隐逸”特征,渗透着佛教和道教色彩,比如:《鹦鹉洲》中鹦鹉诵“南无阿弥陀佛”“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11]等佛教教义,吕洞宾度脱柳树精后返回蓬莱仙岛,《汨罗江》中的渔夫和《滕王阁》中的马当神等是作者有意仙化的人物。从郑瑜留存诗作中可以直观地看出他的精神皈依。《梁溪诗钞》卷十八选录了郑瑜的《园楼夜饮》和《过采石吊李青莲》:
空涧倚城湾,濠梁兴未删。庭阴虚受月,水气远吞山。胜地烟霞外,幽人杖履间。萧然遗世意,真足起廉顽。(《园楼夜饮》)[23]
这首诗选取的意象很有特点,“空涧”“濠梁”“烟霞”“庭阴”“远山”“幽人”都带有朦胧的色彩,远望这些朦胧的景物,仿佛置身于幻象之中。作者即是这“幽人”,行走于缥缈山林之间。这首诗的后两句表明作者远离了庙堂和官场,一直保持着高尚的节操。这首诗中所表现的“空”与世间诸相的虚空相对应,渗透着佛教义理的味道。
秋山万仞落秋潭,湛湛枫林好驻骖。远跨长鲸君不返,独留明月照江南。采石矶头采白云,青枫满地落纷纷。夜深吹笛江亭上,明月窥人恐是君。(《过采石吊李青莲》)[23]
采石矶扼守长江天险,地势险要,锁钥东南,向来是江山易主的必争之地。李白一生多次登临马鞍山,在采石矶写下了《横江词》《望天门山》《夜泊牛渚怀古》等脍炙人口的诗篇。《过采石吊李青莲》这首诗首联宕开写景,由秋山、秋潭、秋枫、秋江、秋声等组合而成的广阔画面,具有一种悠然不尽的神韵。诗中“独留”“夜深”二词构成一种萧瑟自然、风流自赏的意趣,同时也点破了作者孤独的内心世界,流露出一种飘逸不群的隐逸情怀。但是,这种“隐逸”生活并不是作者心中的理想生活。当现实的困窘和苦涩无法改变,满腹的志气和才华也无法付诸实践的时候,作者只能寻求一种自由的、与世无争的方式来消解内心的苦闷,这种苦闷并不会因为“隐逸”本身而冲淡,作者依然饱尝人生的艰辛,常常借助怀旧的情绪来表达对命运的无奈感和对现实的幻灭感。
明清易代,原有的社会秩序轰然崩塌,文人士子兼济天下的责任感促使他们深居庙堂力挽狂澜,而儒家传统教义又督促他们忠于前朝。双重的思想标准,使得明末清初的戏曲作品既有前代的儒家传统又有时代的新变特征。郑瑜的杂剧善于从正史、诗歌、民间传说中寻找素材,在素材处理的过程中少用虚构,加之选材类同,使其戏曲作品显现出死板、缺乏生气的弊端;杂剧的主题倾向反映了作者在易代背景下既追求隐逸自由又渴望劝世化民的矛盾心态;杂剧艺术上的新变主要体现在艺术体制上的创新。总之,郑瑜的杂剧贴合了清初杂剧的总体特征,反映了转型时期杂剧创作的时代风貌,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