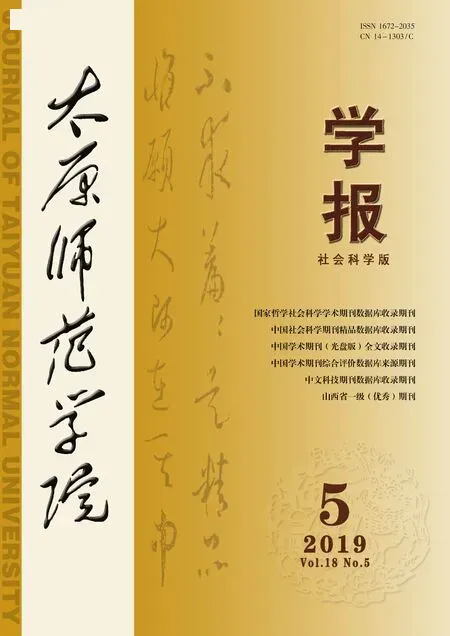论唐宋佛寺壁画诗之演进
2019-01-20贾晓峰闫建阁
贾晓峰,闫建阁
(1.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2.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山西 晋中 030031)
佛寺本身是供奉佛像、持戒安禅的宗教场所,也是建筑、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的荟萃之地。众多佛寺存有壁画,尤其是一些通都大邑的佛寺,由于财力雄厚、交通便利,往往有著名画师在寺中进行壁画创作,如《贞观公私画史》载瓦官寺、法王寺、龙宽寺、王观寺、白雀寺等有顾恺之、顾骏之、石道硕、沈标、董伯仁等所创作的壁画30处。[1]27-29唐代吴道子,北宋高益、高进之、李成等著名画师,也都在佛寺中进行了壁画创作。这些壁画多规模宏伟、色彩富丽、艺术精湛。唐宋文士的生活与佛寺有密切联系,在他们游居佛寺的过程中,壁画常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进而在诗歌中予以吟咏。
一、从简约到尽形:唐代佛寺壁画诗的流变
中国古代最早吟咏佛寺壁画的诗歌当是唐开元年间张说贬谪岳州时所作的《灉湖山寺》:“楚老游山寺,提携观画壁。扬袂指辟支,睩眄相斗阋。险哉透撞儿,千金赌一掷。成败身自受,傍人那叹息。”[2]929此诗首联写诗人来到佛寺观赏壁画,颔联描写诗人观赏壁画释仪像时的情态,颈联描写所见壁画中赌博的局部内容,尾联对赌博的事情发出感慨。诗中有对壁画内容的呈现,有诗人的感怀,似乎中国古代诗人一开始对佛寺壁画吟咏即表现出艺术的自觉,其实不然。张说之后,盛唐吟咏佛寺壁画的诗歌只有四首,分别是孙逖的《宿云门寺阁》、崔国辅的《宿法华寺》、岑参的《出关经华岳寺访法华云公》、杜甫的《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其二。这些诗篇中,佛寺壁画仅是诗人咏写佛寺的一个组成部分,只用一句提及,十分简略。如岑参《出关经华岳寺访法华云公》中称:“长廊列古画,高殿悬孤灯。”[3]2043再如杜甫的《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其二中称:“天阴对图画,最觉润龙鳞。”[4]800这种情形说明,佛寺壁画在初盛唐时还没有真正进入诗人的创作视野。
中晚唐时,诗人对佛寺壁画明显有了更多的关注,笔者初步统计,共有诗27首,数量近初盛唐时的7倍。
中唐的一些诗歌开始关注壁画本身的艺术价值。如孟郊《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昭成寺》中称:“瑶策冰入手,粉壁画莹神。”[5]4233白居易《游悟真寺诗》中称:“粉壁有吴画,笔彩依旧鲜。”[6]4746柳公权《题朱审寺壁山水画》中称:“朱审偏能视夕岚,洞边深墨写秋潭。”[6]5484这种情形说明佛寺壁画艺术开始进入诗人的审美视野,但诗歌表现得十分简约,壁画艺术只是诗人在游寺过程中关注的内容之一。
晚唐五代的一些诗人对佛寺壁画的艺术有了更多的关注。如李群玉《长沙元门寺张璪员外壁画》,郑谷《传经院壁画松》,段成式、张希复、郑符的佛寺联句诗《游长安诸寺联句·常乐坊赵景公寺·吴画联句》等。特别是欧阳炯的长篇歌行《题景焕画应天寺壁天王歌》,篇幅较长,共七十六句六百二十余言,比之前佛寺壁画诗的艺术呈现更为细致,且夹叙夹议,其中有三个部分对壁画的内容进行了描写:
鬼神怪异满壁走,当檐飒飒生秋光。我闻天王分理四天下,水晶宫殿琉璃瓦。彩仗时驱狒犭术装,金鞭频策骐驎马。毗沙大像何光辉,手擎巨塔凌云飞。地神对出宝瓶子,天女倒披金缕衣。
斜窥小鬼怒双目,直倚越狼高半胸。宝冠动总生威容,趋跄左右来倾恭。臂横鹰爪尖纤利,腰缠虎皮斑剥红。飘飘但恐入云中,步骤还疑归海东。蟒蛇拖得浑身堕,精魅搦来双眼空。
逡巡队仗何颠逸,散漫奇形皆涌出。交加器械满虚空,两面或然如斗敌。圣王怒色览东西,剑刃一挥皆整齐。腕头狮子咬金甲,脚底夜叉击络鞮。马头壮健多筋节,乌觜弯环如屈铁。遍身蛇虺乱纵横,绕颔髑髅干孑裂。眉粗眼竖发如锥,怪异令人不可知。科头巨卒欲生鬼,半面女郎安小儿。[7]8728
这些诗句描写了华丽的宫殿、浩荡的仪仗,还有鬼神奇异的服饰、变幻的姿态、壮健的坐骑等,从整体到局部,从静态的场景到动态的鬼神举动,描述得细致入微。这样的描写虽有错杂纷乱之感,但在具体细微的壁画形态描摹上,显然比初盛唐和中唐时的佛寺壁画诗更进一步。
二、呈现与评议交融:宋代佛寺壁画诗的特征
宋代的建立是朝代的更迭,而在文化的承续上并不是一个突然性、断裂性的新变。唐宋文化的转型始于中唐已是定论。宋人在吟咏佛寺壁画时,延续着中唐以来对壁画进行细致呈现的艺术风貌,只是更多融入了诗人对画作的评议,这是宋代佛寺壁画诗的显著倾向。
对佛寺壁画艺术进行评点在晚唐已经出现,段成式、张希复、郑符有联句诗《游长安诸寺联句·崇仁坊资圣寺·诸画联句》:“吴生画勇矛戟攒,出变奇势千万端。苍苍鬼怪层壁宽,睹之忽忽毛发寒。棱伽效之力所殚,李真周昉优劣难。活禽生卉推边鸾,花房嫩彩犹未干。韩干变态如激湍,惜哉壁画世未殚,后人新画何汗漫。”[7]9016诗中较少描摹画作本身,主要是段成式、张希复、郑符对吴道子、卢棱伽、李真、周昉、边鸾、韩干这几位画家的作品分别进行点评,这种评画诗在唐代的佛寺壁画诗中十分稀见,其意义在于开启了用诗歌品评佛寺壁画的先河。宋人则在此基础上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如梅尧臣的《和原甫,同邻几过相国寺净土院,因观杨惠之塑吴道子画,听越僧琴,闽僧写宋贾二公真》:“青槐夹驰道,方辔下麒麟。朅来游绀宇,历玩同逡廵。吴画与杨塑,在昔称绝伦。深殿留旧迹,鲜逢真赏人。一见如宿遇,举袂自拂尘。金碧发光彩,物象生精神。岁月虽已深,奇妙不愧新。惊嗟岂无意,振播还有因。乃知至精手,安得久晦堙。二僧感识别,请以己艺陈。或弹中散曲,或出丞相真。览古仍获今,未枉停车轮。”[8]3017诗中称拂去尘灰,吴道子的画映入眼帘,神采显现,飞扬生动,梅尧臣感慨道:“乃知至精手,安得久晦堙”。全诗没有一句对壁画的内容和艺术作细致的描摹,全是概括性的感慨和议论。从诗歌艺术的角度说,这样的诗篇没有具体的形象呈现,不能使读者对壁画艺术有更为形象的、直观的认知,未免空泛。
画与诗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绘画展现的是一个瞬间的情景,通过画笔细致入微地将整个情景进行全方位的呈现,在线条和色彩流动组合中给观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当诗歌把绘画作为书写对象时,诗歌语言无法对画作的每个部分、每个细节进行细微呈现,其优长在于语言的丰富性有利于对画意进行补充和阐发,揭示绘画者的创作意图和情感,获得更多的象外之意。宋人对这两种艺术门类的区分及交融有清醒的认识,他们的诗中更多是把佛寺壁画的艺术之美和诗人的艺术感悟融为一体,使诗歌呈现出“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9]9的艺术境界。如刘攽的《和李公择题相国寺坏壁山水歌》:“苍山本自千万丈,怪尔断落盈尺中。枯松挂崖正矫矫,白云出谷方溶溶。忆昨高秋十日雨,百川涌溢腾蛟龙。丹青坏劫不可驻,金碧拂地俱成空。人间流落万余一,掇拾补缀几无从。当时画手合众妙,得此诚是第一工。松阴行人何草草,秃帻小盖马色骢。长涂未竟不得息,啸歌正尔来悲风。巨灵擘华疏黄河,夸娥移山开汉东。海波芥子互出没,大雄游戏神与通。我今与君未尝觉,指视壁尽将无同。新诗飘飘脱俗格,得闲会复来从容。”[10]7140诗中详尽描摹了画中的山水,有苍山、枯松、白云、行人、车马、江海等。坏壁上的苍山是断剩的一片,崖上的枯松姿态高峙不凡,山谷中腾起溶溶白云,还有松阴下的行人、青白色的马,以及巨灵疏河、夸娥移山这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情景。全诗语言劲健,如与欧阳炯《题景焕画应天寺壁天王歌》中对壁画内容的呈现相比较,也显得层次更加分明。刘攽用浑荡恣肆的笔触传达出画作的高妙传神,同时还恰当地夹杂着叙事和议论:“忆昨高秋十日雨,百川涌溢腾蛟龙。丹青坏劫不可驻,金碧拂地俱成空。人间流落万余一,掇拾补缀几无从”,叙写壁画毁坏的过程;“当时画手合众妙,得此诚是第一工。……海波芥子互出没,大雄游戏神与通。我今与君未尝觉,指视壁尽将无同”,议论壁画艺术的高妙以及诗人在观赏壁画时的感受。这些夹叙夹议的章法结构使诗歌不再单调和板滞,但其中的议论只有两句,也未免显得不够深透。
在宋诗中既能恰当呈现了佛寺壁画的艺术,又有深刻透辟评议的是苏轼的诗,苏轼在凤翔任签判时作有著名的《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11]317-318。全诗的主要内容就是评议吴道子和王维绘画的艺术差异。诗中称吴道子的画:“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诗歌接着用壁画的具体内容来印证诗人对吴道子绘画艺术的认识:“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这样的描写主要是说明吴道子画作能对形象进行准确生动的呈现。诗中称王维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如果说吴道子画的“雄放”是壁画呈现出来的风格的话,那么王维画的“清且敦”则是壁画意境的揭示。苏轼对王维壁画的内容进行描写时,用“鹤骨”来形容佛祖的弟子,并用“心如死灰不复温”来形容这些弟子枯槁的情态。诗中写“两丛竹”,用“雪”和“霜”来形容竹子的清雅劲节。这样的描写是淡化物态的具体形貌,着重凸显物象的内在意绪。最后,苏轼总结吴道子和王维绘画艺术的高低,称吴道子的画是“画工”之画,而王维之画不求形似,摆脱了形式的过分束缚,意出象外,更显风神,这正是后世认可的中国绘画的较高境界。
南宋佛寺壁画诗的吟咏方式基本延续着北宋佛寺壁画诗呈现与评议相融合的创作范式,如张表臣《观高邮寺壁曹仁熙画水》、曾季狸《雷公保国寺画壁》、杨万里《太平寺水》、释德葵《题海慧寺画水壁》、戴复古《毗陵太平寺画水呈王君保使君》等诗,或表现壁画的内容,或表现对壁画艺术的珍视,或评价画作艺术的高妙,并没有特别的创举。可以说,历经唐宋,佛寺壁画诗从审美视角和叙写方式上臻于成熟。
三、唐宋佛寺壁画诗演变之缘由
从张说的《灉湖山寺》到欧阳炯的《题景焕画应天寺壁天王歌》,唐代诗歌对佛寺壁画的书写明显呈现出从简约到细腻的演进过程。其演进原因从宗教学、壁画史的角度都难以解答,因为佛教在初盛唐时已经兴盛,吴道子这样名满天下的大师也主要活动在盛唐时期,而佛寺壁画诗在初盛唐时期并不发达,所以对佛寺壁画诗演进的原因概只有从唐代诗歌的审美追求上予以探究。
初唐时,六朝的绮艳诗风得以延续,其后以“四杰”和陈子昂为代表的诗人追求情思浓郁、气势壮大,倡导风骨兴寄,佛寺壁画奇幻怪异的格调显然与这一时期的诗学追求不在同一审美视域中。同时,壁画在佛寺中毕竟不是佛寺建筑群的主体,在唐帝国充满勃勃生机的历史时期,人们追求恢宏壮丽,诗人对佛寺的关注也极易忽视壁画的存在,故初唐诗歌对佛寺壁画表现较少的情形便可理解。盛唐诗人崇尚风骨,追求兴象玲珑和自然远韵,在常人眼中怪奇、夸张的佛寺壁画明显与诗人们的诗学追求有着一定的距离,故盛唐诗人对佛寺壁画也较少关注。这种情形至中唐时发生变化,其中出现了以韩愈、卢仝为代表的崇尚怪奇风格的诗歌创作倾向。佛寺壁画的艺术格调无疑与此时的诗学追求相一致,所以出现了一些关注壁画艺术的诗篇,并直接影响到晚唐。晚唐时的社会动荡,使文士的昂扬理想受挫,心态更为内敛,诗歌所呈现出的特征之一是追求细美,情思幽约,诗歌在呈现物象时,往往比中唐诗歌更为深细,于是出现了像段成式、张希复、郑符、欧阳炯等人的诗歌对佛寺壁画的详尽描写。
宋代佛寺壁画诗的突出特征是评议较多,其原因当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北宋文官政治的推行和儒学的复兴,极大地增强了士大夫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北宋自建立起就受到北方契丹族的威胁,之后又受到西夏、金的长期侵凌,使得宋人显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12]35成为文人士大夫中普遍的风气。这种风气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便是多“以议论为诗”。第二,宋代文化昌明,宋人的整体文化水准较高,诸多诗人既是文学家、书法家,又是画家,他们对诸多门类的艺术往往都有敏锐的判断力,具有绘画艺术的眼光,可以对佛寺壁画艺术进行评点。第三,从诗歌艺术的角度而言,诗歌一味地对物象进行呈现,未免单调肤浅,如若单纯地议论又未免空洞浮泛。宋人把绘画艺术的呈现和品评融为一体,既呈现了精妙的壁画艺术,使人历历在目,具体可感,又发挥了语言艺术的特长,进一步补充和阐发画意,弥补了造型艺术的局限,使有限的具体形象和想象中的无限形象相统一,形成如食橄榄、历久弥新的艺术效应,这是诗歌艺术的一种进步。
要言之,自中唐后诗人对佛寺壁画有了自觉的审美观照,这是宋型文化开启的表征之一。至宋代,佛寺壁画诗把壁画艺术的呈现与评点融为一体,反映了宋人好议论、精思理的时代文化特征。唐宋佛寺壁画诗的不同风貌,对我们认识唐宋文化的转型以及同类题材诗歌的创作情况,都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