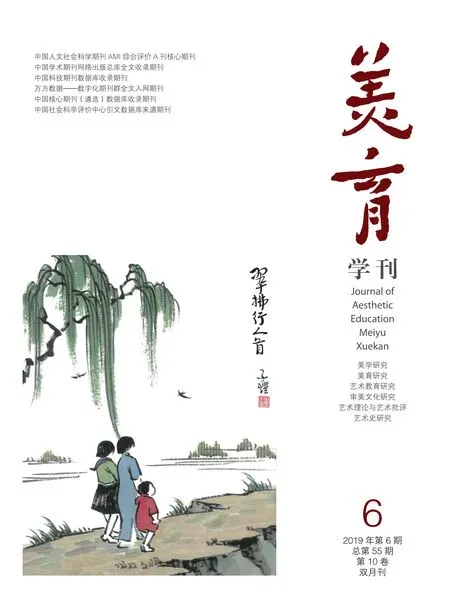现代美学视域下的生活美学思想浅析
2019-01-15都晓晓
都晓晓,吴 聪
(中原工学院 服装学院,郑州 河南 451191)
一、生活美学思想溯源
美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并在中西文化之间相互撞击和融合。在(西方)“他者”镜像的映照下,中国近现代美学逐渐获得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中国古典美学正是获得了美学这个学科视角后,“返观”自身才将那些潜在的美学智慧照射出来[1]54。中国有深远的生活审美传统,而且从未中断,这是和中国自来的文化传统和思想相关,从这方面来说,中国现代的生活美学只是对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回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真正的艺术都在表现一种自然的和谐,这一和谐的重要标志就在于是否出现一种与自然界的生态发展规律一致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如本土道家提倡“法天贵真”“道法自然”的审美理想,儒家强调以“仁”为核心的伦理境界、“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还有中国传统意味的“凝神观照”等思想,都是强调要把观照的注意力倾注于自身,以外在的投射物或参照物为自然,这样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生态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应该效仿自然中的和谐以及这种和谐而呈现的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所以,中国美学理论的建构虽然取向是西化的,但是却蕴含着本土化的意味,它试图通过将审美与生命连通起来,来构建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系统。王国维的“境界—意境”说、朱光潜的“诗境论”、宗白华的意境说,将中国美学的研究对象带入中国古典美学的领域。至此,中国的美学在经过外源式的、后发的建构过程后,与西方美学站在比肩的位置上,生长出作为现代世界美学的三大新潮之一的生活美学。
由此可见,现代生活美学以儒道和中国古典美学的综合审美理想为渊源,以现代人的生活为审美客体。生活美学的研究对象即从古至今的人类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之下所蕴含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感。人们在享受着美食、阳光、空气、美景时,都有一种感性的体验过程,中国自来就有对这种生活中常见美的对象的感性表达,《诗经》即是对上古人民日常生活的记录,其中不乏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分享。儒家“礼者履也”的生活艺术,道家“逍遥乐道”的乐生之美,中国古典美学崇尚的“生生”之观,不论生活的层级,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皆有留存。
(一)据儒依道的生活之美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中考证“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义”。即将“美”解释为“羊大则美”,而“善”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伦理本位特质的词语,儒家美学正是在“美”与“善”交融的意义上来定位的。中国文化对美的解释一开始就是以味觉、触觉的感官为发展基点,结合“善”的伦理本质,最后用美作为审美判断和评价,即“美”的事物或者人物一定也是符合善的标准。
儒家以“仁”为基础的美学思想强调人要遵循仁义之道,才能使个人和社会和谐发展,获得自由,进入美的境界,“仁学的最高境界……是自由的境界,审美的境界”[2]。《论语·先进》记载,曾点对答孔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后孔子叹“吾与点也”。曾晳(即曾点)的行为可能与当时在鲁国兴盛的祭祀之“礼”直接相关,而非仅仅是一场“春游”或“授业”活动。所以说,“吾与点也”的这种认同,其核心就在于祭礼之“礼”而非单纯的“审美”。换言之,曾点所向往的乃是“崇礼之美”,“美”附庸于“礼”而并不独立于“礼”[3]。孔子时代认为“礼乐相济”,但随着“礼崩乐坏”,转化为“礼”“情”的合一。《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即“性感于物而生情”,在儒家的思想体系范围内,一直强调的“仁”“礼”“乐”的核心概念,最后统一归为“情”的主导作用,所以说,儒家的思想可以归为是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
“美善合一”作为儒家美学的底蕴,“仁”作为儒家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其经过演化后最终归为一种有“情”的生活指导思想,最终都落实在入世的生活态度中,作为中国传统审美价值和判断的标准。
(二)“生生之妙”的中国古典美学
从思想根源上讲,儒家和道家思想生成的基本动机都是源于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切忧患意识,不过,他们的应对之道却是不同的,儒家面对现世的忧患意识要求采用仁义之道加以救济,可以说是入世修行,得到个体和社会的和谐从而达到美的境界;道家思想面对现世忧患意识则要求通过“无为之为”达到“与道冥一”而体悟解脱。可以说二者都是由个人的生存意识出发,以现世生存为起点,终极归宿都是求得生命审美境界,即中国传统思想中“美”最开始是作为描述感官之“生”的对象,到后来加入“善”的因素具有的社会伦理意义,最终才作为审美判断和评价的标准。
中国文化内含一种“宇宙大全”化的观念,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观,一切万有(包括人在内)“莫不相互涵盖,相互呼应,心物一体”。由此而言,这种从生命深层“体味”来的智慧,就相应使得中国传统具有了一种“泛艺术化”或“审美化”的精神。也就是说,在人与万物的和谐交融中,都体现出中国人对美的独特领悟,都在较高的境界层面包孕了美的因子[1]33。
一言蔽之,在中国本土化的视野中,不论是“美善合一”的儒家审美理想,还是“美真同一”的道家审美理想,都是在中国古典美学的孕化下生根发芽的,既有面对现世忧患意识的相反的应对方式,又自觉具有同体共生的互补性。儒家“尽善尽美”“美善合一”的审美理想,与道家“道法自然”“美真同一”的审美理想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真、善、美的融会贯通。
二、生活美学的社会渊源
生活美学的研究对象是日常生活中的美学,即在生活中遵循的哲学观、时空观以及生活观,在对生活观做出分析之后,进而需要研究和探讨此种生活观对士人和平民的审美实践的影响,如对自然、艺术、休闲娱乐等问题的观念和理想的影响。《易经·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文化自来就有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之分,所以,生活美学也要研究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的审美现象。这一层面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关涉到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文化层面,如服饰、饮食、园林、日用器物、工艺技艺等;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民俗风情、文娱活动、节日娱乐等相关的精神文化表现[4]。美学是在文化实践中生长起来的,是对文化实践反思的产物[5]。社会与文化状况不仅仅是美学原理产生的条件,后者更是前者的反映。所以,对中国生活美学社会渊源的探索应该从中国传统古典美学下的传统艺术和日常生活中美的事物出发,关注审美现象的表达形式,发掘中国深厚的文学艺术传统和独特的审美传统。
(一)悦心会意的畅形生活
《庄子·知北游》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仪。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认为“美”存在于天地之间,需要人去寻求和了解,而去了解和回归的途径就是通过“道”这种万物之理,还对何为圣人提出了描述,认为圣人应接受天地之间的美,而后能够通达万物之缘由并顺应它,这才是圣人的“无为之为”,也是一种“大为”或“至为”。
从思想根源上观之,儒道两家思想生成的基本动机,同是出于“生活的忧患意识”,不过儒家是发于忧患而要求加以救济,道家则始于忧患而要求得以解脱。由此而来,儒道两家的生活美学都是源自对“礼崩乐坏”或“人为物役”现世的深切忧患[6]。可见,道家关注和忧患的也是从未离开生活的人生——宇宙人生,天道的运行如何落实在人道;道家的美学主要就是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环环相扣的关系中循而向上发展,从而达到一种自然无为的求“道”的境界,一种本真、纯真、至真的“大美”之境。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道家审美理想追求的“大美”就是体“道”后,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并循循相生的美的状态,这状态彰显的是体“道”过程中悟到的自我之“真”、天道之“真”,“美真同一”是道家的生活美学。可见,生活美学的思想渊源中带有一种追求悦心会意的畅形生活,而从生活中抽取出一种类似修炼者的心态来面对人生。
(二)向美而生
原始时期,人类刚刚使用劳动工具,生存的竞争与大自然恶劣的气候和匮乏的资源相关,身边一切的劳动工具、器物、与人相关的物质环境都以实用性为主要目的,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类对于美的意识就已经开始萌芽,或者是从水中看到自己的倒影,或者是从陶土掉进火堆后变得更加坚硬而迸发的灵感,原始人类的审美意识已经产生。这种审美意识是在对大自然的敬畏下产生的,例如原始人的生殖崇拜、巫术、图腾文化等。人、物、自然社会三者对立的状态下,人对物和自然社会的感性认知不会被认为是“美”的,故这个时期的“美”并无造化生活及孕育人类情感的功能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审美经验逐渐积累,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思想争鸣,各种哲学思想相继出现,发展至秦汉时期,儒道思想相继成型,孔子“游于艺”和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等理想化社会思想的提出,已经具有生活审美化的内涵。当时的文化及艺术也遵循这些理想与学说,呈现出一种稚拙古朴、雄浑大气的粗犷气象。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器皿,也呈现出一定的美学特征,如河北满城汉代窦绾墓出土的长信宫灯,以跪坐的奴隶为整体造型,宽大的袖筒是过滤油烟的暗藏信道,既起了分离油烟的作用,又有美化宫灯的功能。可见,这个时代的人们已经开始以自我意识为主导进行审美创造,以现实生活中的物象为载体,将自我的初级审美情感投入到客体对象,再次进行加工创造,人对“美”的追求更进了一步。
魏晋和晚明,是生活美学理论发展的高潮期。魏晋时期玄学思潮深刻影响了六朝士人的立身行事,人们开始了对外形和风姿之美的关注,自觉地开始对服装、容貌、神态讲求审美,出现了对外貌的审美品评,同时开始注重对生活中个人内在气质差异性的认知,对这种差异性进行美学评判,从而促进了审美活动的生活化与人格化。东晋以后,佛教又进入了士人的日常生活,对其生活观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时,世族政治和庄园经济为士人的政治身份和日常生活提供了多重保障,他们籍此方能尽情地追求衣食的享受、山水的娱乐、文艺的创作[7]。他们营构园林,纵情山水,与亲友往来游宴,追求安稳恬逸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态度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具体到服饰上来说是“褒衣博带”,巾、帢、木屐等服饰元素。园林中则有体现士人审美情趣的动植物,文人的游宴,如兰亭之会、金谷之会、民俗节庆等;士人还经常组织“谈玄饮酒,至肤脆骨柔”,配合流行的“褒衣博带”的秀骨清相,一派飘逸灵动的景象。可以说,在魏晋时期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人、物、社会生活在时空上被放大了,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同时也成为审美客体或者审美参照物,日常生活方式的扩张使具体的物质文化与审美现象更多元开放,社会生活真正成为审美对象,审美理论更加具有层次感,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生活化出现第一次飞越。
晚明时期形成了中国传统文人所实践的审美生活,甚为强调行动者“心”所游履、攀缘之场域,应与现实生活保持某种或具体或抽象的距离:其一是超越生活现实、构建出非日常生活范畴的独特景观——以至于行动者将在虚实辩证的情境中,营造其审美生活空间;其二是和光同尘、顺适平常,既不离世间却又能超脱俗累——仿佛行动者系以一种审美心境来参与世俗生活的游戏规则,从而使其日常行动升华为一种审美姿态[4],人对生活审美的认知,落实到修身养性的功夫。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出现为底层劳动人们带来较自由的发展空间,表现在民间是民俗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出现各类民间艺术形式。进而言之,人、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甚至文人与日常之物、日常生活融合为一体。
无论哪个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的艺术、文化、科学、历史等都是向美而生的,生活与美相互渗透,但生活之复杂多样、丰富、深刻远不是被认为的美的艺术品所能涵盖的,在“泛审美化”的当代,生活美学以向美而生的理念将生活与艺术完美整合。
(三)“物”的生活美学
明代后期社会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市民经济开始繁荣,闲适消遣之风日益炽盛,在艺术领域的表现就是民间出现大量关系日常生活的赏玩型器物清玩、渲染闲适生活的小品文和生活美学著作。器物清玩在晚明社会的流行,表明了晚明士民整体日常生活水平的提升,其实质是物质性在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审美和精神生活领域的全面凸显。换言之,晚明时代出现了一种将情感、审美的精神生活世俗化、日常化、物质化的生活美学潮流[8]。可以说,有多少种生活方式就有多少种美的感受,如果将明清时期平民和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划分开来,可以用“雅”和“俗”概括,雅俗在当时社会市民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并无高下之分,所以只要在社会中出现的美化生活的人类行为方式,都可以成为生活美学的研究对象。
对于市井大众而言,表现在民风民俗、服饰、饮食娱乐、日用器物、工艺技艺、节日欢庆等底层人民的生活方式中。民风民俗是地域性普通大众生活方式的文化现象,是他们对生活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后的情感表达;日用器物是手工艺人精湛工艺技艺的展示,是民间艺术家对于生活中美的理解和传达;服饰、饮食起居都是生活中美的展现,最为大众熟知的是明式家具,其独特的榫卯结构、简洁的造型、流畅的线条,提升了中国传统家具的艺术价值。
对于当时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审美鉴赏力的文人士大夫而言,这种生活美学的要义在于借助“物”来装点和营造一种审美化、艺术化的日常生活情景,以便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积极的情感和审美体验,进而彰显其才情和趣味[6]。例如,花与茶在为中国人提供形、色、香、味等感性的审美感受的同时,还沉淀了历代中国人的生活情趣和理想。正所谓“茶令人爽”“花令人韵”[9],“闲停茶碗从容语,醉把花枝取次吟”的闲雅、恬淡之境,也成为中国人心向往之的理想生活状态。赏花、品茶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的生活情趣之寄托和表达,更开启了一种整体性的艺术化、审美化的日常生活的可能性。[10]
三、现代生活中的生活美学表现
在“审美泛化”的后现代文化中,“美”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从人类居住的乡村、城市、建筑,到人类的着装、使用的日用品,还有美食、美景等都有“美的踪迹”,大众的日常生活被越来越多的“艺术的品质”所充满。那么现代生活中的“美”到底是什么?可以从“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两个概念理解。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
通过分析生活美学的社会渊源和人类审美经验的发展可以发现,人类生活既有向美而生的发展意识,也有体现在具体审美物象中的审美经验的积累和审美观念的不断外化与发展。然而在当代,生活中美的事物无处不在,现代的人无时无刻不被美包围,小到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细节,大到一个公共空间建筑设计或城市的规划,皆以美为目的,可以说现在是“审美泛化”的时代。“审美泛化”包涵双重的逆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另一方面则是“审美日常生活化”[7]。“日常生活审美化”是针对文化转向而言,它将审美态度引进现实生活;而“审美日常生活化”是针对艺术的大致取向,现代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日渐消融。
所以,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当代,大众的生活被越来越多的美的物品、艺术的品质所充盈,显然,当代的设计文化在其中充当了先锋角色,即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被设计的,这样就形成了被设计的“审美文化”。这种被“设计”出来的审美文化中,所强调的是任何日常生活用品都可能以审美的方式来加以呈现……这样现代设计所覆盖的领域就被无限扩展,从时装、美容的身体包装到工业设计、工艺品和装饰品的外在成品,从室内装潢、城市建筑、都市空间规划到包装、陈列和编辑图像的视觉表象,都体现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关怀[1]85。这种由审美泛化而来的文化状态,被鲍德里亚形容为“超美学”,也就是说艺术的形式已经渗透到一切对象之中,所有的事物都变成了“审美符号”[7]。
(二)审美日常生活化
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相对的是“审美日常生活化”,在艺术的领域里,“审美日常生活化”力图抹去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欧洲19世纪末出现的艺术思潮如“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在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间得到极力推崇,表现明显的有艺术界的先锋艺术运动。“未来主义”用浮夸的文辞宣告过去艺术的终结和未来艺术的诞生,提倡无政府主义,在绘画上强调速度感、空间的循环、物体的透明以及噪音的韵律;20世纪60、70年代开始,欧美的前卫艺术开始走向观念、行为和装置,走向大地与环境,出现了一种“反美学”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日常生活世界,试图探索艺术与其置身的社会语境与文化背景的关系。就是在这种艺术生活化的趋势中,艺术和日常生活的界限变得逐渐模糊。如后现代“激浪派”代表博伊斯在卡塞尔文献展上策划了种植七千棵橡树的展览,并喊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
现代生活美学思想就是将最广义上的美与生活置于一种辩证的关系中来考察,这两者辩证对话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其实美的活动就是回到事物本身的生活方式,即生活就是艺术。“泛审美化”时代的到来,给现代人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生活美学因其身后的中国传统,具有绵延不绝的审美内涵,经由人、物、社会三者之间审美关系的作用,绘出古代和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素描。同时,现代人类生活方式、物质、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给人类的审美经验以更多的层次。在现代美学语境和社会环境下,生活美学是不断更新完善的,进而指导人们的审美追求,打造有“情”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