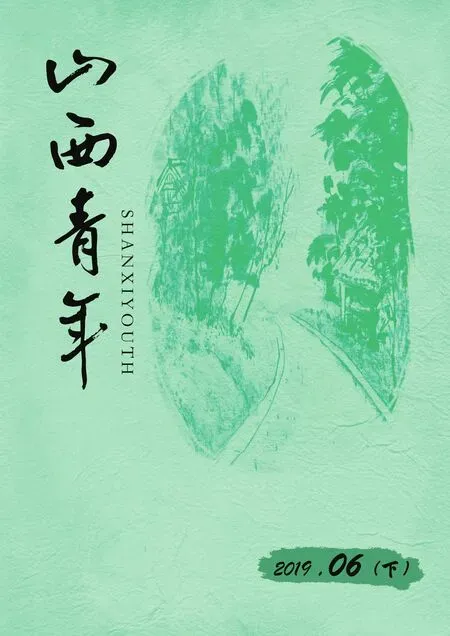论《杜诗详注》中杜妻杨氏的形象
2019-01-15潘越
潘 越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史料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关于杨氏的史料记载仅有两则。《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1]与《云仙杂记》:“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2]从这两则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杨氏出身书香门第,本是大家闺秀,嫁给杜甫后过着清贫的生活。遗憾的是其他史料中关于杜妻杨氏的信息少之又少,且其中许多史料尚存在争议,这为我们解读杜妻杨氏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从杜甫的诗集当中,我们不难窥探出诗人对自己妻子的爱。在那沉郁顿挫的笔调下,依旧有着儿女家长的细腻,二十余首的诗作,为我们展现了一位贤良、勤劳、饱经生活磨难的妻子形象。
一、饱经磨难,吃苦耐劳
乱世出诗歌,人间有情暖。杜甫多次以“老”、“瘦”称妻,其中饱含着夫妇二人对生活艰难的独特理解。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杜甫写道:“老妻既异县,十口隔风雪。”[3]天宝十四年冬诗人由长安往奉先县探望妻儿,杜甫在诗中以“老”形容妻子杨氏,可见杨氏在年仅33岁就已经吃了很多苦,饱受生活的磨难。在诗人的叙述当中,我们看到她长期独自照顾家庭和年幼的儿女,无怨无悔地为诗人撑起半边天。诗人在外寻求功名时,杨氏设法捎去书信慰藉“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丈夫两手空空归家时,也能够面色如故待他如往常般好,“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
杜甫用平实的手法,没有过多的拘泥于杨氏外形外貌的细致刻画,反而只以简单的老、瘦二字勾勒出杨氏那饱经生活磨难的人物形象。乱世能够安家照顾子女,在磨难当中依旧不放弃生活的希望,吃苦耐劳,勤俭朴素。
二、挂念丈夫,思归妇人
杜甫和杨氏对彼此的思念之情在《月夜》和《一百五日夜对月》中最能体现。诗歌写作于被叛军拘押长安期间,以两个不同的角色角度叙述了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诗人设想妻子月下独望,把无形的思念化作了有情的泪水,相思无眠。短短几句就勾勒出了一个美丽的思妇形象。[4]《一百五日夜对月》中借神话牛郎织女的传说以及诗人的浪漫想象,传达出有情人之间感情的真挚与高尚,在清新的文字中又暗含着离别的悲情与苦痛,道出了久别之后双方都盼望团圆的愿望。至德二年八月,分别了一年多的杜甫和妻子终于团聚。诗作《羌村三首》便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人命危浅,命如草芥,杨氏甚至认定他不会生还了,丈夫忽然出现在眼前,这对于日夜思念的杨氏来说简直不敢相信。由“惊定”到“拭泪”,这中间过程的转换是真情的流露,是一个思妇形象最好的阐释。
三、生活艰难,贤良慈母
在生活困苦时,身为母亲的杨氏亲眼看着幼子饿死,她难以抑制内心的悲痛,嚎啕大哭,“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发阆中》中记道“女病妻忧归意速”其中“归意速”可见出杨氏对女儿的慈爱,丈夫离家三月她都没有因为家中的事打扰他。但女儿生病她便乱了分寸,连忙给丈夫写了告急信,催其归来。杜甫深知妻子对儿女的感情,在他看来“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杨氏无愧为一个贤良慈母。在生活安稳时,杜甫“昼引老妻乘小艇,眼看稚子浴清江。”杨氏乐相伴,夫妻二人共乘一支小船,看着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清江中戏耍,共享天伦之乐。杨氏的贤良品质还体现在她比普通的女性更善于营造诗意的生活氛围,会“画纸为棋局”缓解生活的压力。
四、结语
杨氏是一个名门之女,对贫病困苦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不离不弃,甚至用尽自己的能力支撑家庭、照顾儿女。诗人在诗中对妻子的描写包含了感激、内疚、不安等种种复杂情感,他在诗中自嘲“笑为妻子累,甘与岁时迁”。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说:“中国言夫妇之情最好者,莫如处乱离之世如杜甫,处伦常之变如陆放翁等之所作。”[5]诗篇中我们看到了一位贤良、知书达理、饱经生活磨难的女性形象,她坚毅勤俭、热爱生活,在任何时刻都一如既往地支持杜甫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推断,杜甫之所以能够在战乱时代依旧能保持对文学的初心,和妻子杨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文学史上大多关注的是杜甫本人的创作,但是在其背后默默付出的女性形象却少有人知,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伴随着新世纪女性主义的兴起已经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男性诗人背后的成功因素。笔者认为杜妻杨氏身上具有中华民族传统女性的可贵品质,这一类女性身上传承着民族文化的精髓,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