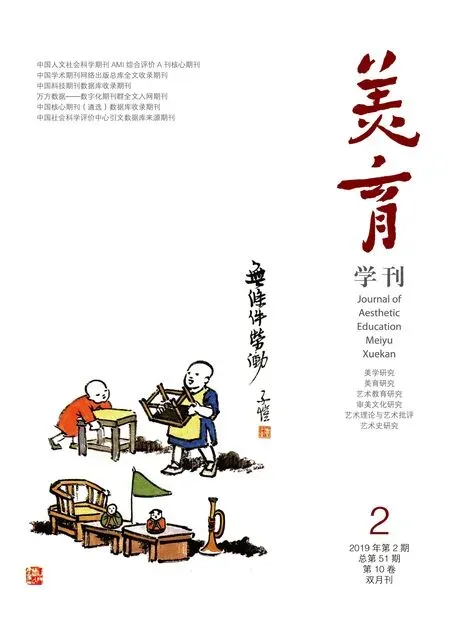论美育在人生论美学中的“目的论”地位
2019-01-15吴时红
吴时红
(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当前的美学研究由于回避和消解了“美论”,从而导致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流于肤浅,致使美学的科学性大打折扣,陷入“有美无学”的泥淖;由于混淆“美论”和“美感论”,从而导致对美感的探讨流于混乱,致使美学的人文性大打折扣,陷入“有学无美”的泥淖;由于歪曲地阐释“美”和“美感”,从而导致对美育的探讨流于片面,致使美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都无法落到实处,陷入“无学无美”的泥淖。
为了将当前的美学研究从上述“泥淖”中打捞起来,我们首先将“美的本质”和“美感”问题,放置到人生论美学视域下,不仅阐明美的本质问题的重要性,并从思维方法革新的角度初步尝试探询和解开“美的本质”的奥秘;其次重审“美”和“美感”的辩证关系,并确立起美感问题在美学基础理论重建中的核心地位。在此,我们还需要在人生论美学视域下,继续对“美育”与上述两者的逻辑关联进行全新的理解与解释,以便凸显美育问题在美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目的论”地位。而这首先要求从“美育”概念的辨析入手。
一、对美育本真内涵的辨析与还原
关于“美育”,一般而言,我们会习以为常地将其看作是“审美教育”或“美的教育”的简称。它的目的是通过“审美”体验使作为个体的人的情感达到感性与理性、个人性与社会性的高度统一而最终进入生存的自由境界。这本是不言自明的基本常识。然若细加斟酌推敲,不难发现,这一对“美育”内涵的常识性的“熟知”,却并非“真知”。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仔细辨析和探究。
第一,“审美教育”或“美的教育”这个概念中的“美”是静态的美,还是动态的美?审美是将美作为“审”的对象或客体,还是审美也就是美?第二,“美育”这里的“美”含义是什么?仅仅只是“优美”形态的美,还是可以包括“崇高”形态的美,甚至包括作为“优美”和“崇高”的“反”“合”形态的“丑”“怪诞”和“悲”“滑稽”等形态的美呢?第三,审美或美+教育构成“审美教育”或“美的教育”的概念组合方式到底意味着审美或美的目的在于教育,还是相反?还是兼而有之呢?对于这些看似常识性的“熟知”的重新回答,恐怕才能构成我们对“美育”的真知。
先说第一个问题。“审美教育”或“美的教育”这里的“美”,在人生论美学看来,既是静态的美,也是动态的美,是两者的有机结合。这是因为,不论把“美育”看作是“美的教育”“审美教育”“美学教育”“美感教育”等概念中的哪一个的简称,其基本的含义大体不外乎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美育一般是指培养“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的“完全之人物”[1](以下简称“完人”)的理想教育,它的要旨在于培养完整的人、完善的人格和完美的人性等方面,因而,它是通过“造就健全的人,进而造就健全的社会”[2]31的教育。狭义的美育一般是指“专人”(与“完人”相对)的现实教育,它的要义在于培养艺术专门技能和专门人才等方面,因而,它是培养“艺术欣赏能力”[2]31的人的教育。所以,不论是培养“完人”还是“专人”的“美育”,其实都是首先将审美活动作为美育的最基本的手段或材料。具体来说,就是将不同的客观对象的“美”(主要包括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不同表现形式的“美”(包括优美、崇高、悲、滑稽、丑、怪诞),不同存在方式的“美”(静态的美和动态的美),都纳入审美活动的视野,作为美育的手段和材料。因而,作为人生论美学视域下的“美育”,就不仅包括自然美在内的“客观对象”所进行的审美活动,还是围绕以包括优美、崇高等在内的“表现形式”所进行的审美活动,也还包括围绕静态的美和动态的美两种不同的美的“存在方式”所进行的审美活动。
再说第二个问题。“审美教育”或“美的教育”中“美”的含义,在人生论美学看来,是“大美学”视野中的美。首先,这里的美,既可以看作是“优美”等美的不同表现方式,还可以看作是作为美学基础理论之核心内容的“美感”,也可以看作包含上述二者的“美学”(思想或理论体系)。所以,简单地将“美育”拘囿在美的某一表现形式(如优美)或“艺术”的领域,则是十分狭隘的。因为“美学绝不限于艺术哲学,在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也存在审美的现象”,因而“美育也绝不限于艺术教育,美的形态很多,审美教育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3]33其次,作为“美育”概念里的美,应看作是立足于“美的本质”探询之思想前提的“美”与“美感”的辩证统一,是以“美论”“美感论”等为前提的美学对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的教育,因而,谈论美育,绝对不能一上来就将“美”局限在审美现象的世界,排除美之为美的本体探询,一开始就在美与美感的随意混淆中,将美育作狭义的理解,认为美育只是优美的教育。而应对这里作为“美育”之“美”的含义的理解始终秉持宏阔的视域和开放的视野:美不仅包括优美,还可以包括崇高、悲、滑稽、丑、怪诞等美的不同表现形式。这样来理解美育,我们才能真正走出当前美育研究中“无美无学”的泥淖。
再说第三个问题。“审美+教育”或“美+教育”构成“审美教育”或“美的教育”(均可简称“美育”)的概念组合,既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审美的目的在于人的教育或育人,也不是相反,人的教育或育人,最后笼统地落实在审美问题上,在人生论美学看来,它实则是审美和教育的有机融合。因为,正是通过审美或美作用于人所产生的影响、教育和教化,最终使感性的人上升到理性的人,并使两者达到完美的统一。因而,我们需要将美育看作是“以美育人”,使人成为人格完善、人性完美的完整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统一的人,审美或美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正如席勒所深刻指出的:“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3]116与此同时,美育还可以是“以育美人”。因为,正是包括教育在内社会劳动的专门化和分工化的出现,才使得一部分人可以专门从事精神创造的事业,这样教育就承担起了对这部分人的素质和能力进行培养的天然使命,不仅一般意义上国民的审美素养的提高有赖于教育,专业化、技能化、精巧化的艺术能力(如罗丹所说的“发现美的眼睛”)和本领(如马克思所说的“音乐感的耳朵”)的修得,更是与教育的环节密不可分。这也是罗丹的名言,这个世界不缺少美,缺少的只是发现美的眼睛和马克思的名句“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4]所揭示的基本道理。
因此,正如在教育领域培育人的审美眼光与美学眼界和能力,就是美育题中应有之义一样,在美学领域提升人的品格,实现人的境界的完善,也是美育题中的应有之义。总之,审美教育这里的美或审美,既是教育的手段和材料,也是教育的目的和成品,“如果把美育理解为以美为手段,从而达到道德的目的,那就是把美降低为功利性的东西,有失美之真谛”[5]。反之亦然,审美教育这里的教育,既是审美的手段和材料,也是审美的目的和成品。审美和教育这两者是有机一体,水乳交融,不可拆分的,共同达到我们所谓的“以美育人”和“以育美人”的辩证统一。
二、从“美”与“美感”的不同层面来综合推进“美育”研究
在对“美育”的本真内涵进行了以上辨析和探究之后,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来推进“美育”研究呢?
结合在人生论美学视域下对美学基础理论的全新解读和阐释,我们认为,应根据“美”与“美感”的不同层面来综合推进美育研究。具体说来,应在“优美”—“悲”—“丑”,“崇高”—“滑稽”—“怪诞”这两组“美”的表现形式的有机链条及其所引发的不同的“美感”中,全面地考察和辨析美育问题。这里至少有这样两方面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首先,从“美育”与“美”的逻辑关联来看,人生论美学认为,美育并非只是美对人的教育,准确说,美育不仅是优美意义上的美的教育,还包括崇高甚至还可以包括悲、丑、滑稽、怪诞等这些不同“表现形式”上的美对人的教育。它们与优美意义上美的一样,都是美育题中应有之义。过去我们一提及美育,不论是将其作为上述论及的美的教育、美感教育或美学教育中哪一种的简称,我们这里所谈论的“美”,一般而言,都几乎一致是指一种优美形态上的美,这样的一种对于美育理解,显然是十分狭窄的。
这是因为,如果按照李泽厚将美的形态划分成“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这样的三个层次来看,这种被狭窄化了的美育观念中所探讨的美,只是相当于李泽厚所说的“悦耳悦目”审美形态上的美,而抛弃了“悦心悦意”和“悦神悦志”形态上的美。如果我们再翻检一下西方美育史,不难看到,无论是现代西方美学思想的奠基人康德,还是“美育”思想的系统阐述者席勒,都没有如此狭隘地看待美育与美和美感的关系。康德认为,“形式上虽然优美高于崇高,但在内容上崇高却胜过了优美。这样,在达到‘最高的善’的历程中,崇高比‘美’又更进了一步”[6],所以要实现康德哲学所追求的人自身的本体建构,“美”与崇高这两者又是缺一不可的。以康德美学为思想基础来系统构建西方美育理论体系的席勒,更是明确地指出:“假如没有美,我们的自然使命和我们的理性使命之间就会有不断的斗争。假如力求满足我们的精神使命,我们就会忽视自己的人性,并且准备离开世界的一切时机,在这个我们必定依赖的活动范围内就永远只能是些陌生者。假如没有崇高,美就会使我们忘记自己的尊严。我们被接连不断的快感弄得虚弱松懈,就会丧失性格的朝气蓬勃,而且我们被存在的这种偶然形式紧紧束缚住,我们的永恒使命和我们的真正祖国就会从眼前消逝。只有崇高与美结合起来,而且同等程度地培养我们对二者的敏感性时,我们才是自然的完美公民。”[7]107基于此,席勒呼吁“崇高就应该联合美,以便使审美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7]106-107,从而实现其“全面和谐发展的完整的人”[3]16的审美和美育理想。综上不难看到,那种望文生义、顾名思义地认为美育只是美的教育的观点,不能不说是对于美育的一种极大的曲解甚至是误解。
其次,从“美育”与“美感”的逻辑关联来看,人生论美学认为,美育并非只是一种“优美”形态的美所引发的“美感”(不妨简称“优美感”),作用于人所生的爱怜感和同情心的教育,还应是一种“崇高” 形态的美所引发的“美感”(不妨简称“崇高感”),作用于人所生的敬畏感和尊严感的教育。两者共同构成美感和美育的“正”面关联;与此同时,美育还应是一种“丑”和“怪诞”形态的美所引发的“美感”(不妨分别简称“丑感”和“怪诞感”),作用于人所生的羞愧感和亵渎感的教育。两者共同构成美感和美育的“反”面关联;还应是一种“悲”和“滑稽”形态的美所引发的“美感”(不妨分别简称“悲感”和“滑稽感”),作用于人所生的彻悟感和乐生感的教育。两者共同构成美感和美育的“合”面关联。综合起来,在美育和美感的逻辑关联上,存在两组“正反合”的有机链条:“优美感—丑感—悲感”的美育;“崇高感—怪诞感—滑稽感”的美育。
先说有机链条上“正”的方面。美育应包括优美感和崇高感之于人的教育。在人生论美学看来,“优美感”和“崇高感”尽管属于不同的美感形式,但二者都具有美感的“正”价值属性。所以我们在探讨“美育”问题的时候,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看待,既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厚此薄彼。在我们看来,以优美感、崇高感作为美育的手段,能够真正实现人的爱怜感和敬畏感等情感持续保有的目的。
这是因为,大凡基于感性对象和个人趣味,并力图实现对个人欲望的超越,从而使人达到个人性和社会性、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而进入生存的自由境界的内容,都属于美育所需要培养的情感。这其中以优美感和崇高感为首要的构成方式。所以,人生论美学视域下的美育观反复强调,要造就具有健全人格和完美人性意义上的“完人”,除了优美感的教育之外,还同时需要崇高感的教育。只有将这两种美感整合起来,我们对美育的理解才可能是完整的。与此同时,人的爱怜感和敬畏感等人的情感的持续保有的真正实现,反过来又会促进人的优美感、崇高感的形成,从而使优美感、崇高感的培养成为美育的目的之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度申明美育是广义的和狭义的统一、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
再说有机链条上“反”的方面。美育还应包括丑感和怪诞感之于人的教育。在人生论美学看来,“丑感”和“怪诞感”尽管属于不同的美感形式,但二者都具有美感的“反”价值属性。因而,以丑感、怪诞感作为美育的手段,目的并不在于宣扬和倡导这两种美感所引发的羞愧感和亵渎感等情感,恰恰相反,目的在于通过对于引起人们的丑感和怪诞感的事物和对象的厌恶和抛弃,进而真正实现人的优美感和敬畏感等情感持续保有的目的。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艺术和审美领域,尽管也常常描写和直面“丑”和“怪诞”的事物和对象,但它们的全部要义并不是在于“对丑的病态追求”[8]和怪诞本身的过度偏好(即便是一向以“丑”和“怪诞”的展示为叙写能事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也是如此),而往往是以实现对二者的超越和提升为旨趣的,否则这样的“病态追求”和“过度偏好”就是对于当代艺术的糟蹋。正如罗丹所说的,“平常人总以为,凡是在现实中认为丑的,就不是艺术的材料——他们想禁止我们表现自然中使他们感到不愉快和厌恶而触犯他们的东西。这是他们的大错误。在自然中一般人所谓的‘丑’,在艺术中能变为非常的美”[9],罗丹身体力行的艺术杰作《欧米哀尔》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化丑为美”,化丑感为优美感。正如桑塔耶纳所说的,如同“出色的机智昭示新鲜的真理”一样,“出色的怪诞也会呈现新鲜的美”[10],这种“新鲜的美”,也就亲近我们所谓的“崇高”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化怪诞为崇高”,化怪诞感为崇高感。
最后是有机链条上“合”的方面。美育还应包括悲感和滑稽感之于人的教育。在人生论美学看来,“悲感”和“滑稽感”尽管属于不同的美感形式,但二者都具有美感的“合”价值属性。所以我们在探讨美育问题的时候,也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看待,既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厚此薄彼。在我们看来,以悲感、滑稽感作为美育的手段,能够真正实现人的彻悟感和乐生感等情感持续保有的目的。
这是因为,如果说人生的根底注定是“悲”的美感体验的话,那么,人生在世时更多的是“滑稽”的美感体验。也许有人会担心这种“悲”“滑稽”的美感体验之于人的教育,是否会产生种种负面的消极影响,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人生论美学所重构的美育观看来,悲感作用于人的美育所谈的“悲”,并不是悲观厌世、消极避世之“悲”,而是悲悯怜人、悲愤感人、悲怆敬人之“悲”,“悲的体验中不仅有损失的悲哀和痛苦,而且也有光明的感觉”[11]138。滑稽感作用于人的美育所谈的“滑稽”,并不是全盘消解价值和意义世界之后一味的戏谑和搞笑,而是伴随着深沉的生命顿悟和乐感意识而来乐天和自嘲意义上的“滑稽”。可以说,这里的作为“合”价值属性的悲感和滑稽感是完全综合并融通了优美感、崇高感和丑感、怪诞感之正反价值属性的。与此同时,人的彻悟感和乐生感等人的情感的持续保有的真正实现,反过来又会促进人的悲感、滑稽感的形成,从而使悲感、滑稽感的培养成为美育的目的之一。因为“人在深深地怜悯悲时,不仅体验到感情极度紧张后的轻松和某种缓和,而且在道德上变得高尚,在审美上豁然开朗”。[11]138
综合起来,人生论美学视域的美育,不仅是优美感和崇高感之于人的教育,而且还包括丑感和怪诞感、悲感和滑稽感之于人的教育。是这两组与“美育”紧密关联的“美”和“美感”有机链条的合理展开。如果说,优美感和崇高感作为美感的“正”面价值属性,更多的是在“积极入世”的维度展开人生论美学视域下的美育观念和实践的话,那么,丑感和怪诞感作为美感的“反”面价值属性,更多的是在“消极避世”的维度上展开人生论美学视域下的美育观念和实践的。两者构成饶有兴味的有机互补。而悲感和滑稽感作为美感的“合”面价值属性,更多的是在融通了“积极入世”和“消极避世”两个维度上展开人生论美学视域下的美育观念和实践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但都毫无例外地加深了我们对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领悟和理解。
三、确立“美育”在人生论美学中的“目的论”地位
通过上述我们对于美育的本真内涵的辨析和还原,以及对于美育与美和美感不同层面的逻辑关联的考察,不难看到,在人生论美学看来,美育不仅是广义的,而且是狭义的。美或美感不仅是美育的手段,还是美育的目的。美育不仅包括优美、优美感的教育,还包括崇高、崇高感等在内两组“正反合”有机链条中不同的美的形态和不同的美感形式的教育。至此,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对于美育的全新阐释,对于人生论美学视域下的美学基础理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美育在人生论美学视域下的美学基础理论中又应居于何种位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美育与美学基础理论,美育与人生论美学理论体系这两者的关系分别来谈。
首先,从我们对于美学基础理论的理解与解释来看,美育是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目的、落脚点和归宿。关于此,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美学是美育的起点,美育是美学的归宿。美学不应该成为虚幻的、高不可攀的抽象物,它通过美育实现人类对真、善、美追求的最高境界。”[12]因而在人生论美学看来,美学基础理论一般包括“美的本质”“美感”“美育”三大基础理论,这个意义上的美学研究通常应由“美的本质论”(简称“美论”)“美感论”“美育论”三个方面构成。以上三者虽各有侧重,却有机一体。其中,“美论”是基础。它为美学研究确立科学的思想依据和理论前提,我们所反复申明和强调的实践论美学的理论精髓,正集中地体现在这个方面,这是我们在第一部分所集中论述的主题。“美感论”是核心。它为美学研究构建起美轮美奂的美学理论和思想体系的大厦,人生论美学所蕴含的基本观念正集中体现在这个方面,这是我们在第二部分所集中论述的主题。“美育论”是目的和归宿。它为美学研究落实、应用并转化“美论”和“美感论”研究的理论成果,并最终将其与人生论美学所追求的理论目标直接关联起来。而这也正是第三部分所集中论述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作为美学基础理论重要构成部分的“美育”问题,不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它关涉到美学基础理论本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践问题,因为它关涉到美学基础理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可以说,从目的和归宿的维度来看待和定位“美育”之于美学研究的地位,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于美学基础理论的理解和阐释,而且使我们在美学研究中始终能秉持和坚守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理论立场和综合视域,从而不仅使我们在汲取实践论美学理论精髓和中西方优秀美学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人生论美学成为一门有理论说服力的美学,而且还使我们依据这样的美学理论和思想体系重新理解和阐释的美学基础理论,走向行动,走向人生,走向对完美人性、完善人格乃至“完整的人”的重塑的康庄大道上。这样的“走向行动”“走向人生”“走向对完美人性、完善人格乃至‘完整的人’的重塑”的美学,才是真正融理论性与实践性于一炉的人生论美学。
其次,从我们所构建的人生论美学的理论体系看,美育也是美学研究的目的、落脚点和归宿。如前所述,依据实践论美学所确立的科学理论基础和思想依据所构建的人生论美学,是致力于研究人(作为个体的人和社会的人有机统一)的生存活动及其意义和价值的美学。因而,这样的美学理论体系是注定会以落实并力图完成“人是目的”(康德语)、“完整的人”(席勒语)、“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语)等“人学”目的论意义和价值为理论旨趣的。这是因为,作为实践论美学当代构建的人生论美学,其不同于中国传统和近现代以来的诸多人生论美学思想的最明显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坚守“美的本质”的探讨并以其作为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从而自始至终保证了其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立场;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之前和之后的西方诸多人生论美学思想的最明显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坚守“美感”的多维度多层面的探讨并以之作为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从而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其美学理论体系的人文性立场。而且,它还始终坚守上述科学性立场和人文性立场的辩证统一,并力图将其落实到“美育”的研究上来。从而使人生论美学视域下的“美的本质”“美感”和“美育”问题真正连缀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不仅有效地回应了上述我们对于美学基础理论的理解和阐释,而且使我们将这个“完整的有机体”的美学基础理论,放置到人生论美学视域下的研究,具有了很强的理论自洽性和完整性。
所以,在人生论美学看来,美育问题的全新理解与阐释才是使人生论美学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还“改变世界”[13]的“实践的”“行动的”美学的最后环节。从而也使我们阐明的人生论美学所追求的理论目标:“使艺术、审美和人生走向统一”[14],在此真正落到实处,从而变得可能、可行起来。
总而言之,不论是从美育与美学基础理论的关系来看,还是从美育与人生论美学理论体系的关系来看,我们之所以老生常谈地将“美育”这一美学基础理论问题,放置到人生论美学的理论视域下进行重新阐释,实际上也正是旨在将实践论美学和人生论美学中美论、美感论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内涵,贯彻到美育论的研究之中。唯如此,我们美学研究才能真正将“美的本质”和“美感”问题的研究最终落脚和归结到“美育”问题上,而真正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