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授眼中的中国民居
2019-01-10张知依
张知依


“多年以来,那仲良宏大而敏锐的研究,已经让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开始深入地认识中国民居空间的美丽与复杂。”耶鲁大学历史学者史景迁在《图说中国民居》的序言中写道,“甚至进一步引发了我对更广泛的中国经济和政治议题的思考。”
1965年在台湾田野调查时,那仲良教授被一座矗立在水稻田中的民居深深吸引,从此将研究兴趣转向中国传统民居。1968年,那仲良从匹兹堡大学获得人文地理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后,一直任教于美国纽约州大学新帕尔兹分校。
因为良好的汉语基础,在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20世纪70年代,那仲良成为最早一批来到中国进行学术考察的美国学者。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那仲良造访了中国上千座民居,足迹遍布东北三省以外的所有中国省份。他于1986年出版的《中国传统乡土建筑:普通住宅的文化地理研究》(China's Traditional Rural Architecture:A Cultural Geography of the Common House)是第一部将中国乡土建筑介绍到西方世界的英文著述。
在完成诸多学术著作的同时,那仲良还撰写了一本面向大众的作品《图说中国民居》,如今由三联书店推出了中文版。
从北京胡同的四合院到福建山区的土楼,从江南水乡的文人旧宅到黄河流域的农人窑洞,那仲良小心翼翼地选择了过去五百年间建造的十七个民居案例。
史景迁曾一度感叹未能及时从发展的洪流中拯救出中国的建筑遗产,但看了那仲良的这本书后,他觉得也许为时未晚。
这原本是面向美国读者的,或许也可以为很多中国读者补上一课。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举办的《图说中国民居》的活动上,一位年轻读者对那仲良表示感谢。因为北上求学,她离开了福建老家,读了这本书,她才重新认识了老家的土楼民居——那里面有“土”与“土”的智慧。
讲述中国民居的故事
● 记者:是什么让你对中国传统民居产生兴趣?
● 那仲良:我的研究始于个人兴趣。对美国读者来说,我们之前读到的关于中国的著作里通常都说“中国民居大同小异”。在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人对于中国民居的理解是非常局限的。他们接触到的中国人往往来自大城市,对农村居民和民居了解甚少。我很幸运能够在中国广泛旅行,发现民居其实非常多样,我非常希望了解为什么存在这些差异。
这本书的目标读者原本是美国人——他们对全世界的建筑感兴趣。此前,美国读者对英国、法国、德国等民居风格比较了解。对于亚洲民居,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都是日本,因为美国从19世纪开始便有介绍日本民居的书籍了。很长时间,美国人对中国民居一无所知,所以我希望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研究,呈现出中国民居的特别之处。
● 记者:你研究中国民居,角度和中国学者有何不同?
● 那仲良:我刚开始写中国民居的时候,没有中国学者在写相关题材的著作。那是1977年,百废待兴。中国年长的学者过去做过研究,但是很多手稿丢失了,一些书是集体著作,没有单独的作者。
早先中国的书籍充满了事实、理论、数字和图表,那些论据和观点诚然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读罢觉得非常充实,但还是缺少点什么——我一直希望能够填补空白,就是把关于中国民居的研究写成一个故事,我希望以记者的视角讲述一个故事,让读者感到他们能从书里学到一些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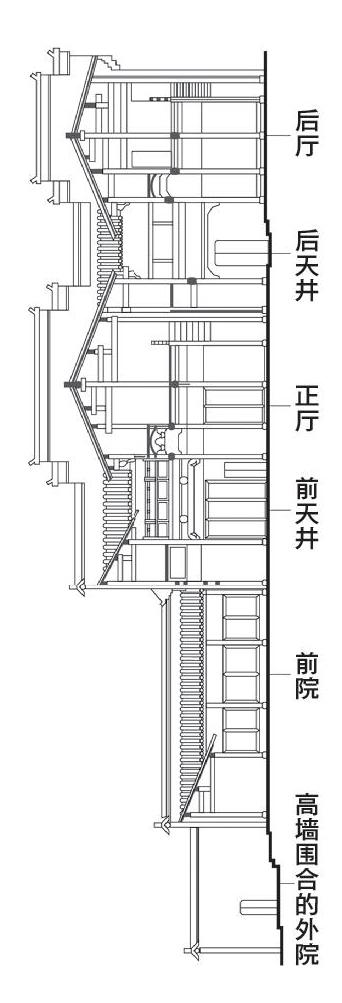
安徽黃山宏村中心的月沼,不仅倒映着周边美景,还为村民提供了生活和消防用水
● 记者:作为一个外国人,进入中国乡土最难的是什么?
● 那仲良:让我先来说说好的部分吧。1965年我开始研究中国民居的时候,只有25岁。1977年当我真正开始在中国乡间行走的时候,我37岁。当时的我精力充沛,喜欢农村生活,喜欢散步和远足。中国农民非常淳朴善良。当你进入一个村落,他们邀请你喝茶,和你聊天,你问一个问题,如果他们不知道答案,还会找别人解答。
所以困难在于,很多时候没有人能够真正解答你的问题。有时我们考察一栋民居,上面有一些字符,随行的中国研究者并不知道这些术语。民居的主人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们知道这个短语的意 思。
另一个难点是人为破坏。太平天国和近代事件,对民居造成了很多破坏。大家经常谈论现代人对建筑的破坏,其实近代更是关乎破坏和重建的历程。但我坚持认为,没有人可以扼杀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植根于人们的生活和观念中。在一些时期人们会抛弃传统,但不会永远分离。
● 记者:在研究过程中,你看到了中国文化怎样的意涵?
● 那仲良:中国民居的智慧在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对于自然的本质的理解。中国人洞悉太阳在天空中的运行轨迹,风的方向,水的流动方式。我教了很多年自然地理,很多美国学生其实不了解生活的基本常识。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经与自然相距甚远。恰恰农村居民能了解这些,因为口口相传的自然知识。比如说在北方的气候中,民居最好朝向东南;如果人住在多雨的地区,房屋就需要屋檐,否则雨水就会冲走墙体……这些都是基于传统经验的知识。
过去关于民居和建筑的很多著作里,作者会介绍他看到的某种装饰物或者建筑结构,但是不会解释这代表什么内涵。而我试图发现每件事物的意义。我之前写的一本书叫《中国人的生活之家——信仰之家》,你会发现中国人在民居和建筑方面的符号通常有两种意义:寻求好运和避免不幸,这是两条互补的轨道。今天这种象征或符号没有那么常见了,但总会在一些场合显露出来,比如结婚时挂出“双喜”等等。
一旦失去居民,民居就会步入消亡
● 记者:你在书中提到,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大多数传统民居和地方建筑正在被新的住宅形式不断侵蚀和替代,在你看来,哪些重要的东西消亡了?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消亡?
● 那仲良:有一个美国俚语叫“有样学样”(Monkey See and Monkey Do)。假设一个村落里每个人最开始都很贫穷,其中一个人率先致富了,他会建造一栋更好的房子。其他人这个时候“有样学样”地效仿起来,很快半个村子都林立着第一座民居样式的建筑。
一方面,我很早前就发现,在中国农村,很多人希望将自己的财富投入在房子的建筑装潢中。过去,很多村落,传统是几代人住在同一个房子里,所以很多人会盖非常大的房子,远超过他直系家庭规模的需要。但是现在,年轻人倾向于到大城市结婚与定居,农村的大房子实际上只承载了一对老夫妇和少数几个孩子,可以说是一种空间与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我意识到,流行文化和人们意识对房屋的影响。有时候民居盖起来时非常简陋。但是它会随着主人的财富积累,一年比一年好。主人会装潢新的地板,摆放更好的画作,安装更好的门。所以每栋具体的民居也会随时间推移而发展。
● 记者:所以,“人”在民居里的作用至关重要。
● 那仲良:是的。在这过程中,“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旦失去了居民,民居就会缓慢步入消亡。
我经常说,中国农村很多传统民居被破坏了,但还有很多好东西保留下来。但有时我们能保存的只是一个外壳,没有人再像一百年前那样去生活了。有时候我走进一所古老的民居,会发现主人非常看重这个居所,他们知道房子的历史和世代相传的价值。另外一些人则毫不珍惜,会去出售画作和装饰品,房子逐渐失去了美感。
● 记者:今天的中国,有些人拥抱西方的态度非常明显,不论是古城保护,还是民居建造,“洋气的”就是领先的。而你走在中国乡村却看到了传统民居的价值。
● 那仲良:很多年前,我和一位建筑师在浙江省工作,他带我拜访了一些他非常喜欢的村落。他说,因为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和他同行,村民们开始意识到这些民居在西方人眼中的价值,他们带我去这些地方帮助拯救了一些房子。这很有趣,但我想也非常真实。
在保护传统建筑方面,其实美国和欧洲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改进过程。我居住的美国村镇上有一些17世纪的建筑,相当于中国明清时代的房子。在19世纪末,美国人认为这类民居太老旧了,所以很多房子都被拆掉了,直到后来它们才被认为是具有历史价值的,于是开始保护它们。
到现在为止,要想以正确的方式维护这些民居都是很困难的。如果没有人生活在房子里,建筑恶化非常快,产生屋顶漏水或墙体塌陷等等问题。美国和中国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我们失去的比我们得以维系的更多,悔之晚矣,没有人能够挽救那些错误,人必须向前看。
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不傻,但是大家都有可能犯错。在过去,情况变化非常缓慢,错误比较容易被修正。但在今天,弥补一个错误可能需要一掷千金。
● 记者:在城市化建设中,民居在发生变化,“好”的民居的标准也在快速变化,标准化的房屋、北欧式的装修及欧式别墅的建筑正在定义“新”与“好”。这些甚至是城市中产对“好家”的唯一定义。
● 那仲良: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社会,尤其是年轻人酷爱追赶时尚。但也有人不一样,在韩国在日本,有可能一个年轻人的祖父母拥有的东西就已经足够好了,大家不需要添置漂亮的新家具取代它。他們一辈子都用同一个杯子。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如此之大,事物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方式,在各个地区发展和变化。我们很难盖棺定论地概括中国。还有很多中国村庄的复兴源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艺术家。他们厌倦了疯狂的大城市生活,希望在乡下定居。这种自发的个人行为实际上拯救了很多的村落。当一个人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定居之地,他会广而告之,最后更多人搬到了那里。与此同时,这些新居民会带给这个村庄一些生机,尽管可能不是传统的生活方式。


福建省龙岩客家土楼的振成楼。晚秋斜阳下,振成楼内环瓦屋面上投射出一道弧形阴影,阴影环绕之中,一间祖堂赫然耸立
“复制品”般的村庄可以和原版一样好
● 记者:你的旅行研究比很多游客更有趣。今天很多人为了在社交网络上证明自己“去过”某处,把任何一个地方当做背景,拍了照就完事了。
● 那仲良:大部分游客看到民居是没有太多感触的,美国人也一样。我去乔家大院,第一次去时没有什么游客;后来再去时,已经有形形色色的游客,但他们对建筑并不怎么感兴趣,更愿意走进特定的房间,观看那些影视剧照。旅客对民居本身并不感兴趣,所幸的是建筑因为这些游客仍然被完好地保留了。
我认为,这还是兴趣使然,当我和妻子去博物馆时,她会阅读几乎所有的说明,到闭馆时能学到很多东西,相反我在这方面就只是个走马观花的游客。但是当我走进一栋民居,我会充满好奇地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如果我有疑问,我会想要找出答案。所以好奇心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对旅行。
● 记者:你在书中提到,“任何一座民居都需要历经长时间的塑造过程才能最终成形”,那你如何看待今天中国重建古镇的行为?
● 那仲良:1987年我去拜访西递宏村,那是我在中国去过的第一个需要购买门票的村庄,尽管当时几乎没有游客,但当地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开发旅游业了,很快村民被要求搬出去,由企业管理运营这个村庄。后来住在村子里的人,其实都不是本地居民。
旅游业在中国和在美国大同小异,在我居住的小镇上,大学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其次就是旅游业。游客想要各种吃喝玩乐的体验,如果你创造了一个旅游产品,能够赋予它有趣的故事就能从中赚钱。但也需要看到,像乔家大院这样的地方,其实也正是因为旅游被保留了。
人们的教育水平和兴趣导向是不同的。有些人不需要看到真实的旅游景点,在电视屏幕上看看就足够了。但还有一些人希望获得原真的体验。这样的人进入博物馆,看到一件復制品可能会很失望,其实复制品可能和真品一样漂亮,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只能展出复制版。一个“复制品”般的村庄也是类似的,坦率地说,我觉得复制品可以和原来的村庄一样好。大部分游客需要的是拍拍照,体验当地美食,置身于传统的氛围和传统的空间,复制品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好了,问题仅仅在于有时这些景点人满为患。
几年前我和妻子去欧洲旅行,维也纳和布拉格附近有很多古镇和美丽的建筑,当地人几乎都靠卖旅游纪念品为生。就像丽江,每个街区都有纪念品,每个街区卖的东西也大同小异。一个旅行者需要站得远一点才能欣赏那里的建筑。但是,恰恰因为有商店和旅游业,建筑才得以受到保护。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个挑剔的人。毕竟,热门景点之外也还有很多小镇和村落能够满足旅行者对于体验当地生活的需要。
这可能是中国的现状。过去20年中,高速公路正在包围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和村落。高速公路的出口建在哪里,哪里就会被现代交通和生活重塑,更多的基础设施将会建设起来以便满足游客。但是在高速公路的出口与出口之间,还有大量的地带,能够供期待原真体验的人探索。
摘自公众号“何四在人间”,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