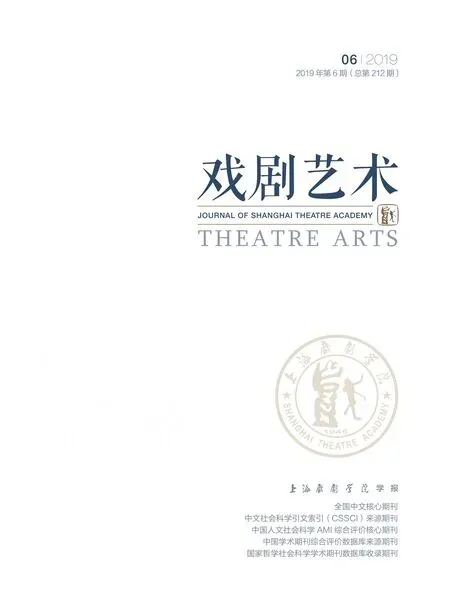清代杂剧研究格局的现代构建与反思
——以民国时期戏曲史著为考察对象
2019-01-09
相比较元明两代杂剧而言,学界长期以来对清代杂剧缺乏应有的关注与研究: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张庚、郭汉城等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对清代杂剧作家与作品几乎不曾着墨,即便有三言二语,也多为贬抑之辞,这也再次印证、强化了前人有关清杂剧衰微不振的论调。另一方面,学界对已有的清杂剧研究成果也未给予应有的梳理与总结。事实上,民国时期的戏曲史著对清杂剧就有不少论述,涉及作家作品、文本体制、剧场、演出、发展历程等诸多问题,初步构建出了现代学术史意义上的清杂剧研究格局。学术史研究的出发点,在于“摸清”前人留下的“家底”,以更准确、更有效地把握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并以此作为再出发的起点。故此,本文不揣谫陋,冀对民国时期戏曲史著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加以梳理与分析,评价其中的利弊得失,以为今后清杂剧研究与杂剧史撰写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
在被誉为中国戏曲史开山之作的《宋元戏曲史》(1912年)中,王国维认为明代杂剧“既无定折,又多用南曲,其词亦无足观”。(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181页。去元不远的明代尚且如此,遑论时过境迁的清代了。相较于元代甚至明代,清代杂剧更少得到人们的关注。王国维偏重“文章”的戏曲史撰写理路,也对其后戏曲史家多重“曲”而轻“剧”现象的出现以示范性影响。
《顾曲麈谈》出版于民国五年(1916年),吴梅虽然承认“清代曲家,不如明时之盛,而所作则远胜之”(2)吴梅:《顾曲麈谈》,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101页。,但他仅是对清传奇有所评说,杂剧基本上付之阙如。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吴梅撰写的《中国戏曲概论》开始对清代杂剧有所关注。吴氏将包括杂剧在内的清代自开国以迄道光间的戏曲发展历程,大致分为“顺康”“乾嘉”“道咸”及“同光”四个阶段。(3)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卷下,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第1-2页。其中涉及一些不同时期的杂剧作家,如吴梅村、尤侗、蒋士铨、杨潮观、杨恩寿等。尤为难得的是,吴梅还单列“清人杂剧”一节,列举了20位杂剧作家的146种作品,并对其中一些名家名作加以评述,表明吴氏已开始将清杂剧作为整体来加以考察。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吴梅对清人杂剧的关注,基本上仍为曲辞曲律的品评、风格情趣的鉴赏、曲坛掌故的摭谈等,依然是在传统曲学体系内进行的。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是在王国维的影响下问世的。严格来讲,这部被誉为“以严正的史家态度,详究戏曲之渊源,以明其变化陈迹”的戏曲史著(4)王古鲁:《译者叙言》,《中国近世戏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页。,却难称得上“初步描出了整个中国戏曲史的轮廓”(5)王古鲁:《译著者叙言》,《中国近世戏曲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1页。,青木氏仅对明代杂剧的发展历程作了大致梳理,清代杂剧的论述却非常简略,且和传奇放在一起。青木氏用了不少篇幅来叙述剧情,所作评价也是多引用他人观点。由此可见,清代杂剧仍不是他关注的主要对象,更说不上将其作为独立对象来加以研究了。
王易的《词曲史》(1932年)虽然将杂剧与传奇放在一起论述,但他还是注意到了二者的区别。他将清代杂剧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明末清初,创作杂剧的有吴伟业、尤侗、郑瑜、周如璧、邹式金、王夫之、嵇永仁、洪昇等,其中最著者为吴伟业和尤侗。(6)王易:《词曲史》,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第434页。乾隆中期,杂剧家则有蒋士铨、桂馥、杨潮观、舒位、陈于鼎等,成就最高者为蒋士铨。第三个阶段为晚清,杂剧作家及作品仅有周乐清、黄燮清等,作家寥寥,整体成就也不高。王易由此认为,“清代戏曲始盛而终衰”。(7)王易:《词曲史》,第504页。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像其他史家那样,将杂剧发展的历程叙述到乾隆中叶之前为止。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及郑振铎先生。郑氏虽未撰写过戏曲史专著,但自1930年代开始,他便致力于清代杂剧文献的搜集与出版,先后印行了《清人杂剧初集》和《清人杂剧二集》,可谓是别具慧眼、着力肯定清杂剧历史价值的拓荒者。在为《清人杂剧初集》所作的序言中,郑氏对有清一代杂剧的发展历程、作家作品及其历史地位都有所肯定,初步勾勒出了清代杂剧发展的历史脉络——“考清剧之进展,盖有四期”。第一个时期为顺康之际,这是杂剧的“始盛”期,以吴伟业、尤侗、张韬、嵇永仁等人成就最大,“为后人开辟荆荒,导之正途”。第二个时期为“雍乾之际”,是为杂剧“全盛”期,以蒋士铨、杨潮观和桂馥成就最为卓著,“尤称大家,可谓三杰”。文人“短剧”也在这一时期成熟,“风格辞采,以及音律,并臻绝顶,为元明所弗逮”。第三个阶段为“嘉咸”时期,杂剧作家有舒位、石韫玉、梁廷枏、徐爔等,虽然全盛时期的“流风未泯,然豪气渐见消杀,当为‘次盛’之期”,这一时期徐爔的写心剧,“以十八短剧自写身世,创空前之局”,值得称颂。第四个时期即为“同光间”的杂剧“衰落”阶段,虽然黄燮清、杨恩寿、许善长、袁蟫、刘清韵诸家仍在从事杂剧创作,但总体上“亦现捉襟露肘之态,颇见迂腐,殊少情致”,“杂剧之于清季,实亡而未亡也”。郑氏由此对清杂剧的发展演变总结道:“盖六七百年来,杂剧一体,屡经蜕变,若由蚕而蛹、而蛾,已造其极,弗复能化。同光一期杂剧,成蛾之时也,然僵而未死,间有生意。”(8)郑振铎:《清人杂剧初集序言》,《清人杂剧初集》,长乐郑氏影印本,1931年。郑氏既肯定清杂剧的成就,也不讳言其不足甚至缺陷,显示出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与客观公正的学术精神。郑氏赞赏清人杂剧为“纯正之文人剧”,乃立足于文学层面上的评价,与王国维对元杂剧的推崇遥相呼应。
在出版于1933年的《明清戏曲史》中,卢前将明清戏曲的发展亦分为四个时期:第一、第二个阶段主要在明初至万历年间,第三个阶段从明天启、崇祯年间一直到清康熙初年,戏曲创作进入复兴与繁盛期,第四阶段即从康熙中期开始直至清末。卢前没有将传奇、杂剧分开而论,对清杂剧进行独立研究的意识还不明显。即使对清代几位主要的杂剧作家及作品有所论及,基本上也与乃师吴梅一样,以曲辞鉴赏、品评为主,间有评价性意见,亦多为片言只语,极其简单。不过,这种情况在次年出版的《中国戏曲概论》中得到了纠正。在这部被作者自认是“记载全部中国戏剧的第一部”(9)卢前:《中国戏曲概论序》,《中国戏曲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第3页。的戏曲通史中,卢前确实单列一章《清代的杂剧》,专门论述有清一代杂剧作家、作品以及清杂剧的发展演变。他借鉴郑振铎《清人杂剧初集序言》的提法,也将清杂剧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卢前认为,杂剧发展到黄燮清、陈烺、徐鄂等人的时候,已经进入了衰微的尾声,“戏曲的格律已不渐为文士所知,其间作家却也不少,大概是‘不知而为之’者居多”。(10)卢前:《中国戏曲概论》,第208页。让读者感到缺憾的是,这部受到吴梅戏曲观念影响至深的第一部戏曲通史,很少见到作者发表的独立见解,更多的是吸收别人的意见,进行归纳、分析与评说,也很难让人看到戏曲“史”之脉络。
在1936年出版的篇幅简短却颇具通史性质的《中国戏剧史略》中,周贻白对清杂剧只有几行字的描述:“杂剧的体制,经明人一番改变,也被此时的剧作家采用着,如洪昇除作《长生殿》外,又作有一折短剧四种,名《四婵娟》。他如具有玉茗风格的蒋士铨、杨恩寿等,都是杂剧传奇兼作。蒋之《四弦秋》杂剧,谱《琵琶行》事,尤为有名。专门作杂剧者,则有杨潮观,其《吟风阁》三十二种,都是一折的短剧。”(11)周贻白:《中国戏剧史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9页。在篇幅同样简短的《中国戏剧小史》中,周贻白并未提及清杂剧。在周氏看来,明代开始,由于受到南戏与传奇的影响,杂剧固有的文体特征已被打破,清杂剧亦非传统杂剧旧貌,故未加着墨。附带提及的是,徐慕云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出版的《中国戏剧史》,同样没有关注清杂剧,原因在于,“北曲至明中叶,已名存而实亡”。(12)徐慕云:《中国戏剧史》,上海:世界书局,1938年,第68页。
到了周氏撰写《中国戏剧史》的时候,他对清代杂剧特别是南杂剧的作家、作品及其发展历程开始加以关注。周氏指出:“到了清初,剧本的撰作,颇有风起云涌之势。”(13)周贻白:《中国戏剧史》,上海:中华书局,1953年版,第482页。代表性的杂剧作家有王夫之、吴伟业、尤侗、蒲松龄等。雍乾间最著名的作家是蒋士铨和杨潮观,还有周乐清、舒位、石韫玉等。周氏还提到了乾隆年间的杂剧作家唐英、徐爔、梁廷枏、陈栋等人的剧作,不过,他只是介绍作者、列举剧名、摘录曲文而已。到了第三阶段道光年间,则有黄燮清、杨恩寿等,他们的剧作已无法与蒋士铨等人相提并论了。周氏仍是将清代杂剧与传奇放在一起来论述。
民国戏曲史家从历史的角度,大致厘清了清代杂剧的发展演变过程,虽然每一部戏曲史的历史分期、关注重点、评价标准等多有不同,总体上还不够成熟、完善,但经过戏曲史家的不断探索,还是初步勾勒出了清杂剧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出了清杂剧的艺术成就,明确了清杂剧在古代戏曲史中的地位。
我们也注意到,大部分戏曲史著对清杂剧发展历史的论述,几乎均止步于乾隆中叶。究其原因,正如许之衡所言:“乾隆以后,虽亦间有名著,然大多数皆不足观,不惟曲律瞀无所知,即文词亦远非元人矩矱。其稍佳者,亦律赋试贴之气味耳,皆于曲门外汉也。”(14)许之衡:《戏曲源流》,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自刊本,第64页。董每戡于1948年完成的《中国戏剧简史》,对明代与清代的杂剧都没有涉及。因为董氏认为,这一时期的“戏剧艺术渐离大众”(15)董每戡:《中国戏剧简史前言》,《中国戏剧简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第7页。,这种已经“渐离大众”的杂剧也就不值得去浪费笔墨了。文学史家刘大杰也认为,“乾隆以降,代表中国旧剧的杂剧、传奇,日趋衰落”,其原因就在于被称为花部或乱弹的地方戏,“带着腔调、乐器、色艺丰富多彩的不同特点,从各地汇集而来,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对昆曲形成较大的优势”。(16)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19-1320页。这种清中叶杂剧衰落、成就不高的戏曲史“共识”,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末完成的《中国戏剧通史》,仍未将清杂剧列为论述的对象。
二
尽管每一位戏曲史家都有其独特的戏曲史观,每一部戏曲史著撰述重点也多有不同,但关注对象的大致相同,亦可构成诸多戏曲史著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一致性。在上文中,我们对民国戏曲史著中有关杂剧发展历程的论述作了梳理与总结。我们还注意到,这些戏曲史著对清杂剧发展过程的一些问题或现象的关注与探讨,即使在今天清杂剧研究中也不多见,其价值不可等闲视之。
(一)抒情性的强化与自况体杂剧的出现
就杂剧的发展来讲,入清后的杂剧创作主题与情感基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江山易主的黍离之悲,代表性作品为吴伟业《通天台》《临春阁》,另外,陆世廉《西台记》、土室遗民《鲠诗谶》、王夫之《龙舟会》等也是这类作品。吴伟业所抒发的亡国之哀和故国之思,“如第一折通天台下痛哭之独唱独白,字字鸣杜鹃血之声”(17)(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32页。,“正是亡国遗臣的哀音”(18)周贻白:《中国戏剧史》,第487页。,令人不胜感慨,恻然伤心。这类题材在明代杂剧中是极为罕见的,因而格外引人瞩目。另外,抒发怀才不遇、落魄穷愁之悲愤也是清代杂剧的一大主题,如尤侗《读离骚》《清平调》、嵇永仁《扯淡歌》、张韬《霸亭庙》、廖燕《醉画图》、徐石麒《大转轮》、桂馥《投溷中》、叶承宗《孔方兄》、邹兑金《空堂话》、吴藻《乔影》等,都是如此。这类杂剧所抒发的情感,也引起了众多文人剧作家的强烈共鸣。
就杂剧作品情感抒发的强度来讲,戏曲史家注意到清代出现了一批仿照徐渭《四声猿》而创作的杂剧。卢前在《中国戏曲概论》中,对“《四声猿》的模拟者”加以特别的关注。这些杂剧包括张韬《续四声猿》、桂馥《后四声猿》、裘琏《四韵事》、曹锡黼《四色石》、舒位《瓶笙馆修箫谱》等。徐渭《四声猿》引起了清代杂剧家强烈的共鸣:“睹其悲凉愤惋之词,想其坎壈无聊之况,骨竦神凄,泪浃巫峡,何待猿啼。”(19)澂道人:《四声猿跋》,《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58页。对清代抒情短剧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显著的影响。这些作品所表达的文人才高不遇的失落与无奈,都带有作者强烈的感情色彩。可以说,仿《四声猿》杂剧成了清代文人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书写怀抱、寄托幽思的别具意味的文体样式。
戏曲史家注意到,在这些作品中,剧作家与剧中主人公无论是在历史处境,还是在人格气质、人生经历等方面都颇具相似性。这类作品即是戏曲史家所说的“自况性杂剧”。吴梅指出:“《通天台》之沈初明,即骏公自况。”(20)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卷下,第10页。郑振铎认为,“故炯之痛哭,即为作者之痛哭。盖伟业身经亡国之痛,无所泄其幽愤,不得已乃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21)郑振铎:《清人杂剧初集》。王夫之《龙舟会》杂剧,以李公佐隐写身世,以谢小娥暗寓心志;桂馥年近七旬,却职微俸薄,僻处南国蛮荒之地,疾病缠身,“才如长吉,望如东坡,齿发衰白如香山,意落落不自得,乃取三君轶事,引宫按节,吐臆抒感”。(22)王定柱:《〈后四声猿〉序》,《后四声猿》,清道光二十九年味尘轩木活字本。故而选择与己身世相似的李商隐、白居易和苏轼的人生遭遇,借题发挥,传达其不得志之苦闷情怀。尤侗“自制北曲《读离骚》四折,用自况云”。(23)尤侗:《悔庵年谱》,清康熙间刻本。这类自况性杂剧最突出者,就是廖燕的《柴舟杂剧》,而《醉画图》《诉琵琶》及《镜花亭》三剧的主角就是廖燕本人。《醉画图》开场便将自己的籍贯、个性、才能、经历以及愤懑不满,尽付于嬉笑怒骂之中。正如吴伟业为李玉《北词广正谱》作序时所指出的那样:“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慨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盘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24)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陈古虞等点校《李玉戏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86页。我们知道,有清一代的杂剧作家,如吴伟业、王夫之、尤侗、洪昇、厉鹗、蒋士铨、杨潮观等等,多为文学名家,但在现实社会中,各自有着不幸遭遇,郁积着满腹的悲苦辛酸,有着不吐不快的抒情诉求。在自况性剧作中,作家或是构建“自我”与剧中人物的对应关系,或是径直登场,以本尊示人,而非通过角色代言、剧情演绎来传情达意,因而情感的表达更为直接,也更强烈。
(二)短剧的繁盛与文人剧的成熟
杂剧经明正德、嘉靖年间徐渭、汪道昆以及隆庆、万历年间陈与郊、沈自徵、叶宪祖等人的大力创作,体制规范逐渐松弛,并随着杂剧南曲化、传奇化,单折或二三折的短剧也异军突起。发展至清代,短剧因其体制灵活、结撰随意,便于文人寄情言志,又能咏唱搬演,遂为众多杂剧作家所喜爱。“一折成剧,简短精悍,如齐梁之小乐府,如唐诗之绝句,出岫无心,回甘有味,别开戏曲之一途。”(25)卢前:《明清戏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页。吴梅指出,“如《拈花笑》、《浮西施》等,以一折尽一事,俾便观场,不生厌倦。杨笠湖之《吟风阁》,荆室山民之《红楼梦》,分演固佳,合唱亦善,此较明人为优者一也”。(26)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卷下,第2页。又云:“为此文者,往往不论南北,不备角目,称心而出,如题而止,其于排场规律,不甚措意。”(27)吴梅:《郑西谛辑〈清人杂剧〉二集叙》,《清人杂剧二集》,长乐郑氏影印本,1934年。正是因为短剧的这些“便宜”特点,它在有清一代颇受欢迎,一大批文人才子操觚染翰,纷纷加入创作者行列,短剧数量亦因之激增。当然,吴梅认为,“至清而有一折短剧,若西堂之《清平调》、杨笠湖之《吟风阁》、徐榆村之《写心剧》,大利于戾家生活,是亦清代创作也”。(28)吴梅:《郑西谛辑〈清人杂剧〉二集叙》。这样的说法至少是不准确的,因为一折短剧在明代即已出现,并非清人首创,但短剧在清代的繁荣则是不争的事实。
卢前对短剧的发展历史作了大致梳理。他将短剧定义为“单折之杂剧”,认为始作俑者乃元末王生,其《围棋闯局》不过是偶尔为之,非为常例。后来经过明正德、嘉靖年间徐渭、汪道昆和隆庆、万历年间陈与郊、沈自徵、叶宪祖等人的创作而逐渐流行,是为短剧流行的初期。“入清以后,短剧日盛。顺康之际,徐石麒、尤侗、嵇永仁、张韬并有妙造。雍乾之世,有桂馥、曹锡黼,而杨潮观尤臻极诣。降及嘉咸,有舒位、石韫玉、严廷中,亦一时能手。同光而还,始稍稍衰矣,然如陈烺辈,犹学步邯郸,未尽绝迹。此短剧流行之后期也。”(29)卢前:《明清戏曲史》,第79页。他将清代短剧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主要作家与作品加以简评,充分肯定短剧“已非元百种中之所能囿,固关、马、宫、乔笔下所未有者也”。(30)卢前:《明清戏曲史》,第88页。
在戏曲史家看来,明、清短剧的最终完成,是由杨潮观来实现的。卢前评价杨潮观的《吟风阁杂剧》说:“一折的杂剧,到了他才集其大成,案头场上,两得其便。如橄榄之在口,以少许胜多许,而其味弥隽永。与西方的独幕剧性质相同,不过此有曲文,更饶诗意。”(31)卢前:《中国戏曲概论》,第198页。称许杨潮观“固定了短剧的规模,开文士剧的风气,其功终不可埋没的”。(32)卢前:《中国戏曲概论》,第203页。吴梅也注意到,杨潮观的杂剧“每折一事,而副末开场,又袭用传奇旧式,是为笠湖独创,但甚合搬演家意也”。(33)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卷下,第23页。卢前所谓“开文士剧的风气”,倒也未必,因为文人剧早已有之,但传统杂剧的文体形式和功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确是显著的事实。
文人剧发轫于元代,经明代数百年的发展而在清代最终成熟。郑振铎指出:“明代文人剧,变而未臻于纯。风格没落尘凡,语调时杂嘲谑。大家如徐(按,即徐渭)、沈(按,即沈璟)犹所难免。纯正之文人剧,其完成当在清代。三百年间之剧本,无不力求超凡蹊,摒绝俚鄙。故失之雅、失之弱,容或有之。若失之鄙野,则可免讥矣。”(34)郑振铎:《清人杂剧初集序言》,1931年。郑氏所言的“纯正的文人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清代杂剧作家,几乎全是文人才子,其剧作所选择的题材,所表达的情感自然是文人化的;二是曲辞风格的雅化。清代文人作剧,视杂剧为抒情言志之载体,雕琢堆砌,在所难免,甚至栝原作诗文入剧,如郑瑜之《汨罗江》,嵇永仁之《扯淡歌》,尤侗之《读离骚》《桃花源》,及车江英之《四名家填词摘出》等,也颇为常见。周贻白指出:“清初以才情见长的剧作家,似无过于尤侗。……《读离骚》谱屈原事,驱使楚辞各篇,若自己出,其魄力之大,在元人中亦为少见。而文词之工整,犹其余事。如第一折《屈原题壁》[混江龙]一曲,以《天问》为张本,格局雄浑,词气磅礴,虽集明代所有传奇杂剧,亦无此一篇。”(35)周贻白:《中国戏剧史》,第488-489页。清代杂剧辞采典雅脱俗,这一点是远过明人的。
就文人化来讲,蒋士铨《四弦秋》等杂剧的出现,实际上代表着文人剧成熟的另一种方面,即追求文辞典雅和历史真实的结合。吴梅评价《四弦秋》道:“凡所征引,皆出正史,并参以乐天年谱。”(36)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卷下,第12页。青木氏评价杨潮观杂剧“悉正写典故而少余味”。(37)(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第419页。吴梅指出,《长生殿》和《桃花扇》问世之后,“于是词人各以征实为尚,不复为凿空之谈。所谓‘陋巷言怀,人人青紫;香闺寄怨,字字桑间’者,此风几乎革尽”。(38)吴梅:《曲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86页。与此同时,文人化杂剧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对教化的重视。刘大杰注意到,蒋士铨的剧作“很重视社会作用,但他所强调的‘表扬节义,攸关风化’”。他评价杨潮观的剧作:“虽都是取材古事,其中颇寓寄托。”(39)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1312页。蒋士铨的剧作也确实如此,张三礼在为《空谷香》作序时就揭示出,蒋氏“填词足资劝惩感发者”。(40)张三礼:《空谷香序》,《蒋士铨戏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33页。蒋士铨、唐英、杨潮观等人正是秉持这样的宗旨来从事戏曲创作的,《藏园九种曲》《吟风阁杂剧》《古柏堂戏曲集》所收的杂剧,多有教化之作。
伴随着文人的参与,杂剧逐渐呈现出案头化特点,其后果便是杂剧逐渐摆脱掉“俗”的特征,成为一种介乎诗文之间的特殊文体。屈原、项羽、阮籍、蔡文姬、陶渊明、李白等悲剧性的历史人物之所以成为清代短剧最为热衷描写、吟咏的对象,其原因也正在此。可以这样说,短剧的繁荣与文人剧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古代抒情文学的表现领域,古老的杂剧艺术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再次焕发出生命力。
(三)北曲的存留与南曲的发达
青木正儿曾援引明代沈德符《顾曲杂言》的观点,认为北曲杂剧在明初势力犹盛,嘉靖之前仍在演出,作者不乏其人。但在嘉靖以后,即呈逐年衰颓之状,至万历中叶以后,“北曲已绝响,为昆曲所并吞”了。(41)(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第197页。不过,北曲在清代也并非完全销声匿迹,还在以其他方式“存活”下来。青木氏再引用明末清初周亮工之子在浚《金陵古迹》自注,认为北曲虽渐将断绝,但“一缕之命脉犹仅赖老乐工系留不断,……南方虽殆近绝响,而北京宫中乐部犹演北曲焉”。青木氏断定,康熙时宫中乐工所奏之北曲,虽非杂剧之全曲,但乐工演唱的散曲,确系正宗北曲。另外,仍有少数剧作家继续坚持本曲的创作:“此时吴伟业、尤侗等新作北曲杂剧者不少,是固出于文人好古之癖,虽非可广行于世者,然此亦非仅为依样葫芦之作,文酒之会,间亦有度曲之事。”(42)(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第175页。吴梅在评价陈栋杂剧时也指出:“清代北曲,西堂后要推昉思,昉思后便是浦云(按,即陈栋),……读浦云作,方知关、王、宫、乔遗法,未坠于地,阴阳务头,动合自然,布局联套,繁简得宜,隽雅清峭。”(43)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卷下,第14页。也就是说,北曲杂剧在清代虽然风光不再,但也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仍有作家在用北曲创作和演唱。
青木氏还认为,在明清时期的传奇作品中,也保留着不少的北曲:“洪昇《长生殿》传奇中,全出以北曲填者,有《酒楼》《合围》《絮阁》《哭像》《神诉》《弹词》《觅魂》等出,此传奇甚盛行,至今歌场犹演之不止。反观之,明代南北合套——一出中混用南北两曲之风已盛行,南戏进一步,往往有插入全出用北曲之出者。汤显祖喜用之,如《牡丹亭》传奇中之《冥判》《圆驾》等出。……此等为昆曲所采入之北曲,万无可保纯粹北调之理,若干部已成‘昆曲化’者,固无论矣,然亦可视为延留北曲命脉之一途也。以此为北曲之旁系。”在青木氏看来,风行于明代的南北合套的形式,一直到乾隆朝均是如此。“乾隆初,皇帝以海内升平,命张照等新制戏曲进呈,以备乐部演习。有《月令承应》《法宫雅奏》《九九大庆》《劝善金科》等,所谱虽概为南曲,然往往有北曲,如《月令承应》,北曲甚多。意者此等北曲,当系依据宫中乐部所传之谱而演者,可得为北曲之正系。”(44)(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第175-176页。青木氏注意到,采入到昆曲中的北曲,亦非“纯粹北调”,而是“昆曲化”,但也是延留北曲命脉之一途,乾隆之后,虽然不知正宗北曲为何情形,甚至恐已湮灭,但“经昆曲家所保存之旁系,及今尤未绝流”。如近代王季烈、刘富梁编辑的《集成曲谱》,也收有元杂剧之散段,再加上尚在演唱的《邯郸梦》《长生殿》等昆曲中的北曲,录存在唱片中的元杂剧《单刀会》之《单刀》《训子》单折,所以青木氏断言“北曲犹未全亡也”。(45)(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第178页。青木氏注意到这一时期北曲杂剧发展的特点:一是文人的创作,如吴伟业、尤侗等,他们仍在坚持用北曲写作剧本;二是传奇中有整出用北曲填词者,如《牡丹亭》《长生殿》;三是传奇一出之中混用南北两曲;四是清代宫廷中北曲散套和宫廷大戏等尚存北曲。在康熙至乾隆年间,尽管南曲盛行,但北曲还是被保存了下来,依然在传唱。
周贻白指出,清人杂剧“只宜于浅斟低唱,……在广大的剧场里,已渐无人领会”。(46)周贻白:《中国戏剧史》,第496页。吴梅也说:“清代词人多不能歌,如桂馥、梁廷枏、许鸿磐、裘琏等,时有舛律。盖以作文之法作曲,未有不误者也。”(47)吴梅:《郑西谛辑〈清人杂剧〉二集叙》,《清人杂剧二集》,1934年。这样的批评大体上是成立的,“以作文之法作曲”确实是清代杂剧家的普遍选择,但也应该指出,他们并非全然不重视协律者,还是有不少作品能被演唱的。周贻白即指出:“当时此项短剧,确也有在舞台上通行者。”(48)周贻白:《中国戏剧史》,第527页。尤侗《悔庵年谱》中即有不少的记载:“予所作《读离骚》,曾进御览,命教坊内人装演供奉。”“阮亭评予北剧,最喜《黑白卫》。携至如皋,与冒辟疆襄、陈其年维崧分授家伶演之。”(49)尤侗:《〈读离骚〉自序》,清康熙间刻本。《清平调》杂剧则由曹寅的织部小班在苏州拙政园演出,梁清标的家乐亦曾演唱。(50)尤侗:《悔庵年谱》,清康熙间刻本。蒋士铨《四弦秋》杂剧曾由扬州盐商江春的家班演出,“观者辄欷歔太息,悲不自胜,殆人人如司马青衫矣”。(51)江春:《四弦秋序》,《蒋士铨戏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87页。一直到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京城还在演出这部剧作。唐英杂剧大都交给自家伶班演唱,浙江巡抚阮元因观看杨潮观《寇莱公罢宴》而“痛哭,时亦为之罢宴”。(52)焦循:《剧说》,《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95页。不可谓不感人。舒位通晓曲律,其剧作老曲师皆按节可歌。这些记载不在少数,不过就总体而言,绝大多数杂剧则很难在舞台上搬演,且越到后期,越发如此。
(四)曲谱的修撰与清杂剧的衰落
如果说历史的继承性使清代杂剧得以延续和发展的话,那么,这个时代的独特性,又赋予其诸多新的特色。
吴梅曾将清代戏曲与明代加以整体性比较,以发明其特色与成就:“虽然词家之盛,固不如前代,而协律订谱,实远出朱明之上。”他认为原因就在于,“明人作词,实无佳谱”,而清代的各类曲律、曲谱完备,给作家创作与演员演唱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清则《南词定律》出,板式可遵矣;庄邸《大成谱》出,订谱亦有依据矣。合东南之隽才,备庙堂之雅乐,于是幽险逼仄,夷为康庄,此较明人为优者一也。曲韵之作,始于挺斋,《中原》一书,所分阴阳,仅及平韵,上去二声,未遑分配,操觚选声,辄多龃龉。清则履清《辑要》,已及去声,周氏《中州》,又分两上,凡宫商高下之宜,有随调选字之妙,染翰填辞,无劳调舌,此较明人为优者一也。论律之书,明代仅有王、魏,魏则注重度声,王则粗陈条例,其言虽工,未能备也。清则西河《乐录》,已启山林,东塾《通考》,详述本末,凌氏之《燕乐考原》,戴氏之《长庚律话》,凡所论撰,皆足名家,不仅笠翁《偶集》,可示法程,里堂《剧说》,足资多识也,此较明代为优者又一也。……订定歌谱,如叶怀庭之《纳书楹》,冯云章之《吟香堂》,又驾临川、吴江而上。总核名实,可迈前贤。”(53)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卷下,第1-2页。清代考据学发达,音韵学也渐成显学,从事戏曲审音定律、考订曲谱的曲家也多有其人。
青木氏对清代北曲杂剧比较关注,,我们在上文中已有所论及。青木氏还认为,北曲杂剧在清代已经式微,即使有留存,也可能受到昆腔的影响而“昆曲化”“南曲化”,但北曲杂剧的曲谱也不乏关注与研究者:“庄亲王奉敕撰《律吕正义》,以余力使周祥钰、邹金生等编《九宫大成南北宫词谱》八十一卷。……当此时也,草野之间,有徐大椿(原注:字灵胎)著《乐府传声》二卷,专论戏曲唱法。其论以北曲为主。……既而有叶堂之《纳书楹曲谱》二十二卷出世,谱北曲若干出。”(54)(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第176页。尽管叶堂为昆曲清唱名家,其北曲大概已是“昆曲化”,难免有非正统北曲之讥,但尚“存北曲之家风”,也为北曲的创作与演唱提供了借鉴。王易也指出,清代曲学成就颇为突出,在曲谱方面,有王奕清《曲谱》十四卷,其中“北曲四卷,南曲八卷,附失宫犯调各曲一卷。曲文每句注句字,韵注韵字,每字旁注四声,于入声字或宜作三声者,皆一一详注,旧谱讹句,亦皆辨正”。同时还有吕士雄、杨绪等合撰《南词定律》,“较沈谱尤为周详”。庄亲王等《九宫大成南北宫词谱》,“持论亦特精卓,多可辟前此词家未发之秘”。在歌谱方面,首推叶怀庭的《纳书楹曲谱》,“其中辨析音律,已极精微”,“此谱已为度曲之科律”。(55)王易:《词曲史》,第505-507页。此外尚有王锡纯编《遏云阁曲谱》、庄亲王《太古传宗》等。因此,卢前认为,相比于明代传奇与杂剧的并臻绝妙,清代也有其独特成就:“曲迄于清,虽稍稍衰矣,而谱律日严,远迈前叶。”(56)卢前:《明清戏曲史自序》,《明清戏曲史》,第1页。我们知道,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礼乐文化建设得到了统治者的有意提倡,也渐趋完备。而随着乾嘉学术日渐繁荣,音律及乐律研究比此前更得到重视,以致文人研讨音律、曲谱等蔚然成风,颇为曲家所热衷。
即便如此,杂剧在清代中后期还是逐渐衰落,即便在晚清民国出现过短暂的“中兴”,但无奈大势已去。原因便在于,即便清代的曲律曲谱的修撰、斠订颇为兴盛,然许多杂剧作家对戏曲创作不熟悉,不懂格律声韵,不懂音乐,不懂舞台演唱,因而即使创作出了大量作品,但绝大多数都是属于案头把玩的读物。案头杂剧关注的是文人喜怒哀乐情感的表达,戏曲也因此最终失去了绝大多数的观众。其次,导致乾隆中叶之后杂剧不振的客观原因,就是常说的“雅部”受到了“花部”的致命冲击。实际上,昆曲的衰落并非仅是受到花部戏曲冲击这么简单,但这些戏曲史著并没有进一步加以探讨,实为可惜。
三
对民国时期戏曲史著的梳理与总结,其目的在于为今后清杂剧研究与杂剧史书写提供借鉴。从上述的研究中,我们至少可以在今后清杂剧研究与杂剧史撰写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思考:
首先,需要明确、具体的戏曲观的统摄。史书编纂,并不等于历史材料的罗列,贯穿在书中的,应该有一种历史观。撰写戏曲史也是如此。戏曲史观不仅表现在史家对历史上种种戏曲现象的评论、判断之中,也表现在对研究对象、史料的选择与运用上。民国时期的戏曲史家由于个人经历、研究兴趣、学术眼光的不同,对史实的评断论析,则常常会因为戏曲史观的不同而产生分歧。
就这一时期戏曲史书写来看,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基本上沿用的是传统戏曲研究方法。在吴梅看来,“戏曲之道,填词为首,订谱次之,歌演又次之”。(57)吴梅:《中国近世戏曲史序》,《中国近世戏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6页。相较于作曲、唱曲、谱曲、校曲、审定曲律,戏曲史既不是他学术兴趣之所在,更不是他所擅长的。严格地讲,吴梅研究戏曲的代表作是《顾曲麈谈》《南北词简谱》,而非作为戏曲史讲义的《中国戏曲概论》。叶德均曾说道:“吴梅以毕生精力虚耗在无用的作曲、度曲方面,以致在戏曲史方面所得有限。”(58)叶德均:《吴梅的霜崖曲跋》,《戏曲小说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76页。作曲、度曲并非“无用”,但叶德均确实指出了吴梅戏曲研究的特点与局限。当然,在历史著作撰写刚刚起步的摸索阶段,吴梅利用他所熟悉的材料、观点及方法来撰写戏曲史,这一点后人不应苛求。吴梅后来也意识到,戏曲者研究缺少史的意识,即会出现“未闻有观其会通、窥期奥窔”之弊端。(59)吴梅:《曲学通论》,第1页。因而,他在为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作序时提倡:“今世好学之士,研讨一事,辄穷原竟委,得综核名实之益。”(60)吴梅:《王古鲁译〈中国近世戏曲史〉序》,《吴梅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第483页。因此,要注重渊源流变的探讨、实际发展情形的把握。
日本坪内逍遥为《中国剧》作序时,曾意有所指地写道:“凡一国特殊之戏剧,由脚本上观之,或以诗歌、文章考察之,或翻译之,训释之,评论之,藉介绍之于外国,东西方文坛固不乏例,而寻绎戏剧的文学之原理,论述戏剧组织及其巧拙,著成一书,以饷世人者,迨乎今日,汗牛充栋。然至由实演方面,讨寻戏剧,考核阐明综合艺术之真性命者,则未多见之,颇为憾事。”(61)(日)坪内逍遥:《中国剧序言》,辻听花《中国剧》(三版),北京:顺天时报社,1920年,第49页。这种戏曲史研究的“憾事”,实际上是这一时期诸多戏曲史著的普遍现象,稍后的周贻白和董每戡肯定也感受到了。周贻白在为《中国戏剧史》作序时指出,“戏剧夙有综合艺术之称”,但是以前的戏曲研究者,往往只是“审音斠律,辨章析句,所论几皆为曲而非剧”。他此前所著的《中国戏剧史略》《中国戏剧小史》,也未能关注到“场上情形”,因此,他专门撰写《中国剧场史》来加以补救。即便如此,他还是为两书将案头与场上各自分开而感到心有未恰,不无耿耿,遂花费十年时间,重新撰写出了《中国戏剧史》。他秉持这样的观念:“戏剧本为登场而设,若徒纪其剧本,则为案头之剧,而非场上之剧矣。”(62)周贻白:《凡例》,《中国戏剧史》,第3页。又说:“撰写《中国戏剧史》的主要意图是,把剧本文学和舞台扮演结合起来,借此介绍中国戏剧所曾经历的一些程途及其如何衍变。”曾有戏班演戏经历、具有舞台实践能力的周贻白希望“在剧本联系舞台这一方面,力矫王国维之失”(63)周贻白《编写〈中国戏剧史〉管见》,《周贻白戏剧论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页。,有意识地突破王国维以降的戏曲史家将戏曲史局限在文学层面的思维定势,将戏曲看作是包括舞台表演在内的综合性的艺术样式,从场上表演出发,将音乐、舞蹈、演员、演唱、声腔、脸谱、剧场等作系统观照。“戏剧非奏之场上不为功”“场上重于案头”,此乃戏曲核心观念之一。(64)周贻白:《中国戏剧史自序》,《中国戏剧史》,第1页。戏剧是一门综合性艺术,除讲究宫调的配合、曲牌的取舍、字句的斟酌以及声韵的协调之外,还涉及故事情节、关目、排场、演员、音乐、演唱、舞台等,需戏曲史研究者加以综合性研究。当然,周氏《中国戏剧史》有其长处,也有短项:他很少对作家与作品加以分析和研究,对剧作内容、曲辞、格律等一带而过,他更偏重于对戏曲场上表演的考察。他的这种做法为其后的戏曲史学者所借鉴,加强了对戏曲舞台演唱、声腔流变等著述,这标志着由王国维奠定的从文学角度研究戏曲史的转型,即由以剧本为中心转移到以剧场表演为中心。
戏曲史家董每戡在肯定了王国维、青木正儿戏曲史著的贡献之后指出:“过去一班谈中国戏剧史的人,几乎把戏剧史和词曲史缠在一起了,他们所重视的是曲词,即贤明如王氏,也间或不免。……戏剧本来就具备着两重性,它既具有文学性(Dramatic),更具有演剧性(Theatrical),不能独夸这一面而抹杀那一面的。评价戏剧应两面兼重,万一不可能,不能不舍弃一方时,在剧史家,与其重视其文学性,不如重视其演剧性,这是戏剧家的本分,也就剧史家与词曲家不相同的一点。”(65)董每戡:《中国戏剧简史前言》,第3-4页。这种观点也导致其戏曲史撰写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偏颇,最明显的是,尽管他认为文学性与舞台性“两者兼顾是最上乘”,但他的《中国戏剧简史》确实存在着对作家、文本等“文学性”关注的不足,也就是同样抹杀了戏曲作为综合艺术的基本特征。戏曲“文学性”独特之处在其文辞能否适宜场上演唱,这也是戏曲研究需关注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吴梅制曲、谱曲、度曲、唱曲,其目的在于提倡“场上之曲”,把作为文学的“曲”与作为表演的“戏”结合起来,考虑的也是戏曲的演出。
从上面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具有何种戏曲史观,也就会产生何种戏曲史研究与著述。这也启发我们,今后的戏曲史撰写,首先要解决“何为戏曲”的观念问题。认真清理历代包括杂剧在内的戏曲观念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以此建构符合杂剧发展实际的杂剧史理论基础。“曲”和“剧”一起,是推动戏曲发展不可或缺的两只轮子,只有从戏曲观和戏曲史观的根本处努力,才可能把握戏曲艺术的本质特性,才能在熟知的戏曲史料中有新发现,作出新的阐释。
其次,需要对戏曲史的诸多现象、问题等作专题研究。卢前在撰写《中国戏曲概论》时颇有感慨:“局部的整理,还没有成功,而要来写一部正确的有系统的全部的戏曲大纲,这的确不是容易的事。”(66)卢前:《中国戏曲概论自序》,第2页。这个“局部的整理”,主要指的就是戏曲的专题性研究。和一般的文学史或某种文体史相比,戏曲史无疑关注面更多、综合性更高、工作量更大。荷兰文艺理论家佛克马与易布思曾指出:“文学研究的方面是如此之多,致使一个学者不可能再顾及这学科的全部领域。面对浩翰繁杂的文学问题,我们的出路只有通过分工合作来进行研究。”(67)(荷兰)佛克马、易布思著,林书武等译:《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201页。这段话对戏曲史研究尤其适合。一个戏曲史家,不大可能对戏曲史上的所有问题都有全方位的把握和精深的研究,只有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从微观的具体现象、具体问题着手,诸如作家与作品、文体与文体因素、南北曲关系、传奇和杂剧关系、杂剧体制嬗变、戏曲音乐、舞台体制、服装道具等,作某一方面、某种层次的专题性的个案研究,这样具有开拓性、独到性的专题性个案研究积累起来,方能在此基础上进行较为宏观层面的研究,最终整合成一部戏曲史著。可以说,戏曲史专题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戏曲史著的总体成就。民国时期戏曲史撰写实际上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尽管还说不上是出于戏曲史家的自觉意识,但他们对单折杂剧、对文人剧、对南北曲的消长等问题的论述,实际上属于一定程度上的专题研究,而这些研究成果称得上是戏曲史著最具价值的部分。
再次,就是戏曲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民国时期的戏曲史家,身处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所见清杂剧文本极为有限。青木正儿、卢前等人在撰写戏曲史时,感叹最深的就是文本的匮乏。一直到今天,我们也未能摸清现有清杂剧的“家底”。这无疑是对清杂剧史撰写的严重制约。史料学固然不同于学术史,但史料无疑是构成学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和组成部分。因此,尽管属于老生常谈,但有关杂剧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比起文学史、或其他文体史,尤其紧迫。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戏曲文献越来越得到重视,但这方面工作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另外,清代以来有关杂剧评价、评点、序跋等,以及近百年来有关清杂剧研究的论文、论著等研究成果,也应该纳入清杂剧史撰写的考察之中。也就说,要在全面、细致地掌握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个案、专题研究,进而对清杂剧的特质、戏曲史地位、发展演变规律等作出富有新意甚至突破性的阐释与书写。
最后,拓展清杂剧研究的领域。正因为戏曲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因此,应完善与拓展清杂剧的研究领域,加强对相关的政治文化制度、地域、流派、作家群体、作家心态、曲谱曲律、舞台演出、传播接受等方面的综合研究。戏曲史面貌和结构的真正改观将取决于综合性研究的程度如何。唯有拓展研究视野,真正把握戏曲作为综合性艺术的本质特征,过去得不到重视甚至不被关注的现象才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才能得到重新审视和评价,才能为清杂剧史撰写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坚实的基础,才有可能真正厘清杂剧的发展线索和内在逻辑。
戏曲史撰述的要义,在于梳理出戏曲的基本观念、范畴的历史发展,从而揭示其发展嬗变的规律,而对已有戏曲历史的研究,正是为了更有效地理解、把握过去,为今后的戏曲研究、戏曲史书写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民国时期的戏曲史著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