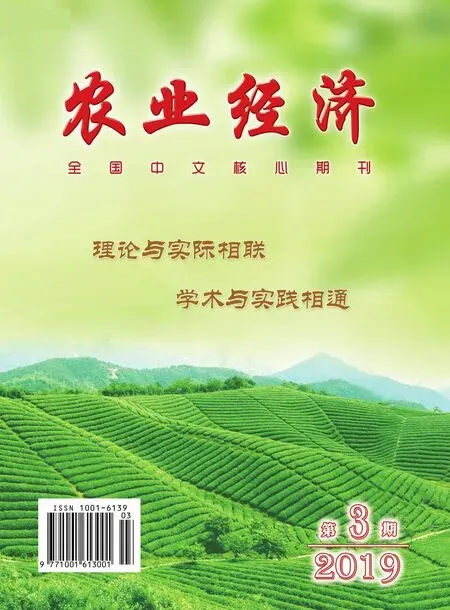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演进路径探析
2019-01-09杨富云
◎杨富云
为了有效化解农户与市场之间的矛盾,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国相断诞生了“龙头企业+农户”、“龙头企业+大户+农户”等诸多类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虽然通过组织形式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农业产业链、增强了产业关联度并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组织形式都是沿着纵向一体化的路径延伸,而分割后的生产要素又被市场交易要素整合在一起,进而产生了高昂的交易费用严重影响了组织效用的发挥。而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一种新的探索,实践证明能够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提供优质农产品的同时,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起源于安徽和江西等地,是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2017年10月25日由农业部牵头共七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应优先培育带农作用突出、整体竞争力强、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为农户参与并分享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并带动农村的产业融合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开辟新的路径。
一、传统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存在的弊端
(一)生产要素流动不畅。实施新型城镇化以来,随着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政支农制度的逐渐完善,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流动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等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呈现出逐渐优化的趋势。但是,在某些关键环节仍然相对滞后,没有形成有效的要素供给机制,阻碍了资金、技术等稀缺要素的顺利导入,导致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仍然较低,尚没有充分替代传统农业生产要素,使得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难以大幅提升,先进要素的缺失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有效提升,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处于更加不均衡状态,已成为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碍因素。
(二)产业链接功能虚化。农业产业链是我国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然而发展至今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分工水平低、产业链接短等,产业链的组织结构和层次分布相对单一,主要停留在“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层次,因而这种组织形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功能虚化。如在“企业+农户”组织模式下,通过龙头企业带动部分兼业型农户从事专业化农业生产,为了顺利地走向市场农户与龙头企业签订农产品销售合同,而龙头企业为了保证原材料的充足供应也与家庭农场签订购买合同,通过契约形式维护农业产业链的稳定,但这种组织模式存在着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因而履约率长期低下,从提高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而言,当前各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均程度不一地存在着内在的缺陷。
(三)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在传统合作模式下存在着较高的交易成本,如龙头企业与家庭农场之间签订的“订单式”及“承租式”合约均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投机风险,龙头企业没有形成专用性投资时会在市场低迷情况下毁约退出,而在形成专用性投资时又容易受到家庭农场的“要挟”触发“柠檬市场”的形成。基于资源共享和风险规避为目的成立的农民合作社,承担着协调家庭农场利益诉求的功能,且需要解决小规模耕地带来的诸多衍生问题,因而运营成本高、合作绩效有限。同时,由于龙头企业处于支配地位,在处置利益分配关系时常常向自身倾斜,而家庭农场则居于产业链的末端,当约束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时各方的利益调节困难重重,因而如何处理各方的产权关系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分配机制十分重要。
二、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创新逻辑
(一)推进要素流动。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创新的有益探索,为农村的产业融合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破解了主体、产业和区域之间的条块分割局面,真正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一方面,通过产业链的重构引入了各种稀缺因素,使农业产业从无序竞争走向彼此渗透,并将组织创新的价值不断内化给联合体内的各市场主体,有效地提升了稀缺要素置入农业产业的效率。同时,联合体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健全的传导机制,可以通过信用传递、风险管控等手段降低资本要素进入农业产业的风险,这种“润滑作用”消解了金融资本进入农业的阻力。
实践证明,联合体可以通过资产、资金、技术、品牌等生产要素的相互融合,打通优质要素进入农业产业的通道,对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以及破解农村产业融合度低等均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以农村金融为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联合体来考量家庭农场的信用状况,同时联合体以协同发展的目的为家庭农场提供信贷担保,进而破解金融机构和家庭农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机构的借贷风险。如在安徽省宿州市的淮河粮食产业化联合体中,淮河种业有限公司作为龙头企业为家庭农场提供贷款担保,而家庭农场则以土地经营权和生产的农产品提供反担保,且为家庭农场购买生产资料时先行垫付资金,在购买家庭农场生产的农产品时予以相应扣除,帮助家庭农场解决了由于担保物缺失所带来的资金问题,从而有效破解了家庭农场贷款难、金融机构放贷风险高等难题。
(二)闭合产业链条。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家庭农场为基础、农民合作社为纽带,其中龙头企业是联合体制度架构的制定者,信息和资金优势明显,直接关系到联合体的组织架构和运营效益是否稳定,但是龙头企业管理层级多、监管成本高,由其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明显不合适,反而作为技术和标准的提供者较为适宜,因此应定位于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的角色;农民合作社是农村互助性服务组织,在动员和组织农民生产以及产中服务环节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因而可以将服务功能适当下移到农民合作社;联合体的基础是家庭农场,家庭农场的生产规模高于普通农户,且拥有土地经营权和熟练劳动力并具备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应主要负责农业耕作和水产养殖等。
因此,总体而言在联合体内经营决策能力突出的龙头企业应负责决策制订,家庭农场负责农业生产活动,农民合作社居中发挥两者之间的服务联结和组织协调等功能,进而通过适度的权力让渡使三者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最大程度地发挥优势。例如,安徽省宿州市以强英集团为龙头企业建立的鸭业联合体,为了更好地激励家庭农场的生产积极性,强英集团积极帮助家庭农场解决养殖设施和养殖用地等问题,以联合体的名义来租用土地和家庭农场共建养殖小区。其中,强英集团负责土地租金和养殖设备等前期投入,农民合作社担负起监管和沟通等职能,而家庭农场则负责水电工程和饲料投喂设备方面的投入,鸭苗和饲料由强英集团提供,家庭农场只负责繁育且产品由强英集团直接收购,通过这种投资模式使联合体内各经营主体实现了“捆绑式”发展,解决了集体行动中“搭便车”以及逆向选择等问题的出现。
(三)稳定利益框架。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构建联合体内各经营主体之间持久稳定合作关系的关键,在本质上而言各方合作的目的是追求合作剩余的最大化,即合作之后产生的剩余必须大于非合作的剩余之和,否则各方势必会失去合作的动力,这就要求合作之后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必须明显提高,同时合作剩余的分配机制也必须完善、公平。对于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来说,随着农业生产服务能力的提高,如何保障那些价格不菲的农业机械满负荷生产成了首要问题,而对于龙头企业来说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公众对优质、安全、生态农产品越来越关注,要求龙头企业必须从源头上把控农产品的品质,因此三方均亟需持续性强的合作对象,把短期合约变为长期合约,以降低市场风险和违约风险,因而联合体能够提供稳定的利益框架。
在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中,龙头企业通过稳定合理的收购价格保证农民在农业生产环节应得的利益,并通过优惠供应种畜、种苗等手段使家庭农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利益补偿,除了采取价格保护策略之外,还能够把加工、销售环节的部分利润返还给家庭农场,尽可能使家庭农场与龙头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处于平衡状况。从安徽省宿州市成立的联合体的实践经验来看,获得稳定的收益是各参与主体的初衷所在,如农民合作社的大型农业机械如果服务于普通农户则每亩收费为50~60 元,每天的最高运行负荷约为60 亩左右,因而一天的毛收入低于4000 元;如果服务于家庭农场,即使每亩只收取30元的服务费,但每天可以作业200 亩左右,在考虑折旧费和驾驶员工资的前提下每天净利润可以达到5000 元左右。因此,加入联合体之后农民合作社的收入状况更为理想,且降低了家庭农场的生产成本,实现了合作各方的共赢。
结束语: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演进过程中,可以发现单一主体独立经营面临着诸多困难,而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最新进化形式,通过生产要素在联合体内的有序流动,促进了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践证明,联合体可以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脱节问题,对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农村产业融合瓶颈的破解,进而实现合作共赢的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