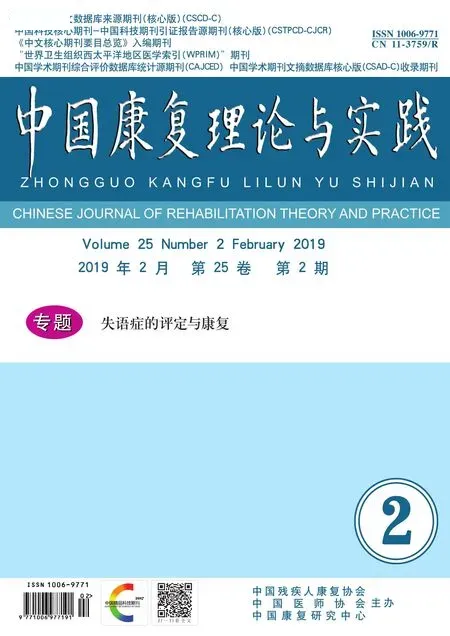老年人噪声下言语识别的影响因素及听觉认知训练
2019-01-07王贞龚树生
王贞,龚树生
1.北京博爱医院听力语言科,北京市100068;2.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北京市100050
日常生活中经常面临在噪声下交流的情况。绝大多数人随着噪声的加大,感觉交流愈发困难,尤其是老年人。即使他们没有听力下降,也经常抱怨在饭店、音乐厅或者街道上无法听清楚别人的说话内容[1]。并随着老年性听力损失的加重而愈发明显。虽然外周听力损失是噪声下言语识别能力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很多研究已经证实,听觉中枢处理能力和高级脑功能认知水平,如记忆力和注意力下降,也是导致老年人噪声下言语识别能力下降的原因[2-3]。
1 噪声下言语识别的神经生理机制
参与言语识别的内容包括低水平外周听力、听觉中枢处理能力和高水平认知功能。外周听力下降是指听力学测听阈值升高,是感觉输入的减少。听觉中枢处理能力是指神经系统将从外周听觉系统接收的信息加工处理,转换成为可感知的成分。准确的听觉中枢处理有对声音和语气的处理,言语信号间隔和持续时间的感知,音素,以及时间包络模式和频谱信息识别[4]。此外,认知功能包括记忆能力和选择性注意力以及信息的处理速度和语义的整合[5-7]也会影响噪声下言语的理解。言语处理过程不仅需要接受到声音信号,并对言语声和单词进行感知和识别,还需要对听到的单词、短语和句子进行整合,以得到连续和确切的含义[8]。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神经网络分别作用于声音感知和言语信号的处理,但是彼此之间又相互关联。将声音投射到语义,依赖于将声学和语音分析的结果与大脑存储的词汇相匹配[9-10]。
正常情况下,输入的言语信息自动处理,建立音位表达。当自动建立的信息与长期记忆库中的信息相匹配时,单词即被感知。但是,如果自动建立的信息不能与记忆中的信息相匹配,例如当信号被降级(如噪声环境下)或者信息输入减少(听力下降)时,一种明确的和更努力的认知处理过程将参与其中,尝试去补偿音位表达和长期记忆库中信息的不匹配。因此,当听觉环境嘈杂或者听力损失时,从上而下的工作记忆或者注意力处理将影响言语的感知[6]。
2 作用机制
老年人噪声下言语识别能力下降与外周听力、听觉中枢处理能力和认知水平三者均有关。相互作用机制探讨如下。
2.1 共同原因
老龄因素同时影响外周听力、听觉中枢处理能力和认知功能。听觉系统与身体的其他系统一样,由分子和细胞组成。因此,听的过程是分子和细胞的处理过程。与老龄相关的改变如脑血管疾病,同时会影响感觉和认知功能[11-13]。
Humes等[14]对年龄、感觉(听觉和视觉)和认知功能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全部感觉功能随年龄的增长会逐渐衰退,认知功能也同时出现下降。所有的感觉和认知任务都涉及刺激物的呈现,感觉系统对刺激物的处理主要在认知之前。只有当感觉系统处理后,认知才能参与。因此,老龄对从环境中提取感官信息的能力产生负面和主要的影响,观察到的认知缺陷有可能是这种感觉缺陷介导的。
2.2 降低-补偿假说
认知可以补偿感觉输入减少带来的影响。老龄大脑在执行有听觉中枢处理和认知需求的任务时,神经生理特征是听觉中枢区域的活跃性降低,同时一般认知区域的活跃性增高。对于老年人来说,双侧对称性听力损失导致听觉中枢处理障碍,特别是颞上回的活动性降低。而作为补偿,大脑认知区域(额叶)的活跃性普遍提高[15]。
当倾听发生在较差环境如在噪声下倾听时,左侧额下回的三角部和左侧额上回表现更加活跃[16]。当然,前额活跃性与老年人噪声下言语识别能力呈正相关。Zekveld等[17]研究发现,阈上听觉处理伴随着数十年的逐渐下降,经过大脑重组,前额叶区域的活跃度较年轻的对照组更加活跃。当言语变得越来越难于感知时,处理过程将更多地依赖额叶自上而下的影响。一个影像学研究得到相似的结论。同年轻正常听力的对照组相比较,听力损失老年组额叶的体积和噪声下言语识别能力具有更高的相关性[16]。即使有更高水平大脑功能的补偿,老年人在噪声环境下或者语速太快的情况下,对言语的理解均有不成比例的困难。
但是这种长时间神经解剖学上的改变,包括调动前额皮层活跃性去保持感觉能力,可能是把双刃剑,这种改变可能导致与噪声下言语识别能力有相关的认知能力下降。
2.3 信息退化假说
降级的信息输入直接影响认知资源。当感觉信号减少,不管是因为刺激减少还是感觉障碍,如噪声下言语信息输入减少,更多的认知资源将被调动去破译信号。有研究通过瞳孔的反应来评估认知负荷。当完成听觉任务时,听力损失者瞳孔的反应性更高[18],说明更多的认知资源被调动。这将导致完成其他认知任务的资源减少。
一些对瞬时记忆能力的研究发现,当回忆被干扰(例如增加噪声)的单词时,即使保证单词可以被准确识别,任务完成能力也会下降[19-20]。有证据表明[21],认知系统需要更多的努力去解码降级的刺激,这些努力占据认知的资源。相同的影响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中都有发现,所以并不是很清楚老龄因素是不是会加重这种不足。
一些研究已经证实,对比听力正常组年轻人、听力下降组年轻人和听力下降组老年人,发现有听力损失的年轻人和与其听力水平匹配的老年人,完成口语短时记忆任务时无明显差异,均明显低于听力正常年轻人[22]。Rudner等[23]想描述和量化感觉输入减少时认知资源的损失程度,引入一个“认知闲置能量”概念。不利条件下的言语交际对认知资源有特定的需求,特别是工作记忆能力和执行功能都参与语音信号的解析。这将耗尽认知闲置能量,并为更高级别的语音处理留下更少的资源。
最近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在噪声环境下听声音时,听觉皮层的活动比年轻人要少,尤其是在信噪比低的情况下,通过调动与工作记忆相关的前额和顶叶区域来进行补偿。
2.4 感觉剥夺假说
感觉剥夺假说认为长时间的感觉障碍导致慢性认知的改变。Lin等[24]研究发现,听觉能力下降的人罹患认知障碍的比率明显升高,同时通过为期6年的临床观察,发现其认知能力下降也更为迅速。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感觉的剥夺,持续不断的努力补偿会给认知功能带来很大的压力,最后导致严重的认知障碍。
对33个研究的Meta分析指出,无论有没有介入康复治疗,存在外周听力下降的老年人,其认知功能均较听力正常者明显下降,听力损害的严重程度与认知任务完成水平明显相关[25-26]。Valentijn等[27]通过一个6年的研究发现,虽然外周听力下降与认知功能测试结果之间存在明确的相关性,但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6年来外周听力下降的基线可以预测认知能力下降;而与认知能力下降更为相关的是中枢听觉处理能力,因此,要更加关注老年人的听觉中枢处理能力。
认知与听觉中枢处理之间明确的因果关系证明,听觉中枢处理能力的衰竭会影响认知功能,既直接又长远[28]。
2.5 认知负荷假说
认知能力低下影响听觉中枢处理任务的完成。听觉中枢处理能力与认知高度相关,很多复杂的听觉中枢处理任务受认知能力的影响。但是,研究者发现,认知对听觉中枢处理的影响并不是纯粹的认知能力下降导致听觉中枢处理能力降低。Pichora-Fuller等[29]报道,外周听力和认知水平均较高时,如果在噪声环境下分辨声音,认知参与的程度也较高。而当认知水平下降时,参与的程度也随之降低,从而影响听觉中枢处理任务的完成。从上述两个假说可以发现,有很强的证据证明认知对于受损的听觉中枢处理能力的调节起到补偿作用。当认知能力下降时,这种补偿能力也随之下降。
对于老年人来说,听觉中枢处理能力与认知水平有明确的关系,不仅随年龄的增长同时下降,受干扰的感觉输入(听力下降或者在噪声下交流)给认知系统带来更多的负荷,占据更多的认知资源,影响认知即时处理。随着时间的流逝,长期的感觉剥夺会导致认知能力的全面下降。认知水平下降导致对听觉中枢处理的补偿作用减小,反过来影响听觉中枢处理能力。
分析以上听力下降、听觉中枢处理能力与认知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也为老年人噪声下言语识别能力的康复治疗提供了依据。提高输入刺激的治疗方法(如验配助听器),听觉训练和认知功能训练[30],有助于老年人噪声下言语分辨能力的提高。
3 听觉训练及认知训练
3.1 助听器
考虑到有听力障碍的老年人在交流过程中尤其是在噪声环境下表现出来的困难,一些方法已经被应用于部分恢复听觉功能的研究中,如咨询服务、听觉训练和助听器的使用。
助听器可以改善可听度,是现在针对轻中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主要的方法。听觉训练可以改善听者的交流,补偿降级的声音信号[8,31]。然而,通过使用助听器获得信号的可听度,是所有训练取得效果的前提。
大量的研究证实佩戴助听器的效果,尤其是在安静的环境下[32]。但是,Humes等[33]跟踪9个双耳佩戴助听器者3年,不同时间段分别进行噪声下音节分辨、安静状态下言语分辨和噪声下言语分辨测试,结果显示无明显改善。有研究对比新的单侧或双侧助听器使用者和有经验的助听器使用者,发现三者之间的言语识别能力仅有很小的增益[34]。即使得到最优的验配效果,老年人也会抱怨他们无法清晰分辨单词,无法理解语言,特别是在噪音环境下。
这些障碍可能是因为年龄相关的瞬时听觉处理障碍。例如,因为神经同步性受损[35]、神经兴奋性恢复延迟[36]等均导致听觉系统无法精确编码言语的时间特性。老年性听力下降易导致听觉中枢对时间和空间的反应性能下降,使目标言语被噪声掩蔽的情况更加明显[37]。助听器放大声音刺激听觉通路,而听觉通路在某些个体中,已经因为听觉剥夺而发生改变。
此外,助听器改变声音的物理特性,这些都可以解释为什么适应新的助听器需要时间和练习。Dawes等[34]研究第1周佩戴助听器和佩戴12周后事件相关电位N1和P2波的振幅,发现没有改变,证明缺乏神经编码的习服。而Rao等[38]评估与认知能力相关的时间相关电位P3,发现经过4周的佩戴,P3a振幅明显降低,说明有生理的变化,但是听觉中枢处理能力的评估-噪声下听觉测试却没有变化。
总而言之,现在还不清楚使用助听器能否有利于听觉中枢处理功能的神经重塑。最近Karawani等[39]对使用助听器后神经和行为改变进行研究,通过对比老年感音神经性聋患者佩戴助听器前和佩戴6个月后,发现神经同步受损和神经恢复延迟等神经系统的不足可以通过长时间佩戴助听器得到部分抵消。但是机制仍不清楚。
3.2 听觉中枢处理和认知训练
听觉中枢处理训练是指对声音的积极反应,通过这种反应,受训者学会对呈现的声音进行系统性地分辨。听觉中枢处理训练的目的是至下而上地对声音进行感觉的提纯。认知训练是指参与标准化、具有挑战性的认知任务,提高不同的认知功能[40]。这两个方法的目的都是开发神经的可塑性来提高功能。
神经可塑性的概念对于存在神经退行性病变的老年人来说至关重要,是解剖结构和生理过程(听觉处理,记忆巩固)的调整。当一个人在训练中获得新的知识或者技能时,这些信息可以加强现有的神经通路和网络,或者导致新的神经回路和突触的产生[41]。计算机辅助下进行听觉中枢处理训练和认知训练,患者接受重复的刺激,反复进行强化听觉中枢处理和认知能力的操作[42],积极的参与训练可以产生大脑重塑性改变,提高听觉中枢处理和认知能力。
为了确定听觉中枢处理和认知训练是否有效,研究者通过评估任务执行能力来判断。任务包括已经训练的任务和通过学习转化的未学习内容。后者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前者[43]。当然,干预只能在坚持训练中才会有效。有研究证明[44],计算机辅助的家用听觉中枢处理训练程序对有听力损失的老年人的言语识别能力有稳定持续性的改善。最初Henshaw等[45]研究报道,家用听觉中枢处理训练程序对听力障碍者的言语识别和认知水平均有明显的效果。之后,一些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向Henshaw等求助这个方法的参数(以家庭为基础,可远程监控)。为此,Lawrence等[46]将这一证据进行回顾,内容包括13篇已经报道的相关文献,均证实介入治疗后言语识别能力得到提高。随后更多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证实听觉训练程序在改善听力损失患者的听觉中枢处理和认知功能方面的治疗意义[43,47]。
认知训练程序可以改善健康老年人[40]、轻度认知损害[48]和帕金森病患者的认知水平[49]。对于听力障碍患者,初步的证据可以证实[45],认知训练程序可以改善电子耳蜗植入术后患者的工作记忆、执行能力、言语记忆和注意力。研究还提出,听觉中枢处理与特定认知能力(注意力和工作记忆)皮层区域相关。Anderson等[37]对比以听觉为基础的认知训练,发现通过训练,噪声下言语的神经反应时间、短时记忆能力和处理速度均得到改善。另外,还有研究报道,工作记忆与噪声下言语识别能力的提高有密切的关系,认知训练程序可以通过训练认知的部分领域(工作记忆)改善认知和听觉中枢处理能力[50-51]。
综上所述,老年人多存在噪声下言语分辨能力障碍。究其原因,外周听力障碍、听觉中枢处理能力和认知功能低下是最主要的原因。研究表明存在行为学上的相关性和病理生理学上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计算机辅助的家用听觉中枢处理训练和认知训练可以很好地促进神经重塑,无论是从听觉训练的角度还是认知训练的角度,均可以明显改善老年人噪声下言语识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