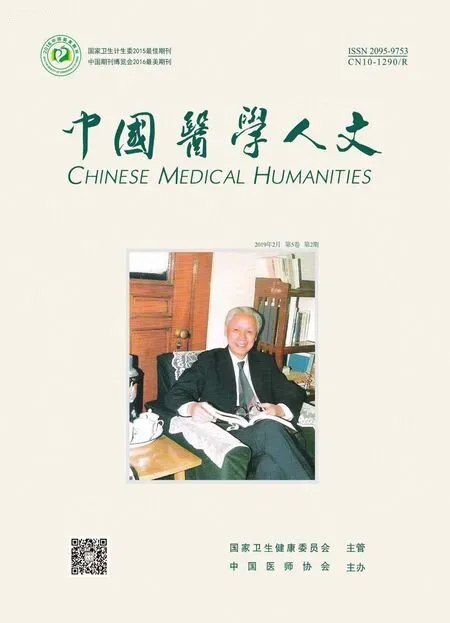病人、医生、家属三重视角下的袁宏道“临终病历”
2019-01-05李远达
文/李远达
袁宏道是晚明文学流派公安派的主将。他从发病到死亡的全过程被其弟袁中道记录在日记《游居杮录》中。这部日记里的袁宏道“临终病历”为我们呈现出病人、医者与家属不同心态、不同立场的三种视角。病人疾病自述中的苦感叙述与生死反思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医者的无能与缺位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古代士人与医者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病人家属经历了由忧虑到痛苦,再到怀念与解脱的复杂过程,也与当下病患家属的心路历程相吻合,甚至更细腻。从袁宏道的“临终病历”中,我们可以窥知古代医学叙事的基本特色与精神意蕴。
考察文学家的临终状态,不仅能为我们提供中国古代医学与文学交汇的丰富侧影,也能帮助我们了解文学家不同的生活面向。晚明文学家袁中道的日记《游居杮录》记录了他的哥哥袁宏道从患病到死亡的全过程。可以看作是一部珍贵的“临终病历”。它的珍贵性,与日记的文体特征有关。日记这种文体,在袁中道生活的晚明时代,基本上还是写给自己看的,因而保证了真实性和连续性。可以说,袁中道的日记是一种非虚构的纪实文体。同样是散文大家,袁中道叙事能力极强,寥寥数语就能勾勒出事件的来龙去脉,描摹出人物的音容笑貌。因而使得日记文字有极强的感染力和亲历感。这份“临终病历”,可以分为病人的自述、医者的形象塑造以及家属的心路历程这几方面的内容。
病人自述:苦感叙述与生命反思
病人的自述,在现代中国的材料中较为少见。因为作为疾病主体的病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在古代中国,恰好相反,文字表达权掌握在士大夫手中,因而是我们能听到部分病人的声音。这些病人心声得以保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患病的士大夫有可能保留自述文字;另一方面是文人雅士自古有叹老嗟病的传统,也容易使得疾病体验文献得以保留。这种传统,从鲍照谈病的诗赋,到杜甫的咏病诗歌中,都有体现。
袁宏道恰好是这样一位既熟悉疾病叙事传统,又有反思意识的晚明士大夫。他是晚明文学流派公安派成就最高的文学家。他少年得志,很早就进士及第,十余年间,就升任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陕西乡试。他的诗文主张“性灵”,名闻天下。这样一位大才子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春请假南归湖北公安故里,没想到当年九月就猝然去世于湖北沙市。
在患病到去世的短短两个月时间里,袁宏道多次向弟弟袁中道表达了患病的身体感受,这是一种苦感叙述:据《游居杮录》卷五记载,万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袁中道为哥哥料理药饵,袁宏道自述道:“昨为医者着一分参,遂热不可支,盖我系阳脏,不堪服补药,又不敢服凉药。不若不药为妙。”袁宏道所患的“火病”,仅据《游居杮录》的材料看,还无法辨明。但用人参等补药,自然会火上浇油,“热不可支”,但又不敢服用寒凉的药物,只能无奈地选择不吃药。这与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年任吴县令时患疟疾的两难处境十分近似:那一次他“医延三人,时踰数月,秋毫莫效,精血损耗,瘦骨如戟,愈补愈虚,转攻转盛。”1(《乞改稿一》)在传统医学的诊疗过程里,如果辩证不准,很容易“愈补愈虚,转攻转盛”。与那次患疟疾的体验相比,这次导致袁宏道死亡的“火病”反而没有那么剧烈的身体反应,至多就是“热不可支”。直到临终之时,袁宏道的遗言还是:“我略睡睡”,似乎没有经历什么痛苦就“坐脱去”了2。以至于这种死亡的方式给了弟弟袁中道很大的安慰,成了他作为家属得以在心理上解脱的重要原因。
人终有一死,如何看待疾病与死亡,体现着病人的思想境界与认识水平。翻阅袁宏道文集,笔者在《德山笔麈》这部语录体著作里找到了这样一段话,是袁宏道对于临终体验的理性分析:
问:“每见学人于疾病临身,便觉昏愦,如何平昔工夫,到此却使不上?”答:“……至于疾病生死现前,虽悟明人,有病亦知痛苦,其临终亦或有昏愦者,皆不足论。盖昏愦与不昏愦,犹人打瞌睡与不宁丁瞌睡,安有高下耶?夫疾病已是苦矣,复加个作主宰之念,则其苦益盛。况临病时,且不愁病,先愁人看我破绽,说学道人,如何亦恁的受苦,遂装扮一个不苦的人,此便是行险侥幸入三塗的种子。噫!自为已知几之学不讲,世间好人以生死为门面者多矣,不如那昏聩的却是自在。”3
袁宏道是一位禅净兼修的大居士,佛教造诣很高。在还未患病之前,他就已经对临终问题进行过一番思考。他认为疾病本身就是一种苦痛,如果害怕别人说你一个修行人,怎么这样痛苦?反而装作不痛苦,那就是给自己加上个“作主宰”的妄念,套上了一重枷锁,不得自在了。他特别谴责那些“世间好人以生死为门面者”,认为他们还“不如那昏聩的却是自在”。袁宏道有着一种对生死的超脱性反思。在参禅拜佛成风的晚明时代也很少有士大夫能达到这样的了脱生死、纯任自然的精神境界。
除了不惧怕死亡,袁宏道还有一套养生之道。虽然他只活了四十三岁,但他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已经在有意识地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忏悔过去的纵情声色。在《游居杮录》里,弟弟袁中道也记载了哥哥袁宏道多次表达的:“四十以后,甘澹泊,屏声色,便是长生消息。四十以后,谋置粉黛,求繁华,便是夭促消息。我亲见前辈早夭人,个个以粉骷髅送死。此后工匠事毕,洒扫楼上,每日坐三炷香,略做胎息工夫。”2袁宏道确实按照道家胎息的修炼方法进行了调养,但世事无常,甚至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在袁宏道已经潜心寻求宗教慰藉之时,他的生命也悄然走向了终点。
医者的形象塑造:平庸无能与叙述缺位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眼中,医者是一个较为寒微的职业,虽然北宋曾出现过一批受人尊敬的儒医,但总体而言,在为士大夫诊疗疾病的过程中,职业医者在权力关系中处于绝对劣势。翻遍袁宏道“临终病历”,两位医者连名字都没有,就很好地说明了问题。
从疾病进程的角度说,袁宏道从患病到去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火病”发作到请李、陈两医诊脉,日记从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细读这五天的日记,在袁宏道患“火病”的初期,袁家曾延请过李姓和陈姓两位医生,两人的诊脉结果竟然都是“无病”2。其中李姓医者已经有八十余岁了。在凭借经验的中国传统医学里,年纪越大,经验越丰富,诊断和用药也就越准确,年龄本身似乎就确证着某种权威性。这一结果也确实曾经使袁中道“意稍安”。然而次日,袁宏道自己就对李医开的药提出了质疑,感到服药不效,还“燥热难支”“不若不药为妙”。作为亲人,袁中道只得安慰他。隔了一天,“中郎火病益甚”,袁中道就派人请来了另一位陈姓医生。这次切脉的结果依然是“无病”,袁中道却没有像前次一样得到安慰。袁中道暗暗忧虑,而这居然引来了身边人的嘲笑。
紧接着袁宏道的病情急转直下。袁中道开始一刻不离地陪护哥哥,直到在僧人祈祷下病情稍有“起色”,这是病情的第二阶段2。在中医理论中,病人神志是否清醒是判断病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八月二十七日这天夜里,袁宏道“神明渐乱”,袁中道急得流了眼泪。二十八日,袁宏道已不能走路,大小便都有血,二十九日饮食渐少。病情越来越重,医药的力量看起来已经不能有效地控制病情发展了,一向信佛的袁氏兄弟想到了求助宗教的力量。九月初一日,袁宏道“病稍可”,袁中道便急忙和僧人宝方在大士塔下祈祷。值得思考的是,医者在这一阶段完全是缺位的。无论是李医还是陈医,只有“服医药不效”这一句与他们有关:他们无论是诊断,还是开药,都没有任何作用。袁氏兄弟宁可求助虚无缥缈的宗教力量,也不愿意再信任近在眼前的医者药方。病患微妙的内心变化颇值得玩味。
接下来便是袁宏道生命的最后三天,也即弥留之际2。九月六日,在袁宏道生命的最后时刻,八十多岁的李姓医者再次出现了。关于邀请医者的方式,袁中道使用的词汇是“急呼”,虽然病人危在旦夕,不假思索,但下意识反应里的一个“呼”字,李医低下的地位一望可知。同时,正是这位李医,前面曾将袁宏道诊断为“无病”,而此刻的诊脉结果则是“脉脱矣”,也就是性命垂危,随时可能死去。前后的巨大反差无异于自相矛盾,其医术的拙劣,不待袁中道点明,读者自然明白。李医给出的最后的办法是古代中医常用的抢救方法:“且试人参汤”。喝下人参汤之后,袁宏道虽然暂时缓过来了,但是气喘不止,在留下临终遗言“我略睡睡”之后,便溘然长逝。
关于袁宏道之死的病因,袁中道在后来写作的《答黄驾部取吾》这封书信中认为是:“中郎未有大病,偶以下血脱气,遂至不支”4。他绝不认同李医和陈医那般颟顸用药,草菅人命。把一个本来不至于死的小病变成了葬送兄长的凶症。孰是孰非,今天的读者已无从下判断了,最终的结果是家属痛失亲人。于是,在由家属整理的这份“病历”里,两位医者的形象必然是无能而缺位的。叙述背后所透露出的士大夫与医者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更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古代士人与医者互动模式的一个典型个案。
家属的心路历程:从忧虑到痛苦、怀念与解脱
家属是医患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既是病人的照料者与感同身受者,也是医生与病患之间沟通的最佳媒介与桥梁。同时,他们往往有自己的观察角度与叙述立场。袁中道的《游居杮录》记载的这份“临终病历”其实就是一份包含了病人自述与医者形象的家属日记。这份“病历”为我们呈现了包括袁中道在内的家属随着袁宏道病情变化而产生的心理波折:从对疾病的忧虑,到对亲人离去的痛苦、怀念与解脱的完整过程。
作为病患家属的袁中道,在兄长袁宏道病中就多次表达过忧虑:八月二十六日,请陈医再次诊治后,袁中道“独予私忧之”;二十八日,看到袁宏道大小便血不止,“予私忧之甚”;二十九日,“予卧不交睫”;九月初四日,“甚忧之”;初六日,“予顿足仆地”。作为旁观者,家属的观察更为客观细致,因而忧虑也更为深刻。袁中道日记中的忧虑真实地反映出古今家属在侍疾时候的心理变化。
袁宏道病逝后,袁中道的第一反应是痛苦:他大病一场,“亦自绝于地,久之始苏”,几乎丧命,可见兄弟感情深挚。袁宏道、中道兄弟相差两岁,自幼一起读书,长大后又多次一起漫游。两人的感情到了“相依为命,一日不晤,便无以为怀”4(《答黄驾部取吾》)的程度。《游居杮录》中抒发了袁中道自己作为亲历者的感怀:“一朝遂失仁兄,天地崩裂,以同死为荣,不愿在人世也。”2手足情深,袁中道亲见兄长的英年早逝,对其打击之深,可以想象。此语绝非俗套,而是真性情的流露与告白。
袁宏道之死,引发了家属持久性的敏感与怀念。日记中的材料屡见不鲜。这种敏感与怀念多数发生在不经意间。家属被毫不相干的情境所触动,在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之间建立起独特的逻辑关系。因其无以名状,故而分外感人。例如《游居杮录》卷五有这样一则记载:“午后过林兰阁,小女儿牵予裾曰:‘我念诗与阿爷听:路逢萧史不回身,风袅芙蓉绣领巾。云里自然标格少,但凭闺艳作仙人。’予不觉泪下,此中郎《游仙诗》也。”2袁宏道的音容笑貌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袁中道的日记才得以跃然纸上。
家属对于逝者的怀念,最突出地体现在梦魂深处。在袁中道的梦境里,哥哥袁宏道出现过五次,其中最精彩的一次在《游居杮录》卷六:袁中道梦到和死去的哥哥对弈,两人相谈甚欢,他用手抚摸哥哥的身体,发现竟然“甚煖,非逝者相也”,这对袁中道来说,是多大的“鼓舞”啊!难怪他要“踊跃欲告人”2。“而醒”二字使得整个故事急转直下,原来是邯郸一梦。“醒”是中国文化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醒”意味着美好的不再,意味着从梦境龟缩回现实,即使冷静地妥协,又包含万种无奈。醒来才知道美好皆成梦幻泡影,怎能不令人悲伤呢。字字平淡,又字字血泪。细细想来,万事到头皆是一个“空”字,美好的事物总是不长久,这种梦魇,对每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恐怕都会不止一次的出现吧。
袁中道对于兄长之死,最终的解脱,是通过宗教的方式完成的。如《游居杮录》卷十,记载了秀才周蕃在冥间看到袁宏道地位尊崇的故事。借冥间为神的袁宏道之口说出那句“大凡作人要好。作人好者,即夭折亦自有佳处可往”2的话,恰是道尽了袁中道对死去哥哥在另一个世界最美好的期许与祝福。将祝福作为麻醉剂,使生者更好地活下去,不失为面对死亡命题时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它脱出了民间信仰层面的躯壳,具有了宗教解脱的意味。
余论:“临终病历”的精神“疗救”
观察作为文化事件的袁宏道之死,除了文学史的意义——改变了晚明时代的文坛格局之外,从医学叙事的角度看,这个事件最值得玩味的是袁中道用饱含深情又懂得节制的文字直面疾病与死亡。细读《游居杮录》,我们可以读到一位与文学史叙述不一致的袁宏道:他才华横溢,放荡不羁,但并不是一味放浪形骸的风流才子。在逝世前不久,他还多次与弟弟谈论养生事:“我亲见前辈早夭人,个个以粉骷髅送死。”然而事与愿违。袁中道的无尽痛苦也是有节制,有解脱的。在哥哥去世那年除夕,袁中道对他的朋友度门说:“今年受生人之苦,骨肉见背,受别离苦,一也。功名失意,求不得苦,二也。自归家来,耳根甚不清净,怨憎会苦,三也。秋后一病,几至不救,病苦,四也。生人之趣尽矣!”四苦并作,袁中道心境差极了。但度门的一番话点醒了袁中道:“不如是,居士肯发此勇猛精进心耶?”2人生的苦难无法避免亦不可逃避,那么无论是儒释道哪一家,都给袁中道提供自我解脱、追寻生命意义的无上法门。
从袁宏道的“临终病历”中,我们可以看到病人、医者与家属三种不同视角下的疾病与死亡,也可以窥知中国古代医学叙事,尤其是士大夫疾病与死亡叙事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病患的士大夫本位意识;森严等级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歌咏老病的叙述传统;疾病与死亡的反思尝试和三教融合的解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