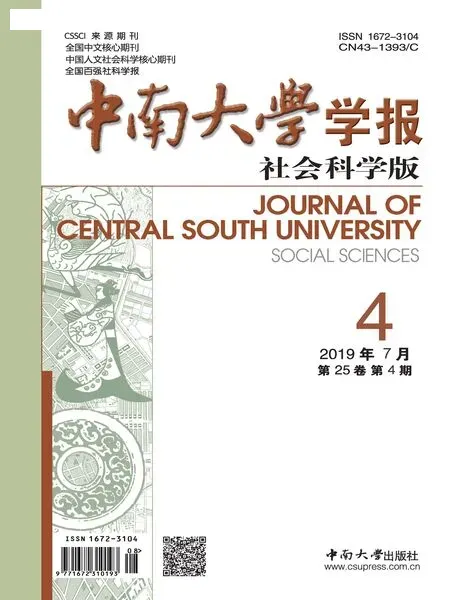论钱曾注《病榻消寒杂咏》对钱谦益形象的书写
2019-01-04张娜娜
张娜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102488)
明清之际的著名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关于他的形象问题,学界虽有较多研究,然多关注其“遗民”或“贰臣”的身份及其忏悔心态,而未能从阐释学角度,通过分析其颇具“筑构性”的诗歌话语来认识其人。诚如严志雄先生所言:“牧斋研究(自觉或者不自觉)泰半仍陷入一种泛历史、泛道德主义的话语、心理形式中。这似乎是一种没有出路的封闭回圈。”①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钱曾对钱谦益组诗《病榻消寒杂咏》46首的注解,来理解钱谦益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物心态和形象,即“以诗识人”“以注辨人”,从而跳出学界的“封闭回圈”。
钱曾,字遵王,号贯花道人,乃钱谦益族曾孙。他亦是钱谦益门生,尝得亲炙后者,其诗歌艺术成就颇高,超越了当时颇具声名的虞山诗人冯舒、陆敕先等。钱曾初步完成对《初学集》和《有学集》的笺注之后,曾就正于钱谦益。钱谦益在《复遵王书》中对钱曾注释表示赞许:“余心师其语,故于声句之外,颇寓比物托兴之旨。廋词隐语,往往有之。今一一为足下拈出,便不值半文钱矣。”[1](1360)钱谦益诗歌晦涩难懂,而钱曾能将这些“廋词隐语”一一拈出,加以注释,“于诗中典故,皆能得其出处,与叩槃扪烛者有异”[2](307)。实际上,钱谦益为钱曾注提供了一定的指导,甚至有学者认为其中有钱谦益自注②的成分。因此,这些注释对于我们理解钱谦益诗歌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钱曾看似在“代下注脚”,且客观地征引文献而少下按语,实则在注释点和文献选择上都表现出一定的主体性,在“发皇”钱谦益“心曲”的同时对其形象进行书写。目前学界多根据历史上的评骘话语来认知钱谦益,较少探讨钱曾注释对钱谦益诗歌解读和形象筑构的意义。因此,本文拟以钱谦益生前所写的最后一组诗歌《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③为例进行分析,立足于诗歌文本,探讨钱曾之注如何从身份与角色、政治时局观和生命情态三方面书写钱谦益形象。
一、角色类比与钱谦益的多重身份
钱谦益诗歌中的经典引用和情感表达都涉及他对自我的认知,他的“自我声音”就隐藏在诗中反复提及的杜甫、王维、韩愈等文人形象中。宇文所安在《追忆》一书中写道:“既然我能记得前人,就有理由希望后人会记住我,这种同过去以及将来居间的联系,为作家提供了信心。”[19](1)“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钱谦益乃至易代之际的诸多诗人都会将“自我声音”隐藏在诗歌所写的前代人事当中。而对于亲受钱谦益指导的“合作者”钱曾来说,他在注释词语、典故及解读诗句时亦相应地选择了一批历史人物,并裁剪他们的事迹或言语来为钱谦益代言。《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诗的注释中出现历史人物40余人,其中有谈忠说孝的名臣贤相,有流恨新亭的诗书文人,也有逃禅隐逸的高士。钱曾将钱谦益所传达的自我形象和注释中的历史人物放置在同一语义场中,客观上形成了角色之间的类比与印证,呈现出钱谦益的不同侧面和多重身份。
钱谦益虽因降清一事而于大节有亏,但成为忠臣贤相是其一生的理想,钱曾注释引用的只言片语还原甚至可能放大了暗藏在钱谦益诗歌中的隐秘情感。比如,《病榻消寒杂咏》其十五中有“羊肠九折不堪书,箭直刀横血肉余”之句。“羊肠九折”在清以前的诗词中,常为困顿文人描写宦海沉浮时所采用,如“羊肠九折歧路,老我惯经从”(辛弃疾《水调歌头》)、“太行羊肠坂九折,云黑风干尺深雪”(岳珂《太行道》)等。钱曾却抛开这些诗文,选择了“以传注诗”,钱曾引《汉书·王尊传》:
王阳至卭郲九折阪。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1](648)
钱曾所引只是王尊传记的上半段。《汉书·王尊传》下半段记载:“及王尊为刺史,至其阪……尊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3](3229)王阳感慨路途艰难,不当以身犯险,王尊则认为作为一名忠臣,必当勇往直前。王尊这一形象在古代诗文中已然成了表达忠臣理念的文化符号,如“公励王尊节,九折驱无难”(王敬臣《古诗送陈宪副雨泉之任滇南》)、“王尊策驭何壮哉,王阳回辙愁车摧”(江源《蜀道难》)、“勤劳本为公家事,非是王尊不爱身”(祁顺《山行写怀》)等,都是借王尊于九折阪的故事来表达忠心为国之意。钱曾以只言片语的注释,提示读者追溯典籍对王尊事迹和人格的褒扬,规约着读者解读诗意的方向,揭示暗藏在诗歌中为“公家事”而九死不悔的“忠臣”理念。钱曾注释以王尊为折射诗歌抒情主人公的镜像,从而书写了钱谦益的忠臣形象。
钱谦益作为文坛宗师,在组诗中常以主盟者的身份评判当时的文学风潮。与此相对应,钱曾在注释中对独持风裁的文坛泰斗着墨颇多,从而衬托出钱谦益文坛盟主的身份。《病榻消寒杂咏》其九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诗歌原文如下:
词场稂莠递相仍,嗤点前贤莽自矜。北斗文章谁比并?南山诗句敢凭陵。昔年蛟鳄犹知避,今日蚍蜉恐未胜。梦里孟郊还拊手,千秋丹篆尚飞腾。[1](643-644)
孙之梅在论述此诗时认为:“钱谦益直以韩愈自况,自信是文章泰斗,诗文可以流芳后世,对那些蚍蜉撼树者不以为然。”[4](421)明末清初,钱谦益在文坛上独领风骚,但时人对其褒贬不一,“誉之者曰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毁之者曰记丑言博,党同伐异”[5](208)。钱谦益以韩愈自况,批判文坛中攻讦自己之人,将他们比作蚍蜉撼树者。首先,钱曾“以钱注钱”,引用钱谦益《跋石田翁手抄吟窗小会》“今之妄人,中风狂徒,斥梅圣俞不知比兴,薄韩退之《南山》诗为不佳……虽其愚而可愍,亦良可为世道惧也”[1](640-641)。此注紧扣诗旨,直接揭示并补充了钱谦益诗歌中暗含的批判之意。其次,钱曾引用《新唐书·韩愈传》进一步阐释钱谦益以韩愈类比自我的心境,其中“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之语,颇似程嘉燧对钱谦益文学地位的评价——“其文章为海内所推服崇尚,翕然如泰山北斗”[6](1212)。钱谦益虽是文坛领袖,若直言自己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便会有自吹自擂之嫌,而钱曾以《韩愈传》作注成功地避免了这一问题。最后,钱曾注引用了《龙城录》中韩愈吞食丹篆之事,此事常被认为是对韩愈提倡的“古文”意趣的暗喻,在此亦达成对钱谦益文学成就的类比。总之,钱曾征引文献从侧面烘托出钱谦益在明末文坛别裁伪体、扭转时风的功绩,确证其文坛盟主地位,缩短了诗人表意与读者领会之间的差距。诗歌和注释之间,钱谦益和韩愈之间,相互补充和生发,塑造出钱谦益如同韩愈一般的文坛泰斗形象。
反清复明运动失败之后,钱谦益借以自我振奋、重塑自我的途径再次被阻绝,故而他在组诗中多次描摹自己在叹老嗟贫之中隐居著述的场景,其中引用了前代著述不辍的隐者或高士形象,尤其是东汉时期才华卓荦、洒脱不拘的仲长统。《病榻消寒杂咏》中有两处提及仲长统,一是“喑讶仲长还有口,痹愁皇甫不关风”,一是“病瘖何敢方河渚,摇笔居然颂独游”。钱曾注释引用东皋子《仲长统先生传》:“先生讳子光,子不曜,洛阳人。往来河东。开皇末,始庵河渚间以息焉。守令至者,皆亲谒,先生辞以瘖疾。著《独游颂》及《河渚先生传》以自喻。”又引《新唐书·王绩传》云:“仲长子光,亦隐者也。无妻子,结庐北渚,……绩爱其真,徙与相近。子光瘖,未尝交语,与对酌酒欢甚。”[1](640-642)钱曾在注释中对仲长统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了细部“特写”,将其和晚年同样患有瘖疾的钱谦益放置在同一文本中进行对比,铺陈演绎了诗文中的寥寥数笔,揭示了钱谦益以仲长统自喻的隐秘心理。注文中“守令至者,皆亲谒,先生辞以瘖疾”,道出士大夫在尧年值雪之时仕与隐的问题,这关乎钱谦益乃至所有易代之际文人的生存困境。仲长统“著《独游颂》及《河渚先生传》以自喻”,也是钱谦益晚年借助诗文扭转身份并尝试进行自我救赎的真实写照。钱谦益虽不像仲长统一样弹琴饵药以终其世,但是参考注释,读者会跟随钱曾注释的指引,将诗文中的抒情主人公和仲长统放置在同一个语义场中进行解读。严志雄先生在《〈病榻消寒杂咏〉论释》一书中认为:“牧斋以己为高洁自持,特立独行之高士矣。”[6](258)此外,瘖疾而不能言语,不只是钱谦益身体的病苦,也可能是其心理状态的写照。钱谦益《嘉禾访梅溪大山禅人四绝句》其四中有“莫怪机锋都未接,老夫原是哑羊僧”句。钱曾注“哑羊僧”:
虽不破戒,钝根无慧……不知有罪无罪,若有僧事,两人共诤,不能断决,默然无言,譬如白羊,不能作声,是为哑羊僧。[1](169−170)
背负降清之辱,钱谦益晚年抗清的志向和事迹很难为世人完全知晓。这种“病瘖”的身体状况和哑羊僧的形象塑造,是明清交替之际士大夫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创伤性言说方式。
作为“失根”士人群体中的一员,钱谦益以降清保全性命,却遭受强烈的道德谴责,其诗常有自嘲、自伤之语。组诗的第一首写道:“年老成精君莫讶,天公也自辟顽民。”[1](636)按《尚书正义》,“顽民”本义为殷商遗民,即“殷之大夫士从武庚叛者,以其无知,谓之‘顽民’”[7](617)。钱谦益以“顽民”自喻,寄托遥深。钱曾注释未用《尚书正义》这一更早的文献作注,而择取了“蔡洪赴洛”的故事情节,巧妙地挖掘出钱谦益的难言之隐。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君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洪曰:“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耶?”[1](637)
蔡洪以“得无诸君是其苗裔耶?”一句反驳洛中人,认为洛中人同样是身侍二朝的殷商遗民,并无资格讥讽自己。作为西晋大文学家,蔡洪以“圣人不必常处”的理念身侍二朝,但心中依旧盛赞故国④。正如钱谦益常在诗文中以伍子胥自比来暗示投身新朝之举的正当性,钱曾在注释中借蔡洪之言暗示了钱谦益为济世而降清及其对明王朝的追怀,可以视为“从往事中寻找根据,拿前人的行为和作品印证今日的复现”[19](1)。钱曾用蔡洪类比钱谦益,在某种程度上对钱谦益身侍两朝的行为进行了辩解和肯定。
需要注意的是,钱谦益常在组诗中以前贤自比。例如,他在《病榻消寒杂咏》其二十七描写了陆机和伍子胥的困顿生活,诗末一句“叹息古人曾似我,破窗风雨拥书眠”[1](661),俨然将自己类比为陆机和伍子胥。同时,钱谦益也会以贬斥描述对象的方式为自己正名。比如,《病榻消寒杂咏》其十三以“纱縠禅衣召见新,至尊自贺得贤臣”[1](646)句刻画宿敌周延儒。钱曾不厌其烦地征引史书中对汉代佞臣江充和董贤的记载,以二人因色见幸、年少僭位元僚的事迹讽喻了“美丽自喜”、二十余岁便为崇祯皇帝宠信的周延儒。钱曾注引用历史上典型的奸佞小人的传记,进一步延伸了钱谦益对周延儒的刻画,诗意表达因而更为狠辣:一方面鞭挞周延儒,加强了钱谦益诗中怨愤之情的表达,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彰显了钱谦益的正直与忠良,塑造其怀念前朝、指斥群佞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钱曾或基于钱谦益诗歌提供的线索来指引读者理解语意的方向,或在注释中就诗歌原文的只言片语进行铺陈和扩写,以历史人物的多个侧面凸显并强化钱谦益的多重身份,帮助钱谦益完成自我角色定位。
二、援古证今与钱谦益的政治时局观
对长期浸润儒家文化却失节故朝的钱谦益来说,政治时局观是其于世变之际呈现士大夫历史责任感、重新树立个人形象并影响公众舆论的重要途径。遗憾的是,史书对此并无明确记载,而钱曾注释引用的大段史实则提供了一些细微线索。[8]除此之外,钱曾对钱谦益诗歌典故的注释亦值得关注。刘勰《文心雕龙》将“事类”定义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9](614)。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着眼于钱谦益诗文对典故的运用,以诗史互证的方式推演钱谦益反清复明的心迹。钱曾之注同样援引古代典故以注解今事,解说钱谦益对朝政得失的讽喻和对光复大计的勾画, “混今合古,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10](209)。
孔子作《春秋》便提出“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点。在清朝,儒家的这一政治理念更激励了文人士子捍卫华夏中原的决心。钱谦益在《病榻消寒杂咏》其六言:
悬车束马令支捷,蔽海牢山仲父谋。聊与儿曹摊故纸,百年指掌话神州。
钱曾注先引《汉书·郊祀志》:
齐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束马悬车,上辟耳之山。”[1](640)
次引《国语》:
管子曰:“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贾侍中曰:“海,海滨也。有蔽,言可依蔽也。”韦昭曰:“牢,牛羊豕也,言虽山险,皆有牢牧也。”一曰:“牢,固也。”[1](641)
又引《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1](641)
其实,钱谦益在《一匡辨》中,便盛赞管仲辅佐齐桓公讨平夷狄之举,称述孔子所言“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可以说,钱曾之注逐步解开钱谦益诗歌这一晦涩的语言编码,为我们解读诗意提供了更多信息。在第一条注释中,钱曾对“悬车束马”的注解明示齐桓公征讨异族、一统天下的雄心,是对钱谦益反清复明心态的彰显。第二条注释来源于《国语·齐语》,齐桓公问管子南伐、西伐、北伐之事,管子主张疆土巩固之后再尊王攘夷。钱曾还称引韦昭旧注解释蔽海、牢山之义,并专门强调了防御疆土、不为四邻所侵的重要性。钱谦益早期就喜好谈兵,标榜自己治理边疆的才能,其《谢象三五十寿序》中言“海内士大夫自负才略,好谈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22](1018)。钱曾此处两条注释进一步暗示了钱谦益于晚明之际对边事的关切。崇祯朝期间钱谦益曾多次奏请朝廷加强对北方边境的防御,他曾在《向言》[22](673-678)中钩沉史事,建议加强对居庸关和紫荆关的镇守,这和钱曾注释中描写的情形十分相似。此外,在第三条注释中,钱曾虽然没有注解“令支”⑤一词,但引用《世说新语》来注释“神州”却别有意味。钱曾借“神州陆沉”回顾了东晋桓温批判王衍诸人空谈误国,从侧面印证了钱谦益曾提及的“世降”与“道衰”之关系,“世降道衰,教学偏背,烦芜之章句……充塞抗行,交相枭乱,而斯世遂有陆沉板荡之祸”[1](785)。从以上三条注释中可以看到,钱曾进一步阐发了钱谦益对齐桓公征讨异族的缅怀、对管仲谋略的激赏、对空谈误国的批判、对神州陆沉的哀痛以及对恢复中原的希冀。可以说,钱曾的注释使诗歌不只是一句慨叹往事的抒情,还可以召唤读者想象钱谦益于明末声望颇高之时,忧心国事并为之奔走的情形。钱曾的注释不仅诠释了钱谦益对政治时局的关切,也大致表明了诗歌中的“管仲”就是钱谦益的“自我声音”。
“悲中夏之沉沦”是钱谦益入清后所作诗歌的主调,从钱曾注释引用的典故中可以挖掘出这些看似单纯抒发情感的诗歌中暗含的政治意蕴,崇祯与诸臣多次商讨的南迁之事便是其中之一。《病榻消寒杂咏》其十八:“神愁玉玺归新室,天哭铜人别汉家 (一云“共和六载仍周室,章武三年亦汉家”)。迟暮自怜长塌翼,垂杨古道数昏鸦。”钱谦益在该诗的末尾自注“记癸卯岁与群公谋王室事”。异文“共和六载仍周室,章武三年亦汉家”句暗含军国之关键,钱曾作如下注解:
《史纪·周本纪》:“厉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蜀志》:“章武五年,夏四月,先祖殂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大赦改元,是岁魏黄初四年也。”陈孔璋《豫州檄》:“方畿之内,简练之臣,皆垂头塌翼,莫所凭恃。”[1](650-651)
钱谦益诗中的“仍周室”“亦汉家”有维护汉人正统之意,而钱曾注挖掘了更深层次的信息。根据钱曾所引文献可知,注释中涉及两个重要的政治事件:第一是周厉王出逃之后到周宣王即位之前的一个时期,召公保护太子,并和周公实行短暂的共和;第二是刘备去世后,刘禅继位,蜀汉暂得偏安。这两个事例都是在家国风雨飘摇之时实行的权宜之计。钱曾在注释中暗示了崇祯年间诸臣商讨的南迁之事,而《钱牧斋先生年谱》对癸卯岁的事件记载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春间李忠文公邦华北上,要先生至扬州,嘱先生:‘东南根本地,有警当与宁南侯共事。’”[11](938)钱谦益在《李忠文公神道碑》中称南迁为“经权战守、万全之策”[1](1208),钱曾用典故揭示了钱谦益的隐秘情感。然而,南迁之策没能实行,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缢。
君死国亡之痛使钱谦益晚年缠绵病榻时感慨“迟暮自怜长塌翼,垂杨古道数昏鸦”。钱曾就其中的“塌翼”两字征引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为这句抒情诗增添了一层政治意味。《豫州檄》在历数曹操罪状的同时指出汉室的现状:“方今汉室陵迟,纲维弛绝,圣朝无一介之辅,股肱无折冲之势,方畿之内,简练之臣,皆垂头塌翼,莫所凭恃。虽有忠义之佐,胁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节?”[12](1973)这也正是崇祯十六年(1643)明王朝的真实写照。时李邦华主张遣太子监国南京,崇祯帝已然心动,光时亨反驳,诸臣皆“垂头塌翼,莫所凭恃”,无怪崇祯自缢前书御书于衣襟云“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13](335)。钱曾对这一历史典故的注释是对钱谦益诗歌及其自注的延伸。钱谦益试图用自注告诉读者,他也曾在明末复杂的政局中,为复兴明王朝而出谋划策。钱曾的注释则进一步揭橥钱谦益的历史观念,即明朝灭亡的根源不仅在于“都将柱地擎天事,付于搔头拭舌人”之君王,更在于“垂头塌翼”“不争气的蠢公侯”。总之,钱曾注释根据钱谦益所提供的语意片段,通过阐释前代政治典故开掘了另外一种语境,指引读者循着历史的相似性去探寻诗歌隐含的信息。
钱谦益入清辞官后就投入到反清复明的活动之中。《病榻消寒杂咏》其二十一云:“鱼鳖星微沉后浪,鼋鼍梁阔驾中流。”钱谦益自注为“读元人《岛夷志》有感”[1](653)。东南海隅曾为抗清斗争的腹地,钱谦益在病榻上读《岛夷志》并非纯粹消寒度日,似有关心海外残明势力动向之意。钱曾征引《三氏星经》解释“鱼鳖星微”,“石申氏曰:‘鱼一星在箕南河中,鳖十四星,在斗南。’”[1](653−654)这一注释十分客观,更像是对星象知识的普及,而“斗南”实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隐秘线索。钱谦益注杜甫《秋兴八首》其二云:“‘每依南斗望京华’,皎然所谓截断众流句也……万里孤臣,翘首京国……唯此望阙寸心,与南斗共芒色耳。”[14](560)钱谦益又在《后秋兴》中写道“杂虏横戈倒载斜,依然南斗是中华”[20](2)。其中南斗即为中华,鳖十四星在南斗之南,即中华之南。“鱼鳖星微”即中华之南的鳖十四星黯淡无光,恰似南明政权偏安一隅的情形。钱曾引用李善对江淹《恨赋》的旧注来解释鼋鼍。李善旧注写周穆王起九师伐荆楚,叱鼋鼍以为梁。历史上的周穆王是史官笔下一位统御四方、威震宇内的君王。联系钱谦益晚年尝试联络东南的反清力量、配合郑成功水军进取南京的事件可知,这也正是钱谦益对海上明朝残存势力寄托的深切厚望。
要之,身涉复杂的政治历史事件,钱谦益只能借助各种事典的迷障抒发胸臆。钱曾基于钱谦益诗文,用注释说话,揭示钱诗中隐去的部分,填补其中的语意空白,以一种“隐微注释”⑥的方式在狭小的诠释空间里尽量还原钱谦益的政治时局观。通过注解钱谦益的政治时局观,钱曾刻画了一个自始至终都在勠力上国的遗民形象。
三、博采文献与钱谦益的生命情态
晚明时期,钱谦益因仕途坎坷而常在诗歌中作“穷途之哭”,入清之后,更因降清之愧辱心态而多作“新亭之泣”,这种转向自我内心的表达更为贴近真实的钱谦益,也折射出易代之际士人心态演变、精神沉浮的过程。钱曾在注释中征引了不同的文献,或“以诗注诗”,或征用传奇、词赋和佛道典籍来阐发诗意,再现了钱谦益“苦恨孤臣”的生命情态。这种注释方式与西方的互文理论有某些相通之处。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15](150)这与刘勰所谓“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9](614)相互对应。可以说,富有张力的诗歌语言本身就是不同文体相互交织融合的结果。在语言环境极其敏感的易代之际,钱谦益的“隐微写作”与钱曾的“隐微注释”共同合作,最大限度地传达隐秘的情感。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注释中征用除诗歌以外的其他文体可以和诗歌形成交叉和互补,表达出诗歌文体不能或者难以独立表达的情感。
钱谦益晚年诗歌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用亡国之痛消解降清受辱、全躯丧乱之悔。钱曾“以诗注诗”,其注释与钱谦益的诗歌客观上构成了一个文学情感整体。《病榻消寒杂咏》其六:“稚孙仍读鲁《春秋》,蠹简还从屋角收。” 钱谦益此诗借稚孙读《春秋》之事,写经学纷争和王朝兴衰。钱曾选择了吕居仁的“篱根留敝履,屋角得残书”(《兵乱后杂诗》)[1](640-641)一句作注,其内在深意颇值玩味。吕诗写靖康年间金兵攻陷汴京的过程,和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背景十分相似。诗中“晚逢戎马际,处处聚兵时……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等句所传达的亡国之恨和家国之悲都与钱谦益的心境极为贴合,揭示了钱谦益隐去的写作动机,并很好地诠释了钱诗主旨。释文使北宋末期和明朝末期形成对比,指引读者体会钱谦益遗民旧老式的亡国之悲,而非失节之痛。与此相似,《病榻消寒杂咏》其十七云:
桃叶春流亡国恨,槐花秋踏故宫烟。
于今敢下新亭泪,且为交游一惘然。
钱曾引《明皇杂录》:
天宝末,贼陷西京,禄山大会凝碧池……王维拘于菩提寺,赋诗曰:“万户伤心生碧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1](640)
钱曾所注为安禄山陷西京,王维被拘赋诗之事。王维《凝碧池》中的“秋槐”已然成为明遗民的公共话语,诸如“莫奏霓裳天宝曲,景阳宫井落秋槐” (吴梅村《永和宫词》) 、“已见秋槐陨故宫,又看春草生南陌”(吴梅村《临淮老妓行》)之类。钱谦益著有《秋槐诗集》《秋槐诗别集》,“秋槐”皆出自“秋槐叶落空宫里”句。《秋槐诗集》是钱谦益入清后颂系金陵所作,“盖‘牧斋’之遗民形象,自此奠定,为其入清后自我建构(self-constitution)不可或缺(甚或最重要)之一环”[6](298)。因此,钱曾注出已为时人所熟知的典故,除了便于后世读者理解,也在某种程度上突出王维秋槐诗对钱谦益的重要意义,且客观上获得以下艺术效果:钱谦益诗沉痛而收敛,王维诗则张扬浓烈,在一张一弛间,钱谦益隐藏和节制的情感得以宣泄;用王维被迫事敌来暗示钱谦益降清实属无奈之举。钱谦益的忧时感乱、忠心为国的情感,也因此具备更多的历史层次感。
钱谦益在为期甚短的仕途中曾两度下狱,数次被贬,故于暮年依然慨叹仕途坎坷。钱曾在注释中博采文献,更加具体入微地道出钱谦益如履薄冰的仕宦经历。《病榻消寒杂咏》其十五中“伶仃怖影依枝鸽,吸呷呼人贯柳鱼”,写为官之人宦海沉浮的心态和境遇。钱曾在注释中大段直录李复言《续幽怪录》中的情节,大意为薛伟任经州青城县主薄,生病危在旦夕,梦中变鱼,被自己的渔夫、杂役和厨子穿腮、转卖并斩杀。[1](648-649)这个故事十分形象地说明了钱谦益仕途中历经波折、备受煎熬的心理状态。钱谦益的诗歌咏叹有很强的抒情性,而钱曾注中的传奇故事表达更具叙事性、情节性。诗、注并读可用笔记小说的叙事性补充抒情诗难以表达或者囊括的内容,达成文体上的互补。此外,汪辟疆在《唐人小说·薛伟》的编后叙里说:“此事当受佛氏轮回之说影响,李复言遂演为此篇,宣扬此法。唐稗喜以佛道思想入文者,此亦一例也。”[16](225)所以说,除了诗意上的延伸和补充,钱曾此注也印证了钱谦益晚年归于佛道,参悟佛法的境况。
钱谦益组诗中多次追怀和柳如是的情感,钱曾注再现这一美好姻缘的同时,也表现了钱谦益凄清孤冷的幻灭感。比如,《病榻消寒杂咏》其三十四:
老大聊为秉烛游,青春浑似在红楼。
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生年百岁忧。
留客笙歌围酒尾,看场神鬼坐人头。
蒲团历历前尘事,好梦何曾逐水流。
钱曾注:
陆友仁《吴中记事》,“姑苏壅熙寺,每月夜向半,常有妇人往来廊庑间歌小词,闻者就之,辄不见。其词云:‘满目江山忆旧游,汀花汀草弄春柔。长亭舣住木兰舟。好梦易随流水去,芳心空逐晓云愁。行人莫上望京楼。’”
钱谦益自注曰:“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1](664-665)崇祯十三年(1640),柳如是拜访钱谦益,半年后二人结缡成就了一段风流佳话。钱曾注引小词《浣溪纱》,该词传为北宋姑苏士人慕容岩卿之妻所作。据说岩卿之妻死后,其幽魂常歌此词。钱谦益本诗追怀二十年前与柳如是文宴浃月的旧事,缘情绮靡,笔致清灵,但对两人相处的细节着墨不多,而钱曾注所引小词弥补了这一不足。借岩卿之妻所写江山旧游和赏心乐事,钱曾将钱谦益与柳如是当年神仙眷侣一般的生活约略描摹了出来,为钱谦益雅正的诗歌平添一份细致的柔情。多情词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忘却意中人,正如多年后坐在蒲团上的钱谦益本该五蕴皆空,唯与柳如是之间的旧事刻骨铭心。借助钱曾的注释,钱谦益诗中节制的情感在这里充分地释放了出来,情余言外,哀怨无穷。
钱谦益几乎亲历了鼎革之际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立场的游移,行为的改易,既是其复杂矛盾心态的反映,又加剧了其心灵的苦闷。故其诗歌反复歌咏逃禅隐居、著书立说之事,以期超脱纷扰,重获心灵的安宁。但是,参考钱曾注释,我们可以窥见这种渴望承载太多的不甘和悲怆。如《病榻消寒杂咏》其二十七:
由来造物忌安排,遮莫残年事事乖。
无药堪能除老病,有钱不合买痴呆。
钱曾注:
放翁《北斋书志》诗:“百年从落魄,万事忌安排。”(注曰:“徐仲车闻安定先生莫安排之教,所学益进。”
放翁《春晚雨中诗》:“方书无药医治老,风雨何心断送春?”[1](659)
钱谦益十分推崇陆游,因其倡导,在明末清初出现过“《渭南》《剑稿》遗稿家置一编,奉为楷式”[18]的局面。钱曾注释所引“百年从落魄,万事忌安排”句,指明了钱谦益对陆游诗歌的效法和学习。再看陆游《春晚雨中作》,除去钱曾注释引文,其下半节为:“乐事久归孤枕梦,酒痕空伴素衣尘。畏途回首涛澜恶,赖有云山著此身。”[17](3122)该诗所摹写的情境和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组诗的整体情感基调十分相似:二人同样于暮年之时叹息“无药堪能除老病”;陆游的“乐事久归孤枕梦”概括了钱谦益从“买回世上千金笑”到“顾影有谁同此夕”的自伤自怜;钱谦益“羊肠九折不堪书”的仕宦生涯也是对陆游“畏途回首涛澜恶”的隔代呼应。宇文所安认为:“正在对来自过去典籍和遗物进行反思的、后起的时代的回忆者,会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19](22)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钱曾从陆游身上发现了钱谦益的影子,通过称引陆诗将钱谦益诗中隐秘的情感铺陈开来。借助钱曾之注,我们可以看到陆、钱二人相似的身世之悲、家国之恨,以及他们渴望跳出纷扰却不得的无奈与悲怆。况且,钱谦益作为文坛宗师,却背负降清之耻,以陆游般“忠君爱国”比之,可以说是对他的一种精神救赎。
正如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解释“互文性”所说:“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23](5)钱曾引用的诗文杂说和钱谦益诗歌构成互文关系,揭示并凸显了钱诗中隐秘而又克制的情感,也使钱谦益的形象更为真实和丰满。
四、余论
钱谦益曾道其晚年诗作:“孤臣泽畔自行歌,烂熳篇章费折磨。似隐似俳还似谶,非狂非醉又非魔。”[20](70)而《病榻消寒杂咏》中的“廋辞隐语”犹如诗人的面具,使诗中悲凉复杂的故事显得十分委婉曲折。钱曾之注揣摩诗意,发皇钱谦益心曲,在前代诗文、事典之中寻找或者印证着钱谦益的身影。其中,十分值得关注的是他在《病榻消寒杂咏》中所采取的注释策略:首先,钱曾所作注释将诸多历史人物和钱谦益放置在同一语境中,以一种类比的方式,用这些历史人物的剪影拼贴出钱谦益的多重身份,使钱谦益成为一个立体的人,而非片面的“遗民”或者“贰臣”的身份标签。其次,对于涉及政治时局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诗歌,钱曾十分隐晦地援用古代典故暗喻今事,揭示更深层次的诗歌意蕴。最后,钱曾征引了诸多的诗文杂说,使所征引的文献和钱谦益诗歌构成互文关系,从而扩充了诗意容量,揭示并增强了诗人隐秘情感的表达。尤其是注释中除诗歌以外的其他文体与诗歌产生文类交叉和互补的作用,诠释出诗歌难以独立表达的情感。而且,这种注释方式推及钱曾对《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的注解,亦值得进一步探究。
清代许多诗歌注释和钱曾注释钱谦益诗歌的方式极为相似,尤其是清代前中期乾嘉考据风靡之时,即多历史事件、典故、地理、语词等客观考据,少主观鉴赏和点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清代诗歌注释之学缺乏深入挖掘的文学价值,正如钱曾一样,他剪裁前代历史文献,并以其独特的注释技巧开掘诗歌中蕴含的文学意味。当然,诗歌因其表达内容的不同,常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钱谦益自己也说过,诗歌注解如“过客径须迷出入,居人不自解东西”,“今人注杜,辄云某句出某书,便是印版死水,不堪把玩矣”[1](1359−1360)。钱谦益诗歌的遣词用字并非都有一定的来源,因此本文所谈论的问题只是提供一种可能,在抛开对钱谦益功过是非评判的基础上探寻其诗歌背后的隐秘世界,为我们进行清人注清诗,乃至清代诗歌注释之学的研究提供一点借鉴。
注释:
①关于这一点,严志雄先生在《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论释》一书中有十分精彩的论述。严先生认为:“我们赖以论述牧斋的,主要是他的诗文,而牧斋构筑的,本质上是一个隐喻性的文字、意义体系,从中浮现的是其文本身份(textual identity),充满筑构性(constructedness)。”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2年,第 16页)。严先生的相关研究为本文的撰写提供诸多借鉴和启发,在此深表感谢。
②清人竺樵在钞本《初学集诗注》序后题记中说,“东涧翁《初学》、《有学》二集诗注,从祖一老先生谓余:‘此直是东涧自注者,而托名为遵王。故其于典故时局,曲折详尽,所以发明其诗之微意也。’” 此题记见于周法高《钱牧斋诗文集考》,周法高《钱牧斋吴梅村研究论文集》,台北:台北编译馆,1995年,第12页。
③该组诗歌描写内容跨越时间长,且涉及钱谦益一生中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孙之梅在《〈病榻消寒杂咏〉与〈投笔集〉——兼论钱谦益七律诗在题材上的开拓》(《求是学刊》,1993年第6期)一文中将之归为一部充满感伤主义的梦幻式的个人小传。
④《世说新语·言语篇》中的另一段文字可作参考,洛中人又问蔡洪:“吴旧姓何如?”蔡洪回答说:“吴府君圣王之老成,明时之俊人……张义让为帏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参见(南朝)刘义庆著,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61页。
⑤有一种可能是该条目在传抄印刷中缺漏,另外一种可能是钱曾避而不注,因为“令支”位于东北辽地,最后为齐桓公所统一,亦是后来满族人崛起的地方,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
⑥郑雅尹在《钱谦益〈西湖杂感〉诗中的废墟与记忆》(《中极学刊》第七辑,2008年6月版)一文中借用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写作与迫害的技艺》中“隐微写作”一词。利奥认为“隐微写作”产生于某种历史处境,尤其是在失去公共谈论自由的极权政治下,会迫使所有持有异见的作者都产生一种特殊的写作技巧,即“隐微写作”,也促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按:如果说钱谦益的写作有“隐微写作”的成分,那么,笔者认为钱曾也会有“隐微注释”的可能。在涉及清朝的重要政治事件上,钱曾注释并非直接揭发钱谦益诗旨,而是同样用一种暗示或者指引的方式启发读者群体,从而协助钱谦益表达诗意,并规约着读者对诗人、诗作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