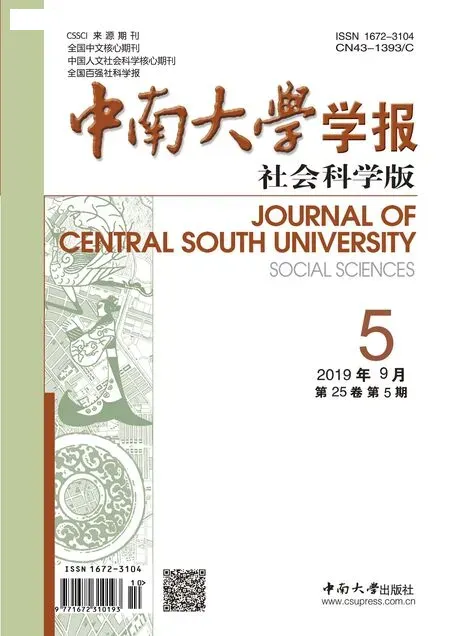多模态:文学意义研究的新维度
2019-01-04张昊臣
张昊臣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近年来,文学与其他艺术、媒介之间的跨界互动成为一个重要现象[1](209-216)。由此引发的“文学与图像”“文学与声音”“文学与表演”“文学与媒介”等诸多话题,受到广泛关注和热议。在相关讨论中,肇始于20世纪晚期的多模态研究颇具代表性。“模态(mode/modality)”一词有两层基本涵义。一是强调符号接受者的“感觉(sense)”甚至“多感觉(senses)”,进而区别于脱感觉的抽象“概念(conception)”。福赛维尔(Charles Forceville)指出,“模态”本质上是一种“感知过程”,包括视、听、嗅、味、触等感官经验,不同模态在感知活动中常常相互作用[2](22-23)。二是强调符号本身的物质性。克莱斯(Gunther Kress)认为:“模态是指由社会所形塑、由文化所给定且能够产生意义的一切符号资源。图像、书写、设计、音乐、姿势、演讲、动态影像、音带、3D(3D objects)物等,都是在表征和传播领域中经常出现的模态示例。”[3](79)正如一些文学多模态研究者所见,“多模态(multimodal/ multimodality)”这一术语在字面上易形成某种暗示,即似乎还存在所谓的“单模态(monomodality)”。然而事实上,“多模态”或“单模态”首先不是对符号的分类,而是审视符号意义生成的两种不同视野。不同于传统语言学视野,多模态视野旨在强调:第一,“所有传播活动都是多模态的,即使写下来的语言文字也同样如此”[4](116);第二,语言的运用经常“与其他多种符号相互关联”,“各种符号是一个联合与整体,而非单一模态的孤立运作”[5](8)。
由多模态视野重审文学,可以看到:语言文字兼形、声、义三维,又经常与歌咏吟诵、乐舞图演、书写物材、媒介技术等互相交织,多模态经验深度参与到文学意义生成之中。由此重审文学实践,诸多看似不同的文学现象之间也就勾连出一条彼此贯通的线索。比如:中西文学传统中对声、韵、腔、调、节奏、停延、语音象征等听觉向度的运用,在联边、离合、拆形、嵌字、回文、神智体、图形诗等视觉向度的探索;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实验中涌现出的残词、混成词、文字游戏、发音改拼、图文互渗、文体混杂、异形印刷、跨行留白、打孔、活页、拼贴、声光诗、声音诗、杂语诗、诗歌装置、纸牌小说、剪空小说、拼贴小说;当下数字技术催生的超文本文学、动画诗、移动定位叙事、VR叙事、交互式小说;甚至包括不具有或不止于固定文本形态的口头文学、表演文学,以及通过视听媒介对书面文学的再表演化……面对这一广泛存在且不断扩容的文学现象,文学理论特别是文学意义理论层面的回应就日渐显得必要。
“语言转向”以来,“意义”始终是语言(哲)学关注的焦点。20世纪文学理论之所以具有异于古典诗学、鉴赏批评、史证研究的所谓“理论”指向,不仅因为它借鉴了“语言转向”带来的一系列概念、框架、方法,更因为它和“语言转向”共享了“意义”这一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仍具主体间约束力的规范结构。可以说,“意义研究”既是语言(哲)学研究向文学研究转捩的关节,也是文学理论自我生成和发展的基点。通过对语言学范式的运用和转化,结构主义、现象学、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文论,对文学的“能指”“所指”“形式”“结构”“作品”“层次”等诸多面向展开了丰富讨论。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多模态维度虽然也受到关注(这一点在听觉模态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却始终难以推进到文学意义层面。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初步探讨一个基本问题:多模态在文学意义构成中具有何种重要作用?这对于我们审视文学当下的发展具有何种启示?
一、文学意义理论的语言学范式
在受“语言转向”深刻影响的文学理论著作中,韦勒克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无疑是一部代表之作。在韦氏的思想脉络中,文学作品的“本体论地位”既是“内部研究”的基础,也是作为“系统知识”的“文学理论”得以展开的基础。为了寻获这一牢固的“本体”,韦勒克采取了一种从“外”向“内”逐层排除“谬误”的论证思路。第一重“谬误”是将文学视为“人工制品(artefact)”,即认为文学“同雕刻、绘画一样具有物质性的客体”。韦勒克列举了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中大量存在的视觉探索,并且强调,即使在并非有意凸显视觉维度的一般文学作品中,书写和印刷在诗行、诗节、分段、眼韵、双关、拼写等方面仍发挥重要作用,是“文学作品不可分割的要素”;他甚至认为,“中国诗歌中如画的表意文字构成诗的整体意义中的一部分。”然而,虽然如此,他仍坚持将视觉维度排除在文学作品构成之外。对于文学听觉维度,韦氏的立场相对缓和,他注意到“在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抒情诗)中,声音是构成作品总体结构的重要因素”,押韵、拟声、声音描绘(sound-painting)、声音象征①与声音引发的联觉经验、节奏、格律等都在文学意义构成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韦勒克强调:他所关注的“声音”是抽象的“声音图式(sound pattern)”,而非具体的“声音施演(sound performance)”。所谓“施演(performance)”,既包括创作者、再创作者对作品展开的“表演活动(performance)”,如表演文学,也包括读者、接受者对作品展开的“施行活动(performance)”,如读者在吟诵中对诗意的体验品味过程。在韦氏看来,从“施演”角度来理解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声音,正是他要排除的第二重“谬误”。他所关注的“声音图式”不仅去除了基于身体经验的声读甚至默读,也忽略了施演活动所衍生出的腔调、音质、音高、快慢、轻重等个性化听觉效果。在排除前述两重“谬误”之后,韦勒克又进一步排除了“接受谬误”(从读者体验来理解作品)和“意图谬误”(从作者经历来理解作品),最终才找到展开文学意义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理论研究的立足点:文学作品是一种独立于任何物理经验和心理体验的“观念对象(an ideal object)”[6](142-173)。
作为20世纪一位十分重要的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向来以视野开阔、思维缜密为人称道;但在处理文学多模态这一问题上,其论述不能说没有问题:如果视觉在文学审美中确实发挥重要作用,又为何仅将其视作“外在的”要素?如果离开身体与施演来讨论文学声音,抽象的“声音图式”又能否被真正“听”到?如果忽略作者和读者置身其中的在世处境与效果历史,一个纯粹精神性的“作品”本身对我们而言又意味着什么?韦氏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可能出现的理论困境,他甚至试图对“经验对象(an object of experience)”与“观念对象(an ideal object)”两种立场进行调和。但总的来说,在韦勒克及其他深受语言学范式影响的文学理论家那里,观念论始终是文学意义研究的主导取向。所谓“观念(idea)”,是对象独立于经验流变而持存的普遍“共相”,进而在主体表象活动中成为对象自身同一性的逻辑基础。从认识论和语言学来看,“观念”经常表现为通过“种加属差”所严格划分、确定的“概念”,比如:作为“属”概念的“桌子”超越了经验中千差万别的具体桌子,进而确保日常经验和科学认识的顺利展开;作为“种”概念的“这张桌子”超越了观看它的不同时空视域,进而确保对象是其所是的自身同一性。应该说,没有“观念”对同一性的先行担保,日常交往和科学认知都无法顺利展开。这一点对于文学意义研究而言同样成立:“作者意图”“作品结构”“理想读者”“阐释社群”——这些概念虽各有偏重,却都是为确保文学意义同一性所提供的理论前提。
然而,正如梅洛-庞蒂所指出的,观念论的主要困难在于:它将语言感觉经验和语言意义之间的关系视为彼此外在的,由此出发,语言的物质可感性也就沦为意义的“外壳和外衣”[7](235-239)。如果对西方哲学传统特别是近代意识哲学传统稍作回顾,可以看出:观念论几乎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在黑格尔那里,“(诗的)语音作为感性材料对它所传达的观念思想之类的精神内容并无必然的联系”,心灵“把语言因素只当作工具”;甚至诗的接受方式是听或是读、“由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由韵文改写成散文”、由一种音调变为另一种音调,其价值都“不会受到严重的损害”[8](7-10)。在赫尔德那里,人类原初的“自然的语言”不仅能“自行显示”情感,还能“唤起图像”,这成为“演说家和诗人的魔力所在”;但是,“自然的语言”仍停留在“前语言”的原始状态,真正理性化的“人为的语言”则是“一个明确的意识行为的标记”,“词的外部音响在此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9](4-5,11-12,35)。在索绪尔那里,能指不是声音,而是对声音形式化抽象后的“区别性特征”,它本身的听觉可感性让位于对所指(意义)的快速辨识;“能指”和“所指”作为一种“居于主体之内”的“内心语言”,即使无需发声也能在精神内部完成“说”与“听”[10](85)。在胡塞尔那里,手势、表情、记号甚至一般表述的感知层(如语言声音和文字书写),与含义之间仅具有偶然联系;只有通过意识活动所展开的赋义行为,感知层才能转化为具有含义的“符号”。可以说,在观念论这一点上,“语言转向”中的许多思想流派与意识哲学传统之间仍有深刻联系,即将观念意义与身体感官相互对立,为了保证前者而将后者清除或对后者进行“形式化”处理。在批评这种思维方式在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时,伊格尔顿形象地指出: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通过“观念”及其变式(“形式”“结构”)来把握文学意义,被精神之光彻照的文学语言“道成肉身”,“它的物性存在仅仅是意义的透明表达”——“在作品的物质之身中,没有哪个部分是不能被观念所充分消化的,没有哪种特征是不能被意义模式所统一吸纳的”[11](208-209)。由此切入文学语言,感觉与意义势必互相割裂开来,多模态也就难以真正进入文学意义层面。
二、具身、多模态与意义构成
多模态研究者克莱斯指出:符号“总是具身的(embodied)”,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模态所具有的用以产生符号的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s)才能成为具形的(embodied)。没有任何一种符号能够仅仅保持在一种纯粹‘心智的(mental)’、‘概念的(conceptual)’或‘理智的(cognitive)’状态”[3](76-77)。这一论述所凸显的“具身/具形(embodiment)”思想,在当下西方多模态研究中很有代表性,对我们突破语言学范式的单一视野亦有启发。
具身思想萌芽于胡塞尔。在他看来,感知总是从“我的”第一人称视域以侧显的方式向我以展示,进而受“我的身体”的时空位置的限定;在他后期的思想中,动感(kinästhese)及其所关联的身体经验在意义构成中的作用被进一步强调。梅洛-庞蒂发展了胡塞尔的具身思想,特别是胡塞尔晚期关于身体二重性的讨论。胡塞尔曾注意到:在以右手触摸左手的感知经验 中 ,同一身体的双重感觉(施动感和物感)之间呈现一种可逆性,这揭示出正在触摸的现象身体与被触摸的实在身体之间的原初交织。由此出发,梅氏认为:穷究的先验还原最终触及还原得以展开的前反思基础——现象身体与实在身体之间、自我与世界(包括在世界中的他人与它物)之间的含混性,这一具身在世之维成为描述意义构成活动的真正前提[7](6-10)。从具身思想来看,“意义”不是一种纯粹观念性的“逻辑含义”,而是整个“生命活动”开展的“原生的意义(sens autochtone)”②[12](232),它接近于海德格尔的“含义的关联整体”或“意蕴(bedeutsamkeit)”[13](102)。就此而言,身体、动作、言语、语言之间,感觉与观念之间,也具有一种从“本义”到“转义”的含混关系。在思辨现象学传统之外,另外一些学者则尝试以更为平易的方式对语言意义的具身性加以探讨。塞尔(John Searle)的“中文屋”思想实验试图表明:“符号通过具身性被接地(be grounded)——获得它们的意义”,这是语言意义理解的必要条件;如果越过这一条件而将对语言意义的理解等同于对语言规则的单纯运用,将会归谬出有悖于日常经验的结论③。巴萨罗(Lawrence W.Barsalou)则通过神经认知研究表明:对语言概念的学习和理解是一个伴随具身经验的“概念化过程(conceptual processing)”,多模态感觉经验不仅沉淀在概念之中,而且随着概念的再度运用也不同程度地被激活[14](84-91)。
从一般语言意义推进到文学语言意义,克莱斯所谓的“具身/具形”特征会更为凸显。“具身”着眼于读者的接受过程,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从多模态角度看,文学接受不仅是“阅读(reading)”,还包括“使用(using)”“参与(engaging)”“施演(performing)”“跨模态建构(transmodal construction)”等面向[15](421)。“具形”则着眼于语言文字的媒介物质性,按伊格尔顿的说法,“‘诗性’的关键内涵之一在于意义与物质性的共生;就此来说,正是凭自己的内部运作,诗的物质性身体(material body)才能不断超越自身以向世界敞开。这一点适于所有语言,但诗表现得最为突出”[11](205)。这里,我们不妨以口头、印刷、数字化三种不同媒介的作品个案来做进一步分析。
口头媒介。安尼·瓦尔德曼(Anne Waldman)是美国当代著名表演诗人,她的许多作品不仅以诗集形式出版,还以现场表演形式展示,并发布在电台、电视、网络上。比如,2015年4月,纽约WNYC广播电台为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组织一场公益活动,瓦尔德曼现场表演了诗歌《饿鬼》(Hungry Ghost)。在气候大会背景下,“饿鬼”所暗示的主题不言自明。然而,《饿鬼》的“诗意”不能被还原为这一“主题”,也不止于单纯语义层面的象征或隐喻,而首先展现为极具穿透力和陌生感的听觉效果,比如:“To never have enough be enough get enough/To never have enough be enough get enough/Enough enough enough”,大量快速叠加的“enough”不仅扰乱了常规句法,还凸显出该词两种不同含义之间的张力(“To never have enough be enough get enough”中的“enough”表示“满足”,而“Enough enough enough”中的“enough”则带有“受够了”的怨怒意味);在“Ravaging and ravaging ravaged and will have ravaged and will ravage and will ravage and will have been ravaged”中,“ravage”一词的不同时态和语态无规律地重复,生成为致密黏稠的声音团块;在读到“where the enemy turn it around and the tear of insatiable hunger for oil,oil,oil”时,每个“oil”的发声都介于读与唱之间,叠连的喉音持续拖长和锐化,如同受火刑炙烤时发出的尖叫;在“What he wants,what she wants,what they want/What the‘I’thinks since at once hieroglyph of the hungry ghost”中,人称代词“he”“she”“they”“I”等都被重读而富有击打感,显示出“饿鬼”的无处不在;瓦尔德曼还经常发出感叹、咒语、吟唱之类无明确意义的语音,比如“Sexy ghost,a performer,a demon,a gadfly,a fun huh”,结尾的感叹词“huh”,吐气由宽而窄最后碎化为蛇信般的嗞嗞声,为前面“fun”的词义增添了奇异感……瓦尔德曼的表演诗代表着一个十分庞大的文学谱系——从传统的口头文学、表演文学,到超现实派、达达派、投射派、垮掉派、语言派等前卫诗歌表演,再到黑人说唱、鲍勃·迪伦所代表的流行文化,文学意义正是通过表演中的声音、神态、动作、场景等多模态经验才得以实现。
印刷媒介。美国当代小说家乔纳森·S.弗尔(Jonathan S.Foer)创作了不少多模态小说,其中以2005年出版的《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 Loud & Incredibly Close)最为著名。小说主线是托马斯在“9.11”事件中不幸丧生给家人特别是九岁儿子奥斯卡造成的伤痛;然而,弗尔的叙事并未止于“9.11”事件本身,而是由此深入到父子关系、家庭伦理等更为细微的日常层面。比如,托马斯生前有看报圈批的习惯,在他离世后,奥斯卡正是通过整理托马斯遗物中的各种圈批痕迹来进一步了解父亲。奥斯卡在遗物中发现了祖父西尼尔“写给自己未出生的孩子”的两封信,上面布满托马斯的圈批:除语法、拼写错误的文字外,还包括诸如“I love you”“my child”“you”“your father”等词句。通过被圈批的信件,有两位叙述者同时说话:一位是西尼尔,他向“未出生的孩子”讲述自己二战时的经历,表达自己对孩子的悲悼;另一位却是托马斯。然而,托马斯近乎沉默的痕迹在说些什么呢?从小说中我们得知,西尼尔其实有两个“未出生的孩子”:他年轻时热恋的情人安娜所怀的孩子,但已有身孕的安娜却不幸死于德累斯顿大轰炸;另一个则是他的妻子生下的托马斯,因为西尼尔在妻子怀孕后就抛弃了她,因此,在托马斯心中,自己之于这位从未相见的生父也等同于“未出生”。在由西尼尔和“第一个未出生的孩子”所搭建的“叙述者-受述者”结构中,托马斯的圈批不断质疑叙述者所构建的“父亲”身份、扰乱叙述语词所携带的稳定意义,进而使创伤经验在语义与视觉的张力甚至悖反关系中被呈现。除此之外,《特别响,非常近》还运用了图片、颜色、标点、字体、空白、语体、印刷变形、报纸剪贴等样式,来传达常规话语难于言述的创伤经验。在现代主义诗歌和后现代主义小说中,这些样式被大量运用,且常常和语义之间呈现出反讽甚至矛盾的复杂关系。
数字媒介。在早期数字文学中,雪莉·杰克森(Shelley Jackson)以Storyspace软件创作的超文本小说《拼缀女孩》(Patchwork Girl)堪称经典。它与另一部19世纪的经典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形成一定程度的“戏仿”关系:后者讲述了启蒙时代医学世家子弟弗兰肯斯坦如何用不同死者的尸块拼缀出一位活人怪物的故事;而杰克森则尝试以图片、网页和超链接对这一“拼缀”经验重新加以呈现。进入《拼缀女孩》,读者首先面对五个主链接:“墓园”“日记”“编织”“故事”“破碎之音”。点进“墓园”,屏幕上出现一段墓志铭:“我被埋葬于此。你能将我复活,但只能零碎地复活。如果你想看到我的整体,就得亲自将我缝合。这里是头,躯干,右臂,左臂,还有右腿,左腿,也有各式各样经过适当排列好的器官。上帝保佑它们安息。”每一个身体部位又是一个次链接,进入后则是这些身体片段所有者生前的经历。而点进“破碎之音”,映入眼帘的则是一张分成若干部分的人头颅骨图片,每个部分又是一个次链接,保存着不同身体片段所有者的生前记忆。在其他三个主链接中,也同样有各种分叉的次链接:人物的回忆、幻想,来自文学作品、哲学作品甚至时装杂志的引言,拼缀女孩的自述,由这一自述衍生的情节和评论……显然,在由主链接、次链接、分叉链接层层相织的阅读之网中,在由女孩、尸块、引用书目、衍生评论杂合共生的叙述混音中,读者无法获得一个统一稳定的意义框架。阅读中所感受到的迷失、破碎、混乱、残断等具身经验,恰恰将我们自己作为数字化主体的“拼缀性”凸显出来。从数字文学文库“Electronic Literature Collection”收集的235部代表作品来看,当下数字文学的多模态呈现早已超出《拼缀女孩》所代表的第一代数字文学,除超链接和多媒体外,动画、游戏、数据自动生成、数据可视化、移动互联、3D、VR、AR等新技术样式都得到运用。
上述分析表明:如果忽视甚至排除多模态维度,感觉经验在文学意义构成中的重要作用、不同模态之间及它们和语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就难以得到深入探讨。其实,无论是我国关于“形文”与“声文”(刘勰)、“形美”“音美”“意美”(鲁迅)、“音节”与“绘藻”(闻一多)、“音律的绘画的文字”(宗白华)之诸多阐发,还是西方从“姿势”(孔狄亚克、维科)、“音乐”(卢梭、尼采)、“视觉和弦”(休姆)、“招贴画性质”(马雅可夫斯基),甚至“声响”“重量”“气味”(马里内蒂)、“团块”(阿尔托)、“球形物”(布朗肖)、“书脸”(利奥塔)、“宏大的视觉与卓越的听觉”(德勒兹)等维度对文学语言展开的各种解读,都从不同侧面触及文学多模态面向。然而,要整合这些零散评论并形成一种理解文学意义构成的基本视野,还需进一步廓清感觉意义与概念意义之间的关系。
三、感觉意义、概念意义与关联意蕴
感觉意义与概念意义的区分来自梅洛-庞蒂。当符号和语言的感觉经验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不能相互分离时,它所表达的就是一种感觉意义,梅氏在不同语境中称之为“动作意义”或“情绪意义”。显然,在他看来,动作是最能体现感觉意义的一种“样板”:动作所显示的情绪并不藏在它的“里面”或“后面”,“我在动作中看出愤怒,动作并没有使我想到愤怒,动作就是愤怒本身”“动作和动作的意义有共同的东西”[7](240-243)。关键在于:作为一种表达活动,动作所谓的“什么(what)”总是通过它的“怎样(how)”显示出来,二者不能分离;无论人们对动作的施为意图或施为效果做出何种区分(如生活中的愤怒神态或舞台上对愤怒的表演),动作都是一种通过展示其“方式/模态(mode)”来实现其“意义(sense)”的表达活动。梅氏还曾将音乐和绘画这两种表达活动与动作进行类比,并指出“在一副绘画或一段乐曲中,观念只能通过颜色和声音的展现来传递”[7](199)。
与此相反,如果表达方式的可感特征仅成为“意义的载体”,并最终“在意义面前消失”,我们所获得的就是一种概念意义,一种“能用散文来表达”或“抽象地表达”的意义[7](199-200)。与感觉意义相对,在概念意义中,表达活动的“什么(what)”与“怎样(how)”可以相互分离,并成为能够“没有歧义地指示事件、事物状态、观念或关系”的“表达的纯粹情形”或“精致的含义系统”[16](1,16)。比如:像“树是木本植物的总名”这类科学表达或“山上有很多树”这类日常表达,它们或精于定义或便于交流,表达活动的“怎样”并不凸显;反之,像西西短篇小说《依沙布斯的树林》中的句子,“当你到达山城,你会看见数数不不尽尽的的树树,各各式式各各样样的的树树,密密麻麻的的树树,高高矮矮肥肥瘦瘦的的树树。榆树。枫树。楠树。榛树。栎树。樟树。榉树。栗树”。此处密树映眼的意续正是凭借表达活动的“怎样”(木旁的联边与文字的叠复)显示出来,表达活动“蕴藉”着某种概念意义,却无法“还原”为这种概念意义。再如:拜伦《哀希腊》中的一句诗“the hero's harp,the lover's lute”,英文原句的可感特征体现为前后句对称音步、“h”头韵和“l”头韵;胡适译为“英雄瑟与美人琴”,可感特征转变为汉字“瑟”“琴”的联边;黄杲昕译为“豪杰的号角,情人的琴弦”,可感特征转变为前后句对称节拍、“hao”韵和“qin(g)”韵。我们当然可以“认定”这三个诗句具有相同的概念意义(它们是同一首诗中的同一句话,且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但在具身阅读经验中,它们却以不尽相同的方式“蕴藉”着这一概念意义,进而也显示出不尽相同的“怎样”。
对梅洛-庞蒂而言,一方面,在文学语言意义构成中的感觉意义无法脱离概念意义,概念意义与由其组建的理解背景,为作者与读者之间、不同读者之间、甚至不同语言共同体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含义的公共平面”。有赖于此,不同视域展开的体验才有相互协调的可能,不同处境做出的阐释才有彼此争执的动力。另一方面,感觉意义对概念意义进行了一种“秘密的扭曲”,“使意义作为一种新的感官置于作家或读者中,并向我们的体验开辟一个新的场或一个新的领域”[16](12-13)。梅氏的这一说法意在表明:在感觉(sens)与意义(sens)、物与词互相关联组建的意蕴整体中,文学语言所提供的新表达不仅是一个孤立事件,也是对这一意蕴整体及受其影响的观看方式、聆听方式乃至意味领会方式的重构。经此重构,不同语词之间生长出新的组织脉络,不同人情物事之间伸展出新的联系。对此,不妨来看两个例证。
先看穆木天的《苍白的钟声》。全诗有两大主韵:“钟声”“朦胧”“玲珑”“蒙蒙”“谷中”“暝暝”“古钟”“千重”“万重”“千声”“万声”“月影”“荒径”等为“ng”韵,它将山谷、钟声、衰草、天光、北风等意象聚集在一起,并在如古钟闷响的闭塞浑浊鼻音中共振;“飘散”“消散”“逍遥”“萧萧”“飘飘”“渺渺”等为“a(a、ai、an、ao)”韵,它将水波、树梢、风声、月影、白云等意象聚集在一起,在如钟声扩散的开口散气元音中共鸣。全诗一至六节,“ng”韵字数分别为22、6、21、10、13、27,一、三、六节相对密集;“a”韵字数分别为9、25、7、18、17、12,二、四、五节相对密集。经由两韵的开阖与意象的聚拢,寻常的故园意续也被重新点染着色。正如列维纳斯在谈及文学声音时所言:通过韵律和节奏,词语凭借自身包含的“声音的物质内容”展示出一种“感觉和音乐性”;词语“脱离了其客观意义,以又一种不同的方式回归了可感的要素形态:它归附于纷繁众多的词义,并从和另外一些词的近义关系中获得了一种暧昧性”[17](57-58)。
再来看陈黎的《战争交响曲》。全诗仅由“兵”“乒”“乓”“丘”四字密集排布,前16列为“兵”字密排,自17列始“兵”字中渐杂“乒”字和“乓”字且字数渐少、空隙渐疏,第33列后则皆为“丘”字密排。凭借四个字点画的递减,诗人试图展示从两军对阵(“兵”)到肢体伤残(“乒”“乓”)再到坟茔满野万骨枯(“丘”)的悲剧历程。其实,从字词本有的语义看:“丘”字像山中穴坑之形,“兵”字会两手举斧之意,“乒”“乓”则是后起的拟声词,它们之间本无意义关联;但陈黎借用汉字思维见形取象、谐声取义的特点,使“乒”“乓”转生出“伤残之兵”的“形意”和“刀兵相接”的“声意”,使“丘”转生出“坟中之兵”的“形意”。除印刷版外,该诗还曾以多媒体动画效果和诗人吟诵的方式呈现:在读到诗尾“丘”字时,陈黎将“qiu”的发声拖长,吐气渐宽渐缓渐渺茫,声音渐远渐苍凉,宛若秋风瑟瑟之气、大荒寂寂之音——通过吟诵,“丘”又转生出新的“声意”。
这里,文学多模态呈现的意义质态无疑是一种形、声、义与概念、感觉、意续所构织的意蕴整体,是不同具身在世主体与具形在世文本相互照面时开启的“姿态关联(einstellungsbezug)”和“发生事件 (er-eignis)”[18](13,68)。因此,它的可感性和蕴藉性与由“认识关系”(而非“实行关系”)决定的“表象性”意义指向也就存在根本的不同[17](19)。
四、余论
20世纪初,几乎就在“语言转向”发生的同时,文学实践领域也出现了一股堪称“转向”的潮流:诗歌领域的象征派、立体派、未来派、超现实派、达达派、意象派,小说领域的乔伊斯、贝克特,都开始尝试对文学语言视听模态的深度开掘;二战以后,具象诗运动、垮掉派、投射派、语言派等不仅承续了现代主义实验指向,还进一步推动了诗歌与表演、装置等艺术样式的结合;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书写印刷上的探索又使得后现代小说中涌现出一个数量庞大、样式繁复的群类——“多模态印刷小说(multimodal print novels)”[5](1);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大量数字文学作品利用新媒介、新技术进一步继承和拓展着早期现代主义的先锋探索,它们因此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数字现代主义(digital modernism)”④。就中国文学来看,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受西方“总体文学”思想影响,留学日本的中国台湾诗人詹冰就创作了大量图形诗,试图打破文学、绘画和音乐的界限;此后,白荻、洛夫、纪弦、陈黎、叶维廉、萧萧、商禽、苏绍连、管管、王润华、刘以鬯、西西、海子、顾城、朱楹春、曹志涟、李顺兴等诗人和作家,尝试将汉字汉语视听特质与印刷媒介、数字媒介的表意空间相结合,创作了不少兼具中国味与现代感的多模态作品。应该说,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数字现代主义的发展中,在先锋实验文学拓展语言极限、突破媒介边界、开启新感性的历次尝试中,多模态探索始终是其中的重要动力。今天,重新来看这场持续一个多世纪之久还依旧生机勃勃的文学潮流,我们或许可以说,新媒介、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不仅没有导致文学的“终结”,反而激活了文学本有的多模态潜质,改变着文学的视听表现样式,推动着文学与其他艺术的跨界互动。而对于文学发展形势和方向的不同判断,实际上也隐含着看待文学的不同理论视野。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意义论分野的背后可能隐含着更为深层次的思想分野。一些学者注意到,在观念论传统中,纯粹主体和纯粹语言之间相互支撑,它们共同提供了一种关于意义理解的诺斯替式理想——意义的直接在场可以不通过世界,或在经过世界之后离弃世界;这也就意味着“可感身体的消失”和“外在性的消失”[20](98)。按照这一“理想”,西方表象化思想传统中的“人类学”和“语言学”也就常常呈现出一种相互投射甚至相互生成的关系。“人类学”表象化地理解“人”,就必然要通过“人”与“非人”的区分、“人”之群类的区分甚至“人”性内在的区分,来最终确定“人”之所“是”。同样,“语言学”表象化地理解“语言”,也就必然要通过“声音”与“书写”的区分、“分节音”与“噪音”的区分、“意义”与“无意义”的区分,来最终确定“语言”之所“是”。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人类学对“人之本质”所展开的表象(“身体—心灵—精神的统一体”)不断投射给语言,语言也就相应地区分为不同部分。“把语音形象和字形看作文字躯体,把音调和节奏看作语言的灵魂,把合含义的东西看作语言的精神。”[21](392)“纯粹的人”不断提纯着“纯粹的语言”,“纯粹的语言”通过“声音/书写”“分节音/噪音”“意义/无意义”等区分机制,又不断生产着“纯粹的人”和“非人”。这一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发生伊始就表现得很明显。比如,在洪堡特将西方观念化的分节音确认为理想语言的过程中,“动物”“儿童”“自然”“汉字与汉语”“印第安文与印第安语”都被不断地划拨到区分线的另一端。随着在现代性进程中理性语言向科学语言甚至技术语言的一步步窄化,由“语言学”理想所反馈的“人类学”理想也就引发了“现代性反思”中关于“太人性”(尼采)、“人道主义危机”(海德格尔)、“人的厄运”(梅洛-庞蒂)、“非人”(利奥塔)等警示。从这一背景回看先锋实验文学多模态探索,那些在传统语言之所“是”内部展开的种种突破,不仅为我们提供了重新理解语言的可能,也为我们提供了通过语言来重新言说、重新聆听甚至重新领会我们自身之所“是”的可能。
注释:
① 韦勒克区分了“拟声”与“声音描绘”,比如丁尼生的一句诗“the murmuring of inumberable bees(无数蜜蜂嗡嗡嗡)”:其中“murmuring”是拟声词,以其发音直接模仿蜜蜂叫声;“inumberable”却并非拟声词,而是通过其中字母“m”与前面“murmuring”的呼应和两个字母“b”与后面“bees”的呼应,“描绘”出群蜂嗡鸣的可感效果。“声音象征”是指:发音时的口型、舌位、气流阻塞、徐疾锐缓等听觉和动觉特征与人情物态之间的关联。比如:前元音“i”“e”因开口小声音短,常常表现迅捷的事态或明快的情绪。
② 法文“sens”一词兼有“感觉”“方向”“含义”等意思。梅洛-庞蒂多次强调:“图形-背景”结构是感觉经验的最小单位,而何谓“背景”何谓“图形”,则取决于具身主体的“方向”。就此而言,“感觉”和“方向”本身已经孕育了一种原初的“分节(articulation)”,它和语言的“分节”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这一看法也可视为对“sens”三种意思之间互含关系的阐明。
③ 塞尔假设:只懂英文、不懂中文的“塞尔”被封闭在一间屋中,屋外人看不到屋内,只能将写有中文提问的纸片通过狭槽送进屋内;屋内有用英文写的规则手册,指导“塞尔”如何为陌生的中文字符配对,再通过狭槽送往屋外。如此往返,屋外人每次送进的中文提问都能得到“正确”的中文回答,这使他相信屋内人与自己一样理解中文;而事实上,作为规则手册执行者的“塞尔”对中文的日常理解和丰富意味仍旧一无所知。借助“中文屋”假设对语言具身性展开的相关讨论,可参见,夏皮罗的《具身认知》,李恒威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页。
④ 比如,普雷斯曼在《数字现代主义:新媒介新眼界》一书中,选择了不少创作于2000年之后的数字文学作品,并试图揭示出它们与马里内蒂、乔伊斯、庞德等20世纪早期先锋文学代表之间的深刻联系。See,Jessica Pressman,Digital Modernism: Making It New in New Media,Oxford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