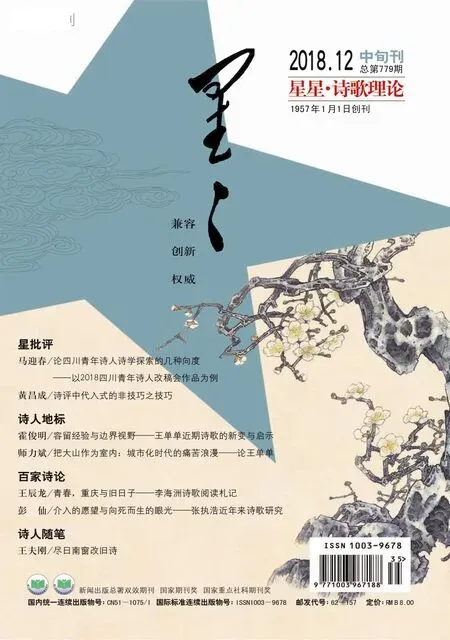介入的愿望与向死而生的眼光
——张执浩近年来诗歌研究
2018-12-30彭仙
彭 仙
一、诗与生活:打成一片
张执浩“对生活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梦想‘在远方’到‘继续下潜’进入生活内部的转变”[1]。与此相应他的写作与生活间的关系也经历了矛盾冲突、直面和解并最终深入内在的阶段性过程。诗人最终选择了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找寻诗意,同时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对生活,对美的理解和认识。随着诗人生命体验与生活态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创作观念上的转变,其笔下的诗歌情境也由最初的浮于生活之上的童话世界逐渐下潜到现世生活内部,并逐步意识到好的诗人应当与生活打成一片,而不是脱离生活。诗人终于在天真美好的童话世界与严峻的现实世界间找到了平衡的契合,将诗歌的激情与生活的热情相融合,将诗歌的触角伸展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发现生活中的爱和欢喜,也抚摸到生活的温暖和疼痛。
(一)介入的愿望与不止于“平行者”的眼光
张执浩早年的诗歌风格轻盈甜美,用一种近乎孩童般纯真的视角来打量这个世界,发现与感叹这个世界的新奇美好。代表性诗作有《糖纸》《三个小女孩和一只雏鸡》《蜻蜓》《撒落的苹果》《苹果堆》等。在这类诗作中,诗人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小女孩、春天、苹果等自然万物的溢美和赞叹,阳光透过糖纸折射出斑斓炫目的光芒,诗歌中弥漫着糖果的甜香。诗人这一时期的写作饱含着激情,然而这种全力以赴的歌唱热情并没能持续很久,诗人很快便看清了生活的真实一面,在丰富美好而温暖的表象下内蕴着其实更多的是残酷和无奈,痛苦与迷茫。《倒塌的花架》中“生活”作为一种之前未有的“异质”介入到了张执浩的诗歌中,小女孩的童话世界里开始出现“外来人”:
我退出来 让时间喊疼
我 陷得太深
如同血液中的血液 也像是海洋里的水滴……
如果今夜有月 我将把它端出大海
如果朝霞出来
我将从中取出 滚烫的髓岩
献给四周沉默的石雕(《拔》)
在诗中,诗人相信自己遇到的是“重”,或者他把“轻”转化为“重”,因为生活本身就不能称得上轻盈,真正的诗人是能看清生活的这份沉重,并向着生活和内心的深处去找寻答案凝聚成诗的一群人。
在这种对生活高度且饱含同情的介入与同在感中,在坦然面对生活的反复磨打并与之打成一片后,诗人认清了生活的真实面容:它不是透明的,也不是温情的,甚至不是污浊的,它仅仅是本真的。诗歌与生活具有合一性,诗歌更需要的是“回归内心”,回到日常生活的现场,去表达那些最普通的事物与最朴素的情感,因而张执浩的诗歌专注于描绘日常生活中的俗事俗物,并不加以美化和修饰地还生活以具体琐碎的面貌,从他后来所提出的“主动生活,被动写作”的诗歌创作主张就可看出,诗人是一个“与生活走得很近的人”。
(二)行有不得求诸己的圆融与和解
随着诗歌童话般的吟唱深入现实生活的内核,诗人不可避免地要遭遇现实生活的阻击,形而上的分裂逐渐在其诗歌(如《内心的工地》)中显现。但诗人并没有就此放弃眼前这难以维系的理想世界,他开始反思生活,对自我进行无情的解剖,主动承担起这种分裂的痛苦并深入生活和诗歌内面去寻找答案,最终在时空的纵深与意象的充盈、生命体验的完整与诗歌语言的成熟过程中逐渐实现了“童话”与现实间断裂的弥合(《美声》)。
诗人在中国乡村的童年经验和成长经历以及后来受教育的环境,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家初入诗坛的写作面貌和艺术选择。诗人称“试图通过写作将他重新带回活的源头:明净、散漫、清贫却富足……”[2]在他的创作中,一支饱含童真般美好情愫的笔直指童年世界,这个世界透明清澈且轻灵,与棉花糖、糖纸、蜻蜓、萤火虫、油菜花、乡村丰收等触及童年记忆的事物有关:
他是烈日下之下的一截枯竹棍
是仲夏夜的哨兵
他是张嘎 也是潘东子……
无论我走到哪里
他总在那里 站着
张望着我内心的裂隙((《喂,稻草,人》))
稻草人是乡村生活的一个典型事物,颜色金黄形象蓬松,与广阔的田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安静从容、闲适而温暖,所以作者才让它张望着自己“内心的裂隙”。创作之初童话世界的美好愿景和理想构筑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意气风发的年轻诗人所共有,只是不论是当时还是现今,现实生活中都不存在这么一处可泠然安置这份初成且还十分幼嫩的意识的神龛。于是在生存适应的过程中就必定会出现创擦,会有由身体而心灵的创痛感。张执浩选择了回归到原初生命和原生生活中,在最平凡的字眼和最日常的生命事物中去找寻答案,寻找二者平衡共生的契合。经历了现实的历练和打磨过的诗歌意象在被注入了生活的气息后,最终呈现出的将是一副具有健康生命力和顽强适应性的面貌,在丰富了诗歌表现力和情感厚度的同时,诗歌理想与现实终将合为浑然圆融的境地。
二、诗与生命:向死而生
张执浩的诗歌中经常流露出一种朴素而浓烈的生与死、撕裂与反抗的意识,原因在于诗人在生活的磨练中逐渐体会到生活的原始素朴之美以及人对生命、时间的刻骨铭心的疼痛。诗人笔下的疼痛是一种可以触摸到的疼痛,是一种由肉体而灵魂的内植于生命的疼痛。面对这种无可逆反的生命无常与时川不息,诗人确是抱着一种向死而生素日可期的悲悯与温情,坦然应对时光血腥无情的舔舐并在生活内部做出源于对自身体验的剖析与追问的反抗。“这种将对生命和时间的形而上的思考与生活的具体物事结合在一起的体验与思索,温暖、及物、刻骨而又震撼。”[3]
(一)生命无常时川不息的疼痛与思索
诗人的疼,是贯穿其漫长一生的体验,是一种对疼痛发端于生,而时光无可逆反,“生”的无从选择与“活”的疼痛必然产生无可奈何又不愿放弃的复杂感情。生活是琐碎冗长的,生命注定会有疼痛,诗人对生命、时光的描写于是灌注了一种刻骨的温情,而不只是一种简单的“逝者如斯”的喟叹。这种经由肉体之痛上升到生命之痛和生活之痛的形而上思考,在超越肉体层面的感知,打破对日常话语常规理解的基础上,赋予了平淡的生活意象以新的内涵,使人们在琐碎生活的重复中逐渐模糊钝化了的生命触角重新焕发敏感。诗人的诗歌就蕴涵在这种平凡的日常里,既深刻体验疼痛,又在疼痛中反复书写,达到对生命的一种哲思体验。
(二)无可挽回的死亡与时间
张执浩诗中的疼痛,还源于一种无可挽回的死亡与衰老,他的诗歌作品中不断出现类似“火葬场”“掩埋”“黑暗”“地狱”(《内心的工地》)等意象,在预示死亡当下性的同时流露出诗人直面这种极限体验的勇气与决心。
张执浩诗歌中的“变声期”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状态,更是一种处于彷徨阶段的心灵与精神状态:就是这种被砖头与混凝土浇筑的令人窒息的工地,也依然无法扼制失常少年体内原生的生命力量,然而这种发育,这种身体机能上的进化却要以“学会拒绝梦想”为代价,能拿来回应未来的只有逐渐酣畅的鼾声,面对清水洗净后的自己,少年看清的却是“潜伏在他骨头里面的父亲”。诗人从朴素的日常生活出发,发现并道出了这种困扰着每一个平凡生命的“变”与“不变”的生命体验与生存状态:
一个肩扛镐锹的老人独自走进黑松林
他埋头挖掘着自己从前填下去的泥土
他挖着,挖着,随后就消逝在了土堆中
他看见自己的儿子——另一位老人
正在另一个地方抽泣(《尾声》)
疼痛的另一个来源是衰老意识,一种无可挽回的衰老,就像黑夜,从过程的酝酿到结果的降临间只有一刹那的事情。诗人撕开自己疼痛的伤疤,反复地用“衰老”来表达时光的无情和命运的捉弄,在诗歌中反抗时光的无情和死亡的无息。有人说我们是在等待中衰老下去的。张执浩也曾说:“在我眼中,古往今来最优秀的诗人不是别人,不是那些创造了多么‘杰出’诗篇的人,而是西绪福斯,这个被诗篇创造出来的人。造就西绪福斯伟大之处的并非‘地狱’这个黑暗的空间, 而应该是‘一天又一天’这样的时间状态。”时间造就了西绪福斯的伟大,因此也成为了张执浩诗歌中的关注点。
(三)向死而生素日可期的现世热情
或许彼时张执浩就已经意识到,真正的诗人,不仅能够用诗歌开辟出一方属于自己的心灵净土,并试图就此高蹈在自己诗歌理想中的人。一个优秀的诗歌创作者是在清醒认识到生命索然轻猝,死亡和疼痛是为必然的生存现实后仍能坦然接受并与之为伍的人,是以向死而生素日可期的现世热情与悲悯同情拥抱生活的灵魂歌者。于是到了后来,他与生活间的紧张局面开始出现缓和,心态也渐趋平稳,思想情感则相应地有所变化。一如他在《理想》中所表述的那样:那时 我的理想是孤立/独自 一无所是/尽情的衰老吧/并深深爱上 这衰老本身。尽管这种衰老仍然是属于诗人一人,是孤独的是无果的,但与往先不同的是,衰老中感伤幻灭的诗人情绪逐渐为坦然沉着的生命状态所淡化,一种平静感已经蔓延开来:我知道大海的苦胆早已为此碎裂/我挤着自己所剩无几的甘美之心/潜下去 直至心碎/(《继续下潜》)。
如果说从《理想》一诗中我们还依稀能读出诗人那种掩抑不住的对于“理想”孤立无援且意义飘渺的无奈和迷茫,“尽情的衰老吧”和“爱上这衰老本身”这些近乎勉强的呼喊和自我暗示透着的是苦涩味;而《美声》中“过去的不会重演/未来的勿需闪避,我更倾向于珍惜这战败的肉体,而不是/拖着皮囊去与时光作对”,多了份看清时空现实后的理性与哲思,那么紧接下来的《继续下潜》中诗人的一番行动——怀揣着自己所剩无几的“甘美之心”,明知会“心碎”也不计后果地“潜下去”到生活深处——则以一种向死而生的现世热情向生活也向诗人自己的诗歌理想做出了感人肺腑的宣示和表白。
在经历了疼痛、迷茫、回忆、挣扎与和解后,诗人最终回到以饱含着柔情如小女孩“蜂蜜”般善意的眼光上来打量这个世界,回归到了恬静和谐的生命和写作状态中来。尽管回忆里有令人不愿卒读的苦涩,诗人发现或许自己真正想要的和要寻找的一直就是生活的这种“本身”。而“青春的死结”“前程的虚无”都能在这种时间和生命的沉淀中转化为一份“随着人群在风筝的阴影下慢跑”,与小女孩一同加入到“落花流水的队伍”中的恬淡。正如诗人在《高原上的野花》中诚挚告白的那样,“我愿意,我真的愿意做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在诗歌和生活双重维度上不懈求索十余载的诗人,最终在“高原”之上完成了对守护那“全人类最美丽的女孩”许诺的回应。
【注释】
[1] [3]梁桂莲、刘川鄂:《饱含着真实生命体验的睿智之思——张执浩诗歌艺术论》 ,《江汉论坛》2009年第1期。
[2]张执浩:《从写作的激情到生活的热情》,载张执浩:《内心的工地》(未出版诗集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