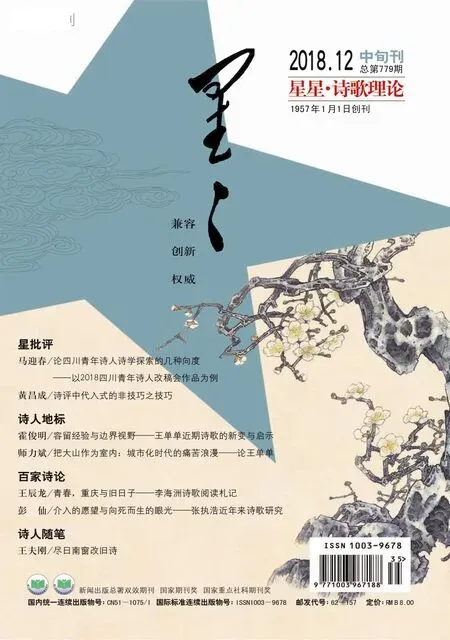论四川青年诗人诗学探索的几种向度
——以2018四川青年诗人改稿会作品为例
2018-12-30马迎春
马迎春
四川省作协和《星星》诗刊遴选出省内20位青年诗人,于2018年11月11至14日,在宜宾长宁举行了改稿会。改稿会作品呈现出青年诗人们艰辛的诗学探索精神和不同于前辈诗人的诗歌风貌、诗学品格。诗作或深切、悲愤,或冲淡平和,或诗中有画,或试图在现代诗中接续中国传统诗学的优秀血脉。他们努力对语言进行最大化的诗性开拓,审美取向健康、纯正。这些青年诗人的审美追求和诗学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为四川诗坛乃至全国诗坛增添了一抹亮色,成为一道独特的诗学风景。这些青年诗人的诗学探索既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又风格各异,大体显示出以下几种探索向度。
首先,普遍重视对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大力开掘语言的诗性功能。这一点是这些青年诗人的鲜明标记。诗是什么?这个问题答案多种多样。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诗”是对生活的摹仿,只是它们采用不同的媒介,取用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方式,因而就有了悲剧、史诗等的分别。[1]这显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诗。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2];中国传统诗学说,“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3]但这样的答案似乎并不太令人满意,因为它们只涉及诗歌的内容方面。这显然是偏颇的,因为一段语言符号光有情感和“志”还不能成为诗。比如表达爱情,一般人说,“我爱你”,情感(“志”)有了,但这一串语言符号并不是诗。那么什么才是诗呢?诗是语言的艺术,诗就是对情感或者“志”进行艺术性的、诗意的、修辞技巧性的言说。任何诗都要表达情感或“志”,重要的是怎样表达,这就完全依赖于语言的运用技巧了。所以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说,文学性(诗性,笔者加)就在文学语言的联系和构造之中。[4]诗意同样在语言符号的构造组合当中。如此,上面表达爱情的例子,如果是一个诗人,他会说,“在镜中乘着金子的翅膀向你求爱/我的灵魂不可无主”(蒋艾历);也可能这样说,“立冬以后,走累了/妻子,是我的故乡”(阿加伍呷)。
所以,这些青年诗人对语言进行诗意开拓是值得肯定的,他们真正诗意地走向了诗歌,而不是反向而驰,解构语言和诗意,让诗句沦落为大白话、口水话。在每位诗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见语言创造性运用的闪光点,比如:“新娘穿着白色婚纱/若桃子罐头里的两块果肉”(侯存丰);“唯有雨过天晴/我家门口才经得起青苔的反复推敲”(程川);“池水中鱼儿夜游/那些细密的美学的涟漪在水面上奔跑”(高亮);“风是草原的牧场”(阿加伍呷);“物质的肿瘤在扩散/冷漠是颗肾结石/人性在街上碰瓷”(谷语);“拐弯处,月亮猛吼一声秦腔/将深埋地下的王朝一一喊醒”(梁先琼);“故乡的棺材越长越大”(蒋艾历);“长庚星像一位亲人/近近地挨在门口/让文明,看起来/像一场乘凉”(凌风);“他仍然衣衫整洁/在院子里,淘洗正午的阳光”(路攸宁);“老人,您是婴儿长胡须卷起的轮回感”(阿炉·芦根);“搂着风和空气,在孤独中/把命运攥紧”(罗强);“瓶口收束最后的倔强”“那朵开花的旗袍也怀念我”(卓兮);“一个人要以自己的身体修补整个村庄”(马青虹);“爱,不按日出和日落”(张丹);“他在一碗盛开的茶水里伫立,怀念一片落叶”“月亮打开她十八岁的影子”(木易);“镰刀向土地索取的弧度/似一张弯弓瞄准死亡,搭在弦上的都是最亲近的人”(宋逸);“烹饪出来的夕阳,云不是放多了/就是放少了”(闫画晴);“十七楼酒幕缓缓地撑出/词语的绣花针”(罗耀);“不能从灯火与酒色中归来/就让一刀刀疼痛,失去绝响:(景心);“流泻月光轻拭两岸垂柳的泪/绚丽烟花照亮喜乐人生”(沙马石古)。
程川在这方面表现不俗,比如《梦里也曾有狭小的相逢》这首诗,“那年我在柯寨驻守落日,残光虚掩着凹陷的阴影/一度以为自己隶属黑暗的臆想/如同现在,你掌着昏暗的油灯/豢养我体内的佛堂。时常抱着这贫穷的比喻,摇摇欲坠/覆盖在黑暗表面的瞌睡替我抚摸那些镂空的喜悦/我替黑暗隐瞒这满目疮痍的人间”,这些诗句就是语言创造运用的好例证。“驻守落日,你掌着昏暗的油灯/豢养我体内的佛堂、抱着这贫穷的比喻摇摇欲坠、镂空的喜悦”,都让人感到惊奇。更重要的是,这些让人惊异的句子里面蕴藏着丰富的情感意蕴,过去和现在、时间、救赎、面对疮痍的人间的悲悯……似乎都压缩在这首诗里面了,只要读者接触到这些诗句,对这些符号进行解码,它蕴含的意义就会膨胀开来。作品集中,程川的大多数诗歌都体现出对语言进行诗意开掘、创造性运用的努力,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感伤的、悲愤的、悲悯的、抗争的程川。
可以看出,这些青年诗人的诗歌血脉实质上接续了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努力在语言运用上开掘诗意,即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通过词语的嫁接、超常组合、出人意料的比喻等方式凸显语言本身的诗意。什克洛夫斯基说,手法就是艺术,艺术就是手法,他说“诗歌派别的全部工作在于,积累和阐明语言材料,与其说是形象的创造,不如说是形象的配置、加工的新手法,而艺术的手法就是‘陌生化’,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诗歌的语言是经过加工的、困难的、扭曲的语言。”[5]由此,我们不仅肯定,并且提倡进行语言的诗性开拓和创造性运用,因为诗意的构成首要因素就在于语言,语言是诗意的重要载体,欣赏诗歌,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欣赏语言。如果阅读完全剔除了修辞,不讲究语言只注重思想的诗歌,就像吃牛肉,你只嚼一根干巴巴的牛筋,那是相当没有味道的。古人向来就有“文质之争”,对于作为语言的艺术的诗歌来说,“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然,也反对修辞过度、堆砌辞藻。
其次,大多数青年诗人力图在现代诗歌中注入传统美学思想。中国新诗有两种血脉:中国传统和西方影响,前者是抒情的诗学,后者更多是叙事的诗学。从“五四”以来,中国诗人似乎都比较注重向西方诗歌学习,早期的郭沫若,紧接着李金发等象征派诗人,以及当今的杨炼、欧阳江河等等,向西方学习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但是重西方轻传统也带来了弊端,比如叙事泛化,把诗歌写成了“故事诗”;过度追求深度写作,故作艰涩;另一个极端是受西方解构主义影响,拆解诗意,口语泛化,使诗歌成为了口水话。
须要说明的是,诗学探索不应该也不可能专制,因此不仅不反对学习西方,并且提倡学习国外诗歌的优秀技巧。我们只是反对过度追捧西方,蔑视、贬低传统诗学。众所周知,汉语和西方语言是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在表情达意上各有长短。汉语表意,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一种诗性语言,因此汉语天生就是适合抒情、进行意境营造的语言,比较含蓄;而西方语言(以英语为例)逻辑性较强,更长于叙事,即使是浪漫主义诗人,叙事因素仍然较强。所以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文学实践都是以抒情文学为正宗,相反,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叙事就是主流,抒情只是一股时断时续的小流。再者,绝大多数人面对的国外诗歌都是翻译文本,能够鉴赏、学习英文原诗的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下学习的应该不是语言,而是国外诗歌的诗学理念、结构。那么,怎样将西方诗学实践的经验嫁接于中国诗歌?新诗发展已经一百年,但这仍旧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面对这一问题,大多数青年诗人似乎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向中国传统审美靠拢。就改稿会作品集来看,多数都是走的抒情一路,并且抒情方式多样,在抒情中又能保持克制,这实质上体现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强大影响和生命力。毕竟中国古代几千年的诗学实践,创造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高峰,累积起了符合汉语表达规则和中华民族审美习惯的丰富美学实践经验,这种影响力已经深入到一代又一代诗人的血液中。比如,即使是今天,诗歌创作还在使用《诗经》赋比兴的手法;今天讲究诗要有意境,要有情味,这仍然是古典诗学的要求。
虽然青年诗人大多都努力在现代诗歌中注入传统审美经验,体现出一定的共同性特征,但是向传统取的经、采取的路径不一样,便会展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面貌。比如凌风,他在借鉴传统美学经验时,力图再次接续王维诗中有画、有禅的美学野心。看看他《深秋》这首小诗:雪线回落了/草垛。有雪山的形状/收走了衣服,晾晒场干干净净/屋子深处的小孩,在画秋天深处的山果/他们一样酡红/无知。并醉心于一场更大生命中的脱落。这首诗给人的感觉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一幅深秋的图画展现在眼前,和现实纷纭浮躁的世界形成对比,体现了诗人对宁静生活的向往,“他们一样酡红/无知”,这里的无知并不是贬义,恰恰相反,是天真、纯洁,像大自然本身一样没有受到污染的意思。再往深里挖掘,“并醉心于一场更大生命中的脱落”,这是不是有了几分禅意?言浅意深,言近旨远,讲究含蓄蕴藉的情味,正是唐诗的精妙所在。
其他如蒋艾历也在进行这方面的诗意开掘,他不但借用了古典诗词的题目,并且直接引用古诗词入诗,如“梧桐更兼细雨”“东临碣石”“穿林打叶”等,古典语言的引入,诗意显得更加凝练,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纠正现代诗歌过于散文化的作用。而长于国学的女诗人景心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她的诗歌较多地体现了一种古典韵味。我们并不知道这种探索结果怎样,但我们肯定这种探索精神,向古典取经不失为一条可以尝试的途径,毕竟已经有人做出了好的榜样,有了不俗表现,如郑愁予脍炙人口的《错误》《水手刀》等就是例证。
第三,在叙事中开疆拓土,挖掘诗意。上文说过,西方重叙事,中国传统美学重抒情,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诗学实践中就没有叙事。恰恰相反,中国古典诗学实践里面同样有叙事。比如《诗经》里面有较多叙事,《氓》就是绝好例证;《离骚》后半段“升天求女”就是叙事;白居易《琵琶行》《长恨歌》就更是古典文学中杰出的叙事性作品。但是应该看到,这些作品里面的叙事服务于抒情的目的,叙事实质上承担着抒情的功能。换句话说,里面的叙事因素并没有冲淡抒情效果,而是对诗歌艺术的抒情技巧进行了有效开拓,丰富、充实了诗歌的抒情手法。
这些青年诗人中有的就诗歌叙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并且让叙事服务于抒情和诗意营造。比如程川、高亮、阿加伍呷、蒋艾历、宋逸、罗强、木易等,他们都在这方面不同程度进行了探索实验。而走得最远的并且取得了一定艺术效果的是侯存丰和路攸宁。作品集收录的侯存丰的一组诗都是叙事的,叙事不是关键,关键是他通过叙事营造出了意境,创造出了诗意。比如《忆刘海平》《与别》《散步后》《居民区》等诗歌,虽然是叙事性的,但是字里行间弥漫着一层细雨般的诗意氛围,叙事性句子里面蕴含着大量的情感性息,抒情性极其浓厚,充满了对逝去岁月的怀念,以及想要逃离现实、回归简单淳朴、回归乡村和大自然的渴望,迷离恍惚,如梦似幻,将读者完全笼罩住。这样的叙事并不是平白简单、讲故事一样的叙事,而是让叙事服务于诗意营造,张扬的仍旧是诗歌的抒情传统。路攸宁的《冷葡萄》《无处可逃》《岁月老》《炉边岁月长》等诗歌,也都是通过叙事营造诗意的好作品,体现了诗人对时间、现实及亲情的思考、追问。
这些诗人在叙事维度上进行诗意开掘,并且大胆在诗歌写作中糅合进了小说及散文笔法,比如以对话入诗等,显示了在艺术探索上的可贵精神和勇气,值得肯定与鼓励,但是也应保持警醒。比如,如何在叙事开掘的同时避免掉进流行的深渊,避免过度叙事及散文化,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诗歌主要功能不是讲故事,讲故事是小说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也有史诗和诗体小说,讲故事,塑造人物,但是由于这种体裁的特殊性,应另当别论。
第四,立足特定地域、民族特色,深入开掘。从普遍意义上讲,每位诗人都身处某一地域、民族文化传统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该地域、民族文化的鲜明烙印,会受其山川、水文、地理、风俗传统、民族文化、日常生活细节,以及沉淀在意识深处的特定精神气质的影响。但是,有的地域、民族特色表现得尤其突出,哺育出了风格独特的诗人。
来自大小凉山的阿加伍呷和阿炉·芦根两位诗人的作品就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他们立足于自身生活的彝族村寨,进行诗意开掘,艺术地表达他们的生命体悟和“彝乡经验”,对本民族进行诗意关照。阿加伍呷试图围绕他的贡尔巴干建构诗歌世界,他的《凉山与族人》《贡尔巴干与月亮》《立冬以后,妻子是故乡》《写给我的贡尔巴干》等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本民族进行了注视和表达,“秋天过后,山瘦了/祖父说,俄尔则俄山头,开始有积雪/再过一个月,牧场上的牛群,就该回家了……数一数蓝天里的白云,有几朵,已经开始/泛黄,像木叶一样落下来/我不会离开贡尔巴干”(《凉山与族人》),诗人描绘了一幅彝乡风俗画,让读者感受到独特的地域色彩,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故乡的执着情感。
阿炉·芦根同样立足于彝乡经验进行抒写,但是相对于阿加伍呷,显得要沉静、内敛一些。他的《弃婴归来》《招魂》《哭嫁歌》《在彝家岗》等诗作都写得引人入胜,让读者感受到鲜明的彝家风俗和诗人的独特经验。“当我耳语般轻喊一声‘罢了’/会不会/百亩裙裾沉下去/一畦银饰长起来”(《哭嫁歌》),艺术地再现了彝家的婚嫁传统,“百亩裙裾”“一畦银饰”,读者仿佛看到了婚礼上裙裾飘飘、银饰摇晃的场景。
总之,从这些青年诗人身上,体现了他们在继承前辈诗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诗歌艺术方面勇敢探索、开拓的勇气和可贵精神。从他们的作品来看,呈现出了新的风貌,既有一定的共同特征,又具有各自独特的艺术品质。
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一直处于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诗学两种精神的影响之下,既相冲突又相融合。但从目前新诗的创作实践看,二者的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在新诗中有效引入传统诗学精神,又积极学习、借鉴西方诗学经验,创造出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有本民族特色又表达了人类普遍性经验的作品,这是所有中国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应当深入思考的问题。作为新一代的四川诗人,应该沉下心来,在传统和现代、西方与东方、表达与节制、抒情和叙事、感性和理性、流行和个性、文与质之间找到融合点和突破口,创作出既有佳句又有佳篇、经得起检验的文本。
【注释】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 译注,商务印书馆,2010,第27-37页。
[2] [英]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载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3页。
[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6页。
[4]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48-49页。
[5 [俄]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载[爱莎尼亚]扎娜·明茨、伊·切尔诺夫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编译,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第212-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