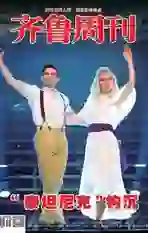西伯利亚夏天的洗碗工
2018-12-15吴永强
吴永强

1941年8月26日,法西斯铁蹄笼罩全球,俄罗斯远东鞑靼自治共和国叶拉布加镇,一群从莫斯科逃亡而来的作家准备开设一家作家食堂。一个49岁的女人萌生了一个念头,去这家食堂做一名洗碗工。
一份文件保留了她当时的申请表,从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半张纸,上面的笔迹一如她数十年来书写时清晰、工整,又显得急剧。上面写道:兹申请担任即将开设的作家基金会食堂洗碗工,敬请接纳。
此时的她,女儿已被捕,丈夫死了(但她不知道),几年后儿子参军死在战场(她更不知道)。战争、疏散、一波接一波的贫困、屈辱……她想,多么可怕的街道,以前还会写诗,可现在什么也不会……洗餐具我还可以。
但,有如最后一根稻草的普通工作她没有得到。
也许她最终会得到,等到11月,食堂开张的时候,也许她就会成为一名辛勤的洗碗工。但她等不及了——
4天后,她自縊身亡。
同样是在茫茫西伯利亚的原野上,她曾经的恋人,少年时乘坐火车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来看她的那个人,早已于几年前死去(她同样不知道,那个人的死讯要到很多年后才会被人提及,但他的埋骨之所无人知晓)。
可以提她的名字了: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称其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诗人,没有之一。她曾经的恋人,曼德尔施塔姆,也是一位可与其比肩的诗人。
也许记录是不准确的,在茨维塔耶娃妹妹阿霞的记录里,洗碗工事件并没有强烈刺激诗人,那是她们一帮女作家在战争的离乱期间抱团的一种方式,充满了悲剧性的温馨。当时,茨维塔耶娃愉快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半开玩笑似的写下了那张申请。
不管哪种说法,洗碗工事件都可算作是她人生最后时刻的一个临界点。这位少女时便名满全俄,这位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的好友,这位20世纪世界文坛最伟大的灵魂之一,在困厄到极限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至于她的儿子,可怜的穆尔,1944年2月19岁入伍,是年7月,牺牲于与法西斯匪徒的战斗中。但直到1978年,家人才找到他的确切坟墓。她的大女儿阿莉亚,曾在集中营待过17年,后半生致力于整理母亲的遗作,1975年,精疲力尽却未完成便去世。
一个伟大诗人最后的时光,注定消融于西伯利亚茫茫原野。她一生漂泊,颠沛流离,最后死于自己文学的和身体的祖国。这个有着旺盛生命欲望的女人,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她所构筑的辉煌的诗歌地理,早已超越国界,映照着从欧洲到美洲,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无数追随者。她的“迟到”“约会”与“死亡”,在约会中,“我赋予我的爱给你,它太高了。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现实的葬礼归于何处?西伯利亚柔弱的女性身躯,如何去承受现实的戕害?葬礼之前,面对死亡,她说:“最后一个钉子已经拧入。是一颗螺钉,因为棺材是铅的。”
许多年后,当地作家协会在叶拉布加坟场立了一块花岗岩纪念碑,铭文写道:“在坟场的这块地方,安葬着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可惜,她的准确墓地没能标出,人们只知道是在靠近坟场的右墙边。
然而,就是那块象征性的纪念碑,山岗上早已踏出了一条小径。
再次回到那些少有却又极度恬淡的岁月,在女儿阿莉亚的观察中,“一生中的每一天,她都怀着如同工人走到车床前一样的责任感,必然的、不可能不这样的感情走到书桌前。”当然,她的后半生根本找不到一张完整的书桌。她用笔记本写作,字迹工整,甚至在给印刷厂誊写手稿时,会使用印刷体字母。
她经常收到来信,那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在和她沟通,大都是载入世界文学史的著名人物。她爱他们,回信速度很快,先写草稿,然后誊抄,一丝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