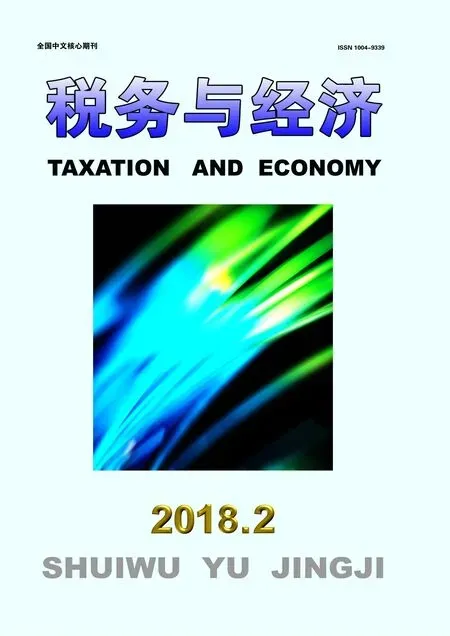纳税人知情权保障的美国经验和中国进路
2018-12-06王婷婷杨雨竹
王婷婷,杨雨竹
(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重庆 401120)
近年来,国家借助“征税之手”介入市民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以获取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源泉已成为租税国家运转的基本样态。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现代法治原则,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也应当有知晓国家课税依据、明晰课税程序以及了解税款支出途径的权利。然而,由于信息获取的滞缓和信息披露的局限,纳税人知情权受到侵害的现象屡见不鲜。从刘雷诉乐清市地方税务局不履行说明义务*原告刘雷与第三人高某分别于2014年1月和2013年12月竞得被告所在乐清市司法拍卖的房产,在所适用法规无修改的情况下,原告与第三人分别为之缴纳了3%和1%的个人所得税。2015年1月,原告向被告举报其城关分局对该第三人买受的房产少征收了2%的个人所得税,由于被告未向其说明处理情况,原告提起诉讼。一审和二审法院均以刘雷“与被诉的请求事项没有利害关系”因而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为由,驳回起(上)诉。、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普遍偏低*据上海财经大学发布的《2016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显示,全国31个省份的年平均得分仅为42.25分,只有宁夏、湖南两个省份超过60分,最低为江苏的23.71分。等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到,如何重视并从根本上保障纳税人知情权利的行使,依然是我国纳税人权利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观察民主法治建设起步较早的美国可以发现,经过漫长的利益博弈,纳税人知情权于1988年的《纳税人权利法案》中得以确立。而随着纳税人知情权重要性的日趋显要,美国近年来更是在《国内收入法典》以及联邦税务局所颁布的一系列税法文件中丰富了纳税人知情权的保障内容。鉴于此,本文拟从分析知情权的概念及权利属性出发,借助对美国知情权保障的最新制度发展及制度特点的考察,为我国纳税人知情权保障的障碍破解和全面保障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一、纳税人的知情权及其权利属性认知
(一)纳税人知情权的概念及其权利属性
知情权又被称为“知的权利”,是指公众享有最大限度地知悉和获取各种信息的自由和权利。随着纳税人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纳税人保护法律羽翼的日渐丰满,知情权被各民主国家逐渐确立为纳税人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民主政治权利。尽管目前学界对于何为纳税人的知情权依然众说纷纭,但通说认为,所谓纳税人的知情权,是指纳税人享有的主动了解税收规定、税收程序、税款去向等信息以及被有关国家机关主动告知相关信息的权利。[1]根据笔者的理解,知情权至少应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要义:
1.纳税人的知情权是位居首位的纳税人权利。纳税人权利体系是一系列纳税人权利的综合,而知情权居于首位。究其原因,一方面,纳税人知情权的实现是纳税人其他权利实现的前提条件。诚如美国总统杰弗逊所言:“要防止人民犯错,就应将关系其本身事务的全部资讯给予人民。”[2]因此,只有在纳税人能够充分行使其知情权、对征纳税信息进行充分了解之时,才能够有机会、有途径实现其他权利。例如,纳税人所享有的税收监督权即以纳税人知悉税收活动过程为前提,可以说,纳税人知情权是其他权利行使的“先行要件”。而另一方面,任何基于民主的决策均须以参与者能够获取真实、充分的信息为前提,知情权的实现程度反映了纳税人对于民主政治的参与程度。就此而言,没有纳税人知情权这一基础性权利,纳税人的其他政治民主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
2.纳税人的知情权是一项公领域信息权利。与调整公民间关系的私领域相对,纳税人的知情权是基于纳税人对公权力的监督而产生的依法获取征税机关公共信息的权利,是一项公领域信息权利。在纳税人知情权体系中,其权利主体纳税人与义务主体征税机关具有权利义务的不平等性。征税机关享有国家公权力,其往往处于较为强势的地位,对公共事务信息通常具有独占的控制权。因此,为保障纳税人的权益,需要由法律赋予征税机关的信息披露义务和纳税人主动了解涉税信息的权利,由此能够有效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并使纳税人更好地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
3.纳税人的知情权是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的综合。日本宪法学者芦部信喜认为,知情权不仅是一种“接受”信息的消极性权利,还是能对信息源提出获取“要求”的积极权利。[3]就此而言,纳税人的知情权亦是一项综合性的权利,包含了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两个方面。[4]当作为一种积极权利时,纳税人的知情权主要体现为信息收集权(行动权利),即纳税人有权请求征税机关对特定信息进行公开和告知。具体表现为:一是纳税人通过行使请求权,要求征税机关提供某些税收信息,征税机关应当提供相应信息或获取相应信息的方式,而不能以沉默回应;二是纳税人是否行使知情权,由享有该权利的纳税人以一定意思表示自主决定。当作为一种消极权利时,纳税人的知情权主要体现为信息受领权(接受权利),即在某些情况下,征税机关在享有知情权的纳税人没有作为时,也负有依法主动告知、披露信息的义务,纳税人对这类信息的获知和接受,即为纳税人知情权消极性的体现。因此我们说,纳税人的知情权是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的综合。
4.纳税人的知情权覆盖了征税与用税的全过程。纳税人知情权的客体具有确定性,是指国家机关尤其是征税机关的公共信息。这里的公共信息,不仅包括实体层面税收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具体内容,也包括程序层面的税收征管所应当遵循的正当程序;不仅包括征税阶段的信息,如征税依据、计税方法,也包括用税阶段的信息,如用税效率、支出方向等。在征税过程中,纳税人的知情权能够帮助纳税人更好地履行义务,配合征税机关完成征税活动,同时防止征税机关的不当侵害;而用税过程中纳税人的知情权则有利于监督公权力的行使,是防止税款滥用、防控腐败的重要“门阀”。
(二)纳税人知情权保障的法理根基
1.纳税社会契约的应有之义。无论是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的联合体说*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认为,国家是“一群自由的人为享受权利和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整的联合体”。,还是英国学者霍布斯的信约说*英国著名思想家霍布斯认为,国家起源于“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均将国家与民众之间认定为一种契约关系。反映在税收层面,社会契约论认为,税收是国家与公民之间基于合意所达成的一种“交易”,民众以缴纳税款的方式将部分财产权利让渡给国家,国家则须为之提供充分、合格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这种具有“公共报偿性”的交换关系中,纳税人以牺牲自身财产为代价支撑起整个国家权力体系的运作,自然有充分理由要求国家为自己提供高质量的服务。[5]由于民众对何为符合质量要求的公共产品具有评价权,而这种评价理应以“知情”为前提,这就要求赋予纳税人知晓涉税信息的权利,防止自身权利因违法或过度征税而遭到税务机关的侵犯,并据此监督政府按照约定的公共意志来使用税款。就此而言,赋予纳税人以知情权在本质上是纳税社会契约的应有之义。
2.保障征税公平的基本要求。 从广义角度来看,征税公平既包括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公平,也包括不同纳税人之间的公平。[6]一方面,就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公平来看,根据公共经济学,政府与纳税人具有平等地位,政府享有征税权力的同时负有提供相应公共服务的义务,纳税人负有纳税的义务同时享有接受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而在实践当中,由于政府处于强势地位一方,其往往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征税,而纳税人则因处于“信息的弱势方”,很难知晓政府征税活动的内容。为此,只有赋予并保护纳税人的知情权,让纳税人更为直接地了解到征税活动,方能让征税机关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约束,推动政府与纳税人间征税公平的实现。另一方面,就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公平而言,则要求税务机关平等地对待每一位纳税人,坚持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即当纳税人之间能力和处境相同时,应当承担同等的税负;纵向公平是指“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即对于情况特殊的纳税人,可基于实质公平使其享受不同的税收待遇。的统一,做到“相同税负能力的人同等纳税,不同税负能力的人区别纳税”。但这种公平抑或正义的实现不应在封闭的“黑匣子”里完成,而应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纳税人展示,使其能够获悉与其同等能力的纳税人是否承担了相同的税负、与其能力不同的纳税人是否承担了具有差异的税负,以此来实现税收公平的基本要求。
3.落实纳税监督权的必经渠道。当今,我国的财政支出仍然存在着透明度不够、效益不高等问题,特权及浪费开支并未完全杜绝。[7]落实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是确保税款得到高效利用、保护纳税人权益和行政机关公信力的必然要求,而保护纳税人的知情权是加强监督财政支出、增强财政资金运作透明度的应有之义。一方面,纳税人能够通过行使知情权了解自己所缴税款即财政资金的运作过程,这是其行使纳税监督权的前提和必经渠道;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的公开和透明也为更广泛的公众舆论监督奠定了基础。因此,赋予纳税人广泛、充分的知情权,能够使征税、用税机关在审计监督、权力机关监督之外接受公众监督,进而能够真正确保税收活动的高效有序和国家机关行为的合法与廉洁。
二、美国纳税人知情权保障的历史沿革及制度考察
(一)美国纳税人知情权保障的历史沿革
美国纳税人的知情权并非一项自始就存在的权利,它的确立过程正是其与政府信息保密权进行充分博弈的过程。总体上,我们可以将美国纳税人的知情权保障划分为萌芽时期、初步确立时期以及专门保障时期三个发展阶段。
1.纳税人知情权的萌芽时期。历史地看,受国家威权主义的影响,纳税人的知情权在美国的确立并不顺利。1946年杜鲁门总统签署了《行政程序法》,该法原本旨在尽可能地公开政府事务,但由于其本身规定的种种例外,反而为行政机构拒绝公开情报提供了依据,如行政机关可以依据公共利益以及可自由解释的正当理由拒绝公开。此外,该法还要求那些可以公开的情报只向具有“正当理由并且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提供”,这使得难以证明直接利害关系的纳税人更加难以获得相关信息。1966年为反对二战中因保障国家安全而不公开政府信息的做法,美国通过了《情报自由法》,取消了“直接利害关系”的要求,并对不予公开的例外做了限制性的明确规定,成为当时纳税人维护其知情权的重要依据。[8]1976年美国又通过了《阳光下的政府法》,与《情报自由法》不同的是,依据该法纳税人除了可以获知政府的公开文件,还可以了解相关会议的进程及其文件和信息。[9]可以看到,在该历史时期,国会应当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政务信息的权利这一主张已逐渐为美国社会所接受,并确立为一项法定主张,但由于纳税人的知情权仅在其他法律制度中进行了原则规定,其范围依然不够明晰。
2.纳税人知情权的确立阶段。随着纳税人权利保护运动的兴起,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税制改革中专门制定了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法案,对纳税人知情权的保护做了详尽细致的规定。其中,美国1988年的《纳税人权利法案(一)》*TBOR1是1988年规范税的征收和使用的一部综合性法律《技术和其他收入法案》(Technical and Miscellaneous Revenue Act of 1988)的一部分,是其子标题J 的名称。即要求征税机关以简单易懂的非技术性语言说明国内收入局执行国内税收法律可以使用的程序*TBOR1.SEC.6227.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shall…prepare a statement which sets forth in simple and nontechnical terms… (4)the procedures which the Service may use in enforcing the internal revenue laws”.,纳税人的知情权从中得到了保护。但遗憾的是,由于欠缺不按照规定进行说明的惩罚措施,对纳税人知情权的保护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此后,美国又分别于1996年颁布了《纳税人权利法案(二)》*TBOR2于1996年7月30日颁布,全名为《增进纳税人保护的1986年国内收入法典修正案》(An act to amend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86 to provide for increased taxpayer protections),简称“纳税人权利法案二”。、1998年颁布了《纳税人权利法案(三)》,这两部法案对纳税人知情权的保障均有所加强。例如,《纳税人权利法案(二)》规定,对于已经离婚的原联合申报人,一方有权请求财政部长提供关于另一方是否被采取强制征收措施的信息*TBOR2.SEC.403.“If any deficiency of tax with respect to a joint return is assessed and the individuals filing such return are no longer married…the Secretary shall disclose in writing to the individual making the request whether the Secretary has attempted to collect such deficiency from such other individual.”,这种要求征税机关配合以了解相关信息的规定,有助于纳税人知情权的实现。而《纳税人权利法案(三)》更是强调了加强信息披露的重要性,要求财政部长拟定一系列信息通告以保障纳税人的利益,通告内容包括上诉程序的解释*TBOR3.SEC.3504.“Explanations of appeals and collection process.”、就纳税人定税问题与第三人的联系记录*TBOR3.SEC.3417.“The Secretary shall periodically provide to a taxpayer a record of persons contacted…by the Secretary with respect to the determination or collection of the tax liability of such taxpayer.”等与纳税人权益关系密切的信息。在此基础上,美国国内收入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制作了发给每个纳税人的宣传手册《作为纳税人您所享有的权利》,“清单式”地列举和说明了纳税人在税收事务中享有的各种权利,而其中的第一条即规定纳税人享有获取信息的权利。[10]2014年6月10日美国国内收入局正式发布了新《纳税人权利法案》。有分析认为,新法案将成为关于美国纳税人权利的基础性文件,以帮助纳税人更好地理解其享有的权利。[11]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在不断修订和完善的过程中也逐步融入了《纳税人权利法案》的法律理念,其中也确立了纳税人可以有针对性地获悉所有实体性和程序性税法内容的权利。由此可见,美国纳税人权利保护体系当中,对纳税人的知情权保护极为重视,相关规定对纳税人的知情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保障。
3.纳税人知情权的专门保障阶段。伴随着金融危机以来财政的吃紧,美国加紧了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的监督。为了有效减少联邦政府在公务支出中的浪费、滥用以及低效行为,美国众议院议员James Lankford于2011年12月8日向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提出了H.R.3609号《纳税人知情权法案》,随后参议员Tom Corburn向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提出了一个配套法案S.1957。而在113、114次国会期间,James Lankford再次向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提出H.R.1423号《纳税人知情权法案》,根据该法案的要求,政府机关必须准确认定其管理项目所需耗费的管理成本、服务费用、项目受益人数量以及项目涉及的雇员数量,并将上述信息在各机关网站进行公示。在115次国会期间,美国众议院议员Tim Walberg再次提出了H.R.71号《纳税人知情权法案》,该法案强调了网上信息公开的重要性,要求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对预算超过一百万美元的项目的开销与执行情况提供更多网上信息,并对相关信息种类进行了明确,如批准该项目的立法、针对该项目的主要法规等,旨在进一步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些法案都处于“动议”阶段,尚未实质性地上升为具有实效的法律规定。
(二)美国纳税人知情权保障的制度考察
由上可知,美国在纳税人的知情权保障方面既有综合性的《纳税人权利法案》以及《国内收入法典》进行保护,又有处于立法动议当中、为诸多国会议员屡次提请的《纳税人知情权法案》来呼吁强化用税阶段的知情权。总体上,美国纳税人的知情权保护制度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知情的主体。从美国纳税人知情权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最初,纳税人的知情权是列属于广义的公民知情权的一部分,而随着纳税人权利保护运动的发展,“纳税人”的范畴也逐步成为公民概念在财政税收领域的“具体化”,是指一切可能作为税收相对人的自然人、法人以及社会团体。就美国而言,纳税人知情权的主体也应当作广义的理解,既包括居民纳税人,也包括非居民纳税人。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伴随着税收法律域外适用效力的扩张,享有知情权的纳税人的范围应当更加广泛。以美国国会2010年通过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为例,根据FATCA法案,凡是居住在美国境内、在海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资产或者居住在美国境外、在海外拥有2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美国公民和持有美国绿卡的外国人都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向政府申报纳税,藏匿海外资产拒不申报被视为有意逃税,一经查出会被处以高达5万美元的罚款,严重的还会被判刑。[12]由于这份法案将直接影响到“海外”纳税人的财产权利,因此,许多“海外”纳税人主张,应当享有得到对FATCA法案适用的合理解释权利以及相关涉税事项的知情权。 就此而言,享有知情权的纳税人的范围较为广泛,凡是有可能被课税的民众都应当成为纳税人知情权的主体。
2.知情的范围。美国具有极高的纳税遵从度,这也与税法信息的公开、透明分不开。在税法内容的知晓方面,纳税人无论是对实体税法制度抑或程序性的税法事项,无论是在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哪一过程,无论是在征税事项还是在用税事项上,纳税人都具有获取和知晓特定涉税信息的权利。
第一,知悉国家税收立法事项的权利。公平、安定的税法秩序是纳税人权利保障的源泉,要使纳税人的知情权得以保障,首先应当让纳税人了解税法的制定过程、税权的分配以及课税的基本要素。作为民主宪政发展走在前沿的国家,美国《宪法》明确规定了“税收法定原则”,其第1条第7款规定:“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第1条第8款规定:“国会有权规定并征收税金、捐税、关税和其他赋税,用以偿付国债并为合众国的共同防御和全民福利提供经费;但是各种捐税、关税和其他赋税,在合众国内应划一征收”。尽管其中并无专门的关于纳税人知情权的保护条款,但细察之,这些均为国家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揭示税法的制定过程以及征税的目的奠定了基础,从中纳税人可以知晓税法的制定机关、制定的方式与程序,享有对宪法、税收基本法到各项税收法律法规、政策、判例、公告等法律渊源的知情权。与此同时,纳税人还可知晓税收的主要用途应当是“公益性”的,凡是非用于公益目的的税收不具有正当性。而在纳税人知情的途径方面,美国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让纳税人知晓相关立法信息。(1)税收立法案的公布。美国于税收法定原则指导下的税收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通常以发布政府公报、报纸刊发、在政府网站公开以及在税务所公开等方式向纳税人传递税收立法的议案和草案信息,并及时公布已经生效的税收立法,使纳税人能够从中知晓立法的依据、可能涉及的利害关系人范围、立法内容及立法理由等内容。(2)税收立法案的听证。作为一种吸纳民意、汇集智慧的民主立法方式,听证制度有利于纳税人第一时间获悉相关税收立法信息,进而保障纳税人知情权的实现。例如美国税收立法议案由众议员提出后,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都会提前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对所有公众开放,任何利益方均可在此期间向委员会官员提出质询或向财政部代表就立法的细节问题提出询问。[13]
第二,知悉税收执法事项的权利。税收执法是一项将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转变为现实义务的过程,它直接与纳税人的财产增减挂钩,因此,美国税法规定纳税人在此过程中具有相应的知情权利,并通过税务机关的解释、告知和说明义务予以实现。(1)获得税收法律与征税义务解释的权利。税法是一门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法律,在如何适用税法及相关法律条文的理解上,纳税人难免心生疑惑。为此,在税务机关向纳税人征税的过程中,赋予纳税人要求税务机关对税收法律做出相应解释的权利即为知情权的重要内容。因此,根据美国1996年《纳税人权利法案(二)》的规定,纳税人有权利全面准确地了解税法内容以及在税法安排下他们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他们有权利了解各种形式的税收法律以及IRS的征税程序,并有权利被IRS告知所针对于他们的征税决定以及关于他们收入来源的详细解释。[14](2)获得征税程序与纳税人权利告知的权利。税务机关在进行具体的征税行为之时,必须遵循正当、合法的程序方能获得有效的纳税遵从。因此,为保障纳税人的财产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征税机关具有告知纳税人相应征税程序以及纳税人享有的合法权利的义务。例如,根据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7521条b款第1项的规定,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在第一次查询之时或之前,应当向纳税人说明有关征税的调查程序以及纳税人享有的程序性权利。[15]近年来,这种“被告知”的权利已经成为美国纳税人服务的核心部分,并与一般意义上的“正当程序权利”紧密相连,诚如刑法“非经正当程序不能定罪”的原理一样,如若未经过正当的告知程序,纳税人也不能被征税。[16](3)获得征税事项的解释与说明义务。当税务机关根据征税的程序以做出征税决定时,还应当说明做出决定的理由,并及时通知纳税人。对此,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7522条a款规定,任何适用本节的通知,应当说明到期税款、利息、额外款项、附加税以及可评定的罚款的税基,并确定其数额。(4)获得征税决定的听证权利。“听证是为了更好地知情”,通过听证,纳税人能够直接了解与征税决定相关的事实认定、调查过程、理由以及其他相关书面文件的信息。因此,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6330条a款第1项规定,除非在征税之前以书面形式通知纳税人根据本节规定享有的听证权利,否则禁止对其任意财产或财产权利进行征税。
第三,知悉税收使用事项的权利。由于对税收使用的知情权既能确保纳税人能够获悉税款是如何使用的,且能够监督政府合理、有效地使用税款,提高税收使用效率,因此,针对政府浪费公共财政以及运转低效的严重情况,美国希望能够通过赋予纳税人知情权来督促政府高效率地、负责任地用好税款。根据美国1976年《阳光下的政府法》的要求,政府必须尽可能地将预算进行公布。但由于该规定较为原则,且需要受到美国《联邦政府隐私权法》的限制,美国预算信息的透明度并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为此,在前述《纳税人知情权法案》中,更加侧重要求对预算项目的公开,根据该法案第2条的要求,政府机关必须对其所管理的预算项目提供详细的项目介绍、成本测算、支出情况,并在相应的公网指定页面进行公示以供公众知晓。该法案第3条则对美国预算管理办公室的信息披露义务做出规定,要求其必须对政府项目运行的成本以及可能重复使用的领域做出年度报告。据此,纳税人可以借助对预算编制、预算审查和批准、预算支出和执行以及预算决算情况的了解,更好地监督政府是否按照预算目的来使用税收。
3.知情的方式。在美国,纳税人知情权的实现既是一个纳税人主动“求知”的过程,也是立法、财政、税务机关不断加强立税、征税、用税过程透明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纳税人的请求、立法案的公开、征税过程的说明、重要事项的听证都成为纳税人最为主要的知情方式。而在这些通常性的知情方式之外,美国还要求OMB、IRS承担一定的主动宣传义务,将纳税人的知情权保障作为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例如,IRS应通过网站、宣传单、视频等多种渠道告知纳税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并对税收征收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予以指导。而当IRS针对某一个纳税人采取征税或审计等措施时,应当用专门的信件寄送《作为纳税人您所享有的权利》,进而帮助纳税人了解所享有的权利以及救济方式。
4.知情的救济。发展至今,知情权已成为美国纳税人最为重要的权利之一。作为一项纳税人积极主动地寻求获取信息、要求有关部门公开信息的权利,纳税人的知情权还需要依托必要的救济途径来予以保障。对此,在美国1998年《纳税人权利法案》之前,纳税人只可对IRS的鲁莽或故意行为提起赔偿之诉,而不能针对于IRS工作人员的过失行为带来的损害提起诉讼。1998年的《纳税人权利法案》则改变了这一做法,它和后续的法案规定,纳税人可以因IRS工作人员的过失行为而获得最高10万美元的赔偿,从而赋予了纳税人通过诉讼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途径。与此同时,美国还设立了专门的纳税人支持服务处,一旦纳税人在权利保护领域遭遇难题,纳税人支持服务处可以帮助纳税人解决相关问题,并帮助纳税人向IRS和国会提出意见或建议。[1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美国对纳税人知情权的保障采取了集中的法典式保障模式,为纳税人的知情权提供了从立法规范到司法救济、从征税事项到用税事项的全面保障,且在知情方式上,不仅仅是在形式上要求对纳税人的知情权予以“宣誓性”的保障,更强调对立法、财政以及税务机关告知、披露、说明、听证等义务“强制性”实施来予以保障,有效地提升了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也增进了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
三、我国纳税人知情权保护的立法现状及其问题
在我国,2001年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最早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纳税人的知情权。根据该法第7条,税务机关有义务对税收法律、法规及纳税知识进行宣传,并有义务对纳税人的咨询、询问进行无偿解答;根据该法第8条,现行法律赋予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了解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此外,上述主体还有权对纳税程序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解。此后,我国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发布了《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该《公告》首次提出了纳税人知情权这一概念,而在该规定涉及的14项权利中,知情权处于首要地位。根据该《公告》,按照我国现行税法规定,“纳税人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除上述专门的税收规定外,《行政复议法》及《行政诉讼法》等行政法律规范以间接方式同样体现了对纳税人知情权的保护。如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3条第2款,纳税人在作为行政复议的申请人、第三人时,可以对被申请人即征税主体提出的书面答复、所为行为的证据及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进行查阅,复议机关应予配合,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者除外;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0条,纳税人在行政诉讼中,其自身或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在经过人民法院许可的条件下查阅相关庭审材料。
以上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出台为我国纳税人知情权的保护奠定了基础,但整体而言,我国纳税人知情权的权利范围和方式还比较模糊,目前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纳税人知情权的法律保障过于原则
首先,我国《宪法》并未对纳税人的知情权做出明确规定,使得纳税人的知情权保护在宪法层面存在缺失。而从笔者以上所列举的法律规范来看,我国法律多以概括方式对纳税人的权利内容做出规定,并没有给纳税人权利保护确立具体的途径和方法。其次,从对征税信息的了解来看,相关法律规范对纳税人的征税知情权尽管有“向税收机关了解…”、“无偿咨询”等表述,但客观地看,这些规定并没有对具体的知情途径做出规定,没有相应法律和制度的规制及相应的告知制度,并未明确告知的范围、程序以及责任,因此欠缺可操作性。[18]此外,在《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中,仅规定了纳税人有权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程序规定,所包含内容仍限于法条规定,没有明确纳税人对具体和实质性问题知情的权利。而就纳税人对用税事项的知情权保障来看,随着纳税人知情权保护的呼声愈高,政府也愈发重视财政信息的透明度。如我国2015年修订后的《预算法》增加规定,对经批准的预算和报表等,应当在批准后20日内由政府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开,并对本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安排、执行情况以及举借债务的情况等重要事项做出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条:“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预算调整、决算、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报表,应当在批准后二十日内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开,并对本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执行的情况以及举借债务的情况等重要事项做出说明。”;又如在2017年4月的年度中央部门预算公开中,首次在财政部门户网站建立的 “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和中国政府网专门栏目中集中公开,且对预算情况的说明更加细致。[19]尽管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政府对保障纳税人知情权的决心,但现有法律规定仍然过于原则和笼统,“向社会公开”的具体程序、“重要事项”说明的详略程度都直接关系到纳税人知情权保障的充分与否。退一步说,公开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公众知情,若信息公开全部以专业术语表述、大量堆积原始材料、表达方式上晦涩难懂,纳税人的知情权仍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只有制定详细具体的标准,才能保障纳税人知情权的充分实现。
(二)纳税人知情权保障途径的被动性
当前,我国纳税人知情权的保障途径仍然具有一定被动性,这主要体现为政府主动披露信息的义务、披露信息的范围不明确。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使得财政公开缺乏统一、完整的法律保障。我国现行财政公开规定大多散见于《宪法》、《预算法》、《税收征管法》、《审计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单行的财政公开规定大多为财政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效力层次较低,直接影响了财政公开法律规范的权威性、稳定性。[20]这种统一规范的欠缺、较低的效力层级均削弱了对政府主动披露信息的约束力,相对而言,在政府披露信息方面纳税人的被动性就更明显了。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政府信息的公开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证,但是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内涵的界定等仍欠缺明确的规范,不予公开的标准仍然很模糊。《条例》中“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限制性条款,实际上也给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留下了一个模糊地带。[21]纳税人这一获取政府信息、保障自身知情权的途径,使得政府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位置,纳税人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体现为纳税人对信息的参与度低、依申请公开数量少、救济渠道使用少等问题[22],其知情权难以得到足够充分的保障。
(三)纳税人知情权救济的条件严苛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配套的救济方式是纳税人知情权得到保障的必然要求,但在我国,纳税人的知情权很难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3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政府信息公开具体行政行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纳税人若以上述规定为依据救济自己的权利,必须先满足相应的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的条件,且对于一些征税机关违法不作为的行为,在不满足相应条件时无其他救济方式,因此纳税人的救济途径无疑受到了限制。此外,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把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解释为两层含义:一是必须为切身的,而不是为任何公众利益;二是要求是直接而不是间接的。但实际情况中,往往纳税人的知情权已为国家机关所侵害,却由于相关信息的公开与特定主体间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导致此类无“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纳税人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原告,无法得到相应的司法救济。[23]救济条件严苛,使得纳税人的知情权更易受到侵害,同时,纳税人知情权被侵犯的后果也难以得到补救。
四、借鉴美国的做法完善中国纳税人知情权保护制度
与美国相比,我国纳税人知情权的保障尚处于初步阶段。因此,有必要借鉴美国纳税人知情权保护的最新立法理念和制度内容,为我国纳税人的知情权保障提供有益借鉴。
(一)完善立法保障:提升纳税人知情权保障的层级
我国宪法并未对公民的知情权做出明确规定,相应地,纳税人的知情权保护在宪法层面就有了一定的缺失。目前,在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法律体系中,除《税收征管法》由全国人大制定外,其他大多有关税收法规、政策都是以“暂行条例”、“通知”等形式存在,层级和效力都较低[24],这与税收基本原则之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仍有差距。所谓税收法定原则,是指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税法主体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25]因此,为全面有效地保护纳税人的知情权,应当完善立法保障,提升纳税人知情权保障的层级。首先,应当在宪法中明确公民的知情权。有学者认为,可通过宪法解释方法将知情权列入宪法基本权利中,因为尽管我国宪法没有直接规定知情权,但在地方政府规章及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多确认了公民的知情权,此种解释具有充分的基础[26];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在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中,增加公民享有“知情权”的条款。[27]我们认为,相较而言后一种观点更加合理,能够使知情权保护的重要程度相应地体现在我国的根本大法中,为纳税人知情权的保护奠定基础与提供依据。其次,《税收基本法》起草项目已经列入我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这标志着《税收基本法》起草工作正式启动[28],该项法律将成为我国税收法律的基本法,因此应当在该法中明确纳税人的权利,对纳税人的权利进行明确而集中的规定,这将为我国纳税人知情权的保护提供更为直接的依据。
(二)破除制度障碍:明确税务机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税务机关的信息披露义务是纳税人知情权保护的必要回应。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审计法》等对税务机关信息披露义务做出了要求,然而,对于信息披露的具体程序和程度仍然没有明确的依据,这对于纳税人知情权的保护而言是一种制度障碍。如何才能使税务机关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真正保护纳税人的知情权?结合美国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思考:
第一,对披露信息的种类作细化规定。如美国在2015年提出的《纳税人知情权法案》中,要求在网上对年预算超过100万美元的联邦项目的财产清单进行公开。*Taxpayers Right-to-know Act 2015.SEC.2.(a)(3)(C)“include on the website—(i) a program inventory that shall identify each program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which there is more than $1,000,000 in annual budget authority…”该规定对应公开项目作数字化的要求,使得信息公开有更加明确、可视的标准。这与我国目前适用的描述性标准相比更具确定性*如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其中对什么是影响了切身利益、什么需要公众广泛参与,并没有确定的标准。,既给行政机关提供了公开的标准,防止因对描述性标准理解不同导致的冲突,也给公众即纳税人以知情和监督的标准。
第二,对信息披露的频率作明确要求。如美国在2014年提出的《纳税人知情权法案》中,要求总审计长维护一个公众可进入的至少一年更新一次的网站,对部门会议对于总审计长在第21条(a)项下的年度报告中事先确定的建议措施的回应情况进行追踪。*Taxpayer Right-to-know Act 2014.SEC 4:“…by adding a subsection‘(b)’requiring that the Comptroller General maintain a publicly available website, updated at least annually, that tracks the status of responses by Departments to Congress to suggested actions that the Comptroller General has previously identified in annual reports under subsection (a) of Section 21. ”而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信息公开的频率要求中,仅做出了“及时更新”的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九条:“行政机关应当编制、公布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并及时更新。”,何为“及时”并没有确定的标准。因此,在相关部门事务繁重而更新信息又没有强制性标准时,就更倾向于做出暂不更新的决定。
综上,我国应当对行政机关尤其是税务机关信息披露义务做出更加明确的规定,破除制度障碍,对应披露信息的种类、信息更新的频率做出具体要求,一方面防止税务机关因没有确定性标准而在信息披露上相对草率,另一方面也给纳税人知情权的保护提供一个可期待的供参照标准,加强纳税人知情权保障。
(三)构建救济制度:纳税人知情权受侵害的请求权保障
如前文所述,在现行法律规定下,纳税人难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使自己的知情权得到救济。在纳税人知情权的司法救济方面,有学者认为,在这种诉讼形式中,原告纳税人起诉并非由于自己的权益受到某种直接的侵害,而是为了维护客观的法律秩序或抽象的公共利益,这样的公益诉讼已经超越了现有的诉讼法体系。[29]因此,我们不妨借鉴美国的方式,建立专门的纳税人诉讼制度,保障包括纳税人知情权在内的纳税人权利之实现。
纳税人诉讼应当是一种公益诉讼,即原告以保护税收公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而提起的诉讼,其本身与诉争的行政行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不要求其是某个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在我国,构建这种纳税人诉讼制度,可以说是对现有诉讼类型功能的重要补充。但这样的独立诉讼制度应当采取怎样的立法模式?有学者认为,由于纳税人权利尤其是知情权的实现是一种用税监督过程, 而相应税收法律是征税用税的根据,因此应当由《税收基本法》(已列入我国立法规划)赋予纳税人以诉讼资格,并通过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完善相应部门法以构建纳税人诉讼的制度框架。[30]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对我国纳税人诉讼制度的构建起着良好的参考作用。回看美国,正是由于纳税人诉讼制度的存在,才能在判例中不断体现纳税人权利的重要性,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这样的判例又推进了相关立法活动。一方面,现行法律规定的缺陷可以在这样的诉讼制度中得以暴露,立法者可以采取行动完善相关规定;另一方面,这样的诉讼活动也是对纳税人进行税收法律普及的重要方式。可见,纳税人诉讼制度在纳税人知情权救济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经验,根据我国国情,建立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纳税人诉讼制度。尤其在我国纳税人权利意识不强的背景下,适当的纳税人诉讼制度有助于促进纳税人积极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四)提高权利意识:推进纳税人知情权的主动保护
美国是一个纳税人权利意识普遍较强的国家,与之相比,我国纳税人的权利意识较弱,纳税人对权利的认识程度不高,普遍认为义务多而权利少。[31]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与中美两国文化传统的差异是密不可分的。在美国,“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贯彻社会生活始终,因此,美国纳税人更加重视自己财产的去向,对征税和用税的情况及相关信息更加关注,由此纳税人知情权意识也较强;而在我国,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曾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主流意识,受其影响,人们更倾向于对国家公权力的绝对服从,而不是质疑及主张权利,因此,纳税人也不善于行使知情权。
当下,我国的法制水平及公民权利意识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因此国家也逐渐将“聚光灯”放在了纳税人权利保护领域,而这也必然要求对纳税人的知情权这一基础性权利给予更多的关照。因此,国家应当不断加强立法建设和制度配套,推进纳税人知情权保护的法治化。一方面,应当从法律的运行过程中着手提升纳税人的知情权意识,即从立法、执法及司法的角度贯彻和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如在立法中进一步明确纳税人行使知情权的具体途径及程序,确保税收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全面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等。另一方面,应当重视税收法律及相关知识的普及,如明确税收部门应当定期举办税收普法活动等;同时,与此相关的国家部门的媒体也应当积极普及纳税人的权利知识,如“中国法院网”官方网站、“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等。由于纳税人的权利构成一个体系,各项权利相辅相成,因此纳税人在接收到相关法律知识时,不仅会主张行使知情权,而且在行使其他权利时,为获取相关信息和资料,也会促进其知情权的行使。综上所述,国家的法律活动及普法宣传对我国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提升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提升又是其行使知情权、保障知情权的重要基础,有助于推进对纳税人知情权的主动保护。提高纳税人的权利意识,推进纳税人知情权保护法治化,既是纳税人知情权保护的振兴,也是公权力监督的重要途径。因此,国家应当采取措施,注重提升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为纳税人的知情权提供有效保障。
[1]华国庆.试论纳税人知情权及其法律保障[J].法学家,2006,(2):93-99.
[2]张庆福,吕艳滨.论知情权[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1):106-114.
[3][日]芦部信喜.宪法学Ⅲ:人权各论[M].东京:有斐阁,1998:270.
[4]林爱珺.知情权的法律保障[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6.
[5]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4:78.
[6]李森,刘亚林.税收公平新论[J].税务研究,2016,(1):32-37.
[7]闵睿,王太金.用税监督权与纳税人诉讼[J].理论界,2006,(3):99-101.
[8]黄德林.略论美国“情报自由法”之形成与发展[J].法学评论,2000,(1):147-151.
[9]张成成.中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0:10.
[10]丁一.纳税人权利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57.
[11]赵岩,赵艳清,安剑.美国发布新《纳税人权利法案》[J].国际税收,2014,(8):76-77.
[12]李关云.美国海外账户纳税法案.凤凰财经[N/OL].2014-06-30.[2017-06-19].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630/12624477_0.shtml.
[13]汤贡亮.中国税法监督基本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6:60.
[14]Allison Christlans. Taxpayer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J/OL].SSRN,2017-01-26.[2017-06-19].https://ssrn.com/abstract=2809750.
[15]施正文.税收程序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66.
[16]Lacey,Nicola.State Punishment:Political Principles and Community Values[M].Routledge Press,1988:18.
[17]朱大旗,张牧君.美国纳税人权利保护制度及启示[J].税务研究,2016,(3):78-84.
[18]林琪,张睿华.浅析纳税人知情权[J].知识经济,2010,(11):11.
[19]姜贞宇.中央部门集中晒账本:“三公”经费将怎么花?[N/OL].中国新闻网.2017-04-08.[2017-04-23].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4-08/8194016.shtml
[20]周晶.公共财政支出的信息公开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09:16-17.
[21]朱友刚.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政府信息公开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67.
[22]莫于川,许莲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初次年度报告的若干特点[J].南都学坛,2009,(4):72-76.
[23]杨支子.纳税人知情权法律保护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5:17.
[24]常钊川.纳税人知情权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9:28-29.
[25]张瑜.纳税人权利保护制度研究[D].长春:吉林财经大学,2013:10.
[26]章剑生.知情权及其保障——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例[J].中国法学,2008,(4):145-156.
[27]江必新,肖国平.论纳税人的用税知情权及其实现[J].行政法学研究,2012,(1):39-42.
[28]李登喜.关于制定《税收基本法》的思考[J].法学杂志,2006,(5):59-62.
[29]林莉红,马立群.作为客观诉讼的行政公益诉讼[J].行政法学研究,2011,(4):3-15.
[30]陈晴.以权利制约权力:纳税人诉讼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276.
[31]徐小菲.中美纳税人权利意识比较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