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 有一说一的“哲学农民”
2018-12-01陈竹沁
陈竹沁

图/彭辉
农民
同济大学云通楼,最早是经管学院地盘。一个长方体连接一个圆柱体,法国人的设计,孙周兴觉得蛮好。人文学院搬进来后,一众师生最喜五楼露天中庭,一度兴致勃勃说要在这儿种菜。十多年过去,菜是一天没种,木栅栏隔起的方寸之地,落得杂草丛生,庭院荒芜。倒也不失为野蛮生长的自然之风。
曾有好事网友指着大楼内部的旋转结构,猜测“云通”有“平步青云”的意思。2006年同济百年校庆那会儿,孙周兴主持的校园建筑命名方案要是成了,赤峰路南校门这一侧,就该是“阳明”对着“歌德”(人文学院对面中德学院)了。八年后有过一次重啟讨论,到底还是不了了之,留下“彰显大学之道,汇通中西文化精神”的初衷,搁在方案设计书开篇。
“农民”是个他常挂嘴边的词儿,自我解嘲调侃他人两相宜。公开演讲,不管是吐槽自己的绍兴口音,还是看不惯别人的套路,都大可盖上“农民”的戳记——在他来说,农民嘛,好坏都有,就是个“中性词”。
“现在不少人说西方完了,马上轮到我们中国人了,只有儒家能救世界了。不能这样想的。现在文化现实依然是欧洲科学文明决定。正是因为他们的主导性,当代思想才说要寻找多样性,在科技工业之外开辟新的思想可能性,因而关注东方。这个时代需要多元思想,我们也应该采取开放的姿态。”
孙周兴是1960年代生人。绍兴老家留给他的童年记忆,只有山村夜间的狗吠、不充足的口粮和墙上反复涂抹的标语。第一年没考上中专,母亲让他去找泥水匠拜师,他要求复读一年,临近高考胸前被毒蚊子咬了个包,严重到撑破后背,高烧不退,却意外让他超常发挥。数学三道大题不会,如有神助地写下正确答案,中间毫无论证。考分足以任挑大学和专业,他填了浙大地质系。
1984年毕业,分配到山东矿业学院教书,对本专业兴趣寥寥,日子也乏善可陈。昔日的校园诗社青年,连诗都写不下去了。在图书馆翻看60年代旧杂志,偶然读到北大熊伟先生翻译的《论人道主义的信》,孙周兴开始惊异于哲学的奥妙。这篇海德格尔写给崇拜者的信,批判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标志着海德格尔的思想转向,其中已透露出其有关“遮蔽-解蔽”的存在本质的玄思。
也正是这篇文章,开启了孙周兴与熊先生的通信。孙周兴发狠自学德语,考上浙大哲学硕士,毕业论文解读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熊先生只用了一句话评阅,表示“足供论文得以通过”,私下却来信指出几处十分细微、不易发现的错讹。孙周兴论文中提到一本海氏遗著,以为尚未整理出版,80高龄的熊先生亲自跑去复印给他寄去。
熊先生曾留德,亲聆海德格尔授课,却不愿自称其门生。去世前,这位中国海德格尔研究奠基人对学生陈嘉映等人说,“孙周兴是我的学生。”他在孙周兴身上留下的影响,是诗与思的通达之境,是课堂上和学生拿着自己的译文逐字推敲研讨。
想起浙大导师刘锡光先生,孙周兴也悲叹不已。刘先生讲学神采飞扬,吸引一众理工学子,落笔表达却逻辑不清而难解。他后来才惊讶地得知,刘先生曾在离他家不足五公里的采石场劳动,说不定他曾经路过并见到他,还骂过几声“臭老头”。熊先生也几乎是“述而不作”,二人都堪称时代悲剧下的“失语者”,错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
海德格尔是当代国际显学,著作和二手文献汗牛充栋。如今放在汉语学界,孙周兴是绕不过去的名字之一。除了最早的《存在与时间》,海氏著作大多数中译本出自他手,“孙译海德格尔”名声远扬。
同济人文学院教授张永胜写过一篇《哲学农民孙周兴》,正是借这个词称道他在哲学领域的辛勤耕耘,“且不说他的这个‘夫子自道与海德格尔对大地和农人的推崇有无关系,农民性格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信邪,同时相信一分汗水一分收获。”
今年6月,历时六年组织编译出版的30卷总计1100万字的《海德格尔文集》发布。孙周兴办公室的墙脚堆了一排,“中文世界的海德格尔研究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文献积累,从而有了一个比较坚实的讨论基础”,最多再补个十卷就够了。
“德语太难了,我还是没学好。”孙周兴自谦。工作任务还剩一套《尼采全集》,“海德格尔算是大概把握了,尼采还得深入,每个领域都至少得花十几年功夫才行……”张永胜于是说,“像孙周兴这样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哲学农民,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大概还真就他这么一个。”
未来
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手,孙周兴自认,论哲学译著,孙周兴在中国可能是数一数二的,读者也最多。1996年他出版《海德格尔选集》(两卷本)被评为年度“十大好书”,后来成为学界外国哲学著作引用率第一名。目前,《海德格尔文集》商务印书馆首印4000册已告售罄。
在电脑前摆弄学术翻译,曾是孙周兴最大的“快感”来源,因为有种平安的感觉。在他眼中,反复敲打词语,纯属“职业良心”。他推崇鲁迅先生所说的“硬译”,留下“本有”(Ereignis)、“集置”(Ge-stell)、道说(Sage)等等生词,汇入哲学常用语库。
如今他保持着每天写作的习惯,翻译则偶尔为之,新技术开始动摇他对这项事业的热情,“有人说,孙老师我们还等着读你的翻译呢,我说对不起啊我马上不译了,这个时代马上过去了,我跟机器人怎么斗?”
“现在是专业和专家时代,一般人会守住自己的地盘不放,成了某某或者什么专家。我如果能做好海德格尔和尼采研究,应该也差不多了。这时候再去拓展什么,实在是不无冒险的。没想到我接着去搞艺术哲学,现在又搞技术哲学去了。”孙周兴笑说,“千万不要把我塑造成一个德国哲学权威,海德格尔、尼采权威,那很傻啊。”
顺着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思路,他提出“未来哲学”,简而言之:哲学在“完成”意义上达乎“终结”的过程,与技术工业的扩张一体。艺术和政治将代替哲学和宗教,和技术一起成为时代决定性的命题。未来哲学首先是一种科学批判,必然要与艺术联姻。
最近,他刚刚和一家高科技企业合作,在浦东张江成立一个未来研究机构和艺术空间,预计每年举办一次“未来哲学论坛”,预计一年搞六到八次研讨会,八个展览,他一个晚上就把主题给编了出来。11月23日开幕的首届未来哲学论坛,请来斯蒂格勒等欧洲哲学明星,还有生物技术专家裴刚院士和人工智能专家陈小平压阵。孙周兴正考虑去某个机器人实验室学习两个月,加深对技术前沿的理解。
他两年前出版的一本解读尼采思想的专著,被他取名为《未来哲学序曲》,副标题是“尼采与后形而上学”。他希望接着尼采来思考未来。
“现代大学制度问题繁多,实际上演变成一种无奈的抵抗。对个人来说,更多是对日常生活的无聊、重复、无意义的抵抗。尼采说,我们每天都在重复,why,彻底一点来说没意义,哲学要论证这个过程,这个论证本身也是一种抵抗。人生很多面向,都有抵抗的主题和要求,对学哲学的人来说可能更强烈。”
孙周兴过去常说,尼采“太野”,还是喜欢海德格尔的沉稳,更合他的心性。但走出书斋,公共领域中的他,更像忍不住要戳皇帝新衣的顽童、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我算是善于抵抗的人。但我有绍兴人的特点,打不过赶快跑。(笑)虽然嘴上说,等我脱件衣服再跟你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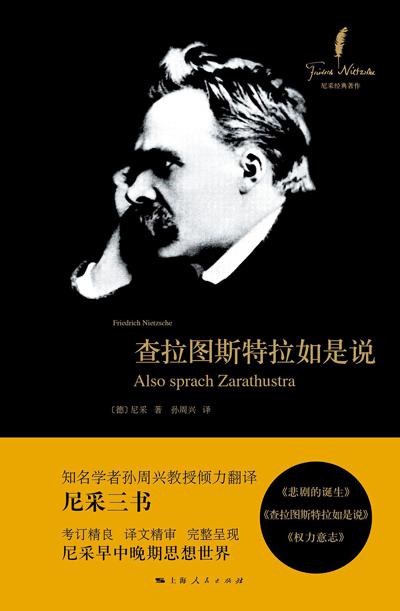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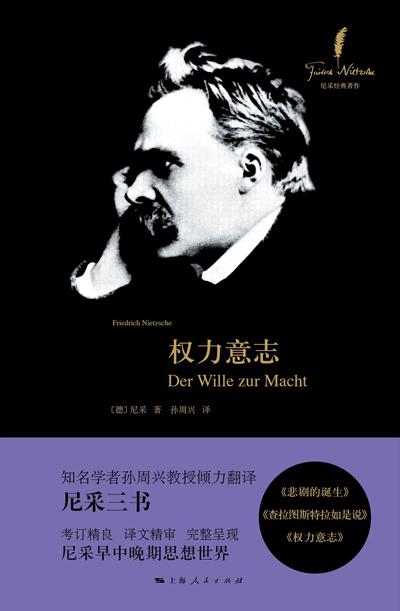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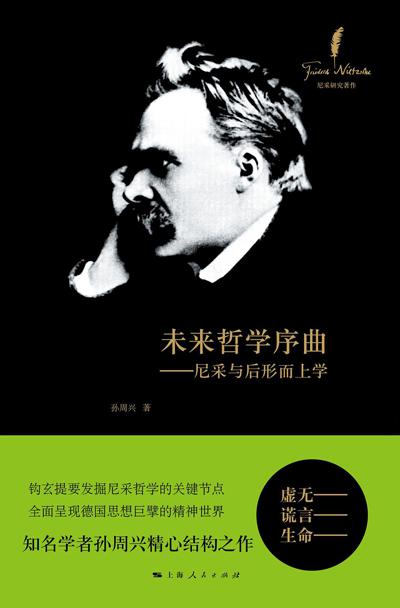
肉搏
采访这天,孙周兴一身深蓝衬衫牛仔裤,一件皮衣外套。常戴的白色贝雷帽,压过眉梢。单眼皮和眼角向下耷拉,躺在阴影里,略一严肃,似有睥睨万物的神气。帽子遮掩下的头发,同胡茬一般短,灰白相间如两块山水相隔的盐碱地,又为他素有的粗犷加上一分。
更年轻时,他披着一头过肩长发,乌黑、浓密、微卷,朋克气场更足。几年前他还会跟人打架。茅台喝过四两,老男人哭着抱上来,管他什么人物,一巴掌就扇了过去。唯一一次清醒状态下打人,也是在饭局上,则是为一位受压制的年轻教师出气。
“学术的本质是自由,应该有一套与之相应的管理方式。”当院长11年,孙周兴最得意的,就是建立起一套教授治校的学术民主规则。一个教授委员会对接学校层面七八个委员会,决定人事、职称评定等重大事项,院长也只有一票,因此从没有教师给他递烟送酒。这听起来很荒谬:好像行事粗放,但又特别在意规则。
孙周兴说,绍兴人的性格综合鲁迅的阳和周作人的阴,他两点都沾一些,被朋友评价为:外表粗犷,做事却细腻周到。他写绍兴“师爷鼻祖”徐渭,证明文化基因里内在的刚烈性格。
去年年初,他在个人博客上踢爆核心期刊(“C刊”)合作互相引用以提升“影响因子”的潜规则,戏言将按“市场规则”对其主编的《同济大学学报》进行整改。早在2012年,有同行邀请座谈共商“合作引用”大计,他果断拒绝,回头就发了文章批判。但荒诞之事不绝于耳:一个大学两本杂志办公室门对门互相引用;一个省的十家学报形成省内引用同盟,于是全成了C刊;一些杂志一条引用甚至内部标价500元。
“为什么人文学者对今天的技术时代没有反应?”孙周兴转而体恤当今学人,“学哲学的人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利益的要求,如果连做学术的尊严都没有,那他连最初的梦想都没了,看到的都是虚伪和肮脏。如果整个社会都处于虚假中,大家就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判断一个事物,我们就处于傻逼状态,和今天的技术现实格格不入。”
孙周兴将在同济的创业史称为“肉搏”,根本问题是一所工科院校的评价体系与人文学科格格不入。眼下让他头疼的是,校方对职称评定用论文数一刀切,文科学者的专著不算数,令学者们有苦难言。“有的人文学者只写书而不写论文,不行吗?”
孙周兴写下一本《欠改革的中国大学》,留下若干思索与实践。从一个人的研究所,到邀请陈家琪教授加入,三年时间完成硕博点,两人一个往前冲,一个往回拉,性格刚好互补。每当陈家琪叹气,孙周兴就劝他“不要紧张”,慢慢地这成了他的口头禅——与海德格尔所谓“泰然任之”(let be)异曲同工。
拿自己和周边人事打趣,算得上孙周兴不自觉的乐事。不久前的一个周四,一位台湾学者在云通楼报告厅做完报告,孙周兴致谢总结,“难得今天是周末”,在座者无不窃笑。他似有所感,转移话题怪起麦克风来,“同济设备不大好,自从我不当院长以后越来越差……”笑声终于抖落一地。
沉潜
荷尔德林诗云:“我们每个人走向和到达,我们所能到达的地方。”孙周兴的哲学之路充满际遇的偶然,他极认真地说,他的人生轨迹本该是一个泥水匠、包工头、建筑商,搞得好的话今天也在上海,该是他来给高校捐款才对。
六七年前,他当院长时,有几位企业家给学院5000多万的赞助款,多半是冲着他来的,他在学院设立人文基金和理事会,补贴院内学者的囊中羞涩,这才有了人文学院这些年的稳定和发展。他定下一条规矩,凡老师们争取来的赞助,都有奖励。但院长除外。“现在想想有点傻啊,不是自虐么?”
听说获得《南方人物周刊》年度魅力人物奖项,太太跟他说,应该学习萨特拒领。孙周兴则戏称自己也有虚荣心,“但我当院长时规定,学校里评各种奖,院领导一律不参加,不能与民争利。”
青年时代,孙周兴曾对城市生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自比“以进城农民的眼光窥视着城市”。讨厌上街,一进市场就发怵,太太采取各种手段把他拉向闹市商场,若干年后终于放弃了。今年“双十一”刚过,太太网购的快递件在自家门前堆积如山,他哭笑不得,“怎么我们家变货运公司了?”他从中意识到,钱日益化身虚擬货币,待未来社会物质极度丰裕,或将失去意义。
“人,詩意地栖居”被视为海德格尔广为流传的名言,很少有人知道是引自荷尔德林的诗,前一句讲的是“充满劳绩”。孙周兴以为,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未来世界的斗争,将在无业的普通人和技术专家之间展开,为有没有劳动的权利而斗争。
最近他更感兴趣于尼采的惊人预言:“末人”(最后的人)是对进入技术工业的自然人类之本质的规定,他们被量化、规划、计算,“超人”则是关于未来新人的天才般的预感,他们引导人类文明的方向,重新回归自然。两者之间纠缠着自然与技术的二重性运动,寻找新的平衡。
海德格尔的时代,已经见证自然物和手工物的退出,工业制品丧失个性、千篇一律,人的感知经验逐步落空,基因工程更可能在智力和知识结构上把人拉平,个体扁平化、同一化、集约化,个体自由解放的人类理想,可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面前被消灭。孙周兴感叹,“如何保护个体自由以及让个体有进一步创造的空间,将变成以后人类文化的一个很核心的命题。”
孙周兴借用海德格尔思想,认为未来哲学要协助唤醒一种神性敬畏,“在一个后宗教的时代里,心灵的神圣之维依然留存,我们依然需要一种‘后神性的神思。”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共同信仰力量。当技术统治日益主导我们的生活,更应该推进重整全球性个体参与的讨论。正如基辛格呼吁的,全球政治家、技术专家、明星人文学者,应该尽快坐下来共同商讨技术的发展方向。
前年退休辞去院长职务,孙周兴慢慢淡出体制,时至今日,他的焦虑更多源于对未来技术的不可知。“海德格尔所谓‘既惊恐又畏惧的压抑,以及更后来的所谓‘泰然任之,也是一个指向阴沉莫测的时代境况的诉求,呼吁着思想之重量与生存之定力。”由此,孙周兴呼吁“一种沉潜稳重的思想姿态”,“为的是告别,为的是期备。”
堂吉诃德面对的风车,正在加速度膨胀。艺术和神秘,遂成最后的堡垒。
多年前,孙周兴便开始涉猎艺术现象学,从瓦格纳到博伊斯再到基弗,串成一条线,均在发掘民族传统神话和神秘主义元素,重新激活当下的神秘感和意义感。这块研究带给他很大刺激。“艺术不再停留在绘画、雕塑等传统样式上,而是被赋予新的要求,就是对技术世界进行抵抗和反思。当代艺术发展了观念艺术,观念艺术就是哲学艺术,新的样式一出来,艺术一下子扩展了,变得很有力量。”
孙周兴印象很深,去年汉堡G20峰会期间,有一个“千人行”(1000 GESTALTEN)的行为艺术表演,他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作品。200多个艺术家在网上发起民众参与,共有千人之众,都扮成灰色灰脑的僵尸,在街上走了好几公里,最后脱去伪装。“我想这个作品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没有个性的人,都变成了僵死,你们20个国家元首讨论的政治跟我们有关吗?我们在哪里,我们每个个体在哪里?我们的政治呢?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太有力量了。这就是博伊斯的当代艺术。”
孙周兴说,当机器取代人做重复性劳作,创造性的工作和游戏性的活动还将保留,这里面就有哲学和艺术的用武之地了。“人有些行为是很怪异的,比如我在这儿跟你面对面聊天,我心里其实在想我夫人或女儿,或者别的什么事,我不告诉你,你是不知道的。这就是人类特有的大尺度的、跨越性的想象力,这就是创造性活动。人的自由就保持在这种奇思妙想中,这种奇异性是人工智能目前替代不了的东西。所以,我在几年前就说了:人文科学的时代到了。”
获奖理由
历时六年,30卷 《海德格尔文集》 于今年6月正式出版,中文世界海德格尔研究终于有了完备的文献积累,主编孙周兴居功至伟。“孙译海德格尔”独树一帜,自上世纪90年代起便深刻影响中国知识界。而他并未止步于此,循着现象学的脉络,转向尼采研究,艺术哲学、技术哲学多点开花,探望未知的未来世纪。在象牙塔内,他用规则保障学术自由,用行动捍卫学术尊严,创造着这个时代宝贵的精神财富。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