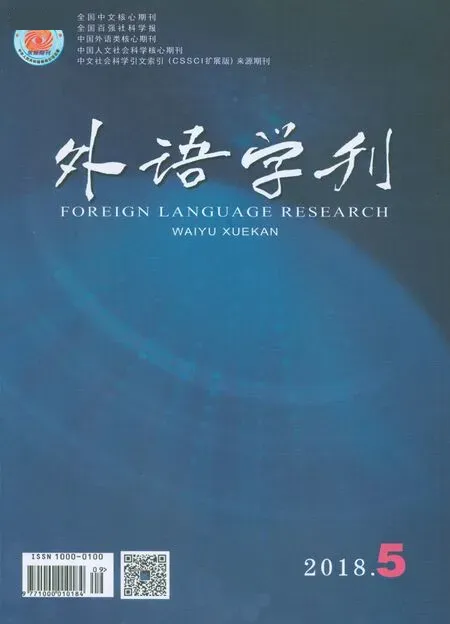创伤、视角与声音:《上海女孩》的女性创伤叙事解读*
2018-11-28董晓烨
董晓烨
(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 150040)
提 要:《上海女孩》是一部女性主义叙事和创伤叙事特征非常突出的小说。邝丽莎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和华裔女性的声音,讲述一对华裔移民姐妹经历的性别、战争、家庭、文化和种族等各类创伤事件。本文尝试从女性创伤现象和创伤叙事视角解读发声与创伤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声音与创伤具有紧密的关系;叙事视角在创伤叙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传达出叙述者的伦理立场;《上海女孩》成功地运用创伤叙事,在体现作者关注华人女性命运的同时,为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解读视角。
1 引言
创伤视角是解读华裔美国文学的一个突破口。许多华裔美国作家具有浓重的创伤意识,在其作品中呈现大量的创伤事件,如《女勇士》和《喜福会》中的女性受压迫的创伤体验,《吃一碗茶》和《蝴蝶君》中华人男性被去势化的创伤经历,《中国佬》和《家园》中历史和文化被褫夺的创伤感受等。创伤与发声具有紧密的联系。经历创伤之后,受创主体常常表现出失语特征。在权力不均的环境中,发声与噤声具有隐喻意义。能够自如地发声表明发声者在社会等级中占据较高位置;被强制噤声表明被噤声者在社会体制中处于属下地位。鉴于族裔与权力问题的关联,以何种视角看待创伤记忆的变形,克服创伤应激反应,顺利发声就成为华裔文学领域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邝丽莎(Lisa See)的《上海女孩》可以用作研究女性创伤叙事的典型案例。“一百多年前,黑格尔称美国为‘未来国土’。”(胡全生 2017:115) 邝丽莎作为当前华裔美国文学创作低迷时期中活跃的华裔美国作家之一,研究她的作品有助于寻找当前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突破口。
2 华裔女性的创伤与沉默
创伤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热门话题。后工业革命时代大量出现的工业创伤事故和19世纪末弗洛伊德对于创伤心理的探讨预示创伤话题的兴起。弗洛伊德对创伤心理,尤其对受害人在经历创伤事件后形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状态的研究奠定当前创伤理论的基础。20世纪被称为创伤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核爆炸、冷战和越战等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女性遭受的家庭暴力和社会暴力,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美国和南非等地种族隔离背景下的种族创伤和宗教冲突,9·11事件引发的恐惧,疫病、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的肆虐以及灾情之后的心理重建等都促使人们开始关注由战争、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宗教冲突、文化冲突和自然灾害等引发的各类创伤,尤其是随之引发的创伤治愈问题。恰如有学者指出,“即使是引以为傲的自由竞争也隐秘地与暴力、高压、歧视相联系。个人的‘有害的知识’或是集体的‘痛苦的经历’引发各类创伤,应对创伤是丧失权力的个体仅存的选择”(Biti 2016:55)。随着大范围密集创伤事件的出现和汇集,创伤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从病理学范畴扩展到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学、哲学、宗教和文化研究等其它学科领域。伴随跨学科性的发展,原本侧重身体和心理创伤的探讨进一步扩展到文化研究层面。当前,创伤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知识话语和研究范式。在文学研究的范畴内,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福克纳的《八月之光》、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和莫里森的《宠儿》等大量经典作品都可以作为创伤叙事得到解读,而且“文学性创伤叙事能够起到更好的警示、感染、触动、教化和引领的作用”(李桂荣 2010:262)。创伤研究虽然已经引起重视,但相关的理论建设仍有待加强,这成为今后创伤研究的方向。本文运用叙事学理论分析创伤现象,尝试探讨运用具体的叙事手段来表现和治疗创伤的方法。
族裔文本为创伤研究提供丰富的案例。历经各类创伤是华人女性移民的真实生活状况。讲述华裔女性在个体、家族、种族、历史和文化等多个层面上经受的各类创伤事件有助于发挥文学作品警示、感染、触动、教化和引领的作用。在《上海女孩》中,创伤事件推进情节发展。主人公兼叙述者珍珠经历失恋、破产、被卖、父亲失踪、母亲死去和被强奸等一系列的创伤性事件建构出故事的叙事进程。在叙事的最初,珍珠年轻、貌美、富有,对爱情和未来充满向往,但是一夜之间,她原本安逸的生活环境被彻底摧毁。先是父亲输光家产,为还赌债,将两个女儿卖给素不相识的金山客。再是珍珠发现她爱恋的Z.G.其实对她并无爱情,拒绝与她一同出逃。接下来,父亲失踪、侵华战争爆发、母女3人仓惶出逃。逃亡途中,母亲为保护女儿在两个女儿面前被强奸致死,珍珠也被日军轮奸。在饱受磨难、历经艰辛之后,珍珠姐妹终于逃亡到洛杉矶,虽然逃离战乱却又陷入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牢笼。人物的悲惨经历激起读者的同情。戏剧化的、令人唏嘘的情节对读者产生吸引力。创伤与性别、种族和文化视角的结合赋予这部作品以严肃意义。
在叙事进程的推进中,创伤经历成为作者塑造人物的手段。创伤威胁到个体的主体性。珍珠在经受创伤后,丧失对自身身份的明确认知,陷入精神危机。“面对突发的或灾难性的摧毁性事件,个体通常会表现出延迟的、无法控制的、重复出现的暗恐和侵入性现象。”(Caruth 1996:11) 这种“延迟的、无法控制的、重复出现的暗恐和侵入性现象”,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创伤后应激反应,这些负面情绪在珍珠的身上典型地体现为焦虑、冷淡、失语、忧郁、自卑和胆怯等症候(同上)。
创伤事件常常致使受创者情绪焦虑、冷淡或暴躁、易怒,从而质疑家庭、友谊和爱情等基本的人类情感需求。在得知自己被卖之后,珍珠作摩登女孩的梦想破灭了,她感到“身陷险境、孤助无援,感到窒息”(See 2009:33)。在陆老头家里,珍珠姐妹被当成财产和生儿子的工具,身份建构的创伤进一步延续。创伤性事件不但破坏自我建构,而且破坏良性的人际关系。家庭创伤使珍珠表现出自卑、自闭、伤痛、麻木和疏离等创伤性人格特征。由于父亲的嘲笑和讥讽,珍珠感到自卑,与父亲的情感疏离。在经历一系列创伤事件之后,珍珠与婆家人的关系冷漠、疏远,缺乏情感沟通。原本情窦初开的少女失去爱的能力,甚至与自己的丈夫也无法建立亲密、和谐的关系,时常感到精疲力尽和恐惧。
珍珠也是战争创伤和性暴力的受害者。惨遭日军轮奸的经历使她险些丧命并失去生育能力,身体创伤最终转化为精神创伤。亲眼目睹母亲受辱致死使她心生内疚,无法自拔。战争和暴力对身心的残害引发创伤性焦虑。珍珠常常心生警觉,难以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归属感。珍珠和梅在到达旧金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法融入新生活,她们唯一的愿望就是逃跑。创伤后应激反应甚至引发迫害妄想症。当珍珠在唐人街上和家人走散时,尽管她知道“任何人都没法诱骗我或伤害我,但我还是紧张、害怕……我紧紧抱着乔伊,惹得她放声大哭。周围的人盯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坏妈妈似的。我想大喊:我不是个坏妈妈!这是我的孩子!”(同上:189-190) 创伤经历抑制珍珠的发声能力,接踵爆发的创伤事件影响受创者的历史认知和世界观。在经历种种重创后,珍珠看待自我和世界的方式发生改变,其表征为自我身份认知的紊乱和丧失。在经历一系列创伤事件之后,原本时尚、靓丽、自信的上海女孩变成唐人街上平庸、胆小、冷漠的妇人。
对于受创者来说,创伤事件常常是“难以想象和无法言说的”(Edkins 2003:2)。阿瑟·弗兰克(A. Frank)将这种创伤超越语言、故事和形式的现象称为叙事触礁(narrative wreckage)。在战争、性侵犯和种族恐怖主义等的暴力残害下,华人移民女性被剥夺话语权利,成为种族、性别、文化和社会的边缘人和他者。在女性主义的研究视域中,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被人为质询为歇斯底里和失语症患者。父权制的话语体制强制剥夺女性的发言权,使女性处于沉默和从属的地位。这一论断在种族和文化霸权语境下同样适用。战乱中的流亡和移民经历再次给华人移民女性带来创伤体验。在文化帝国主义话语体制的压制之下,边缘群体的真实经验被压抑在无意识层面而无法言说。因此,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来说,无论何种形式的创伤都存在于语言之外,而非语言所能表达。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何种视角看待创伤,进而发出被压抑的声音,就成为解除创伤的必要手段。对创伤的再现视角和发声的探讨也成为创伤叙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华裔女性的创伤记忆与再现视角
如上所述,创伤给受创者带来的最大危害在于创伤的重复性和持久性。创伤事件在初始时期并没有被吸收和体验,而是形成延迟性或延后性的基本症候。因此,创伤研究涉及创伤的记忆和接受问题。身体和精神创伤折射在记忆当中,在沉淀一段时间之后,创伤经历演变成创伤记忆,对受创者施加重复性和持久性的影响。解除创伤记忆的方法是对其进行讲述和疏导,因为“讲述可怕的事件是恢复社会秩序和治愈个体创伤的前提”(Herman 1992:1)。在重新挖掘创伤记忆的过程中,以何种视角再现创伤记忆就成为创伤叙事的重要内容。创伤记忆通过特定的叙述视角再现出来,特定再现视角的选取表明人物叙述者和作者的伦理立场。
第一人称内视角有利于创伤叙事。《上海女孩》借由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重新挖掘主人公萦绕不去的创伤记忆。在叙事之初,珍珠以内视角聚焦记忆中家人相聚的场景。一家人吃饭时,父亲和母亲总是亲热地坐在梅的两边。第一人称回顾性内视角的讲述拉近人物和读者的距离,促使读者对人物产生移情,对珍珠由于不受宠爱而产生的失落和被抛弃的创伤心理感同身受。第一人称视角还有助于展现创伤的延后性。珍珠对家人用餐的画面形成创伤性记忆,被压抑在记忆中,在受创人随后的生活中以变形的形式反复再现。在父母面前失宠,使主人公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这种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在珍珠随后的生活中反复重现。因此,妈妈讲的故事让珍珠想起“爸爸不像宠梅那样宠我”(同上:91)。陌生女人对珍珠母女3人的不同态度使珍珠感到“难道即使是陌生人也把我看得一文不值”(同上:89)。出嫁之后,珍珠觉得自己被当成家里的佣人,而梅却不受约束,尽情享受着外面的新世界。可见,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形成叙述者和人物相结合的受创者视角。这一视角的运用不但有助于直白地展示人物情感,而且有助于表现创伤的难以愈合。
第一人称讲述还赋予人物受创者和见证人的双重身份,也进一步赋予个人的创伤经历以集体表征性。“个人性的创伤可以传递到与自己相关的种族、文化或性属集体内部。”(Balaev 2008:150) 作为千百万华裔美国移民群体的一员,珍珠是历史的见证。珍珠讲述的“我”的故事,也是千百万“我们”的故事。从珍珠的第一人称讲述中,读者通过珍珠的视角见证其他华人移民的创伤经历。从这一点来讲,第一人称叙事有助于达到主题深化和外扩的目的。
聚焦对象的变化给创伤事件带来多重维度的象征意义,并在由内省到外察的叙事视角转移中修正和改变自身认知。在姐妹俩的婚礼上,珍珠眼中的梅“孤零零地站在房间中央,看上去那么伤心、那么垂头丧气”(同上:171)。叙述视角的变化有助于控制叙事内容。在叙述者最初的讲述中,读者透过叙述者的视角看到的梅是随性而自私的。随着叙事视角的变化和叙述的移情,读者体会到梅对姐姐不乏关心。叙事情感的转移丰满了人物的形象,加深读者对人物命运的认识。另外,叙述者还行使摄影机之眼的功能观察美国华人社区的生活。透过珍珠的视角,读者得知:尽管唐人街的男女比例是10:1,但是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女孩却很少嫁给华人。阿尔弗雷德和珍珠站在华人移民的视角,讲述移民眼中在美出生的华裔女性或“太美国化”或“戒备心强”的形象,不甚赞同的语气呈现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和华人移民的文化冲突(同上:181)。这样,通过叙事聚焦的变化和外扩,个体创伤叙事转向集体创伤叙事。
通过以性别、种族和文化等多重边缘视角看待记忆的变形,珍珠经历的个人创伤被赋予隐喻意义和文化外延,进而从心理创伤转向文化创伤,从个体创伤变为集体创伤,从家庭创伤转为种族创伤。正是从这一意义来讲,“记忆可以作为自我复原的催化剂”(Hooks 1990:40)。对于记忆的追溯有助于揭露人类发展的历史真相。邝丽莎通过将个体生命的创伤体验和历史真实性、集体记忆、身份认同等一系列的问题联系起来,以创伤叙事创造对抗记忆,“一种地域的、直接的、个人经历的记忆方式”,从而将变形和遗忘的记忆变成文化协商和斗争的场所,用以探索和分析华裔女性遭受的各类压迫(Lipsitz 1990:223)。
在霸权体制之下,叙事聚焦的对象与叙事伦理的表达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父权制聚焦的女性身体在女性视角下具有更为丰富的含义。在文学创作实践中,身体经验具有文化隐喻。身份的丧失在隐喻层面将个人焦虑转向文化焦虑。珍珠姐妹的经历说明身体创伤的喻意。在父权制视域内,女性身体成为男性主体凝视的对象。在创伤研究视域内,创伤常常投射在身体上,身体是创伤记忆的载体。“创伤叙事处于主体性和象征秩序之间,这个边缘位置使得我们能够追溯隐藏在社会关系、社会机构和身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能够认识到身体叙事过程就是在揭示文化,文化就包含在身体之中。”(Kleinman, Kleinman 1994:710-711) 在进行女性身体的自我呈现时,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交替出现。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下,珍珠被轮奸后的身体“五脏六腑被粉碎……神智错乱……如同一只受伤的毛毛虫”(同上:97-98)。透过珍珠的视角,读者看到母亲如同“一个遭受难以承受的痛苦似的动物”(同上:97)。在此,叙述视角的设计再次引导读者认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将日军的暴行鲜血淋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控诉日军暴行。将人体与损毁的动物形象相联系,表明人物在暴行中被褫夺身份和尊严,肉体和精神被任意践踏。另外,“受伤的”“难以承受的”“冰冷的、死尸般的”等词语赋予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丰富的主观情绪。在父权制和战争的暴力摧残下,女性受害者的身体变成供陈列的有关神秘、怪异、病态和死亡的陌生化形象。第一人称内视角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联合使用不但使读者对人物的创伤感同身受,而且引导读者的价值判断,促使读者控诉战争和种族暴行。
4 华裔女性的创伤修复与发声
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巨大影响往往使受创者无力表述,从而进入失语和沉默状态,无法与他人沟通,但是有关文化、战争、民族的创伤记忆并未被忘记,而是被压抑成无意识的状态,成为日常生活的障碍。受创者努力消解创伤记忆,重建主体性。“创伤不可避免地破坏受创者原本对自己和世界的认知,这让他努力去寻找新的和更可靠的意识形态,以便在经历创伤后恢复生活的秩序和意义。”(DeMeester 1998:650) 受创者以特定的视角再现创伤经历,使语言与创伤的真实再现产生联系。因而,发声成为治疗心理创伤和进行心理疏导的有效途径。通过发声,创伤记忆被转化为叙事记忆,受创者在创伤讲述和疏导中消除创伤记忆、走出过去的阴影、进行自我复原。对于珍珠来说,她在对创伤的回顾和讲述中完成亚里士多德式的净化和情感宣泄的过程,颠覆种族和男权质询,从而修复创伤,完成身份重构。
除建立话语权威外,声音同视角一样承载意识形态意义。“对于那些一直被压抑而寂然无声的群体和个人来说,声音已经成为身份和权力的代称。”(Lanser 1992:1) 创伤研究同样重视发声的功能和意义。对于受创者来说,只有把被压抑在无意识中的创伤记忆转变为有意识的创伤叙事,才能解构和治愈创伤。因此,无论是对于创伤个体还是集体而言,言说都成为一种挽救策略。对于承载创伤记忆的种族和性别他者而言,打破沉默,夺取话语权,进行创伤记忆和叙事就成为解除创伤、构建新记忆和身份的必要手段。毕竟,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讲述故事、敢于回顾过去的时候,他才彻底康复”(Kolk,Hart 1995:176)。创伤最终被引向语言,女性和族裔创伤诱发女性和族裔叙事。珍珠的创伤性沉默诱发她进行创伤叙事的需求。正如她向读者表述:“我需要有人帮我。我需要有人倾听我的诉说”(See 2009:321)。因此,使承载着创伤记忆的独白被听见,就成为珍珠解除创伤的重要手段。
创伤叙事是创伤复原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幸存者与外界联系的方式。珍珠是一个具备发声能力的斗士。在叙事的最初,她被塑造为一个具有语言天分的人物,能够交替使用普通话、粤语、四邑方言和吴语4种语言。在到达唐人街后,她能讲标准的英语,又能模仿唐人街上的中式英语的发音。语言的自由转换为随后的身份跨越和文化融合提供可能,使珍珠能够在一切象征体系和政治历程中,依照自己的意志做一个获取者和开创者。珍珠最终通过不断的抗争和发声来重组创伤记忆,走出创伤经历和塑造个人身份。珍珠和梅在被父亲用来抵债之后,尝试逃出父权制的凝视去追求美好的未来,她们大声宣称:“我们要搬出父亲的家,开始自谋生路”(同上:33)。陆老头要给孩子取名叫招弟或盼弟时,珍珠再次发出强烈的抗议声:“再过一万年我也不会叫她盼弟”(同上:169)。当珍珠得知陆老头的美国身份是靠欺骗获得之后,她利用机会和陆老头谈判,最终掌握话语权,获得走出父权制牢笼的自由。
创伤康复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个体受创者和朋友、爱人、亲人建立联系”(Herman 1992:5)。伴随着对自身的创伤讲述,珍珠走出封闭的内心,开始关注和了解身边的人。借由发声,珍珠建立起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成为复原创伤的基础。决心走出创伤的珍珠开始在痛苦中寻找意义,最终与同为受创者的山姆产生认同。珍珠主动和山姆沟通,两人开始建立亲密的联系。创伤不宜独自面对,相互关怀和扶持的感情象征性地中和创伤。情感的交流唤醒两人心灵的活力,他们最终摆脱缺失、痛苦、愤怒、无助而重新获得充实、满足和愉悦的心理感受。
创伤叙事同样是解除集体创伤记忆的重要手段。在种族主义语境之下,华人无法与主流话语平等对话,因而被人为地消音,被质询为被动和从属的客体。弗洛伊德将心理创伤的典型特征归纳为悲悼和忧郁。受创的悲悼主体在悲伤一段时间之后, 能够将情感从失去的客体转移到新客体,从而顺利地实现移情,最终解除创伤。受创的忧郁主体却长期沉浸在哀悼的心境中,拒绝移情和承认爱的丧失,因此无法恢复与外在现实的正常认同关系,进而长时间陷于冷漠、沮丧、自责和主体分裂的心理空间当中(Freud 1939:80-101)。珍珠的心理创伤经历忧郁、悲悼、移情和解除的过程,而创伤叙事在重建健康的心理空间和身份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毕竟创伤讲述有助于创伤疏导和身份的重新确立。珍珠的创伤讲述夺取部分历史话语权,将边缘群体真实的创伤历史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发声不但是创伤复原中的必要步骤,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通过发声,珍珠不但消弭心理、种族、历史和文化等各类创伤,建构健康的社会、性别和种族身份,而且构建知识话语,形成政治转向和文化转向。珍珠以自己断裂的和颠覆性的发声挑战性别和种族的权威,确立自己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中的位置。
这样看来,创伤又与社会政治期待和文化心理联系在一起。创伤叙事具有文化编码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所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影响。通过记忆和讲述,饱受创伤的身心在性别、种族、文化的边缘处境中争取自身的权利,确定新的身份。这种全新的身份在多视角的叙事中得到强化。随着珍珠在记忆的讲述中消减危机、寻找记忆,中心人物的声音不但逐渐显现出典型性,成为群体的代言,而且诱发群体的发声,个人型的叙事声音最终转换成集体型的叙事声音。由于“基本上是边缘群体或受压迫的群体的叙述现象”,集体型叙事声音成为女性叙事和少数族裔文学常常采取的叙事形式(王先霈 王又平 2009:679)。叙事者群体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事声音构建具有政治意义的边缘发声和叙事权威。
首先随同珍珠进行边缘发声的是母亲。在女儿面临危险的时候,母亲用屈辱和生命换取女儿的生存。在拼尽全力后,一向默默无闻的母亲在临终前爆发出一连串震撼人心的声音。她讲述珍珠名字的由来:“你爸爸给你取名叫珍龙……因为你出生在龙年,龙喜欢戏珍珠。但我喜欢这个名字却有别的原因。蚌里进一粒沙子,就长出了一颗珍珠。我年纪很小,才14岁时,我父亲就包办了我的婚事。既然夫妻之事是一种责任,我就做了。你爸爸进入我的身体,就像沙子一样让我难受,但结果呢?我的珍珠出生了”(See 2009:99)。这段表述不但道出母亲对女儿的珍爱,而且声明身为女性的创伤体验。从母亲响亮的发声中,珍珠终于感受到母亲对自己深厚的爱。透过女儿的视角,坚强的、勇敢的、智慧的、隐忍的、全新的母亲取代读者眼中原本懦弱、胆小、愚昧,裹着小脚的传统中国女性的刻板形象。
与珍珠的叙事声音形成张力的还有梅的发声。在叙事的最初,读者通过珍珠的视角认识富有魅力、又自私、任性和放荡的梅。直到梅发出自己的声音,读者才赫然发现文本潜藏的叙事冲突和属于梅的个体的叙事轨迹。创伤感受和叙事视角密切相关。即使讲述同一事件,如果聚焦和解读视角不同,读者也会生成不同的阐释。在小说的最后,不受宠爱这一困扰珍珠半生的创伤性事件同样沉淀成梅的创伤记忆。在梅的视角中,吃饭时父母坐在自己身边是因为他们喜欢看着珍珠,而非珍珠以为的父母更喜欢挨着梅。这样的事例在小说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的细节都成为梅的创伤记忆。梅的讲述在宣泄情感的同时,提供对于创伤事件的多重阐述视角并重新编辑和想象自身的创伤经历。通过叙述视角的转移,读者发现,梅并非像珍珠讲述的一般自私。事实上,梅一直努力帮助珍珠走出创伤的阴霾。梅的讲述加强创伤与发声之间的张力。通过叙事视角的转移,读者看到人物形象的多个侧面,领悟到叙事视角同创伤叙事的紧密联系。
在母女3人对自身创伤经历的轮番讲述中,读者聆听到有关心理、种族、历史和文化等创伤的复调式叙事。由不同女性的创伤经历构成的复调叙事再次证明作者将个人叙事扩充为集体叙事的努力。母亲等人的讲述被包容进珍珠的讲述中,借由叙事视角的转变,叙述人珍珠和叙述人母亲等人时而分离,时而合一。通过话语转述,华裔女性的个体发声转变成集体轮言的形式。
5 结束语
叙事学视角的加入对于创伤研究大有助益。创伤与性别、叙事视角和叙事声音等话题具有紧密的联系。《上海女孩》是一部成功的女性主义创伤叙事。邝丽莎对华人女性的创伤症候的探讨为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解读视角。伴随着创伤的产生、沉淀和解除,受创人经历沉默、审视和发声的过程。华裔女性身陷多种创伤,在创伤的延宕中身心受困,发生失语,最终通过以性别、种族和文化等多重边缘视角看待记忆的变形,在对创伤叙事的回忆、讲述和疏导中,克服各类创伤带来的应激反应和负面影响,发出来自边缘的声音,确立她们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中的位置和身份。这样看来,对于创伤研究来说,叙事视角的加入不但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增强理论强度。以何种视角再现创伤记忆不但有助于揭示作者的叙事伦理,而且有助于引导读者的认知、阐述和判断。除此之外,因为发声是解除创伤的重要手段,所以以何种立场和方式发声也成为创伤叙事研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