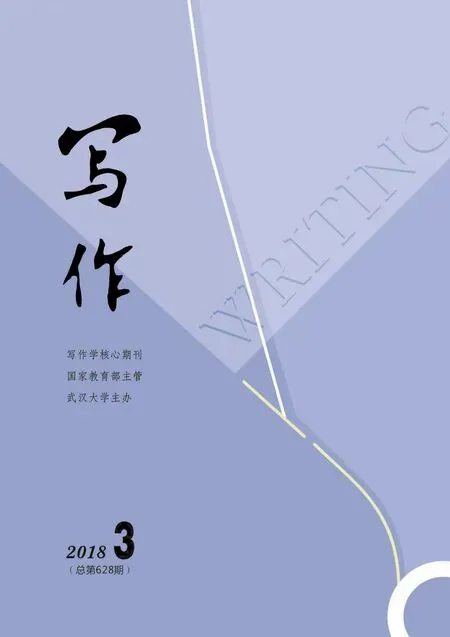小说情节的价值及形态
2018-11-28李道海
李道海
小说吸引人的要素有许多,诸如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与性格,主题,意象,环境描写,叙述的方法与角度,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等等。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首要的还是故事情节。故事与情节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小说元素。关于小说的故事,笔者已有专文进行阐释①李道海:《关于小说的故事》,《写作》2017年第11期。,本文将重点阐释小说的情节。
一、什么是小说的情节
什么是情节?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与理论家,芝加哥文学批评学派领军人物R·S·克兰(1886—1967)将其定义为“作者通过构成创造内容的行动、人物及思想而达到的独特的时间组合”②[美]J·阿瑟·霍雷韦尔:《现代小说中的情节》,焦桐、李保平译,《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第2期。。如果我们不对这一定义的内涵进行深究,则毫无疑问它突出的是时间这一要素在小说中的作用。但时间不仅仅对情节有意义,同样,它对故事也具有相同的意义。因此这个定义还不能区别情节与故事的差异。英国小说家与小说理论家佛斯特(1879—1970)讲得更直白,他说:“故事是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③[英]佛斯特:《小说面面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0页。“情节也是事件的叙述,但重点在因果关系上。‘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是故事。‘国王死了,王后也伤心而死’则是情节。在情节中时间顺序仍然保有,但已为因果关系所掩盖。”④[英]佛斯特:《小说面面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0页。在这里,佛斯特不仅看到了时间在情节中的作用,也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情节体现的是事件与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如果不能体现出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性,那么这些事件的组合就只是故事;当这些事件之间形成了因果关系,就形成了小说的情节。
从以上的小说情节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情节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时间,这是显层面的。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作者创作小说会遵循一定的线索进行结构,串联故事。读者阅读小说,文学批评家分析小说都会把握这样的线索,因而也就有了“情节线”“情节线索”的说法。情节的第二个层面是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这是隐层面(或称“深度层面”)的。一般只关注故事的读者(如儿童)往往忽略这个层面,而稍稍具有批评与分析眼光的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总会去寻找事件形成与背后的原因,追问“为什么”。这样阅读就进入了另一个层次。拿鲁迅的小说《药》来说,其基本情节是:华老栓的儿子小栓得了痨病;为了治病,他花钱从杀害革命者夏瑜的刽子手手中买来了人血馒头;最后,人血馒头并没能治好小栓的病,小栓还是死了。这里简述的是一条清晰的情节线索,这是停留在时间这个层面上的。但我们在阅读该小说的时候不会仅仅看这个时间上的故事,我们还要思考与追问华老栓为什么要买人血馒头,小栓与夏瑜为什么会死,小栓的故事与夏瑜的故事之间的因果关联。这就进入了情节的隐层次,即情节的深度层面。
这两个层面,实际上也就是有的小说理论家所说的小说的两种情节形态:“在我看来,只存在两种小说,一种是情节与故事接近重叠的小说,一种是情节与故事明显分离的小说。愈是手法简单的,叙事变形不大的小说,就愈趋向于故事性;反之,愈是增强和丰富了小说构造过程的小说,就愈显示出情节性。”①李洁非:《情节概论》,《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6期。
二、情节与人物的关系
情节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诸如叙述故事、表现主旨、塑造人物,等等。在这多方面作用中,情节与人物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知道,小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塑造形象,揭示人物性格,可以说人物是小说整个形象体系的核心。而人物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小说的情节。从根本上说,小说情节的安排是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服务的。
小说的情节开展就是叙述事件和事件之间的联系。这些事件有发生、发展与结局的逻辑过程。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物的性格形成、发展与变化的动态过程,是“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不同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②[苏]高尔基:《和青年作家的谈话》,高尔基:《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0页。。在这里,动态发展的情节不过是一种流动的载体,它为人物提供了展示与表现的空间和舞台。在一个一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人物的性格得以形成和发展;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得以确立,形成纠葛、矛盾与冲突,从而进一步使人物的性格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完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把情节与人物的关系概括为:“情节是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运动”,“人物性格是情节发展的内在根据,情节是性格的外在表现。情节和性格互为表里,情节的发展就是性格的显露和运动”③刘世剑:《小说概说》,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页。。说得更浅白一些就是,人物的性格是在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是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人物的性格是在情节的发展中形成、发展与完善的。拿《红楼梦》中王熙凤这个形象来说,她的干练、狠毒、贪婪的性格正是通过协理宁国府、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逼死尤二姐等一系列事件形成的情节凸显出来的。
三、小说情节的形态
这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会看到不同的情节形态。
首先,我们从小说家的表现技法上看,情节有外在与内在两种类型。笔者在阐述小说中的故事时,曾提到小说家表现故事的两种技法①李道海:《关于小说的故事》,《写作》2017年第11期。,即小说理论家W·C·布斯所称的“讲述”与“显示”②[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3、24页。。
所谓外在型情节,即是指小说家置身于事件之外,向读者“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样的情节着力点在于事件本身,故事性强;同时,事件的发生与进展完全由作家操控。中国的传奇、话本大多属于此类,经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是典型的外在型情节。
所谓内在型情节,是指情节的进展主要由作品中人物的性格驱动,在人物的行为、性格发展、矛盾冲突中自然“显示”;人物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决定着情节的发展走向。这种类型的小说,一般来说,情节的发展不受作家操控,而是随着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自然而然地发展。《红楼梦》就是典型的内在型情节小说。从它的情节发展来看,无论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败,还是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都不是曹雪芹外在强加的,而是人物自身性格发展与人物之间矛盾纠葛的必然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红学家和读者对后40回中的诸多情节有的肯定,有的提出了批评与不满。肯定与否定的原因,除了是否符合前80回中的伏线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是否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黛玉的“焚稿断痴情”,抑郁而死,宝玉的出家,等等,是他们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得到肯定。而所谓的“兰桂齐芳,家道复初”,是人为改变了事件的结局,不符合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因而被普遍诟病。
一般来说,外在型情节的小说,无论它的篇幅有多长,串联多少个故事,其情节与结构都是比较简单的,人物性格也比较单一,读者容易理解,不会产生歧义。而内在型情节的小说,其情节与结构大多较为复杂,人物性格也多呈现复杂性,读者在理解上容易产生歧义。
对中外小说史进行考察,虽然外在型与内在型情节的小说都可以构成经典,但当小说进入到现代阶段(一般指自詹姆斯·乔伊斯、普鲁斯特以来的小说,中国小说进入现代阶段的时间更晚)之后,这两种技法有高低之分可能也是事实。就是说,内在型情节形态形成于外在型情节形态之后,因而它的技巧更高,更复杂。在现代小说阶段,高超的小说家一般都着意表现情节的复杂性,特别强化小说人物的内在矛盾,而不是简单地编织外在的情节。有些小说家可能就因为某些情节的外在化而成为败笔。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我赞赏的杰作之一,但我一直对作者处理田晓霞的死那个情节“耿耿于怀”。田晓霞与主人公孙少平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甚至可称为少平的精神导师。为了突出孙少平精神境界的崇高与伟大,作者安排孙少平走进因矿难而死的王世才师傅的家庭,承担起照顾孤儿寡母的责任。为了凸显这个“崇高”,作者安排省报记者田晓霞跟随省委书记报道抗洪救灾,为救洪水中的小女孩“英勇牺牲”。这是作者人为地决定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如果作者不人为地“处死”田晓霞,让她继续活着,把这个外在化的情节转换为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用人物性格的发展来自然支配情节的发展,在爱情与道义之间,在不同人物的情感纠葛之间形成矛盾与冲突,人物形象将会更加丰满,情节也会更加合理与跌宕。
其次,从小说的发展过程来看,情节可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两种。传统型情节是用时间线索相贯穿,突出故事。这种情节的结构形式如长藤结瓜,情节遵循着事件发生、发展与结局的逻辑。中国的传统小说与西方19世纪末期之前的小说多为传统型情节。现代型情节多是心理线索,它以人物的心理、意识为起点,以人物心理的变化、意识的流动作为线索,事件之间的连贯性不强。西方19世纪末期以来的小说盛行这种类型的情节形态。这种情节形态在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两次对中国小说产生影响,改变了中国小说线性发展这种单一的模式,丰富了中国小说情节结构的类型。
另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小说研究中,也有人将小说情节形态分为情节强化型与情节淡化型①李道海:《新时期小说情节淡化浅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两种。情节强化型指的就是传统的以时间为线索故事性强的小说;情节淡化型指的是现代心理结构的弱化故事的小说。
四、情节的节奏
节奏本是一个音乐术语,指音乐中通过节拍、重音、休止等手段形成的有规律的强弱、长短、快慢等现象。其实不只音乐,在艺术领域,包括空间艺术之绘画、雕塑、建筑;语言艺术之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影视等等,节奏作为一种美学现象,都普遍存在。在语言艺术中,诗歌、戏剧、影视等艺术种类的节奏较易为人们理解,我们在此不论。这里单说说小说的节奏。
在小说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关注到了节奏这个要素,如苏珊·朗格(1895—1982,美国符号论美学家)、佛斯特等。苏珊·朗格言简意赅,她认为“小说节奏的本质是指‘一系列相同事件以相当短的、一定的时间间隔的连续推进’。……小说的节奏更多的是通过叙事时间与自然时间的对照表现出来”②邓颖玲、蒋翃遐:《论小说节奏的叙事功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年第1期。。佛斯特则把小说节奏分为两类:简单节奏与复杂节奏③[英]佛斯特:《小说面面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143页。。他的解释或界定“更多的是用比较含糊的辞令,甚至是用类比的方式进行说明”④张福勇:《E·M·福斯特的小说节奏理论新解》,《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9年第2期。。要想具体了解他们的节奏理论,只有去阅读他们的原著和阐释他小说理论的论文。在此不多作介绍。
如果我们必须给小说情节的节奏下个定义,那么,小说情节的节奏就是指情节在发展过程中有规律的强弱、舒缓等变化所形成的美学效果。特别是长篇小说,在情节线索中,人物有序地出场,场景不断地转换或闪回,事件从开端波浪式地向高潮推进,这就形成了有韵律、跌宕起伏的情节节奏。这些也就成为构成情节节奏的最基本的要素。我们看中国古代的话本、章回小说,就像听交响乐中的一个一个乐章一样,其节奏十分鲜明。中国古代小说家,也许他们并不懂节奏理论,但他们根据讲述故事与情节的进程,却能够科学地把握情节发展的节奏,何处停顿,何处舒张,何处复沓,错落有致。我们不妨通过一些作品来领略小说节奏的魅力。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小说情节的核心是人物。一部长篇小说人物众多,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配置,人物故事多寡与地位轻重的安排,人物性格的差异,人物出场的次序与出场场景的选择,等等,都体现着小说情节的节奏。《红楼梦》在这方面堪称典范。我们看到,在人物配置上,它有主要人物、次要人物与串线人物;同为主要或次要人物,其作用、地位、性格各不相同,这无不体现着情节的节奏。这些我们暂不详述,我们在这里重点谈一谈人物次第出场所形成的节奏效果。关于《红楼梦》人物的出场安排,脂砚斋在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回前评论中说道:
其演说荣国府一篇者,盖因族大人多,若从作者笔下一一叙出,尽一二回不能得明……故借用冷子兴一人,略出其文……
未写荣府正人,先写外戚,是由远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出荣府,然后一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仆,其死板拮据之笔,岂作十二钗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写外戚者,正是写荣国府也。故又怕闲文赘累,开笔即写贾夫人一死,使黛玉入荣府之速也。①[清]曹雪芹:《脂砚斋全评石头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3页。
在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中,作者则直接叙述道:
按荣府中,一宅中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虽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没有个头绪可作纲领。正寻思从那一件事,自那一个人写起方妙,恰好忽从千里之外,芥头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向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从此一家说来,倒还是头绪。你道这家姓甚名谁,又与荣府有甚瓜葛?……待蠢物细细言来。②[清]曹雪芹:《脂砚斋全评石头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3页。
上引回前批和作者直白,可谓说出了《红楼梦》艺术之精髓。《红楼梦》人物众多,人物如何出场,怎样向读者逐一展现各个人物的丰采?曹雪芹采用的技巧是:先通过串线人物冷子兴之口、刘姥姥之眼,交代了《红楼梦》里的人物关系,让他们一一在读者与观众面前露面亮相。然后再通过各个情节,让重要人物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史湘云等等,逐一充分地表演与展示,尽显其性格。这犹如舞剧中的群舞与独舞场面的安排。这种安排使整个作品的层次清晰,形成了非常鲜明的节奏。《红楼梦》对贾府、大观园等场景或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都是多角度、分层次展现的;对相近的情节如婚丧、宴饮等或浓墨重彩或轻描皴染,无不显示着节奏的变化。在情节安排上注重弛张节奏的结合,当然不只曹雪芹一家,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可以说俯拾皆是。《三国演义》中曹操月夜横槊赋诗情节的安排一直被人们称道,内在原因就在于这种节奏的变化。读者看到,在魏蜀吴三方紧锣密鼓、剑拔弩张安排赤壁决战的时候,巧妙安排了这个充满诗情的场面,使紧张的气氛得以缓解,就形成了有起有伏、有张有弛的节奏。
总之,情节是小说美学的核心之一,大有深入研究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