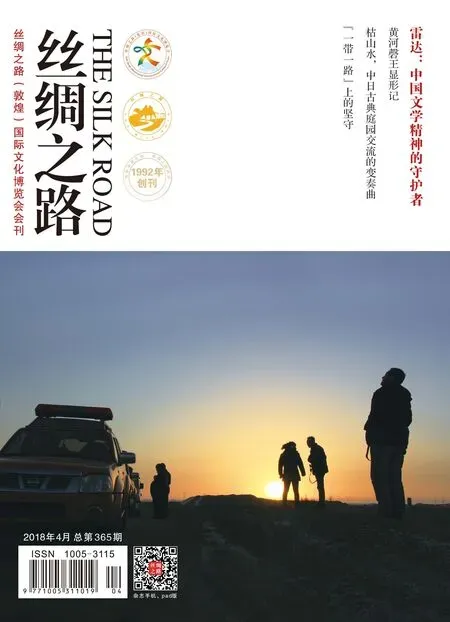雷达在新世纪的散文创作
2018-11-23文/陈霖齐红
文/陈 霖 齐 红
(作者皆系苏州大学教授)
雷达在文学评论之余,一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散文的写作中。在一定意义上,散文创作也是他的文学评论的延续、补充和阐释。进入新世纪之后,雷达的散文创作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出版有散文集《皋兰夜语》 (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其中许多篇什是2000年以后的新作。从2014年起,雷达在《作家》开辟“西北往事”专栏,不定期地推出他关于甘肃以及大西北的回忆或记游的散文。
西部的历史文化、地理风貌和人生故事是雷达散文中集中而鲜明的构成部分。黄河上游及其最大的支流渭河,作为文化地理的突出标识,贯穿着、联系着、滋养着雷达的散文创作:“黄河的声音,至今还会在梦中响起,它成了我解读兰州历史文化的一把钥匙”(《费家营》),而“渭河如弓弦划出一道弧线,好似我臂弯上鼓突的血管”(《还乡》)。在《费家营》 《黄河·远上》 《新阳镇》 《多年以前》等散文中,雷达都情深意切地回忆了自己在西北的生活经历。这些回忆叠映着西部社会变迁的背景,勾勒出作者心灵成长的轨迹。一个个历史事件的书写,不仅再现了战争、饥荒、贫穷、地理风貌、极左政治,而且表现了个体、家庭乃至族群的心性与性格,展示出人在与自然、与社会的互动和冲突中,文化的传承与裂变,生命的不屈与精神的强健。
在这些散文中,雷达以敏锐的感性落笔日常生活,关注点滴细节,引入宏阔背景,兴之所至地娓娓道来。有时候,他就是一个健谈的长者,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传递人生的经验。我们看到那个儿童时的雷达:“背着快掉到屁股蛋下的书包,忽然蹿上台,面对麦克风,先擤了一把鼻子,把鼻涕抹到鞋帮上,在哄笑声中唱开了。”(《黄河远上》)我们听到接受了新式教育而又才华出众的母亲的故事,她在丈夫病故之后,面对生活的各种困境,牺牲了自己的幸福,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地将儿女培养成人(《多年以前》)。嫂子身上表现出的顽强的生命力,同样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这个最穷苦的贫农女儿、童养媳,却在那个荒诞的年代顶起了“富农婆”的帽子,经常被扭去游街,干苦活、累活,“每次游街后,嫂子扔掉绳索木牌,抹去伤痕污渍,赶紧升火做饭,还说说笑笑,像没事人一样”(《新阳镇》)。
有时候,我们则被他带入审美活动的情境之中,譬如,“被岩画之谜吸引着,不由遥想上古游牧人,顶风冒雪,辗转深山荒滩,日夜与牛羊为伴,好不孤单,那种欲与天、地、人、万物生灵对话的强烈冲动难以抑制,却又苦无对象,于是以凿刻为语言,把原始的思维和郁积于胸的怒吼注入了这万古不灭的岩画。”(《走宁夏》) 又如,他让我们在《凉州曲》里领略了一首首民歌。这些民歌与山川形胜、寻常人家、文化古迹、历史人物相得益彰,点染出浓浓的诗情。而在《费家营》里则让我们“艳遇”了一夜盛开的桃花,看到“最鲜艳、最奔放的花儿与最苍凉、最沉默的秃山构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桃林像红霞,像红海,像火焰,在山脚下流淌着,在万古苍凉中寂寞地浮游着,燃烧着”。这不啻为西部精神的生动意象,苍凉贫瘠中崛现的灿烂光华,是不可阻遏的生命力的奋然勃发。
有时候,我们被作者峻急的思考刺激着。回顾少年时代在费家营兰州工农速成中学的经历时,雷达写道:“文革并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突然爆发的,文革的形形色色斗争方式早已有之。”(《费家营》)这呼应着作者更早的时候发出的叩问:“一场大噩梦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了,但那时代的精神因子也永远地消失吗?”(《王府大街64号》)连接过去和将来的是此刻的现实,如此警醒人们对“文革”的反思,须推向人性的深处和精神的黑暗。我们也被作者驱策着面对现代消费社会与大山深处原生样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体会作者内心的纠结:“我的心是多么矛盾:我写文章,希望人们知道扎尕那的美,但我深知,一旦知道的人一多,蜂拥而至,它立刻就会变色变味。”(《天上的扎尕那》)
神秘而贫穷、传统而富有文化多样性的西部,伴随着雷达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每每作为一种精神原乡的存在而被珍视和呵护。他在新阳镇乡亲的脸上,“看到了对祖先、对传统的无比虔诚和敬畏”(《新阳镇》),在固原发出慨叹:“切莫用施舍者的眼光看西部,西部不是可怜巴巴的施舍对象。‘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我深信,不管人类文明发达到了何等程度,我们永远需要不断回归精神的故乡。”(《走宁夏》)所有这些关于西部的散文,都突出体现了雷达心灵深处与西部割舍不断的联系,当倾诉的语流、动人的故事、鲜活的人物、欣悦与悲情、欢乐与忧愁从他的笔端流出的时候,他独具个性的散文书写空间也得以展示。
这样的个性同样体现于雷达其他题材的散文写作。无论是状写人物如《达成先生二三事》 《秋实凝香》 《忠实兄永在我心》,还是发表随感时评如《刘翔退赛是一种解脱》《开幕式能让我们记住什么》,甚至是学术随笔如《李白“故里”在甘肃秦安》,雷达都践行了他自己的散文主张,即如他阐述胡适“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时指出的,其精义“全在于自由、本真、诚挚、无畏”(《我心目中的好散文》),也因此,敏感又随性、坦荡而率真、博闻而善思的写作者形象从他的文字中站立起来,与读者进行亲切而真诚地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