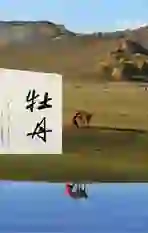《杀夫》背后的女性悲剧
2018-11-22倪琦
倪琦
《杀夫》以最极端的血腥写出了家庭、婚姻、社会带给女人的深沉不幸,集中表现了在男权文化统治里处于性别劣势的女性的生存困境、现实痛苦和极度的精神压抑。本文将从性与食下的女性生存困境、伦理与社会的驯化压抑、同性关系的异化扭曲来解析李昂笔下的女性悲剧书写,同时分析其悲剧背后的女性意识觉醒与毁灭式的自我救赎。
台湾女作家李昂的《杀夫》被奉为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问世以来带给人们极大的震撼和反思。小说的故事原型取自抗战时期刊登在《春申日报》的“詹周氏杀夫案件”,李昂从中得到灵感,体察到传统女性艰难的生存境遇,并通过文中主人公陈林市的杀夫悲剧书写出来,饱含着对女性生存的极大关注、对女性悲剧的感慨痛惜,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指向。男权社会的统治、封建伦理的规训、同性之间的欺压蹂躏,所有一切交织在一起酿成血与泪的女性悲剧。而林市在绝望后的女性意识觉醒与挥刀杀夫的自我救赎,也带给读者最沉痛的生命瑰丽。
一、性与食下的女性生存困境
李昂说:“我的《杀夫》主要在提出女性在无经济独立的情况下,只有依赖男性为主,其可能的悲惨状况为之一斑。”她洞悉女性在封建家庭中的悲剧根源,揭露出男性以食易色、对女性进行经济掠夺的现象,反映出现实的生存困境。
小说主人公林市九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由于不是男孩且母亲有改嫁的可能,母女二人很快被叔父赶出自家屋子,在战争年代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这便是封建社会中现实的性别差异,女性一方面时刻受族权和夫权的压制,完全存活在男权话语场之内;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经济独立的条件只能依赖男性为生,一旦脱离男性“管制”便无法立足、毫无生计,包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林市母亲的悲剧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在长期极度饥饿的驱使下,她或许只有本能地用身体为筹码,接受大兵的以食易性,无暇顾忌一切道德评判。而前来捉奸的人们看不到女人的被动局面和窘迫生计,认为其不守妇道贪欢又贪嘴,最终应照古训做沉塘处理。女性的生存境遇与男性紧紧依附在一起,一旦脱离便危机四伏,这也成了她们固化的宿命。在父权制文化中第二性的女性常被物化对待,在无经济独立的条件下,在食的危机和性的压迫下,成为整个男权统治的工具甚至沦为其牺牲品。所以,林市母亲最终成了杀一儆百的样例,她的通奸是一笔孽债刻在自己的人生中,也永远掺杂在林市的名声里。
同样林市与陈江水的婚姻,也是典型的性食交易,她之所以被叔父嫁给屠夫陈江水,是因为“杀猪陈仔每十天半月就得送一斤猪肉”,这场婚姻不过是一场猪肉换人肉的生意。而婚前的逻辑婚后也依旧延续,林市每每需要忍受性虐才能换取加餐福利,同时陈江水每次凌辱林市前都要带些吃食的习惯也说明婚姻在男性眼中不过是食物与性的兑换,他可以通过控制食物来源对林市构成最致命的威胁,任意欺侮、强加蹂躏,被驯养的女性在生存压力下只能成为对方发泄欲望的器具。其中林市的初夜与母亲最后的受辱遭遇极其相似,她们都是被动接受施加在身上的暴力,嘴里却死命含住施舍而得的奖励。母亲嘴里紧咬住的饭团与初事后塞进林市嘴里的猪肉有同样的象征意义,表现出不同年代的相同困境,而文中林市大口嚼咽淌落嘴角的猪油与流下眼角的热泪也形成鲜明对比,是无声却沉痛的哀鸣。
李昂用直白坦露的描述,为读者呈现残酷的女性生存境遇,在小说写出了饥饿、凌虐、奴役下的畸形夫妻关系,这也是林市悲剧的一个最直接原因。最终,在陈江水极端的身体折磨和精神蹂躏下,林市决绝杀夫,其中有生命安全受威胁的因素,还有长期累积下的生命压抑。
二、伦理与社会的驯化压抑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說:“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女性在男性社会的笼罩下艰难生存,男权文化所塑造的现实阴影则深深烙印在她们的性格命运里。如果说《杀夫》中女性的身体痛苦和生存困境来源于男性的绝对权力,那她们的精神痛楚则更多源自社会秩序中的规训,人们从林市的性格及命运悲剧里便能明显感到社会舆论、封建伦理对她的驯化打击。
作为封建传统女性,林市在生活中常表现得畏畏缩缩,她的惶惑胆小源自其成长环境,也源自社会的舆论压力。寄人篱下让林市很多事情不能自主,母亲的丑闻也让她不能在人前扬眉吐气,加上村中人的评头论足,她变得沉默少语躲藏在边缘地带,面对戏谑揶揄也只会低头逃避。这种性格也使得林市在嫁人后面对陈江水的家暴性虐,逆来顺受不敢反抗。她持家做饭谨言甚微,对于可吃饱可睡足的生活曾一度认为有福气,面对他人的夸奖甚至还会在心里得意扬扬,哪怕每每身体的痛感会使眼睛流泪,但心里早已没有明显的悲伤,她的这种忍气吞声和认命心理体现出封建伦理加给妇人的不平条例,妇德的镣铐一度将她驯化得麻木而平静。同时,封建思想也对林市造成致命的精神毒害。她常被恐惧包裹着,怕受杀猪仔杀生牵连而下地狱,怕因救下上吊未遂的阿罔官而被吊死鬼纠缠,吃了祭拜面线又害怕肚子里存有吊死鬼的紫红舌头……加上村中妇人的故意恫吓和种种迷信的危言耸听,她的精神被摧残、吞噬和扭曲,惶惶不安,战战兢兢。李昂塑造出这一“鹿港版祥林嫂”,是对封建礼教的讽刺和批判,也是对置身其中的无知女性的痛惜。
另外,中国的“示众文化”、人们的看客心理、生活中处处充斥的审视目光同样是可怕的武器,也是无形的残忍规训。在林市的悲剧里,生活的苦难教会她如何忍受痛苦,却没办法让她屏蔽掉一双双窥探的眼睛。她活在人们有色目光中,一举一动都被揣测猜度,阿罔官的偷看和对林市夫妻生活的肆意评判,井边妇人的小道消息窃窃私语,以及村中人结合传闻对她的看热闹心理,使得林市一直在“被看”的审视中煎熬,她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和评价,试图通过努力改变自己来迎合环境,然而终不能抵挡那扑面的消遣。所以,即便是地狱般的他人目光、他人言语,惩罚却都落在林市身上,当周围所有的逼迫压抑到极点时,毁灭也就成了林市最后别无选择的救赎方式。
三、同性关系的异化扭曲
李昂将笔下的女性悲剧给人以彻骨的寒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她敏感地察觉到同性关系在男权社会中的异化扭曲。热闹的看客社会让她们试图从受害者的位置挣脱跳入加害者的行列,从而成为男权的坚决拥护者,将彼此越来越深地困在围城里。这让人们看到被物化的女性除却在两性间也在同性中出现,女人间的相互审视编排消遣往往会更有攻击力,其中的恶意也会成为更尖锐的武器直逼人心。这一点在《杀夫》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林市最终的精神恍惚挥手刃夫与阿罔官等一众妇人的精神碾压有极大关系。
作为封建伦理规训下的传统女性,阿罔官本身同林市一样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她青年守寡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到老即便与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也不免沦为孤家寡人。封建道德观对女性的压制使她不能随心所欲另觅良偶,注定孤老的命运令人惋惜。然而,长期禁欲使她的性格变态扭曲,其他家庭的青年女性也让她善妒压抑,种种现实压迫终使得她从受害者自觉地步入加害人行列,通过践踏同性来宽慰自己。所以,在面对林市等人时,她往往扮演着虚伪的说教徒,肆意去审视、评判甚至编排恫吓他人的生活。她以看别人的受虐获取快感,从中得到精神释放和心理平衡,试图创造更多的比她不幸的人。这种情形在她自杀未遂后更是变本加厉,被林市和村中妇人知晓了自己的丑闻,又恰巧被林市夫妇救起看尽落魄,这让她觉得被所有人看了笑话,势必要找出一个更不幸的人来转移自身的压抑。此后,她便不再维持与林市的表面友好,甚至带有故意的冷落排挤,极尽一切可能给林市施加精神虐待。她常极为变态地偷听林市与陈江水的房事,并将听到的林市受虐的声音添油加醋地诉说给别人,在背后恶意侮辱诽谤,让林市在众人面前变成了一个不知羞耻、胡乱淫叫、贪欢懒做又馋嘴的淫妇,不仅得不到同情还要遭受众人的唾弃讥讽。可以说阿罔官将林市的无措痛楚当作治愈自己的良药,并且将她变为拉拢其他妇人、树立自己威严的工具,可见物化的女性在同性之间同样沦为消遣品。
另外,井边的洗衣妇人也同阿罔官一样是逼疯林市的帮凶。她们往往群聚在一起,以小道消息的灵通作为炫耀的资本,恣意编排揣度他人,言语里不乏冷嘲尖酸和故意。哪家有不幸都会成为她们的谈资,尤其在听到别人的性消息、性传闻时表现得更是异常兴奋,然后大肆评论,包括对她们常聚在一起的“自己人”也常抱着看热闹的心理。而李昂正是通过井边洗衣妇人的群像写尽了女性的丑态,也道出了女性的悲哀。她们无所寄托的空洞人生只有用奚落尖酸填满,用别人的不幸遮住自己的心酸,却同时也将彼此推入深渊。
总之,在林市的悲剧中,以阿罔官为核心的妇女们形成了一股杀人不见血的舆论压力,在个体有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中形成对其人格精神的绞杀,并最终使林市走向杀夫的毁灭。而其中同性间的碾压、同性关系的异化扭曲,也是男权社会压抑统治中的沉痛悲剧,令人痛惜。
四、沉痛背后的觉醒与救赎
《杀夫》曾被评为经典文本的戏仿,书中一些情节与鲁迅的《祝福》极为相似,林市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也像祥林嫂的鹿港翻版。例如,林市在讲述梦境时的语气神态及听众的反应与祥林嫂讲述阿毛故事时的情景极为相似,阿罔官要林市去陈府王爷处虔诚跪拜的境遇与林市的惊恐反应也不得不让人想起柳妈劝祥林嫂捐门槛的经典桥段。同时,李昂在叙述情节中也从宗教写到中元普度写到鬼魂夜访,以当地生活民间风俗贯穿,写出了封建伦理思想对女性的蚕食压迫,在一定程度继承了五四小说的批判意识。与《祝福》不同的是,李昂在戏仿经典中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礼教的控诉和对女性苦难的描述上,她最终以林市杀夫的极端情节传达出女性不只是忍辱负重的悲剧弱者,她们会抗争,也会极力把自己从绝境中救赎出去,即便是在绝望的现实逼迫下,即便终逃不过命运悲剧,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女性的终将觉醒和男权社会的分崩离析,这与《祝福》中祥林嫂临终前的质疑相比是更加彻底、果决的反抗。
林市在绝望现实中一步步的女性意识觉醒,在小说的后半段逐渐清晰明朗起来。文中的一个明显标记就是林市身体的改变,从在叔父家的木刨似的身板,到初嫁后的水漾丰腴,直到最后又再次瘦削下去,身体的转变与思想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記录着林市的坎坷命运,也标志着她的精神崛起。
林市在初嫁时得到了从前没有过的食物保障,这对于在叔父家从没吃饱过的她来讲是巨大的幸福、惊喜。所以,她身体逐渐丰腴起来,认为有吃有睡便是福气,以陈江水为全部依靠,希望努力过生活,但终是抵不过周围的闲言碎语和道德规训。林市曾经尝试着适应这种规训来创造自己,融入到“正常的”妇人集体中,当她满心欢喜去找阿罔官裁衣,却听见了一众妇人对自己和阿母的恶意耻笑,这让她感受到彻骨的现实屈辱,并激起内心的尊严和反抗的决心。其中包括她回家怯怯却坚决地劝陈江水不要赌博免得遭人闲话,并且天真地表示愿与他同甘共苦,然而事实证明男性的权威不容许越界,舆论的控制也不在自己。
林市再次瘦弱下去的身体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精神蹂躏,也是身体内女性意识觉醒带来的精神压抑。她不愿再在早上同耻笑她的妇女们一起洗衣。同时,在面对陈江水的打骂性虐时,无论如何不肯再出声哀叫,她竭力咬牙忍受,甚至出手抵挡以表反抗,拒绝再次沦为他人的笑柄。其中表现最为彻底的便是林市有意识地想摆脱对陈江水的生活依赖,渴求经济独立。她用珍藏已久的铜钱买了一窝小鸭仔,希望母鸭长大能孵仔生蛋,男鸭能卖了换钱,所得收入用来换米维持生计。哪怕过程中还有所顾虑,却也一度满心的欢喜。但她没能看到小鸭长大,陈江水用遍地支离破碎的鸭尸将她最后的希望杀尽。此后,没了鸭仔的林市麻木冷清,对所有事情无知无觉,她的恍恍惚惚也终于激怒陈江水,不给林市提供任何吃食。当林市盯着白米饭,饿得一口口吞咽口水时,陈江水要求林市像从前一样哀叫“我听得有满意,赏你一碗饭吃”。而林市只是看着白米饭困难地摇摇头,尊严的觉醒让她不肯再像往常一样哀求,即便饥饿已无法忍受,哪怕沉默会换来一次次更甚的折磨。最后,在亲眼目睹猪灶的杀猪现场后,在陈江水的身心极端蹂躏下,林市在精神恍惚中以杀猪的方式将陈江水斩成肉块,然后沉沉地睡去,以毁灭的形式完成对自身苦难的救赎。
小说以林市的决绝杀夫为终局,控诉和反抗整个男权社会的冷酷无情,带给人深深的震撼和压抑。哪怕是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这场毁灭式的自我救赎也让人们看到被压迫女性最终的精神觉醒,预示着女性尊严的崛起。然而,这自我救赎背后也体现出社会的残忍压制、麻木冷清,走投无路的女性只有通过杀夫进行反抗时才会受到法律和道德的重视,所谓的道德法律却给反抗者以最严厉的惩罚,以杀一儆百的方式维护社会的男权秩序,这也让人们看到女性的毫无出路,无论如何冲撞结局终逃不开悲剧。
李昂将这场女性悲剧写得动魄惊心,向人们真实展现出封建传统女性在男权统治压迫下的生存困境、精神压抑以及最终的异化扭曲。而文中陈林市的悲剧不单指示女性,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腐朽哀鸣,让人们在反思社会中也反思人性。
(大连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