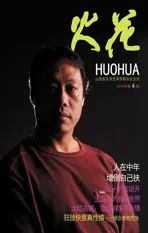由一封信说开
2018-11-21韩石山
韩石山
重庆兄:
前些日子收到新出的自传《装模作样》的样书,便想到该寄赠您一册。此书为二○一一年春天所写,放了差不多一年,二○一二年春夏间修订后,始送出版社。后来我就病了,未管此事。二○一三年元月出来了,因我在病中未能再校一遍,故书中错字时或有之。看时您会发现的。这是一本类似自传的作品。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手头正在写着的,还有一部真正的自传。因为全书的笔调诙谐幽默,多自轻自贱之语,我称之为侧传或丑传。所以寄老兄,是想让老兄了解一些我的身世。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一个出身不好的年轻人,在那个年代是怎么过来的。歧视,屈辱,甚至是凌辱,真能让你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那些年在布告上常看到一些年轻人(不全是出身不好者)[做出极端的事],我是能理解的。当然,我也有可庆幸的地方,那就是我侥幸上了大学。好了,不说这些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也都老了。还要说的是,您寄的笔,确实好,若方便,再寄我几支小楷笔来。后天就是春节,祝快乐。书,今天上午就寄出,印刷挂号。祝文祺!
韩石山 二○一三年二月八日
这是我给湖州徐重庆先生的一封信。
在湖州,徐重庆该是一位名士。
我跟重庆先生,没有见过面,交往不能说多,通信却不能说少。
这话听起来怪怪的,说穿了,一点也不怪。我爱写信,遇上个也爱写信的,书来信往,时日一久,自然就多了。年前去地下室,找一位朋友的信,将过去的信札,一捆一捆解开,不时能看到徐的信。他的钢笔字,很有特色,一眼就能认出。那时他还在病中,也就没有想到整理他的信,不料刚过了春节,就接到他堂弟的短信,说是重庆先生故去了。
以通信的惯例,他的信,该都在我这儿,我的信,该都在他那儿。
不是没有例外。我的电脑里,多少年了,老存着一封给他的信,两页,十行笺,毛笔写就。
纸信寄走了,这是照相。
当时为什么要照下存起来?
想起来了,是觉得这封信写得好,留个底子,说不定日后有用。我说的写得好,不是内容,而是字迹。后来果然用上了。过了一半年,成都一家叫《上层》的杂志,要登我的书法,给了几个页码,除了大幅的,还需要信札,便将这封信,还有另外两封信发过去登了。
现在要写文章了,看重的自然是信的内容。
一说到内容,就得赶紧做个说明。
退休后,闲了,我给朋友写信,若非太长,多用毛笔。
而毛笔写信,我有个怪癖,较之内容,更看重形式。八行笺,绝不会写成九行。该收尾的地方,稍紧一点可以,破坏了版面则不可以。再就是,发现错字,只要意思不相反,也就不改了。
这样,且让我将这封信誊录在下面。方括号里的,是此番补上的字。要不这句话,意思就太突兀了。
我跟重庆先生的交往,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具体的时间,真的想不起来了。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不会迟于2000年。
因为,我的《徐志摩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初版本,是2001年2月出的。而这个版本前面的插图上,有一幅是《海滩上种花》,画面上,一个小女孩正往地上插一枝小花,另一只手上提着一个小喷壶。远处是起伏的海面。这画儿,是凌叔华为徐志摩画的贺年片,一侧有文字:徐志摩拜年。画的说明,我标的是“徐志摩贺年片”。另有一括号,内中文字为“徐重庆提供”。
初版时间如上述,而交稿时间,我清楚记得是前一年八月。
那么,也就是说,在此前,我就与重庆先生有了联系。
而这个联系,想起来了,是起于这幅画。
就是的,是在董宁文编的《开卷》杂志,看到重庆写的一篇小文章,说上海的赵景深先生曾送给他一些纪念品,其中就有当年赵先生得之于徐志摩之手的这个贺年片。(刚才在网上查了,赵先生逝世于1985年,重庆与赵老先生的公子赵易林先生相交甚厚,或许是得之于易林先生所赠。)
极有可能是,从宁文先生那儿,得到重庆的地址,这样就得到了凌叔华这画的复印件。若是从杂志上剪下,我不会特意标明“徐重庆提供”。
秀才人情,得到他的馈赠,作为回报,我会寄了我的书去。
这样一来,就开始了我们十多年交往。
交往中,体会最深的,是他的古道热肠。
论年龄,他只比我大一岁。这是以属相说的,我属狗,他属鸡。将农历生日换算成公历,我就成了1947年1月的生人,比他小两岁了。
他送我的,不光是他的书,有些资料,他以为我应当看,也想法设法寄了来。比如,有一个时期,我对郁达夫很感兴趣,他便将黄萍荪写的,登在《香港文学》杂志上刊载的《风雨茅庐外纪》复印了寄我。
送我最多的,是湖州出版的各种大型文化图册。记得有沈尹的书法集、赵孟頫的书法集、沈行的楹联集、湖州的历史建筑集。
有一次,他送我一个红木的镇纸,既厚重,又好玩,我说这种东西,该是一对才好,他立马又寄了一个来。
前几年,他完成了一个为湖州增光的大事,就劝动赵萝蕤女士的堂弟,将赵紫宸、陈梦家收藏的几十件明清家具,悉数损给湖州,并为这一家人,建了个文化园区。不光是收藏了文物,也给湖州增添了一个景观。
这件事,大约让他很是高兴,便寄了几张刊有消息与图片的报纸给我,从一张图片上,我才看见了他的模样。国字形的大脸盘,坐在那儿,直可说是相貌堂堂。给我的感觉,真是南人北相啊。
正好那一段时间,一位朋友办个《立传》杂志,老要让我写稿。在给重庆的信中,我说,我也不去湖州了,你把你的事迹,详细写了信来,我据之写一篇传记,该不是难事。且说了南人北相的话。
重庆给我回信,说他只是报效桑梓,从未想过要青史留名,婉拒了。说到南人北相,他说了一句挺幽默的话,说那是坐着,要是站起来,就是武大郎了。
不高是真的,以我看到的相貌,他身上还是有种让人敬重的名士气的。
重庆送我最多的,是毛笔。就在这封信上说了之后,给我寄来一盒子小楷毛笔。他的信中说,有一支笔是特制的,秃了,可以将笔杆寄回厂里,厂里会换了笔尖寄给你。我觉得有点过了,没有试过。
我送重庆的,除了我的书,再就是写的字。
记得最后一次寄他字,是在去年秋天,他说湖州要办个什么展览,让好多人写咏湖州的诗,给我分了一道,因为记在本子上,现在还能找见。是元朝人戴表元写的,诗名就叫《湖州》,诗句是:
山从天目成群出,
水傍太湖分港流。
行遍江南清丽地,
人生只合住湖州。
我的字就那么回事,这一幅格外的精神,记得当时写了,心里还美滋滋的,想着,重庆先生见了,一定会认为我是使足了力气写的。
然而,这才几个月,又轮到写这样的文章了,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