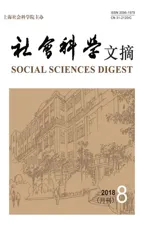转型期国家认同困境与宪法学的回应
2018-11-18
国家认同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的一种想象、归属和心理依附,集中体现了个体与共同体的内在关联。国家认同是国家的生命所在,没有牢固国家认同的国家,就像缺少感情基础的婚姻,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由于关涉国家存续的正当性基础,并与国家的安全、稳定与繁荣紧密相关,国家认同成为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性问题。
国家认同的内涵、结构与功能
国家认同是个体确认自己政治归属的心理活动,它指向特定疆域内国民在政治上的同质性、统一性和整体性。国家认同源于多方面因素的型塑,种族、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政治制度、疆域等因素均能刺激认同的产生。国家建立在各类认同资源所构筑的社会纽带上,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认同赖以存续的支柱性纽带并不一样。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是国家认同最为核心的三项内容。从宏观历史维度看,古代国家认同主要是依靠文化认同,近代国家认同最为倚重民族认同,而现代国家认同则越来越考验政治认同。这三个层面经常混合在一起,当前世界各国的国家认同均可视为这三项内容不同比重的混合物。
国家认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综合性概念,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均可转化为国家认同,但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并不等同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特指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主要表现为政治忠诚和政治服从。文化认同的对象是特定的历史传统和习俗规范,民族认同的对象是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民族,政治认同的对象则是特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国家认同以政治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均可作为国家认同的不同方面,国家往往是分享某种独特文化的民族,按照某种政治理念组建了特定的政治共同体。
在政治尚未开化的传统社会,民众普遍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直接输送政治忠诚来维系国家认同;在民众政治觉醒之后,随着政治理念的传播和政治体制的自主建立,政治认同得以建立并与民族认同共同支撑起国家认同;如果民众政治觉醒,发现无法认同国家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这就会造成有民族认同而无政治认同的矛盾状态,国家认同面临危机。可见,国家认同并不是一开始就只存在于政治生活领域,传统社会的政治并未从其他生活领域分化出来,但随着社会系统的内部分化,整体性的国家观念被分解为政治、文化、历史、法律等诸多面向,个体与国家的政治联结也日趋清晰化和单一化。尽管历史文化、民族意识等均是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资源,却很难未经加工直接提供政治忠诚。
转型期国家认同困境的生成
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启蒙打破了人的自在状态使人成为自为的主体,忠诚和服从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是经过人的理性检验之后的主体确认。国家认同成为一个问题可能肇因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意识的觉醒意味着人不再是国家任意支配的客体。个体和民族均从传统秩序中脱嵌而出,个体向国家争取自由,民族向国家争取自主。
由于封建帝国不能满足觉醒之后个体与民族的意志和利益,也就无法取得人们的认同,故而最终被现代民族国家取代。封建帝国正当性的瓦解堪称世界范围内根本性的国家认同危机,现代民族国家按照新的原则重新组织政治共同体,它重新划定了认同的主体、对象和形式,试图以此克服危机。这个新的原则就是民族主义。然而,民族主义带来的民族认同并不稳固。民族认同不稳固的原因并非像有些论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我们已进入后民族国家时代。只有那些“无国家的民族”才能真切地懂得民族国家的可贵,全球化让那些生活在富裕西方的世界主义者享有后民族主义的错觉。
民族认同作为现代国家的认同纽带的不稳固性,源于民族作为认同对象并不具有一成不变的特定本质。民族意识是想象的产物,能够与各种身份填充物结合。不同理念主导着民族主义,就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民族认同。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民族认同是综合性的产物,而不是某一种因素的必然结果,种族、宗教、历史、语言、文化、地理、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均可以作为界定民族的标准。
民族可以创造国家,国家也可以建构民族。“以‘民族’为国家认同的构成原则,其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无法清楚界定。”民族概念的含混易变,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尽管使用了民族主义的形式,但在民族主义的形式之下并不具有固定内容。有时候,用以界定民族的次级认同标准互生龃龉,更加深了民族认同的不确定性。社会转型催生了整体意义上的含混不清的民族意识,但也不断瓦解着民族意识中的具体内容。无论以何种民族主义为认同纽带,都只是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起点而非终点。随着现代社会理性化过程的不断深入,民族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向前行进,会不断褪去传统社会残留的胞衣。
国家认同成为当代普遍性问题的原因可以被概括为:支撑国家认同的诸要素,包括文化认同、历史认同、狭隘的民族认同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遭到削弱,并与国家的政治认同相分离,而国家没有及时有效地提出替代性的认同纽带来重塑国家认同。由于所有国家都处于持续转型之中,无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还是所谓的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发达国家,均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原生性认同力量的消散而新的认同纽带尚未定型的认同困境。如何在现代性背景下确立牢固的政治认同,成为所有转型国家不容回避的问题。
宪法认同:打造现代国家认同纽带
在自由主义的叙事模式中,国家是自由平等的个体以法律形式确立的政治组织。这虽非国家起源的真实情况,但从法学的视角来看,国家俨然是法律的拟制物。现代国家在建构过程中也都试图运用法律的整合功能,将民族国家打造为“法律共同体”。即便在国家建构完成之后,统一的法典对于国家整合仍旧意义重大。
宪法作为“组织政治共同体的规则”,它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国家整合的过程,甚至作为整合结果的宪法文本也可作为国家一体化的表征。宪法的整合能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宪法的规范作用;二是宪法的象征作用。
宪法之所以能作为现代国家的认同纽带,首先在于国家认同的可建构性。认同感并非天生,所有的认同都是在人与人的互相交往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产生的。现代社会的人则更多地借助于政治信条来塑造国家的政治认同,这些不同的政治信条与原始部落的图腾一样,都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认同的可建构性意味着国家可以能动性地选择认同的对象、方式,进而实现预期的认同效果。
其次,宪法作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拱顶石,能够表达国家的整体性特征。宪法赋予不同民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国民以统一的公民身份,以人民的名义将所有不同自然身份的国民统合起来,在法律意义上完成对国家内部同质性的塑造。除了在多元背景下建构统一的公民身份之外,宪法独特的历史叙事、简明的文本形式以及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分别确保了宪法的独特性、直观性和稳定性,这三者也是表达国家整体性特征的必要条件。
最后,宪法对公民身份和权利的确认与保障,确保了国家对其成员主体性的尊重。现代宪法以人民的同意作为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宣扬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迎合了主体意识觉醒后现代人的需要。任何一种认同形式若想塑造并维系公民的政治忠诚,必须尊重国民的主体地位,满足国民的利益和诉求。
面对转型期国家面临的认同困境,国内不少学者也试图引进西方的宪法爱国主义理论构筑中国国家认同的现代形式。不过,大家似乎并不愿意全盘接收任何一种版本的宪法爱国主义。诚然,与过于前卫的“薄的”宪法爱国主义相比,“厚的”宪法爱国主义无疑往后收缩了一大步,但对于正在朝着现代化方向迈进的转型国家而言,这一步跨得太大了。对试图打破既有的民族国家认同进而塑造出更高层次的政治认同的欧盟而言,宪法爱国主义或许是一种可行的理论方案,但对于试图维持既定疆域内政治认同的国家而言,需要做的并不是认同的替换,而是认同的整合与更新。尤其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和深厚民族情感的国家,我们需要一种“更厚”的宪法认同理论来应对转型时期的国家认同问题。
“薄的”宪法爱国主义以宪法中普适的价值原则为认同纽带,“厚的”宪法爱国主义要求抽象的价值原则与特定国家的历史情境相结合。它们均将宪法抽象为一套价值原则,以之取代民族认同等原生性认同纽带。这意味着,一方面,被宪法爱国主义视为认同纽带的并非宪法的全部,而仅是其中某部分价值原则;另一方面,宪法爱国主义将这套价值原则与原生性认同对立起来,并要以前者取代后者。由于任何一个宪法文本总是包含着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原则,抽离出一套价值准则就有可能扼杀宪法中的其他价值目标。而对原生性认同的对抗态度,则会将宪法与宪法生长的土壤割裂开来,会造成宪法实质正当性与实践有效性的双重压力。
所谓“更厚”的宪法认同理论,就是进一步将宪法爱国主义从理想化的高空拉下,使其扎根于特定国家的文化土壤,同时扩充宪法认同纽带的内涵,将传统认同资源整合进宪法认同的体系之中。这是一种更保守同时也更可行的宪法认同理论,它对既有的宪法爱国主义的“加厚”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对宪法的理解上,“更厚”的宪法认同理论要求放弃对宪法的狭义理解,以一种整全性的视角重新理解宪法。宪法并不仅是对普遍性价值原则的表达与制度安排。普遍价值原则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必定有其特定的表达和实现方式。即便是以价值原则作为公民政治忠诚的对象,也应当从宪法所表达的特定政治共同体的价值诉求中去寻找,而不是预先将某种价值预设作为宪法的普遍价值原则。更何况,宪法往往是政治妥协的产物,本身就夹杂着多种不同的价值原则,这原本就是宪法整合能力的体现。“更厚”的宪法认同就是要找回这些被剔除的价值目标,将宪法的整个价值体系作为认同的对象。除了价值方面的扩容之外,整全性的宪法理解还要求我们去发现宪法的多重面孔。宪法除了对价值体系的确认与表达之外,其文本自身也是如同国旗、国徽一样的国家名片。换言之,宪法不仅在价值意义上统合国家,也在象征意义上直观地代表国家。以宪法构筑国家认同,除了价值认同之外,宪法的其他属性同样可以作为构建宪法认同的资源。
二是在对原生性认同因素的态度上,“更厚”的宪法认同理论要求放弃对原生性认同纽带的敌对态度,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对待其他认同资源。“宪法并非政治体内整合的唯一因素”,宪法对民族精神的表达、对历史文化的确认、对宗教信仰的保护等,意味着我们可以吸纳、转化并规范这些原生性认同资源,将各种有助于塑造国家认同的因素凝成一股更为强大的认同纽带,而不是以宪法认同取代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尤其在对民族主义的态度上,应当吸纳民族情感作为塑造认同的有益资源,宪法的价值认同和制度认同需要民族认同提供情感动因。
宪法塑造国家认同的基本方式
1.理想塑造认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共同政治理想。发挥政治理想的认同塑造功能,是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伟大政治理想,在现行宪法序言中被规范地表述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中国人民的共同政治理想,也是现行宪法中的根本法规范。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政治信条:一方面,在宪法知识的宣传教育中,突出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根本目标的重要性,借助现行宪法的历史叙事,塑造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突出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根本规范的统摄地位,并通过现行宪法的良好实施展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优越性,强化国家的政治认同。
2.利益塑造认同:以人权保障增进国家认同。政治理想代表的是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它总是在国家兴衰和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激发个体的爱国主义情怀。但危机并非常态,激情也难持久,理想的感召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非理性的激情和超理性的信念,只有在特定背景下才能爆发强大能量。在理性自利的观念看来,“个体认同某个群体,乃是因为他们的利益使然”。和平时期的公民沉醉于日常生活之中,往往仅仅是一个个专注于私人生活的消极公民,他们对个人切身利益的投入往往盖过了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注。利益作为认同的强烈动机,意味着任何集体认同的塑造必须建立在对其成员利益的保护之上。在现代社会,基本的个人利益由人权概念予以正当化。人权概念集合了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对人权的保护能够最大程度地惠及所有人的利益,因而成为取得普遍认同的关键。
3.程序塑造认同:民主过程的吸纳与整合。民主预设了平等的公民身份,给予公民表达并维护利益诉求的机会,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能够增进公民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认同。民主提供了一个可供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族群进行对话、协商并最终达成妥协的平台,因而能够在个体和共同体两个维度发挥认同的塑造功能。从个体维度观察,民主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必要手段。基本的个人利益通过法律的普遍化形式成为人权,而人权最终又必须依靠民主制度才能得到有效保护。一方面,人权的具体内容依靠民主制度得以确定。另一方面,唯有通过民主制度,才能保证每个人的利益得到公平对待。在共同体维度,民主的认同塑造功能体现在其有助于国家观念的形成方面。首先,民主过程是一个收集、筛选、提炼公共利益的政治过程。其次,民主制度提供的官员选任程序,有助于国民完成关于国家的政治想象。最后,从民主制度的整体效果而言,民主为国家制度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能够为国家认同提供理性原则的支撑。
4.象征塑造认同:宪法成为国家象征。国家象征是对国家的内在抽象和外在呈现,它以符号的形式将国家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使原本不“在场”的国家“在场”,拉近了个人与国家的距离。当下中国尚未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宪法的工具性意义未能充分展开,但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作为宪法实施制度,其所实施的对象正是作为国家象征的宪法。通过采用与宪法相关的节日、宣誓等仪式化实施方式,唤起人们对仪式所表达的意义体系的信仰。宪法日集体朗读宪法,公务人员就职时的宪法宣誓,这绝不是简单的形式主义做派。宪法成为国家象征以及其仪式化的实施,类似于卢梭所说的“利用神的权威来约束那些靠人的智慧不能感动的人”。每一个宪法日和每一次宪法宣誓,都是对国家尊严和宪法权威的直观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