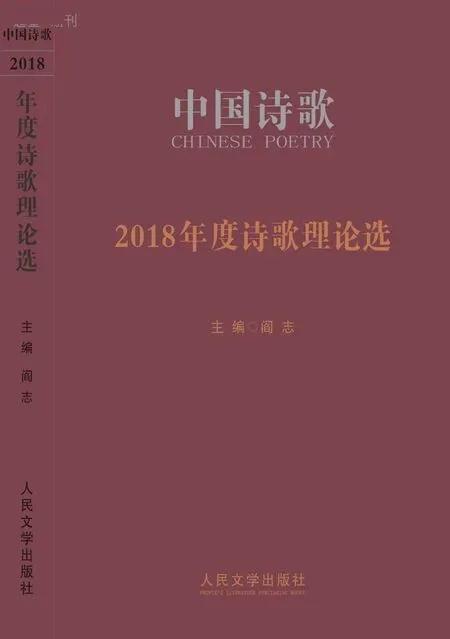中国新诗格律观念与实践的迁变
2018-11-15张桃洲
张桃洲
中国新诗是文化和诗学变革的产物, 相对于古典诗歌而言,新诗在诸多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中尤为显著的是语言与形式, 即以白话取代文言, 并取消了古典诗歌的根本元素——格律。 不过, 新诗诞生后, 自20 世纪20 年代起, 针对初期白话诗的自由散漫而提出的各种格律方案就没有停止过, 对于新诗是否需要格律、 能否建立格律等问题, 至今仍然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综观围绕新诗格律所展开的种种探索——无论理论探讨还是创作实践, 抑或某种学术化的研究——则不难发现, 人们在对格律的理解和界定上显示出两种倾向: 一种是将格律视为诗歌的外部音响特征, 着眼于对诗歌的音步、 韵脚、 平仄、 建行乃至句法的斟酌与探究, 从早期的陆志韦、 闻一多、 朱湘等人的部分实践直至当下的某些理论著述, 无不如此; 一种是试图依据格律的内在化趋向, 重视对诗歌的内在节奏与旋律的经营。 而从格律观念和建构的来源来说, 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一是受西方诗歌的影响较多, 一是强调格律的传统与本土特色。 格律的内、 外之别与中、 西分野, 显然缘于人们诗学意识的差异。
值得肯定的是, 有关新诗格律的探讨显示了新诗形式建设的富于理性的思考, 具有严密、 系统的理论传承性, 为新的诗学建设和创作实践积累了值得珍视的历史经验; 但另一方面, 由于新诗文体的特殊性和历史境遇的复杂性, 一些格律方案存在着较多认识上的偏误, 并且与创作实践明显脱节, 其间的得失亟待进行反思和探究。
1. 技术难题
一般认为, 闻一多《诗的格律》 一文的发表, 标志着关于新诗格律问题系统探讨的开始。 尽管在此之前, 周无、 李思纯、陆志韦等曾针对诗歌的音律、 节奏等话题进行过讨论, 但似乎只有在《诗的格律》 发表的1926 年, 在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 “诗镌” 上, 闻一多通过回应饶孟侃关于新诗音节的探讨,正式亮出了“格律” 的旗号, 以至于以新月诸子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新格律诗派”。 闻一多提出: “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 绘画的美(词藻), 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他还特别强调自己推崇的新诗格律并非来自传统的律诗(并指出了二者的三点不同), 而是更多地取法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
闻一多对格律的倡导带来了双重后果。 从负面的效应来说,就是模仿者亦步亦趋, 认为只要行句“均齐” 即可, 最终使格律在写作实践中陷入僵化, 导致“豆腐干” 诗盛行一时。 对此,徐志摩不得不做出声明与辩解:
(格律) 这原则却并不在外形上制定某式不是诗, 某式才是诗; 谁要是拘泥的在行数字句间求字句的整齐, 我说他是错了。行数的长短, 字句的整齐或不整齐的决定, 全得凭你体会到的音节的波动性; 这里先后主从的关系在初学的最应得认清楚, 否则就容易陷入一种新近已经流行的谬见, 就是误认字句的整齐(那是外形的) 是音节(那是内在的) 的担保。 实际上字句间尽你去剪裁个齐整, 诗的境界离你还是一样的远着……说也惭愧,已经发见了我们所标榜的“格律”的可怕的流弊!谁都会运用白话, 谁都会切豆腐似的切齐字句, 谁都能似是而非的安排音节——但是诗, 它连影儿都没有和你见面! (徐志摩: 《诗刊放假》, 《晨报副刊·诗镌》, 1926 年6 月10 日)
与“建筑的美” 引起的误解(片面追求诗句整齐) 相类似,闻一多主张的“音乐的美” 常常被误解为诗歌的外部音响(外在声音), 将表面的铿锵指认为新诗的节奏。 两种误解都是以表象代替了实质。 就此而言, 梁实秋的疑虑不无道理: “把诗写得很整齐……但是读时仍无相当的抑扬顿挫。” (梁实秋: 《新诗的格调及其他》, 《诗刊》, 1931 年1 月创刊号)
与此同时, 闻一多要新诗格律取法西方诗律的设想, 也遭遇了技术上的难题, 这是因为在汉语形态和西方语言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象征派诗人王独清就深感中国语言(汉语) 在处理“音” 方面的困难, 他列出一个关于诗的公式“ (情+力) + (音+色) =诗” 后解释说, “在以上的公式中最难运用的便是‘音’与‘色’, 特别是中国的语言文字, 特别是中国这种单音的语言与构造不细密的文字。” (王独清: 《再谈诗——寄木天、 伯奇》,《创造月刊》, 1926 年3 月第1 卷) 应该说, 中国语言文字本身在音韵的营构上是有其优势的(比如文言之于古典诗歌), 问题可能在于新诗的格律能否以外国诗律为依据进行建构。 对此, 另一位“新月派” 同人叶公超持不赞成的态度, 他认为“西洋的格律绝不是我们的‘传统的拍子’ ”, “论新诗我们最好能不用西洋名词则不用”, 特别是, “我们语言中就缺少铿锵脆亮的重音和高音, 因此我们也就不能有希腊式的或英德式的音步, 假使有人一定要勉强摹仿的话, 也一定只是费力不讨好的。” (叶公超: 《论新诗》, 《文学杂志》, 1937 年第1 期) 这就从语言差异的角度, 指明了新诗格律之借鉴西方诗律的难处甚至不可能, 毕竟汉语诗的平仄并不对应于西方诗的轻重音和抑扬格。
这种技术难题同样出现在20 世纪50 年代几次关于新诗形式讨论所提出的方案中。 参与讨论的诗人、 理论家、 语言学家贡献了各自关于新诗格律的见解: 王力提出格律应该遵循“有客观标准” 和“具有高度的音乐的美” 两条原则, 认为“韵脚是格律诗的第一要素”, “第二要素是节奏” (王力: 《中国格律诗的传统和现代格律诗的问题》, 《文学评论》, 1959 年第3 期); 罗念生详细剖析了格律所包含的节奏、 顿和韵等要素的特点及相互关系(罗念生: 《诗的节奏》, 《文学评论》, 1959 年第3 期);周煦良指出, “对于一个写诗的人来说, 具备一种格律感是和画家具备一种色彩感或形象感是同等重要的事情” (周煦良: 《论民歌、 自由诗和格律诗》, 《文学评论》, 1959 年第3 期); 金戈提出可以建立两类新格律诗: “较严格的新格律诗” 和“较自由的新格律诗” (金戈: 《试谈现代格律诗问题》, 《文学评论》,1959 年第3 期); 金克木认为格律“大致是以平仄、 单复、 奇偶、 虚实来相间排节奏, 使几种矛盾的因素相反相成” (金克木: 《诗歌琐谈》, 《文学评论》, 1959 年第3 期); 林庚提出新诗格律的关键—— “建行”, 并对之进行了阐发: “中国诗歌根据自己语言文字的特点来建立诗行, 它既不依靠平仄轻重长短音, 也不受平仄轻重长短音的限制; 而是凭借于‘半逗律’。”(林庚: 《再谈新诗的建行问题》, 《文汇报》, 1959 年12 月27日) 这些看法有不少是回应1920—1930 年代关于新诗格律的探讨的, 比如林庚认为应以中国语言文字特点“建行”、 突破“平仄轻重长短音” 的制约, 便是呼应了叶公超的观点。 事实上,他早在1930 年代即开始尝试“半逗律” 和“九言诗”, 惜乎并未得到响应和延续, 这部分地缘于他自己也意识到的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在上述见解之外, 何其芳、 卞之琳关于“现代格律诗” 的阐述格外值得注意。 在《关于现代格律诗》 这篇长文中, 何其芳在充分肯定自由诗“非常富于创造性” 的前提下, 表述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必要性, 并着重就“顿” 和“押韵” 两方面讨论现代格律诗的依据: “现代格律诗在格律上只有这样一点要求: 按照现代的口语写得每行的顿数有规律, 每顿所占时间大致相等, 而且有规律地押韵。” (何其芳: 《关于现代格律诗》, 《中国青年》, 1954 年第10 期) 卞之琳则进一步凸显了“顿” 在现代格律诗中的位置, 将其实践表现细化为两种基本的调式, 即偏向于说话式的“诵调” 和偏向于歌唱式的“吟调” (卞之琳:《哼唱型节奏(吟调) 和说话型节奏(诵调) 》, 《作家通讯》,1954 年第9 期)。 他们的理论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 遗憾的是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支持(尤其在实践方面), 很快被淹没在时代喧嚣和历史烟尘中。 何其芳同叶公超一样, 留意到了现代汉语偏于口语的特性对新诗节奏(“顿” ) 之形成的影响, 却也因为不能摆脱对外在的“韵” 的依赖, 而难掩其过于形式化的不足。
纵览探讨新诗格律的数十年间, 李思纯、 陆志韦、 闻一多、徐志摩、 朱湘、 饶孟侃、 孙大雨、 叶公超、 卞之琳、 林庚、 何其芳、 朱光潜、 王力、 罗念生、 周煦良、 郑敏等诗人和理论家, 从理论、 技术层面所提出的包括“音组”、 “顿”、 “格调”、 “半逗律” 等在内的形式、 格律主张或方案, 为新诗探寻具有可行性的格律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正如当年何其芳批评“民歌体” 在体裁上有限, 句法与现代口语不符, “写起来容易感到别扭, 不自然, 对于表现今天的复杂的社会生活不能不有所束缚” (何其芳: 《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 问题》, 《处女地》, 1958 年7 月号) ——历史和实践证明, 探讨新诗格律倘若仅仅注重外部音响(外在的顿与韵)的话, 其缺陷是明显的。 实际上直至当前, 仍然有不少关于格律的讨论过分注重外部枝节, 导致新诗格律的确立之路趋于闭锁。
2. 语言困境
为何在对新诗格律的理解和构想上, 很多人会将重心放在声音的外在层次? 古典诗歌的音律传统及其形成的对诗歌的惯性认识(思维) 与期待, 固然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某些寄附于这一传统和认识的举动也会潜在地起作用, 比如由“吟” 转化而来的“诵”。 诗歌的表面音响之受到重视, 大概正是受到了朗诵的促动。 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一点: 阅读文字和朗诵文字其实是两种不一样的对待诗歌的方式, 二者产生的效果也迥乎不同。
在此过程中, 现代汉语本身的特性对新诗格律的基础性意义应得到充分考虑。 在一首诗里, 或许不是字数的多少、 句子的长短, 而是语词的组合方式, 也就是它的句法决定了它的声音构成。 新诗在句法上是偏于欧化的, 受西方语法的影响很深, 朗诵的时候较为拗口、 繁琐, 并不符合一般口语的习惯。 朱自清曾经准确地指出了汉语新诗之难以诵读的原因: “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 而是欧化的或现代化的语言。 因此朗读起来不容易顺口顺耳”; 除此以外, “新的词汇、 句式和隐喻, 以及不熟练的朗读的技术, 都可能是原因。” (朱自清: 《朗读与诗》, 《新诗杂话》, 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另一与此相关、 易于陷入的误区是: 由于注重诗歌的外部音响, 人们在关于新诗格律的探索中, 总是力图确立某种固定的格律模式, 这从现代汉语特性来说恐怕难以实现。 现代汉语作为诗歌语言的局限性十分明显, 废名就认为: “新诗的音乐性从新诗的本质来说是有限制的” (废名: 《论新诗及其他》,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他继而提出的“新诗是散文的文字, 诗的内容” 之论, 则从一个侧面点明了新诗的某些特性。 何其芳也提出: “五言七言首先是建立在基本上以一字为单位的文言的基础上。 今天的新诗创作语言文字基础却是基本以两个字以上的词为单位的口语, 用口语来写五言七言诗就必然比用文言来写还要限制大得多。” (何其芳: 《话说新诗》, 《文艺报》, 1950 年第4期) 现代汉语作为新诗语言带给新诗的“限制” 正是如此: 散文化的句式、 芜杂的语汇和日常化、 应用型的表达方式。 这些不仅制约了新诗格律的生成, 而且给新诗创作本身提出了挑战。
面对语言的“先天” 困境, 优秀的诗人总会从上述限制出发, 通过精心锤炼、 锻造, 探寻能够彰显现代汉语特性的诗歌形式及格律。 事实上, 新诗在草创阶段即已体现了这种努力, 如沈尹默的《月夜》 (1917 年)、 康白情的《和平的春里》 (1920年) 等。 《月夜》 被认为是新诗史上“第一首散文诗”, “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 (此为1919 年的《新诗年选》 中“愚庵” 所撰的“评语” ), 其实该诗的“妙处” 便在于现代汉语虚词的巧用: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全诗只有四行, 每行末尾有一个“着” 字, 这构成了此诗在外形上的突出特征。 这四个“着” 字的恣意铺排, 恰好成为引发诗意的源泉: 一方面, “着” 字放在每句的尾部, 在整体上起到一种很好的平衡作用; 同时, “着” 的降调音节显示某种坚韧和执着, 实现了与诗的主题相得益彰的效果。 类似的如《和平的春里》, 其句末虚词“了” 字的运用与《月夜》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当代诗人昌耀的诗歌, 其诗作的某些句子显得冗长, 如《冰河期》 里的一句—— “在白头的日子我看见岸边的水手削制桨叶了” ——共有19 字之多, 不过其中声音的起伏规律是可以进行的, 原因就在于诗句间形成了一种内在韵律组织。 确如研究者分析的: “为了凸现质感和力度, 他(指昌耀——引者) 的诗的语言是充分‘散文化’ 的。 他拒绝‘格律’ 等的‘润饰’, 注重的是内在的节奏。 常有意……采用奇崛的语汇、 句式, 并将现代汉语与文言词语、 句式相交错, 形成突兀、 冲撞、 紧张的效果。” (洪子诚、 刘登翰: 《中国当代新诗史》 (修订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这是现代汉语特性在诗歌中的创造性展示, 同时从另一角度表明, 对于新诗来说, 外在的声音确实不再重要了, 而应该使节奏、 音韵等要素“内在化”。
这种“内在化” 将对新诗格律的探索导向语言的更深层面。人们常常引用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一句名言“诗是翻译中失去的部分”, 来说明诗歌声音的重要性。 不过, 一些诠释者乐于将“失去的部分” 理解为外在的音韵或声音。 诚然, 一首西方诗歌被翻译成汉语诗歌, 亦即经过了一种语言间的转化之后, 原有的声音、 韵脚确实难以保留, 可是倘若细究下去会发现, 弗罗斯特的“失去的部分” 也许更符合俄国文论家巴赫金所推举的“语调”。 在巴赫金看来, 由于“生动的语调仿佛把话语引出了其语言界限之外”, 因此诗人们应“掌握词语并学会在其整个生涯中与自己的周围环境全方位的交往过程中赋予语词以语调” (巴赫金: 《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 《巴赫金全集》 第二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他所说的“语调” 是诗歌中的综合的喻意或韵味, 超越了一般意义的节奏、 音韵。 按照巴赫金的看法, 一个语调放在不同的语境里会生出不同的涵义, 因此语调既包含了诗人的情感和体验, 又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一种特别的上下文关系, 甚至它还包含了倾听。 “语调” 对一首诗的个性的展示十分重要, 它也许是风格意义上的, 但又似乎超出了风格的范围。
在很多人的阅读经历中, 大概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 一首诗从外形看可能是十分杂乱的, 但读过之后却会产生某种强烈的感觉, 这主要是隐藏在其中的语调发挥着作用。 正是语调, 把一首表面芜杂的诗作贯通起来而激活了其内部蕴藏的力量。 与之相反的情形是, 一些表面上很有节奏、 朗朗上口的诗作, 其内里实则空洞无物, 枯燥乏味。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提示人们, 对于诗歌的语调要仔细辨析—— “倾听”。
不过, 这“倾听” 却不是朗诵意义上的倾听, 而是用感知与心智之耳去聆听。 弗罗斯特本人尽管非常强调诗歌的声音, 但他心目中的声音是多层次的, 更多地建立在语调的基础上。 人们常常认为他是一个自然诗人, 然而正如诗人布罗茨基所指出, 弗罗斯特诗中的自然是“诗人令人可怖的自画像” (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 刘文飞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 这里“可怖” 的涵义不仅仅指弗氏诗歌的主题, 而且更指其诗的语调, 布罗茨基显然是从语调上“听” 出了弗罗斯特诗歌的“可怖” 的。 比如, 弗罗斯特很多写田园风光的诗作采用了一种轻快、 咏赞的调子, 但那些诗里更为深层的意蕴, 是一种非常悲观的对自然、 生命以及无形的恐惧, 渗透了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 人们往往忽略了他诗中那一层不易被觉察的语调, 一种深沉的悲音。
遗憾的是, 很多诗人虽然也懂得把自己的语调放进诗里, 却只将注意力停留在表层的字音的协调与顺畅上, 更为深层的语调未能建立起来。
3. 探求可能性
因此, 从现代汉语特性来说, 建立新诗格律的可能之途在于: 舍弃一种形式化的外在的音响, 代之以深入到声音的内在层面进行探究。 正如不少人意识到的, 新诗格律的问题不可能“一次性” 获得解决, 与其提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固定构想, 不如比较一下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变化, 并从实践出发分析一下格律建构的可能性。 从以上分析可知, 今后新诗或许是一种包含了语调的写作, 而不必预设某种固定的韵脚和音节。 或许那样的写作,才真正地回到了格律的本义:
格律是形成整齐的节奏、 从而发挥表现媒介(语言文字)底性能的方法或工具, 它应当使内容起更大更深的作用, 所以必须是整首诗底有机的功能或有组织的力量底源泉……格律在一首诗里的作用乃是使语言作有秩序的、 合乎时间规律的、 有组织的进行。 (孙大雨: 《诗歌底格律》, 《复旦学报》 (人文科学版),1956 年第2 期、 1957 年第1 期)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自由体诗占据了新诗创作的主流,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诗人体会到形式、 格律的重要性。 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格律的意义: “格律当然不是产生好诗的保证, 同样自由诗也不是; 但格律是一定程序上不可或缺的‘组织大纲’ ……正是格律探索使新诗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到: 任何文学样式均有其特征的规定性, 否定了其特征规定性也就是否定了此种文学样式本身; 新诗可以没有固定的形式, 但不能缺失形式意识。”(龙清涛: 《新诗格律探索的历史进程及其遗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 年第1 期) 其中, 宋琳、 王寅、 西渡、 朱朱等新一代诗人的诗歌观念和创作实践, 便显示了这种意识。
对于这些年轻诗人来说, 至关重要的是: 一方面, 他们受到戴望舒、 艾青、 穆旦、 昌耀等前辈诗人的启发, 领悟到新诗格律内在化的趋向; 另一方面, 他们从声音的复杂内蕴入手, 有意识地在其诗歌创作中调配多层语调。 例如西渡诗歌中对双重声音的设置: “一个人曾经歌唱∕现在他一声不响——” ( 《悟雨》 )、“在拐角处∕世界突然停下来碰了我一下∕然后, 继续加速, 把我呆呆地∕留在原处” ( 《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 ); 桑克诗歌中语词的变调处理: “在乡下, 空地, 或者森林的∕树杈上, 雪比矿泉水∕更清洁, 更有营养。 ∕它甚至不是白的, 而是∕湛蓝, 仿佛墨水瓶打翻∕在熔炉里锻炼过一样” ( 《雪的教育》 ); 以及朱朱诗歌中韵律与色调的调配:
雨中的男人, 有一圈细密的茸毛,
他们行走时像褐色的树, 那么稀疏。
整条街道像粗大的萨克斯管伸过。
有一道光线沿着起伏的屋顶铺展,
雨丝落向孩子和狗。
树叶和墙壁上的灯无声地点燃。
我走进平原上的小镇,
沿着楼梯, 走上房屋, 窗口放着一篮栗子。
我走到人的唇与萨克斯相触的门。
——朱朱《小镇的萨克斯》
这首仿佛一幅“印象派” 油画的诗作, 以单纯的布景和简洁的线条勾勒了小镇上宁静、 安详的景象与氛围; 它又宛若一支悠扬宛转的萨克斯曲, 诗中的情绪随着曲调的高低缓急而波动起伏。 萨克斯管是此诗的核心意象, 它对应着小镇的街道, 不仅诗中的各种人、 物围绕它而聚合在一起, 而且全诗的节奏也与它弯曲的形体保持了一致。 作者似乎有意克制自己的笔触, 小心翼翼地不让语言之流恣肆向前。 在雨丝等意象的映衬和变幻光线的照射下, 全诗的色调显得十分柔和; “铺展” 和“点燃”, “小镇”、 “唇” 和“门” 等词, 交织成了一种特别的韵律。 这些创作实践, 无疑拓展了新诗格律探索的路径, 体现了新诗格律从闭锁到敞开的趋势, 令人对新诗格律的可能性充满期待。
或许, 新诗永远无法获得像古典诗律那样“固定” 的格律,却始终应该保持现代意识烛照下的对形式的追求。
从开阔的视野来说, 新诗格律问题集结着传统(古典) 与现代、 本土与西方、 自由与规范等一系列相互纠缠的命题, 既有持续的历史和理论沿革, 又颇具创作实践的指导意义, 还关涉新诗的未来建构。 显然, 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澄清新诗发展中自由与格律相对峙引发的一些问题, 表明自由诗与格律诗这两条新诗主脉, 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可以互相参照、 彼此启发的。 从更深层面来说, 新诗格律折射出一种悠远的民族文化心理(这从近年来旧体诗词创作活跃即可看出), 它毕竟与深厚的古典诗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且一度被视为新诗重返文学中心、 重温古典辉煌的切实可靠的途径。 因此, 对于新诗格律问题的深入研究, 亦可被纳入当前的文化探讨与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