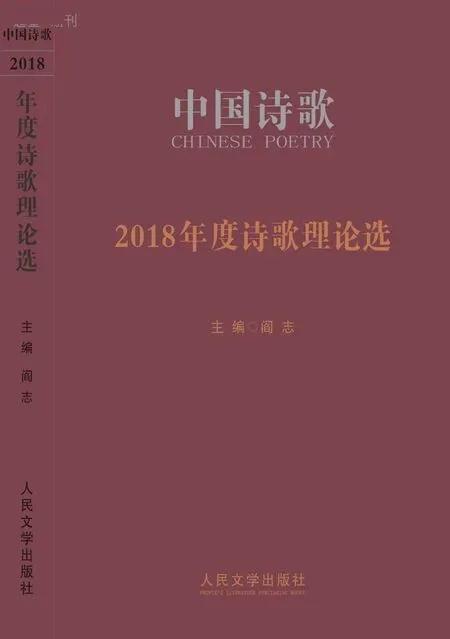当代中国诗歌地理根源探究
2018-11-15李志艳
李志艳
文艺批评的空间转型是当下学术发展的一大趋势, 它不仅能够有效纠正经由时间维度进行诗歌批评的不足, 并且“地缘文化关系、 文化地理差异对诗人和诗歌的影响越来越大, 而不同地域的诗人群落则日益清晰地意识到这种差异的合理性, 并且有效地加以利用” (张清华: 《当代诗歌中的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态——从文化地理视角的观察》, 《文艺研究》 2010 年第10期)。 在此语境之下去探讨诗歌的地理根源, 不仅是对当代诗歌进行空间批评的积极尝试, 更深层次上是在对当代诗歌艺术根性探索的基础上, 回应当代诗歌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 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与共和国的成长紧密关联, 它继承了新诗起源以来对语言的实验性运用, 又与全球现代、 后现代转型纠缠在一起, 而现代、 后现代的更迭与语言学研究连锁环扣。 这导致了当代诗歌创作、 批评, 乃至其他问题如文体学等都围绕着意识形态、 语言学的相关问题来展开, 忽视了诗歌因由发生学根源而引发的诗歌文体构成、 诗歌审美接受等基本问题的连带性思考。 这从学术界寥寥无几的“当代诗歌空间批评” 研究成果就可以得到证明。 两相对比, 对当代诗歌进行截源性研究, 或许能新见冰山一隅。
一、 当代诗歌的地理存在与活动行为属性
考查当代诗歌的地理根源主要有两个维度, 其一是诗人; 其二是诗歌文本的构成。 从两者的关系来说, 诗人的地理属性具有诗歌创作上的先在性, 以它为基础所形成的审美经验是诗歌创作的本质内容。 反过来说, 诗歌文本的固定性显现, 是即时性的记录、 承载了诗人对于地理占有的特殊状态。 邹建军等认为: “作品才是文学研究的根本对象, 也是我们一切文学研究的出发点。” (邹建军、 王金黄: 《文本决定论: 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双向阐发” 的反思》, 《学习与实践》 2017 年第11 期) 即使是文学的外围研究, 也“应该由里到外, 而不是由外到内” (葛晓音: 《读懂文本为一切学问之关键》, 《羊城晚报》 2012 年7 月8日)。 由此, 考查当代诗歌地理根源的两个维度又能辩证统一在一起, 即以诗歌文本为中心, 在逆向性考查诗人外在性地理状态之余, 思考诗人—地理之间互文性关系, 就能进一步探索人—地关系对诗歌创作形成的冲击影响。
在诗歌文本中, 地理根源的显现主要集中于诗歌的意象构成、 叙述的事件对象与语境、 话语特征等。 对于文学地理而言,在一般的空间区域上来认识, 徐国利认为: “要科学规范地界定区域史及其区域, 应当参照和借鉴地理学与区域学中有关区域界定的均性(同质性)、 系统性和独特性原则。” (徐国利: 《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 《学术月刊》 2007 年第3 期) 在特殊性的文学领域中来认识, 梅新林认为: “由于‘文学’ 与‘地理学’ 融合为文学地理学, 这就决定了其研究对象并非一般的地理空间, 而是具有特定内涵与外延的文学地理空间。 具体而言, 即是‘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 的内外互动与交融。” (梅新林: 《文学地理学: 基于“空间” 之维的理论建构》, 《浙江社会科学》 2015 年第3 期) 以此为依据, 可以将文学地理分为四个大的类型。 其一是有着较为明确的物理性、 自然地理状态与边界的地理, 主要包括行政区域地理、 文化区域地理、 民族区域地理。 这三种区域并不能截然分开, 民族区域往往就是文化区域的一种, 而文化区域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 一方面以行政区域为中心, 一方面又能对此进行超越和重组, 比如岭南文化、 巴蜀文化等。 之所以将其分开, 主要是因为区域地理的类型不同, 而导致了诗歌创作的风貌殊异。 如以行政区域来命名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的《中国先锋诗歌地图》 (北京卷) 中收录了唐欣的《祖国》: “一个山东人和一个陕西人/是我的祖父和祖母/而一个西安人和一个重庆人/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自己娶了一个天津人和/一个南京人所生的女儿/而我们俩的女儿 生于兰州/在北京读完中学/ /又去了成都 上大学 至于/以后 她的丈夫将来自/何方 孩子在哪儿出生/现在 我还一点都不知道。” 在硬笔的叙述中, 唐欣无疑道出了首都北京的人员交汇盛况, 并在诗歌结尾以回环的形式道出了这一问题的普遍性, 乃至背后对生命来往的茫然无措感。对于文化区域, 依据文化的属性、 类型以及层次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认识, 比如闻捷的《天山牧歌》 《河西走廊行》 等便是具有鲜明地域标识的文化区域诗作。 而对于如杨炼的《礼魂》 组诗等,则又是在中西文化视域中回看汉诗的创作方式, 是一种广义的国别属性文化区域。 对于民族区域, 代表诗人如吉狄马加、 南永前、 阿尔泰等, 从他们的诗作中“不难发现根源于其本民族的、本地域的历史记忆与集体无意识, 往往最能叩响民族内心的共鸣” (马文美、 涂鸿: 《神灵与生命的礼拜——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从原型到母题的言说》, 《当代文坛》 2012 年第4 期)。
其二是以肉身为中心的身体地理。 身体因为其自然属性、 社会地理文化的被建构属性以及自然客观的显现状态, 是文学地理的特殊类别之一。 身体写作在1990 年代突起风潮, 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其主要的理论支持, 张立群认为: “ ‘身体写作’ 虽然就其来源来看, 它是西方的术语, 但它一旦进入中国之后, 就势必要逐渐成为一种‘中国话语场’ 内的东西。” (吴思敬、 张立群: 《对话: 当代诗歌创作中的“身体写作” 》, 《南方文坛》2004 年第11 期) 身体写作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性别写作, 从创作的源动力来讲可称之为身体写作, 是以身体感知为核心、 非逻辑性的生命直觉写作, 朦胧诗所倡导的灵魂写作, 当下流行的“语感写作”, 如娜夜的《起风了》、 安琪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 杨黎的《A 之三》 等可归于此类; 从创作对象来讲可称之为写作身体, 身体成为创作的对象, 比如沈浩波的《点燃火焰的姑娘》、 尹丽川的《二月十四》、 李红旗的《早晨》 等可归为此类。
其三是以经济、 科技发展, 尤其是数字化网络发展而形成的乡土/城市地理, 自然/科技地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乡土与城市之间在血脉相连的同时, 却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发展, “当代诗歌的乡土经验写作成为时代、 民族、 地域文化相互沟通的精神印记, 通过乡土追溯精神的家园与历史的根性, 成为诗歌精神写作的重要探索。” (周俊锋: 《怀旧病与乌托邦: 当代诗歌的乡土经验写作及转变》, 《江汉学术》 2017 年第5 期) 乡土与城市、 自然与科技并不是对立静止的二元关系, 历史的积淀以及当代社会的加速度进程, 延续了二者相互审视、 相互建构的根本属性。 比如鲁西西的《曾经》 《这些看得见的》 等便是在回望乡土之余, 又对乡土的异变怀有深沉的叹惋。 而另一批诗人却在不断的批判中冷静思考城市的崛起与膨胀, 如杨克的《有关与无关》 《鸡为什么要过马路》 《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 等,均是在城乡互视性状态中, 探讨城乡的共存性发展与人性诗意化道路。 自然、 科技地理的区分主要针对的是网络诗歌, 网络是地理科技化产品, 以自然与科技的结构方式折射出人类活动能力的延伸、 活动方式的革新以及价值体系的重构。 网络诗歌是因为创作工具和媒介的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艺术生产方式与生产观念的时代性发展, 尤其以“bit” 为核心的数字化符号能够直接转化为“一种动态、 多维、 直接呈现的具象符号, 表现为屏幕中可触可感的视觉、 图像、 声音” (吕周聚: 《论网络诗歌的观念变革》,《山东社会科学》 2016 年第3 期), 并在人人触网的生产关系中重构了创作者与接受者的文学活动流程、 空间场域以及艺术理念。 在赵丽华、 诗阳、 鲁鸣等网络诗人的诗作中便可常见各种反常规的实验性创作, 包括创作对象的增容、 诗歌语体的肢解杂糅、 诗歌美学的凌乱锋利、 诗歌价值的无序颠覆等。
其四是杂含性地理或称之为全地理状态。 在当代社会语境下, 随着经济贸易关系的世界化趋势、 交通条件的方便快捷、 文化交流的频繁急切, 杂含性地理(全地理状态) 成为诗歌的一种写作常态。 检视整个中国诗歌当代史, 如此文本不胜枚举, 如黄翔的《冥兽》、 食指的《命运》、 北岛的《结局或开始》、 南野的《实在界的言说》 等。 这其中大致蕴含了两个方向, 其一是诗人有意弱化诗歌中地理的明确标识, 追求诗歌表达与接受的通约性与宽口径; 其二是诗歌创作对于普泛化社会生活公共问题的思考与探寻, 诗歌创作的全球视野与人类学意义决定了文学地理的越域、 杂含, 乃至世界化。
诗歌地理的多元化意味着诗歌创作的丰富性探索, 在本质上是诗人社会生活的在场性与实在性还原。 它首先形成的是诗人主体性, 这来自于诗人与地理之间的生命关系, 也是诗人面对特殊地理形态之中社会生活的独特反映, 诗人主体性不是非此即彼的个性或共性问题, 而是个性与共性交互融合的社会实践。 其次形成的诗歌创作审美经验, 作为诗歌创作的临界点, 它构建的是诗歌创作对象库, 从一开始也就显示了诗歌创作的本源属性, 以及诗人社会生活的审美化积累、 发展与成长。 再次它前定性地控约了一部分诗歌创作的性质, 及诗人对地理主体能动性的接受、 反映与再构, 意味着地理的诗歌艺术化的两个方面, 即诗人与地理的交互主体性建构、 诗歌创作的生命偶发性与必然性行为。 二者相互缠绕纠结、 内属转化, 构成诗歌创作活动的本质, 并由此外浮凸显, 循序推进, 寻求言说, 进而组构诗歌文本。
二、 当代诗歌文本的前世今生
地理进入诗歌, 在本质上是作家主体性社会活动行为的文本艺术再现, 是“缘事说” 的一个发展。 赵辉在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文体发生学时说: “中国的‘文’ 学作品, 也就是社会生活不同性质的行为过程中的‘文字单元’, 即文本; 每一文本的产生, 都有一个‘前因后果’ 的行为过程。 ‘前因’ 即驱使主体写作的事因行为过程, ‘后果’ 即文字言说过程。” (赵辉: 《中国文学发生研究》,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 第61 页) 而对于中国当代诗歌来说, 地理空间研究视域的介入与运用, 不仅能够有效纠正“研究者在观念上朝向时间因素、 忽略空间因素的理论偏废” (傅元峰: 《新诗地理学: 一种诗学启示》, 《文艺争鸣》2017 年第9 期), 更能够在传统诗学理论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当代诗歌文体本身。
首先, “前因” 的远指与近指: 地理之主体活动化与诗歌文本的原型形态。 弗莱认为原型是“在文学中极为经常地浮现的一种象征, 通常是一种意象, 足以被看成是人们的整体文学经验的一个因素” (诺思罗普·弗莱: 《批评的解剖》, 陈慧等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 第526 页)。 文学经验是在作家艺术化在场性社会活动中形成的, 它在直接陈述诗歌创作“前因” 的同时, 还意味着以地理为中心表征的社会文化场域对诗人主体建构, 这历时性先在地确定了诗歌的远指源起。 而近指源起则是诗人在共时性文化圈层中的即时性反应行为, 它反过来建构地理,促发诗歌文本诞生临界点。 洛夫就曾说过: “童年生活不但决定了我从事文学创作这条路, 而且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诗人要“有一份强烈的好奇心, 使他能从平庸烦琐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许多可惊可喜、 可悲可叹、 可歌可泣的事” (洛夫: 《洛夫谈诗: 有关诗美学暨人文哲思之访谈》,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 第2—7 页)。 诗人的在地性具体活动行为引发了诗歌创作。结合前文所论述的诗人主体性问题, 可以发现, 诗人主体性是一个动态性的持续发生性问题, 它是一个空间横断性判断, 标示具体性时间维度, 但并非一个稳定的连续性、 封闭性状态, 诗人的时刻在地性意味着诗人主体性的发生显现的特定的非必然性、 非连续性征象。 当然, 诗人主体变动性特征并非无迹可寻, 它承载、 显现于具体的社会活动之中。 正如荣格将艺术追溯至集体无意识活动、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艺术祖源于神话叙述一样, 都是活动对象和活动本身的统一体。 所以说地理所关联的是诗人和诗人活动行为的统一, 是诗歌创作的始源, 指向确定性、 普遍性和恒久性, 成为诗歌文本的前世与远祖。
其次, “后果” 今生, 地理之主体活动化与诗歌文本的构成。 对于当代诗歌文本的认识, 学术界目前有两条路径, 即或借鉴于西方理论的语言学路径, 或以传统诗学之意象、 意境(境界)、 韵律为依据的三要素诗学理论。 这其中明显的不足在于,西方语言学知识与中国当代诗学批评的“隔阂”, 传统诗学理论对当代诗歌批评存在诸多非适应性问题。 因而探索当代新诗文本理论就显得亟需紧迫。 既然诗歌文本是承载人—地关系的活动行为的言语行为, 是一种表达的固定化与自足性, 那么诗歌文本就可以分为两个基本部分。 一部分是常态性活动行为, 它模仿生活真实, 追求与之对应的言说方式是直陈性表达, 是一种散文体式在诗体中的直接体现。 如于坚的《尚义街六号》: “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老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 韩东的《来自大连的电话》: “一个来自大连的电话, 她也不是/我昔日的情人。” 余光中的《一枚铜币》: “曾经紧紧握一枚铜币, 在掌心/那是一家烧饼店的老头子找给我的。” 在诗歌中, 常态性活动行为显现的是诗歌与现实之间的近亲关系, 在文本中常常构成内部语境, 并成为诗歌诗性成分合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另一部分是异变性活动行为, 它模仿艺术真实, 组建行使艺术法则, 在非常规的话语表述中, 以“陌生化” 的方式构建创造性突破法则, 是一种直接的诗体形式。 在诗中, 活动行为的整个过程往往是通过句子或是诗节来完成的。对比起生活常态,活动行为的异变不仅将诗歌语言由生活语言转换成了艺术语言,并且在本质上构设了诗歌文体学的相关要素。 主要体现在: 第一, 在句子之中, 活动行为构成元素的反生活化、 反自然性, 并以错位的语言关系形成意象, 乃至与之相对应的修辞关系。 如余秀华的《我爱你》: “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 “告诉你……” 这个活动行为以动宾句式构成, 而在宾词结构中“提心吊胆的春天” 是一个错位的语言关系, 修辞手法是拟人。 与之关联的是“春天” 演变成了意象, 并且形成了语意中的“标出项”, 即“从语言表意来看, 能够清晰传达意义的是正项, 大部分人采用的表现方式偏向于清晰传达, 因而迂回表意的言说方式成为异项, 即被标出” (乔琦、 邓艮: 《从标出性看中国新诗的走向》, 《江苏社会科学》 2012 年第3 期)。 标出项的出现意味着对于常规生活语言表意的偏移, 也反过来显现了活动行为的非现实性与去客观化。 语言及语言结构的“陌生化” 延阻了接受顺势, 拉大了审美时空间距, 产生诗意。 第二, 活动行为某些环节的脱落缺失、 特定元素的强化突出、 过程环节断裂重置、 活动与活动之间承转关系的独特设置, 形成诗中“文气” 的流转状态、 情感的运动轨迹, 诗歌语意的空白、 跳跃性。 如唐不遇的《月亮》: “……黑暗中, 死亡嗡嗡叫着/叮了我们一口。 / /我们的皮肤隆起/一块红色的小墓碑。 / /在人世, 每增加一盏灯/都使黑暗更痛苦。”、 “死亡嗡嗡叫着” 是一种原动作行为主体缺省之后的重置, 之后又通过过程环节断裂的方式凸显出“一块红色的小墓碑” 在语句中表意的中心地位, 成为标出项。 最后又在活动行为叠加、 承转的情况之下, 形成叙述视角的转移, 并从一个特殊性活动行为递升为类别式活动行为的抒写, 形成诗意的衍射圈层。 在此之中, 情感浓度不断升华, 并和诗人对于活动行为思考方式的反常化相得益彰, 文气流动也就自然充沛。
再次, 当代诗歌的音乐性。 关于诗歌的音乐性问题, 学术界主要是从语言文字发音的类似性与出现的周期性入手。 本文要提出的是, 诗歌中活动行为的标出项要素的周期性出现、 类比性活动行为的复沓叠加形成节奏感, 实现了诗歌的音乐性。 如李亚伟的《硬汉们》: “……我们尤其相信自己就是最大的诗人/相信女朋友是被飞碟抓去的/而不是别的原因离开了我/相信原子弹掉在头上可能打起一个大包/让我们走吧, 伙计们!” 这是通过类同性活动行为的叠加形成节奏感。 梁小斌的《中国, 我的钥匙丢了》 亦是在多次的“丢钥匙”、 “找钥匙” 的活动行为中形成内在的节奏感。 顾城的《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虽然只有两句, 但是通过活动行为中的标出项“黑” 的二次出现, 以及和语义上的对立标出项“光明” 形成呼应, 进而形成诗歌的节奏感。 以活动行为为基础, 当代诗歌的节奏感形成有一些通约性特征, 节奏感的形成虽然是一个整体性概念, 但在诗歌中依然有层次感和结构性, 即单首诗单个节奏, 和单首诗多个节奏。 节奏的形成意味着活动行为的类集性组合, 它基本指向相对同一的语义话题。 节奏的形成在本质上是通过活动行为的描写来承载情感想象的运转轨迹, 它追求还原活动行为与促动情感想象的同一性书写, 此时还原在情感想象的建构下, 形成修辞, 不断逼近艺术真实。 活动行为形成突显的是音乐的运动属性, 以及舒展自如的创作空间, 它是活动行为及其情感运动本身就带来的, 是生命内在属性的天然袒露, 并在言说过程中自然呈现而已。
当然, 在诗歌文本中, 常态性活动行为与异变性活动行为存在着转换关系。 一般来讲, 通过诗歌文本的上下文、 文本内外语境及其关系, 常态性活动行为能够转化为异变性活动行为; 而在不同的诗歌中, 长期雷同性的异变性活动行为书写会转化为常态性活动行为,并失掉诗意表现的功能和属性。比如王小妮的《我感受到了阳光》, 诗歌一开始说“我从长长的走廊/走下去……” 本是一种常态性的活动行为描写, 但由于诗歌紧扣了活动行为特殊的地理位置“长长的走廊”, 结合社会文化语境中普遍性的人类生存衍变状态, 使得在“长长的” 成为标出项的同时, 促成了整个诗句的象征效果, 进而蜕变为异变性活动行为, 达到了情感动作化、 动作情感化的统一。 诗歌接下来如此写道: “——啊, 迎面是刺眼的窗子/两边是反光的墙壁/阳光, 我/我和阳光站在了一起。” 诗歌前两句是视觉行为的描写, 是一个生活化的常见性行为情景, 但在后两句的承应与加强中以类比联想的方式, 发生情景隐喻性异变, 即通过“寻找光明, 光明便和我们在一起”, 显示出一种乐观果敢、 昂扬奋进的人性精神。
从在地性的活动行为来说, 较之于其他文体, 诗歌具有鲜明的特征。 其一, 从宏观来说, 活动行为的缺省性, 使诗歌创作并不诉之于行为动作对情节构成的完整性, 它往往是行为动作的非完整性撷取, 履行动作行为与表意需求的契合性原则。 在此基础之上, 活动行为的断片截取、 类同性复沓叠加、 常态化与异变性都是常用的手段, 以此实现诗歌艺术修辞和美学价值。 其二, 从微观来说, 单数性活动行为的构成诸要素都可视为书写对象, 在行为动作及其修辞性成分上都存在着创作空间, 以此构成文字媒介意义语言呈现多种变形的前提和基础, 成为艺术语言反叛、 颠覆生活语言的生命力所在。
三、 对当代诗歌批评的反思
龚举善认为: “文学的‘本质’ 乃人为指认, 因而见仁见智, 具有多项生成的动态性质, 不同时代、 不同国度、 不同民族的文学以及不同主体对于文学功能不同层面、 不同角度、 不同先见的观照都会导致对于文学本质判断上的差异。” (龚举善: 《文学本质多向生成论》, 《河北学刊》 2014 年第1 期) 结合前文的论述, 从文学地理的视角出发, 提出诗歌的活动行为本质论就具有了事实性基础和学理依据。 首先, 从发生学来说, 诗歌源起于人—地实践性活动行为所形成的审美经验。 在此在的维度上是诗人的直接赋予; 在存在的维度上是人类历史积淀的支持。 其次,从创作论来说, 无论是诗歌还是文学艺术, 都是以创作主体为核心纽带的多种活动行为在融汇的基础上寻求语言的言说, 是异质活动的公约性沉淀与趋同性发展。 再次, 从文本论来说, 活动行为动作构成诗歌语意传达的层级单元。 它以单个的行为动作为核心, 在毗连性的最小修饰关系中形成诗意的初步传达, 并以此含蕴、 承载、 决定诗歌文字构成的语意分解方式和结构原理。 如田禾《喊故乡》: “……站在更高处喊/让那些流水、 庄稼、 炊烟以及爱情/都变作我永远的回声。” 整节诗以动作“喊” 为中心,通过状语“在更高处”, 宾语“流水”、 “庄家”、 “炊烟”、 “爱情”, 补语“都变作我的回声” 等构成一个趋向完整的事件行为, 与生活常态形成潜在比照而发生艺术修辞, 进而传达诗意。活动行为的复合性修辞, 乃至以此为基础的活动行为的群体集聚, 成为诗歌文本构成的二级层次, 如舒婷的《往事二三》:“一只打翻的酒盅/石路在月光下浮动/青草压倒的地方/遗落一枝映山红。” 便是通过几个关联性动作行为构成具有模糊梗概的事件情节, 并在情感的支配下酝酿成意境特征。 诗歌文本的二级层次是一个具有连带关系的向心性意义群落, 它能够相对独立、较为完整地构成诗歌语意板块, 并且又能在活动行为的同类聚合与异类勾连中完成整个诗歌语意版图的构成。 如舒婷《致橡树》的“如果我爱你……” 的重复出现就是活动行为的同类关系;如王东东《云》: “云, 揭开我头上的伤疤/让我丢弃我的血脉?去看那玉米长矛、 红色印第安人的国度/ /可是我怎样诉说? ——/是怎样的一朵云(轻飘飘的)? 撞伤了我的脑袋?” 就是一种活动行为由果寻因的追问式勾连关系。 当然, 在一首诗歌中, 上述两种关系能够交融一体, 也能独立成篇。 诗歌的终极层次是文本的整体观照, 它是活动行为的全部聚合形态, 但并不简单地呈现为结构发展的因果关系和统一完整性主题。 在当代诗歌的自由理念支持下, 呈现情感、 想象、 思想的运动状态往往是当代诗歌的深层追求, 因此, 诗歌创作是活动行为的言说过程, 从活动到活动也就成了对这种追求的直觉性实现方式, 凸显了当代诗歌的本质属性。
当代诗歌的活动行为本质论是本位于现象学的还原式思考,胡塞尔认为“经验科学是‘事实’ 科学” (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 倪梁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版, 第90页), 当代诗歌基源于诗人在人—地反应关系所生成的审美经验, 对此进行研究, 就是一种事实性的科学态度。 而诗歌是以个体性来完成其创造性的, 个体与本质的关系在于, “ ‘本质’ 首先标志着作为个体的何物而处于个体自身固有的存在之中的东西。” (埃德蒙德·胡塞尔: 《现象学的方法》, 倪梁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版, 第91 页) 诗歌创作是立足于审美经验形成之后的偶然性行为, 审美经验的诗歌文体学言说固有的存在只能是在与之对应的活动行为之中, 它以储存和显现的即时性、 独特性折射出理论规律上的本质性, 显现出征象与本体的统一。 而在地理维度上探讨活动行为, 一是对诗歌创作进行现场还原性思考, 二是对当代诗歌发生缘起的人类学追溯。 格罗塞认为: “生产事业真是所谓一切文化形式的命根; 它给予其他的文化因子以最深刻最不可抵抗的影响, 而它本身, 除了地理、 气候两条件的支配外, 却很少受其他文化因子的影响。” (格罗塞: 《艺术的起源》, 蔡慕晖译, 商务印书馆1998 年版, 第29 页) 诗歌是以地理为中心所形成的生产事业的派生物, 回归诗歌创生的地理状态, 是在回归人类主客体关系思考之余, 对人类与自然、 社会环境关系的始源性探究, 诗歌艺术作为文化生产事业能够体现人类本质结构关系发生及其演变过程。 三是地理及其活动行为, 不仅构建了诗歌的层级单元和意义单位, 更是直接构成传统诗学领域中的基本元素, 比如意象、 意境、 主题、 韵律、 价值诉求等。 以上述三个条件作为基础, 当代诗歌在地性的活动行为本质论, 才能接续中国传统、 对话西方。
对于中国传统而言, 中国古典文论以及赵辉的论著都已经认识到了事件活动与诗歌发生学的关系, 但并没有在诗歌文本内部形成较为有效的批评范式, 是以本文提出的当代诗歌活动行为本质论是在前提下的一个发展, 并且试图融合当代诗歌批评中的中国传统元素与语言学批评的研究成果。 对于西方而言,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哲学思想有一个重大的语言学转型, 包括形式主义批评、 新批评、 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 文化批评等诸多流派都是以文学艺术中的语言问题为核心来进行展开, 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在立足于新诗诞生于白话文的基础之上, 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西方语言学批评的影响。 如赵毅衡就提出: “符号的双轴关系, 是符号学中最有生命力的论点之一, 也是研究当代诗歌演变的重要方法。” 进而提出诗歌是“刺点文本”, “诗歌的定义本身就是反对定义, 诗歌的本质是反定义的。” (赵毅衡: 《刺点: 当代诗歌与符号双轴关系》,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2 年第10 期) 这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 诗歌是语言艺术, 语言与活动之间的关系如何? 第二, “诗歌的本质是反定义的” 本身就立足于诗歌是定义与反定义的矛盾体, 这在本质上是反二元论的二元论, 这其中是否能提出新的本质论对此进行兼容? 其实, 中国传统诗学理论大多具有结构与解构的矛盾一体性特征, 如诗歌的“缘情论” 和诗教化的辩证一体, 关于“道” 之“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 《道德经》 第一章) 中的辩证精神, 都是经典案例。 另一方面, 皮亚杰认为, 活动具有“先后两个相继的时期: 在全部言语或者全部表象性概念以前的感知运动时期以及由言语和表象性概念这些新特性所形成的活动的时期, 这些活动在这时发生了对动作的结果、 意图和机制的有意识的觉知的问题, 或者换句话说, 就是发生了从动作转变到概念化思维的问题” (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原理》, 王宪钿译, 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 第22 页)。 在这过程中, 语言是中介, 同时具有工具论和主体论的双重功能。 其中可以肯定的是, 活动行为对于语言来说, 是对语言的元史学研究, 具有本源性意义。 提出诗歌本质的活动行为论, 注重诗歌的发生、 显现本身, 是一种非逻辑的现象学追问, 是在解构本质之概念局限之后对本源类属性的事实性探索, 是在继承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精神之余对西方语言学批评的对话与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