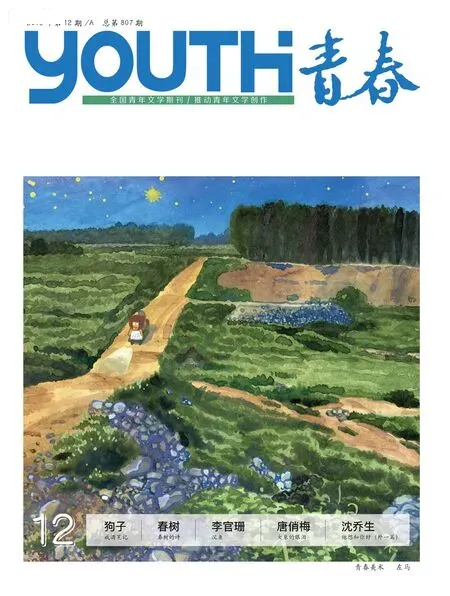猕猴的歌声
2018-11-15杨树直
口 杨树直
1
喜欢街头表演是吧?那你肯定看过那几场热闹非凡的马戏。还记得那两只花豹吗?多漂亮多凶猛的花豹啊,咬得铁笼子嘎嘎响,你一定吓得连连后退,那是我抓来的。你也许还见过另一家马戏团的那只野猪,也是我抓的。
知道我是谁了吧?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没关系。你可以叫我丁九,别问是不是真名,在马戏团,人人都叫我丁九,只有森林公安的通缉公告上才写我的本名。森林公安撵过我几次,像狗撵兔子。我跑得飞快,又善于躲藏,没撵着。能逮着花豹和野猪的猎人,怎么会让人撵着呢?
所以,我怎么翻越那道墙的,就不必问了吧。那么简单的事儿,不值一说。我倒是想跟你打听打听,那道墙怎么建起来的。怎么那么快,我出差半个月回来,金顶山就围起来了,路口还安了两扇大铁门。铁门外用塑钢夹芯板盖了一个亭子,几个穿黑色制服的精壮小伙手握齐眉棍,二十四小时值守在那里。
至于山上爆发瘟疫的传闻,是从你们当中传到我耳朵里的。你们总爱添油加醋,搞出好几个版本,我翻墙上山后,才发现每个版本都……好吧,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倒是可以跟你说说实情,不过,你得保密。
好,那就从那位酷爱珍禽的老鳏夫说起。老鳏夫喜好珍禽,不知道什么时候养起了斗鸡,好像有十来只。白天看斗鸡打架,夜里听斗鸡打鸣。一个晚上,老鳏夫准时准点醒来,没听到鸡叫,觉得奇怪,天亮了到鸡笼边一看,斗鸡们蔫不拉几,没了往日的战斗风采。老鳏夫想,这玩意儿怕是废了。废了就杀来吃,老鳏夫一连好几天炖着鸡肉,方圆百米内鸡肉飘香,搞得路人垂涎三尺,四五条流浪狗流连数日。都说斗鸡肉鲜美无比,看来人狗所见略同。
老鳏夫住村口,紧邻生活广场,是进村的必经之地。流浪狗聚在那里,狗屎熏天,村民和租客都有怨气。有村民气不过,提了条棒子去打狗,打得狗龇牙咧嘴,但是,请注意,这些狗既不汪汪吠叫也不狺狺哀鸣。打狗的人想,老鳏夫是不是给狗吃了什么药,狗都变哑巴了。于是叫老鳏夫出来问个究竟。
老鳏夫出来,听了原委,张口应答,口型如常,却和狗一样,发不出声音。打狗的人当时就傻眼了,怵在那里。老鳏夫看到路人惊惧的表情,才发现自己失声了。老鳏夫惊恐万状,扣嘴巴掐喉咙,拍脑袋捶胸口,就差没遍地打滚。
几天后,整个金顶山上的居民,都得了一样的病,集体失声。
一开始,大家见了面掏出手机互发短信问候,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山上信号没了,只好每人带个小夹板,夹板上夹着一沓信笺,有眉目传情不能完成的交流,就在信笺上写,给对方看。对方需要回复,也是在信笺上写。识字的人都这样交流,少数年老的村民不识字,见面大多挤眉弄眼比手画脚,用自创的哑语与人交流,对方也是一通胡乱比画,谁也不理解谁。
这都是我上山后才知道的。如果提前知道,我就不会傻兮兮的去逗那几条流浪狗和没被老鳏夫吃完的几只斗鸡了。不逗狗不逗鸡,我就不会挨揍。
正如你们所说,山上没有守卫。我翻过围墙后,甩开步子大胆向前,经过生活广场时,不小心踩到一个易拉罐,爆出尖锐的声响。响声引来一条流浪狗,它龇着牙冲我——吠叫,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吠叫。昏黄的路灯下,流浪狗站在离我大约五米远的位置,肌肉紧绷,作出即将投入战斗的样子,脖子向上一耸一耸,嘴巴一张一合,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样子相当滑稽。马戏团老板训斥我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架势。我希望我亲爱的老板像眼前的流浪狗一样,早日失声。
为了欣赏流浪狗的无声吠叫,我使劲跺脚。流浪狗更加愤怒,更卖力地耸动脖子,嘴巴张合的幅度越来越大,频率也越来越高。与流浪狗僵持几分钟,斗鸡拍打翅膀的声音传来,我知道拍打翅膀是鸡鸣的前奏,几步跑到老鳏夫的鸡笼前,想看看斗鸡如何无声地打鸣。
鸡鸣和狗吠极为相似,都是只有动作,没有声音。斗鸡们先是拍拍翅膀,酝酿情绪,然后双腿绷直,胸脯高挺,脖子向上扬,嘴巴同时张得大大的,像盛开的兰花花瓣。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这时候犯职业病。公鸡脖子一上扬,我就给它配音,“哦——哦——咯——”一遍又一遍。不知什么时候,我身后站了两个愤怒的男人。他们看着得意忘形的我,破口大骂,口型千变万化,唾沫横飞,路灯照耀下如毛毛细雨,然而,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哈哈哈……我忍不住大笑,前仰后合。我的嚣张气焰让年纪较大的那位气愤不过,他狠狠地踹了我一脚。笑声戛然而止,我一个趔趄扑在地上,乱七八糟的拳脚冰雹一样砸下来。
醒来时我躺在自己的床上。太阳已经老高,温暖的阳光从只有半截玻璃的窗户投射进来,在灰白的墙上形成上明下暗的金色光斑。我注意到光斑里有丝状的阴影在闪动。转过头去,窗前的老式书桌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稀饭。光斑里的丝状阴影,正是热气的影子。“小玉,你在吗?”我使出最大的力气冲那扇虚掩的房门喊道。门吱嘎一声推开,小玉走到我床前,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我问,“我发烧了吗?”小玉点点头,把稀饭端过来,要喂我。
“我自己来吧,又不是第一次挨揍。”
我支起身坐在床上,接过小玉手里的稀饭,舀一勺,吹凉了送进嘴里。真难吃。小玉的厨艺——这也算厨艺的话——堪称末流。粥糊了。
吃过稀饭,小玉给我拿了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药片。药是小玉配的。小玉在威清路一家小有规模的诊所兼职护理,时间长了,略懂一些医药知识。金顶山出事之前,她每天早上八点去诊所上班,下午六点才回来,换一身装扮,把自己打扮成妖艳性感的妓女,到金顶山下的黄金路站街。
服过药,小玉想跟我说些什么,双手胡乱比画。
我说,“你别比划了,我们都不会哑语,想说什么你写下来吧。”我指指窗前的桌子,“抽屉里有纸和笔。”小玉走到窗前,拉开抽屉,猫着腰翻找纸笔,然后刷刷刷写些什么。小玉的身材真好,腰细、屁股圆。我盯着小玉的后背,神情恍惚,一时间身上的疼痛轻了不少。
转过身来,小玉把纸条递给我:“你还没病,赶紧走吧,不然会被传染的。我们可能要死在山上了。”
“我不想走。”我看着纸条上弯弯扭扭的字,对小玉说,“我喜欢现在的金顶山。”我告诉小玉,金顶山已经被隔离了,我是偷偷翻铁门进来的,现在是携带病毒的人,根本就出不去。小玉很着急,双手又是一通比画。“你别比画了,晃得我头晕,休息去吧,我想睡一会儿。”小玉又走到书桌边上,拉开抽屉,找了一张纸条,写两下扔给我。
“你不要命了?”
“当然要啊。”对于生死,我并没有看透,但我不认为我们会死。我很喜欢金顶山上的这出默剧。我说,“人干嘛非得会说话?如果这世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会说话,会说话的那百分之一就是病人,他们才应该担心。”
小玉给我个失望的表情,转身走了。
吱嘎一声,房门关上了,房间里只剩下我、杂乱的什物和耀眼的阳光。我把纸条翻过来,那是我12月份的工资条,上写着:姓名丁九,职位配音演员,基本工资1950元,代缴代扣0元,津贴补贴0元,月实发工资1950元。
一直都是1950元,很低,不过没关系。其时已经立春,天气会越来越暖,衣服可以不买,暖风机可以不开,收入不变,支出越来越少,日子也会越过越好。要是能抓住那只传说中会唱歌的猕猴,老板还会给我升职加薪。
2
我到雷城谋生是去年9月。由于警察正满世界找我,不方便去正规公司求职,只好到一家争议不断的马戏团做配音演员——给动物配音。工作虽然轻松,但是工资低,租不起像样的房子,一个人,和一群妓女同住在这座城市东南角的金顶山上。冬天,山上寒风肆虐,自然比别处都冷。不光住的地方冷,由于买不起冬衣,身上衣衫单薄,除了马戏团办公室哪里都冷。只要不出太阳,从马戏团到黄金路,我一路上都在打冷颤。而去年冬天,我印象里就没出过几天太阳。因此,一到下班时间,我就开始疯狂地想小玉,想她面前熊熊燃烧的炭火。
小玉一直在黄金路站街。站,只是通常的说法,事实上,她和她的姐妹们自带蓝色的塑料凳,妖娆地坐在关着卷帘门的五金店前。老鸨是五十来岁的老女人,穿着粉红色的格子睡衣,很厚的那种,在长约三十米的妓女队伍边上来回走,张罗生意,见有男性经过,就凑过去,说,“帅哥,叫美女不?”据我观察,冬天嫖客不多,而且天越冷越少,最冷的时候一晚上只有三四个,而这里的妓女有二三十人,供需失衡,她们的生意很寒碜。小玉的生意就更惨了,她总是坐在整个队伍的最末端,还与倒数第二位保持不少于五米的距离,像个良家妇女。
我和小玉,以及妓女们,都有一个共同愿望:希望春天快点到来。不同的是,她们希望春天快点到来是想多接点客,我主要是怕冷。说实话,有时候我挺羡慕她们的,除了年轻、漂亮、比我有钱之外,她们还有火烤。每天出来站街,老鸨会给她们每人一盆炭火,红彤彤的小火苗像神灵的恩泽,照得她们白皙的脸蛋泛着红光。我就不一样了。每天下班后,冷得上牙磕打下牙,走慢了担心挨冻的时间更长,走快了感觉寒风更加凌厉,到黄金路路口才算得救。
一到路口,我就加快步伐,几乎是小跑到小玉跟前,迅速蹲下去,双手放在火盆上,手心手背翻来翻去取暖,小玉则俯下身来,用温暖的小手捂我的脸和耳朵。一起站街的妓女们都以为我是小玉男朋友,经常邀请我一起打牌。她们,包括年近五十,号称赌桌圣手的老鸨,都很佩服我的牌技。当然,她们更佩服我讲故事的本领。我常常编一些诸如动物成精、石头开花、外星人劫持地球人之类的荒唐故事,在麻将桌上兜售给她们,让她们分神,赢她们的钱。
小玉足够漂亮,之所以恩客极少,我认为是因为服务质量太差。我第一次找小玉的时候,她把我带到她的住处,一路上说说笑笑,就跟后来每一次上山一样。到了屋里,她突然变了,变得麻木,高傲,无趣。我告诉小玉,“你太不敬业了,我不喜欢你这样子。”
“我一直都这样,快点吧,说不定你会喜欢的。”小玉冷冷地说,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埋在报纸中缝里的脑袋抬都没抬一下。
我说:“要不我们算了吧,我刚来雷城,你能不能帮我租间房子?”
第二次发生在我跟小玉成为邻居后的第四个周末,那天下班往回走时候,她跟我抱怨嫖客越来越少,生意好久没开张了。我说,“要不我照顾下你的生意,报答你帮我租房子的大恩大德?”
这一次,小玉服务差的第一印象彻底被证实。她还是那样,应付差事一般,仰身靠在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上,手上摊开报纸,高傲地把自己摆在那里。我觉得奇怪,就问,“小玉,你接客时候喜欢看新闻?”小玉说是的。“你看的不是新闻,是旧闻。”报纸上的日期是2011年5月25日。小玉犟嘴,说就是喜欢看。我说,“那我以后天天给你买报纸,怎么样?”
“算了吧,你要愿意,我们搭伙做饭。”小玉说。
不光服务意识淡漠,在做妓女这件事上,小玉的懒惰也是出了名的。只要晚上十点前接不着客,小玉就抛下其他姐妹,自个儿先下班。有时候接着了,小玉又懒得去酒店或宾馆,就提议去她的住处。所以,我没事就守着小玉到晚上十点,等她下班了,一起上金顶山。
回到住处,我煮鸡蛋面或者甜酒汤圆,一起吃过后小玉进她房间睡觉,也就是与我一墙之隔的那间破屋子。严格来说,我跟小玉住同一套房。那本来是一室一厅的房子,房东非要当两个单间出租,小玉先租了卧室,我租客厅。小玉进卧室闩上门后,我换上睡衣坐到床上,用二手市场淘来的旧电脑看动画片《猫和老鼠》。如果没有嫖客同归,我会把动画片声音调到最小,一只耳麦松松垮垮地挂在耳朵上,另一只耳朵腾出来,聆听屋外的响动,希望听到传说中的猕猴的歌声。如有嫖客同归,我就两只耳朵都堵上,看着汤姆和杰瑞的夸张动作,傻子一样放声大笑。我必须检讨一下,小玉生意惨淡,可能多少与我有关。
通常十一点左右,嫖客准时离开。有时候,小玉想早点休息,就施展点不轻易拿出的好本领,三下两下让嫖客完事出门。嫖客走后,小玉起来,把自己再洗一遍,然后关门睡觉。没有嫖客的晚上——这样的晚上占了百分之九十九,小玉睡得更早,小玉说熬夜伤身体,“早睡早起身体健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小玉人单纯,对这些臭了街的真理深信不疑。
我从来都不听小玉的。不是我固执,而是情况不同。小玉每天早上七点必须起床,八点去威清路那家小有规模的诊所上班,给病人输液、打针或者配药,下午六点又得回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站街。我呢,鸡叫第一遍之前,全神贯注聆听山上的动静,鸡叫后睡觉,一直睡到十点。十一点左右洗漱完毕,然后去马戏团,向老板汇报夜里的工作情况,听老板唾沫横飞把我训斥一番。
“怎么可能没什么声音?你他妈是不是根本没注意听?人家可说了,那只猴子经常在广场附近出现。”老板拍打着桌子,“再给你两个月时间,没逮着那只猴子,你,给我滚蛋。”我从老板眼中,看到了他对我的不信任日日加深。
小玉常说,“我们都是苦命人,白天有白天的苦,晚上有晚上的苦。”我不觉得多苦,除了经常被老板训斥之外,对我来说,这份工作不但轻松有趣,还额外为金顶山的治安环境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住到金顶山上不到半年,已经连续三次成功阻止小混混火拼,五个偷盗空调外机的窃贼因为我一声“抓贼”被扭送到派出所。当然,我遭到的报复也不少。我在金顶山上挨揍的次数,已经占到这辈子挨揍总次数的三分之二。这里的好心大妈,包括老鸨,都曾向居委会建议,授予我平安卫士的称号,鼓励更多的人向我学习。但我坚决拒绝,一来怕更严重的报复,二来……我猎取花豹和野猪的那些英雄事迹,不足而外人道也。
尽管我工作热情很高,尽职尽责,三个多月过去了,还是一无所获。我开始怀疑,所谓每到凌晨两三点,会有猕猴从山顶上下来,到金竹巷附近的某栋楼上唱歌,究竟确有其事,还是我们老板道听途说?
不过,在我即将动摇的时候,也就是十二月底,我的新邻居给了我新的希望。他叫康健,是个和善有趣的男人,租住我房间东侧的那间空房子。关于那只会唱歌的猴子的一切,他似乎什么都知道,但是什么都不肯说。
我一度怀疑,这孙子也是来猎猴的。
3
我怀疑小玉搞错剂量了,药劲很大,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九点多。
房东太太来敲门,开门后,她把手里的夹板递给我,上面写着一大段对我表示感谢的话,说没想到金顶山藏得最深的两个窃贼——就是给我一顿狠揍的那两个——被我引出来了,已经被扔到山下。看完夹板上的文字,我冲房东太太笑笑,表示这没什么。房东太太则做了个让我跟她走的动作。我叫了小玉,没应,推开门,发现小玉没在屋里。我随手拿件皱巴巴的衬衣披在身上,捂着左前胸的肋骨,忍着剧烈疼痛,跟在房东太太身后一瘸一拐下楼。
转过生活广场,约五分钟后,我们追上了下山的大部队。由于是下坡路,他们一个个低着头、塌着肩,看起来比我还像伤员。我走到他们中间,想问我们这是要干嘛去。但我没问,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会说话。
沿盘山马路走到山脚下的大铁门前,前面的人自觉排成两列,我站左侧那一列的最末端。我们完全静下来后,大铁门后面有人开始喊话。“我们知道大家遭到了不同寻常的困扰,但是不用怕,根据最新研究成果,那只是一个特殊天体划过金顶山时,对大家的身体磁场造成了一些影响……”我歪出半个身子,看到大铁门外站了七八个穿了白色防化服,带着防毒面具的人,他们后面停着一辆长安轻卡。对我们喊话的大喇叭是从轻卡副驾的位置探出来的,喇叭后面什么也看不见,我怀疑那是录音,真人根本没来。“我们正在研制的药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大家再等等……这期间大家的生活物资持续免费供应。”
开始领取救济物资。门外戴防毒面具的人从卡车里搬出捆扎严实的白色箱子,抬到铁门边,两个人一起抛进来。我们两队人马左一个右一个依次走到门边领取。我是左边队伍的最后一位,最后一个领取物资,正好把这群男男女女筛一遍。老鳏夫、超市收银员、卖卤肉的、文印店老板……就是没看到康健。
回去时候,我强忍着疼痛,走得飞快。被我追上的人,纷纷伸出大拇指,夸赞我身体好,被打成那个样子还能健步如飞。最终,我第一个到达村口。喘着大气蹲在生活广场上,看扛着白色箱子的村民和租客一个个走上来。
我又把人群筛了一遍。康健确实不在。
午饭过后,老鸨来找小玉,约打麻将。小玉问我去不去。小玉比画打麻将的动作非常形象,我一下就看懂了。我艰难地翻身下床,对着老鸨和小玉,做个“哎哟”的口型,披上外套,穿好鞋,跟着小玉去了老鸨家。
麻将打到第四圈,我有点憋不住,叹了口气,发出“唉”的声音。然后,除小玉外,两双惊奇得眼睛镭射灯一样瞬间向我投来。片刻之后,老板回过神来,拿起小夹板,写了句话扔给我:“你能发出声音?”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他们知道我会说话后,会对我怎么样。
老鸨的冰冷目光重新回到我脸上。两双眼睛把我盯得更紧了。
“我……”一紧张,又一个声从喉咙里冒出来。“我……好吧,我跟你们说实话。前段时间我出差了,我不在山上。”我一把抓起小玉的胳膊,“小玉可以作证,”小玉点点头,“所以我……我没事……我是前天晚上翻墙进来的。”
老鸨在小夹板上写道:“翻墙进来?你就不怕被传染?”
“不怕……不,我怕,但是我想小玉。”
我从头叙述如何跟小玉相识,去年冬天如何蹭小玉火盆,小玉还用温暖的小手给我捂冻得通红的脸和耳朵,“这些你是知道的,”我跟老鸨说。老鸨点点头。“我一听说山上爆发瘟疫,就想着怎么上山陪小玉,可惜金顶山让围墙围起来了,半夜里我才翻墙进来,还让两个贼揍了一顿……”
解释完毕,我看到小玉眼里闪着泪光,老鸨也有些动容。我说,“别这样啊,我们继续,继续。”然后,没有谁再多看谁一眼,大家都把注意力都集中到麻将上,我却有点分心,一连输了好几把。要是再输两把,我就得借钱玩了。
为了回本,我决定拿出看家本领。我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从前有座山,山腰的西北面有一个城中村。那里住着几十户村民,和上百名租客,他们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外来谋生的民工,还有躲躲藏藏的逃犯、窃贼……有一天,一位馋嘴老头吃了感染瘟疫的斗鸡,自己也被感染了,还让整座山上的人、猫、狗都跟着遭殃,全都染上瘟疫,集体失声。白天,人们为三餐忙活,时不时的还能听到锅瓢碗盏碰撞的声音,到了晚上,山上一片阒寂,如果突然听到什么声音,那一定是那只据说会唱歌的猴子来村里了。”
“……大姐,别光听,摸牌啊。”
老鸨没有摸牌,倏地站起来,想起了什么似的,又突然坐下,似在沉思。
“大姐,你还打不打了?”
老鸨拿起夹板,写道:“你听到歌声了?”
“什么歌声?”
“猕猴的歌声。”老鸨写道。
“嗨,大姐,我瞎编的,你当真了?”
“你编不出来。”
气氛突然严肃起来。包括小玉在内,三双眼睛,又严肃地盯着我,我不得不据实以告,“猕猴的事是我们老板跟我说的,我移花接木,随口编了一下。”
老鸨不搭茬,歪在麻将桌上,右手托着下巴,脸向上扬,眼睛盯着天花板。我和小玉,还有另一位牌友,知道老鸨在想事情,没敢打扰,各捡一张牌拿在手里,细搓慢捻打发时间,等着老鸨说点什么。
“不打了。”老鸨写下三个字,拿小夹板朝我们一晃,站起来走了。
我拉着小玉,也走了。一路上,小玉魂不守舍。我问小玉,爆发瘟疫那几天,康健在没在山上,小玉摇头。我说摇头是不知道还是不在。小玉还是摇头。我说,“夹板都不带,懒死你算了。”小玉急了,拿起我的手,在掌心里写道:
“不在。”
“那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问。
小玉摇摇头。
回到出租屋,小玉问我,你跟老鸨说的都是真的?我说是真的。小玉说,“你说翻墙上山是为了陪我,是不是真的?”我说是真的。“没骗我?”没骗你。小玉眼泪夺眶而出,丢开小夹板,扑进我怀里抽泣起来。
跟小玉腻了一会儿,有人敲门。没等我走到门边,她就推门进来了。是一位我不确定见没见过的女人。她把小夹板递给我,上面写着,“到小广场开会,带个锅和一把大点的炒勺。”我猜可能要发什么特殊补给品,让小玉也带上。
生活广场上,人差不多已经到齐。老鸨指挥大家十个人站一组,然后给每一组发一张纸。纸上说,自金顶山爆发瘟疫以来,山上的人和动物都已失声,而那只曾经出现在金竹巷巷口,夜半三更哀嚎的猴子,没有失声。如果能抓到那只猴子,把它交给医院,没准能找到大家的病因,弄出治病的药来。
“猴子身手敏捷,何况我们村见过它的人没几个,单凭我们,要抓住那只猴子是不现实的,我们得求助有关部门……”
然后,老鸨让我们拿好锅和炒勺,一起下山。到了山下大铁门前,老鸨指挥大家站成四队,把锅倒扣过来,拿在左手上,右手把炒勺高高举起。准备就绪,老鸨纳粹军礼一样举起的右手,用力挥下去,我们高高举起的炒勺,随之一起挥下,狠狠地砸在铁锅上。举起,砸下,再举起,再砸下……咣当咣当的响声像某家规模不小的商店举行隆重庆典。
我们的阵势吓着了守卫,他们站到铁门前,向我们喊话。我们什么都听不见,就好像他们也失声了一样。老鸨向他们走过去,干瘪的胸部贴到粗大的方形钢管上,右手伸出门外,哗啦啦挥舞着一张纸片。哗啦啦是纸片上下翻飞的感觉,不是声音,我们敲击铁锅的声音把方圆数百米内的任何声音都淹没了。
大门外,十来米远的对街,一下子站了十来个人。他们无一不把领口往上拽,盖住口鼻,好奇的目光盯着我们。慢慢地,人越来越多,但是谁也不敢靠近。前排的人一旦被后面的向前推了一点点,马上转身钻到第二排后面,于是第二排变成第一排,这时候的第一排又马上转身往后钻……就这样无限循环钻来钻去。
打扮得像生化兵一样的那帮人到来的时候,质量差点的铁锅都已经被敲碎了。街对面,海浪一样涌上来退回去、退回去又涌上来的观众,十来分钟后被疏散,两位背着消音枪,手里拿着盾牌,腰上别着甩棍,整张脸罩在防毒面具里的人一脸警惕朝我们走来。到了铁门边,一人接过老鸨手里的纸片,然后转身往停在街对面的指挥车去了。沉重的装备让他们走路的样子像太空里的宇航员。
纸片是请愿书,内容很短,我们却等了两个多小时才得到回复。先是大喇叭传来嗡嗡嗡的电流声,然后是刺耳的啸叫,接着噗噗吹两下,喂,喂……我们立马打起十二分精神,支起耳朵,仿佛悔不当初的犯罪分子聆听宣判。
“金顶山居民朋友们,我谨代表……”我们听得非常认真,没放过任何一个字,无奈连篇累牍都是空话,如果没有最后一句,“请放心,我们一定会抓到那只猴子的。”我们百分百把所有铁锅和炒勺扔到他们头上。
4
晚上,老鳏夫来我住处,问小玉在不在,我在空气里写了个“在”。老鳏夫咧嘴一笑,然后离开,几分钟后,端来一锅辣子鸡,给我亮了夹板,“宰了一只,又吃不死,一起吧。”我敲开小玉的房门,招呼小玉一起吃饭。
饭后,老鳏夫进了小玉的房间,还随手关了门。我知道他什么意思。说实话,我越来越觉得小玉是我的——女人,但我养不起她,我得支持她的生意。这让我很难受,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因为盗猎花豹和野猪,我一年前就已经被通缉,只能在马戏团工作,给动物配音。简单说,就是每次马戏表演的时候,我在幕后拿着话筒,给龇牙咧嘴的动物配上语言,让动物的机械表演产生拟人化的剧情。这一点本事所得到的报酬是1950元,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如果能抓到那只会唱歌的猕猴,我会向老板提加薪要求,要3000块,或者干脆把它高价卖给另一家马戏团,拿了钱带小玉退隐江湖,远走高飞。
不大一会儿,小玉房间里传出撕扯的声音,接着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在那个无声的世界里,那一声“啪”响彻云霄。我从床上弹起来,一脚踹开小玉的房门。老鳏夫立在墙角,左手捂着脸,右手不停地揩胸前的指甲划痕里渗出的血珠。小玉全身赤裸,坐在床沿上,无声抽泣,眼泪汩汩而下。
“怎么回事?”我顾不得暴露自己。
小玉弯腰捡起地上的报纸,递给我,我才发现报纸被撕烂了。
“不哭了小玉,我给你买新的。”然后,我冲老鳏夫吼道:“你撕的?”
鳏夫一把抓起他的衣服裤子,摔门而出。小玉示意我坐到床上,把那份撕坏的报纸拼起来,给我看。报纸是2011年5月25日发行的,对半摊开后,整个跨版是一则社会新闻,《名伶失势入青楼,神猴卖与马戏团》。
新闻有三张配图,一张是歌剧演出剧照,女演员众星捧月,站在舞台中央,脸上打了马赛克,一张扫黄现场的照片,光着身子的妓女和嫖客蹲在墙角,脑袋埋在膝盖上,最后一张是马戏团表演现场,一只灰白色的猕猴围在人群中,手里拿着无线话筒,嘴巴张得圆圆的。
“小玉!”我看小玉一眼,又看报纸一眼,“是它?!”
小玉点点头。
“小玉,跟我说说,猕猴怎么回事?”我已经忘了小玉不会说话。
小玉摇头。
“说说,”我抓着小玉的肩膀,近乎央求,“小玉。”
小玉拼命摇头,泪如泉涌。
“对了,你的夹板,夹板呢?”
我环视屋子一周,没看到,“放哪儿了?”我到梳妆台上翻找,没找到。我冲进自己房间,拿了圆珠笔和那沓没写过几页纸的信笺,又冲进小玉屋里,坐到床沿上,“给你。”小玉没接,越哭越伤心了。
我这才意识到,我太过于自我,太专注于自己的世界,完全没顾及到小玉感受。这时候,什么都不应该问。“对不起,小玉。”我把小玉揽进怀里,捋顺她凌乱的长发,轻轻拍着她一耸一耸的肩膀。
时间在流逝,月亮照进屋里,又一点点退出。小玉的抽泣的节奏早已缓下来,我胳膊酸痛的程度则严重了很多。“小玉,睡吧。”我试探着说。小玉没说话,小腿伸到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下面。我把被子摊开,给小玉盖上。
这时候,我隐隐约约听到了什么声音——
“小玉,听!”
小玉触电一般惊坐起来。
我丢下小玉,闪进我自己的屋子,迅速穿上轻便运动鞋,拉开门,冲进黑暗的走廊,蹬蹬蹬跑下楼。在外面,声音更清晰了。
My power over you,
Grows stronger yet.
And though you turn from me,
To glance behind.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is there,
Inside your mind.
歌声来自山顶的方向,我拿出捕猎花豹的速度,朝歌声飞奔过去。
半山腰上,远远地看见一个黑影站在路中间。黑影手臂舒展,像个十字架。我放缓脚步,慢慢靠近。越近黑影越高大,声音越熟悉——
“康健,是你。”
My power over you,
Grows stronger yet.
“康健,我是丁九。”我朝黑影喊道。
“是你啊,九哥。”黑影转过来,果然是康健。
跟我一样,康健也是翻墙进来的。康健翻墙办法堪称高明。天黑时候,康健穿上地摊买来的仿制迷彩装,头戴安全帽,手里提个灰浆桶,桶里放着一把砖刀,大大方方走到大门口岗亭前,对当班的守卫说,兄弟,能不能帮我借一架梯子,那边的围墙需要加固一下。守卫面有难色,康健说,领导让我来找你们的。说着,赶紧从兜里掏出香烟和打火机,给守卫点上。守卫抽两口,一个打着哈欠回值班室,一个醉酒一样,扶着齐眉棍慢慢瘫软在地上。
眼看周围没人,康健敏捷地爬上铁门,纵身一跃,轻盈地落在了墙内。
“比你厉害吧?”康健说。
“厉害。你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
“杀人。”
“杀人?”
“你猜猜我杀了谁?”
“杀了谁?”
“杀……”康健神秘一笑,“让他们告诉你吧。”
“他们?”我疑惑不解,“哪个他们?”
“那个他们。”康健指了指我身后。
我回头一看,城中村附近光柱攒动,有人向我们逼近。
“走,快。”一把拽上康健。却拽不动,康健说不想跑了,“跑了好几天了,就为了上山给圆圆唱支歌。”我没时间问圆圆是谁。我只知道,只有康健在,我才有可能逮着那只猕猴,卖个好价钱,带小玉远走高飞。
“走,康健!”
我几乎是拿出擒花豹的力气来,拖着康健往山上跑。我们气喘吁吁跑到山顶上,一回头,光柱已经追到我们刚才所在的位置。“走,下山!”我又拖着康健,朝金顶山荆棘丛生的一侧往山下跑。还好,下山路上康健没有上山时候那么沉,但是路况差——那根本就不是路,从山顶到山脚,我们基本上是压着荆棘滚下去的。我身上热辣辣的,不用说,肯定全是棘刺划出的口子。我的额头上,后背上,滚热的液体已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血。康健也一样衣裤湿透。
到了墙角,回头看,光柱没有追过来。我和康健背靠高墙坐下,喘口气。
气喘匀后,我指着靠墙的一棵树,说,“爬上去。”康健说,“你先。”我忍着巨痛,奋力往上爬,到与围墙同高的位置,借助斜逸的树枝,纵身外跳。
刚一落地,墙那边就传来康健的声音,“九哥,你走吧,我去找警察。”
“什么?追我们的是警察?”
“我去自首,放心,我不会提到你的。”康健喊道。
“康健,你不能坐牢,我还没逮着那只会唱歌的猕猴呢。”
“会唱歌的猕猴?哈哈哈哈……”康健用轻蔑的语气喊道,“除了圆圆,谁也不配得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