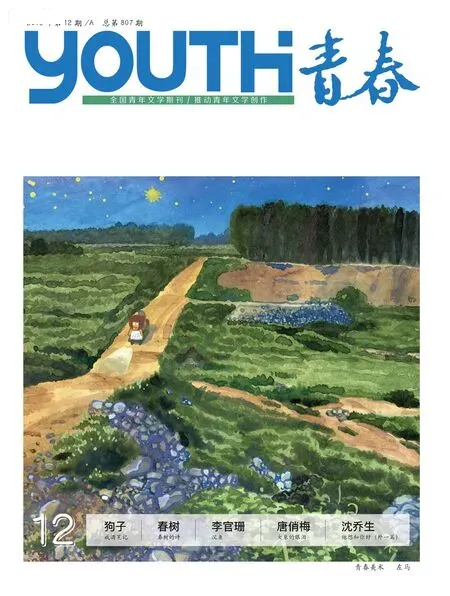母亲进城(外一篇)
2018-11-15钱爱慧
口 钱爱慧
当村里的田地都流转出去以后,我家的一亩三分地,仍牢牢攥在母亲手里。继父和妹妹都在南京,勤劳朴实了一辈子又病痛缠身的母亲依然守着老宅。大家都希望她能随继父一起进城,相互间好有个照应。不行不行不行,我不去,我不去。母亲热锅爆豆子般的“不”字,不用想,电话那端,她的头早已摇成了拨浪鼓。
我知道,母亲不愿进城的原因,是她在乎自己的形象,在意城里人看她时异样的目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需要守护,哪怕是逃避的方式。母亲又何尝不想跟亲人孩子住在一起,有个照应,享受天伦之乐。
又过段时间,妹妹突然告诉我,母亲去南京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怎么可能?真的,都来十多天了,这几天正吵着要我送她回去呢。我想象母亲着急回家的样子,惊喜的心一下沉入水底。我担心母亲太过焦虑,不利身体健康,让妹妹留她再住几天,实在不行再送回家吧。
那些日子,好想跟母亲唠唠家常,又怕自己不会说话,宽慰不了她,反惹得她更加念家,自是不妥,只好忍心作罢。背地里,三番五次从妹妹那里打听到:妈妈今天会用煤气做饭了;妈妈今天找门前遛弯的婆婆说话了,对了,还用手比划来着;今天妈妈一个人到大街上溜达了一会儿;哦,今天妈妈跟爸爸一起出摊了……得知母亲每天的点滴变化,我欣慰不已。母亲正用一股常人难以想象的劲头,一点一点克服她曾认为不可逾越的重重困难,努力改变着自己。两个月后,当母亲独自担着水果在街头大声叫卖时,她从一个无所事事的乡下老太婆,已然变成一个可以在城里自食其力的老太太了。
母亲已65岁,谈起初到城里的那段日子,她有些害羞,更多的则是自豪,摇摇头又点点头,说简直像坐牢,一天到晚,真恨不能生出翅膀,自己飞回来。我笑说,幸亏没有飞回来,你要是飞回来了,我哪里能知道偌大的南京城里那个卖水果老太太的故事呢。
母亲第一回独自出摊,非常紧张,手抖得握不住秤杆,人笨得算不出账。好心的顾客会帮她算好,又悉数将钱数给她,从来不错一分。怎么知道不会错呢?母亲等客人走后,闲下来,将一笔一笔的钱再慢慢细算。她说这不是不放心,是为了学算账,依账算账,好知道自己算得准不准。有段时间,母亲连续两次收到百元大钞的假币,心痛好多天,分毫未赚,白白流了几身汗。这让她恨死了那两个二流子样的小伙子,不过,母亲因此又学会一样本领——识别“真钱”与“假钱”。为了不让我也吃亏上当,母亲举着一张百元人民币对我进行现场教学,传授她用真金白银换来的“真经”,但我只记住其中一招,就是“摸摸领袖毛主席的领子”。
母亲卖东西总让顾客先尝一尝,觉得好吃你再买,不买也没关系。日子久了,很多人成了母亲的老主顾,有的绕路也要过来,都只为买母亲的水果。我心怀感激,这些好心人都在照顾你这个老太婆呢。母亲不无感慨,我心中有数,所以从不缺斤短两,不会好歹不分,好是好的价格,差是差的价钱。
“阿姨,端午节快到了,这是我给你买的粽子。”“阿姨,今天中秋节,你尝尝我买的月饼。”“阿姨,过年回家,我会想你的!”母亲说,听到那些城里的孩子喊我这个乡下老太婆叫阿姨,浑身都暖洋洋的,城里都是好人。城管也是好人吗?我狡黠地问母亲。哦,我怎么把这个冤家给忘了。母亲不好意思地笑,好像她忘记的不是整日提心吊胆的城管,而是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些冤家呀,每天神不知鬼不觉的,别人眼尖脚快,听见“城管来了”早跑得没影儿,我常常连窝儿还没来得及挪一下,他们就到了跟前。有一回,他们没收了我的秤盘和水果,我跛着腿一步不离跟着他们,半道,他们又将东西还我。我挑上担子就往马路中间跑,其中一个城管大步跑来拽住我,老太太,慢着点儿,车多小心!我白了他一眼说,你那样好心,干嘛还要没收我的东西?那人愣住,张嘴望着,没作一句声。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说,你看,你挑着担子满街晃悠,影响市容市貌,你歇下担子做买卖,占道经营,都是不对。没办法哦,我要生活嘛。没办法哦,这是城管的工作嘛,说实在的,他们对你已经很客气了。所以啊,我也不是故意为难他们,开青奥会的时候,我就在家歇了好多天呢。妈,别干了,太累,挑着担子累,挑着担子跑更累。你腿脚不利索,万一跌倒可怎么好?唉,身上的老毛病,站着痛坐着痛躺着也是痛,反正都是痛,我倒宁愿一边痛一边数钱儿呢……
说到钱的事,最近两年来,母亲的心气儿一点也不顺。自从妹妹在她的果篮里设下个二维码,母亲的腰包变得越来越瘦,眼睁睁看着日晒风吹换来的几个子儿,大半都被妹妹收进她的“宝葫芦”。母亲气得牙根直痒痒,她气妹妹,更恨支付宝。找妹妹要账,妹妹不耐烦,今天抠出100,十天半月后再揪出个300。母亲火冒三丈,说你给我挤牙膏呢,这么点钱能进货吗?妹妹塞上耳机,哼着调子上班去了。母亲只能干瞪眼,说恨不能追上去夺过她的手机,砸烂她的支付宝。我笑母亲,就算你能追上妹妹,再把她的支付宝砸成碎渣渣,你的银子也不会哗啦啦滚出来。
母亲那次独自回南京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丫头放心吧,我到家了。我心一动,不知何时起,母亲悄然已把南京当成自己的家了,显然我也多了一个“家”的去处。后来得知,母亲回南京的当天下午,居然与房东大吵一架,隔天愤然搬离那间继父住了20多年她住了5年的小黑屋,以每月多100元的价格重新租了间宽敞的房子。说到新房子,母亲得意不已。
那天,母亲正在洗衣晒被,房东过来,说你那些旧衣烂被有什么好洗好晒的,浪费水不说,整天搭在我家院子里,看见就让人别扭,乡巴佬!母亲一听,暴跳起来,冲向房东,乡巴佬怎么了?对,我是乡巴佬,怎么了?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一场乡下租客与房东之间的战火熊熊燃烧起来。母亲说她本想忍气吞声,但房东这样说话不是一次两次,自打她住进来,一直横挑鼻子竖挑眼。我自觉母亲虽然占了上风,又找到一处满意的房子,但还是心有余悸地说,妈呀,别跟人家吵,有话好好说嘛。出门在外,不比家里,遇事忍一忍,就都过去了。不知母亲听出了什么,突然话锋一转,矛头径直指向我:我说你啊,年纪轻轻,甘心一辈子呆在家里做家务,当保姆?你快出来,找点事情做做,孩子上他的学,你干你的活,两不耽误。
不知今晚,南京的天气怎么样,适合出摊吗,如果可以,母亲会在哪个街边练摊?草场门大街?新街口附近?繁华都市,璀璨霓虹的夜景中,我仿佛看见母亲正一瘸一拐忙着称重、找零……我不自觉拿出手机,点亮屏幕,又摁下锁屏键,将手机放回原处。
挑货郎
张老爹是我邻居,他是个挑窑货的货郎,走村串户叫卖陶制器皿。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陶有多悠久的历史,挑货郎便走了多远的路。
挑窑货是个苦力活,也是个累心活。坛坛罐罐都有份量,大一点的,一二十斤,大大小小装在一起,起肩一挑,两头平齐,百八十斤。出门做成生意,卖掉一只两只,人一下子就会从肩膀轻松到心里面去。当然,这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晦气的是,一天到晚一只也脱不出手,你还得稳稳把好肩上的担子,陪着太阳,不焦不躁、不急不徐地从日出走到日落。
父亲病着身子,央求张老爹带他去东乡进回一担窑货,信心满满地早出晚归连连吆喝三天,卖掉一个大菜坛子和两只小煨罐。父亲笑了,却又剧烈咳嗽起来,他的身体吃不消了。记得最后卖剩下的那只黄彩釉瓮,母亲锥心割肉般拿它做了米缸。家中常年缺吃少米,黄彩釉瓮独自立在房间角落里,我们的目光时常从它身上狠狠扫过,巴望着它能像神话里的坛子那样,一夜间装满了喷香的大米。我蹲下身,轻拍缸壁,却只听到“嗡嗡嗡”的喑哑回声。日子于我们身边悄悄流淌,流水一样绵长,柔软情深。
吃不下那份苦,父亲终是没有当成卖陶罐的挑货郎。并非力气大又吃得苦的人都能做这份活,你得有十二分耐心,外加十二分小心,不能心浮气躁,手慌脚忙。邻村有一位大叔,身强体壮,膀大腰圆。他和父亲一样,都是个“吃不了三顿饱”半途而废的主。听说他挑担窑货出门,沿村叫卖,半天没开张,日过晌午,他坐在树荫里咬牙切齿地咀嚼干粮,一边含糊不清地骂娘。吃饱骂够,憋闷未消反长,愁眉苦脸地担起挑子进村。一位好心的大娘跟他闲扯几句家常,不知是动了恻隐之心,还是真需要,豪爽地买下一只水缸。有了一桩生意,心情自然大不同。
轻了一只水缸的担子才搁上肩,他心里又涌起另一番滋味,惹得他的暴脾气一烧冲天。担子前轻后重,瓮口在屁股上一荡一磕,半天不得平衡,扁担被他扯前扯后,直扯得他心烦意乱。到了村西头,迎面走来一位荷锄的老伯,问他是不是要出村?他点点头。老伯告诉他,村西口的小路上有一道石栏,他这样担着挑子怕是不好过,最好还是原路返回,从东面出村。哼!老子这大半天不知跨过多少道石坎了,还怕你们村的这一道?他心里这样嘀咕,口中没好气地丢下一句“过不去再说。”径直往前走去。到了村口,他两眼瞪得溜圆,横在脚边的石栏既高且宽,真与平常大不一般。他一眼瞥见中间那块棱角突兀的大石头,心里有点发虚。上一秒才后悔没听那位老伯的话,下一秒他又觉得没什么,一道石栏而已,自己人高马大,腿长力足,即使肩上担有窑货,一定也能轻松而过。他踮起脚尖,一手把住肩后的担子,一手托着前头的扁担慢慢抬高,小心地让过身前的挑子,他迈出一条腿,立定,然后又尽力压低前头的扁担,等到挑子差不多触地时,他豪迈地跨过另一只脚,片刻未停,甩步便走。而他不知,虽然自己已经跨过石栏,身后的担子却仍前途未卜,“哗啦”一声,随现一堆碎片。他爆了句粗口,头也没回,走了几步,停下,折回身抡起扁担,对准一只幸免于难的酱钵,左一下右一下,砸到自己气喘吁吁,一屁股坐倒在地。
附近几个村子所有卖过窑货的人,只有张老爹一个人坚持下来。每次他天不亮从村东口出发,步行去很远的地方进货,黄昏时分赶到家。第二天一大早,他带上干粮,担上窑货,又从村南边出门,沿村叫卖:卖缸……卖坛……卖罐喽……七里八村,余音不绝于耳。张老爹很少有空手回来的时候。暮色里,我经常看见他背着一只缸或瓮,扁担另一头缀着一块石头晃来荡去,慢吞吞走在回村的路上。小时我很好奇老爹干嘛要挑块石头回家?原来为了平衡好肩上的担子,使自己走路平稳一些,保护好没卖出去的缸瓮。往自己的肩膀另加一块石头的重量,对张老爹甚至所有的挑货郎来说,是无可奈何,却也心甘情愿。日出而行,日落而归,他们担不离肩,走过一村又一村。
后来,乡村道路日益畅通,货物流通日益便捷,离村不远的杨家市街出现一家专门售卖陶制器品的商店,张老爹这才不得已放下肩上的那根扁担,彻底结束了挑货郎的身份。货郎的路,张老爹一走就是十多年。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张老爹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扛起一大家子的生活。
曲终人散,斗转星移,土制的坛坛罐罐逐渐散尽烟火味道、人世温度,悄悄淡出人们的视线。每一个村庄,如果你驻足凝望,定会看到一些坛坛罐罐的碎片,半掩在泥里土里。偶尔也会瞥见一口完好的缸或罐被主人倒扣在无人的角落,像一个不小心犯了错的孩子,默默低着头,任凭风吹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