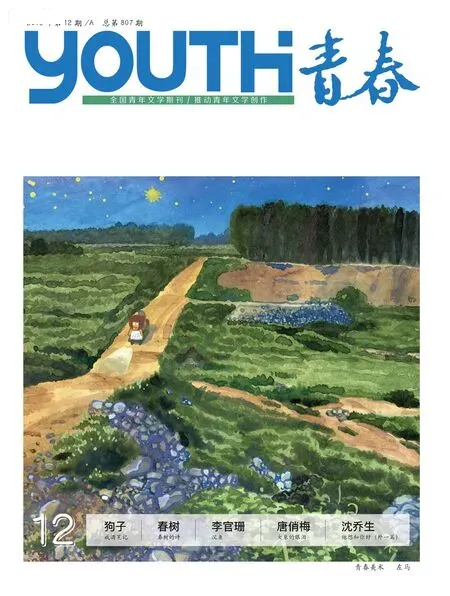沉默之花和它的凋零
——论成秀虎的诗
2018-11-15翟业军
口 翟业军
语言真是一个古怪的东西,它是我们的栖居,是我们最根本的可能性,却又是我们的牢笼。我们从来不是在说话,而是话语在说我们,话语用说我们的方式彻底掐死了我们说的能力,我们只能一再用说的方式确定自己的不可言说。语言的前一种状态,我称之为生成性语言,后一种状态,则是桎梏性的。生成性语言为如同地底岩浆一样灼烫却混沌的印象、感受勾画出轮廓,我们被深深搅动的内心终于显影,甚至有了最初的形式,找到了喷发的出口,于是,这个人就要开口,就要成为说的主体。但是,只要开口,就又时常会被桎梏性语言凝固,凝固成说着这个人的话而不是这个人急于要说的话的形状,这个人与他自己的话语以及他翻腾的内心便错失了,或者被风化。没有说着个体话语的编码,自己的话语便连一秒钟都不会存在,我们甚至听不到自己的话语风化成碎屑时的叹息。不过,在生成性语言和桎梏性语言之间,有一道狭窄、幽暗的地带,为我们挣脱出说的困境提供了可能。这就是那个将说未说的当口,话已经被塑形,却还没有因为那个多余的回头而化作盐柱,于是,它既含混又洗练,既超越又现实,既透亮如晶体,晶体的每一个侧面又各自折射着光华——这就像沉默开出来一朵花,一朵不可能的花非花。
我喜欢成秀虎的诗,就是因为他经常从将说未说的沉默之中开出一朵花非花。他的花分有花的理念,因为它来自他的心灵深处,不可能现实化,就像是不可听的天启之音;花分有花的形体,这个形体却是不可触摸的,就像沉默,就像幻想,但我们可以在阅读的当下径直为它绽出无数朵现实的花,这些花倒映着而非对应着那朵花非花。比如,《仙人洞》有这样一段:“洞内洞外布满石刻/以致难以寻找 一块干净的石头/摹刻模糊的旧事。”这段诗表面上只是在叙述难以找到一块干净的石头的无奈,如此简洁,就像是花非花的绝对轻盈。我们的阅读却可以把它移栽到此岸,蔓生出艳丽的一丛:他是想表达一种对于前文明、前语言、前修辞,还没有任何人刻下任一记刀痕的绝对的干净的怀想?是想说我们的文明太老了,层层叠叠的经典包裹着心灵,遮蔽了天空,文明人已经丧失了与自身素面相见的能力,于是旧事已然模糊?还是想说那么真切的属于自己的旧事在浩淼的文明面前瞬间模糊,欲辩已忘言的他对于文明产生了强烈的皈依,一种淹没自己,让自己彻底消融的皈依?每一种解释好像都有道理,却又无法回溯成那么单纯的诗句,就像武陵渔人不可能再一次进入桃花源——桃花源不就是一朵迷人的花非花?再如,《华阴老腔》这样开头:“几乎是破嗓,在破与不破之间/靠近灵魂边缘/向仙界和凡间喊话。”老腔不美。美是本能,更是传统的濡染,是意识形态的教化,我们被教训着什么是美,顺带自以为窥见了美的门径。老腔的歌者却要以歌声为剑,斩决地劈开美。只有劈开美的层层厚幕,歌者才能向理念,向理念的影子,向影子的影子喊话,那么通透的呼唤在三界之间山鸣谷应。此刻的歌者是通神的,他甚至就是神本身,响遏行云的歌唱正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现场。要注意的是,歌者手中之剑是一把分叉的、带倒刺的钝剑——再钝的剑也还是剑,就像再破的嗓也不会破成其他的什么东西,它还是嗓,它“在破与不破之间”。只有钝的剑能够穿透美的魅惑,从而抵达一个透亮的灵境,否则剑就有可能被美收编,成为饰物,成为美的一部分,就像屈大夫“带长铗之陆离兮”。不过,我解释得太多、太散、太理性了,以致于再也无法靠近老腔,因为老腔骤然从天地间升起,原子一样不能切割,一如成秀虎这几句诗的拒绝诠释的纯粹。
不过,就在沉默中刚刚绽出一朵花非花来的时候,成秀虎每每跨出了那道狭长地带。他有强烈的说的欲望,他要把因为朦胧所以令他无比痛苦并且必须要用一说再说的方式来厘清的感受条分缕析、层层递进地说出来。他没有想到的是,朦胧就是将说未说的微妙,就是不可分析的纯粹,这才是诗。他更没想到的是,跨出狭长地带的他所操持的已经不再是生成性的而是桎梏性的语言,此时,不是他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他,他说出来的大多是一些我们都知道、无需他再说一次的习语,于是,沉默之花凋零了。还是说《华阴老腔》。有这个劈面而来的开头,就够了,它绝对浑成,浑成到不能掺杂任一点水分,绝对剧烈,剧烈到不允许一丁点松懈和拖沓,但是,成秀虎还是娓娓地(娓娓太散文了,它正是浑成和剧烈的对立面)说起“宗族的合力”“贫瘠的生活”“平民的泪水”和“英雄的无奈”,把攒得那么足的一口气生生地泄掉了。其实,老腔所咏叹的无非就是“平民的泪水”“英雄的无奈”云云,但它那“在破与不破之间”的啸叫把这些内容抽象成了一首首无字歌,就像《铸剑》里黑衣人的“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无字歌栖息在那个狭长地带之中,它是歌,却没有字,就像是花非花。再如,《渡》开头的想象真是奇妙啊:“江河宽阔,甚至浩荡/相对于大地,只似一根丝弦蜿蜒/渡,恰如琴弓/来回拉出时缓时急的音符。”但,这把拉着复调的提琴很快就转向唯一的因而令人气闷的终点:“扬起风帆或者舟楫挥舞/总是抵达彼岸。”说一句也许不算题外的话:诗的灵魂就在于超越性的多义、含混,诗的世界中,阴影也许比实物妩媚,废墟可能比哥特式教堂蕴藏着更多的秘密,多到1绝对多于0。
不过,也有从桎梏性语言翻转而回将说未说的狭窄地带,从而把有限带向无限,把确定延展向未知的惊艳例子,就好像“一片一片又一片”的现实雪花最终“飞入芦花都不见”——雪花去了幻境,成了雪非雪?这里,我要说的是《镇江印象》。成秀虎行礼如仪一般一一罗列了水漫金山、甘露寺招亲、“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喟叹、昭明太子编《文选》等尽人皆知的镇江掌故,却在结尾处把这些壮怀激烈、侠骨柔情一股脑地打入日常生活:“做一个平头百姓,肴肉沾着香醋/一碗鳝丝锅盖面,筋道/又回味无穷。”千万不要以为成秀虎站到了几块肴肉、一碗鳝丝面所表征着的日常生活的一边,因为在水漫金山等传奇的映照之下,平头百姓的日子终究是小的,逼仄得令人发疯。但是,你不甘于这样的小,又能怎样,又有几个人能跃入传奇被后世传唱?于是,你最大的可能无非就是在肉和面之间作无穷的回味,无穷到好像你也有了你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回味竟是不甘的另一种表达,而这样的多义性被成秀虎死死地缄默着,正因为缄默,他在彼岸开出了另一朵花非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