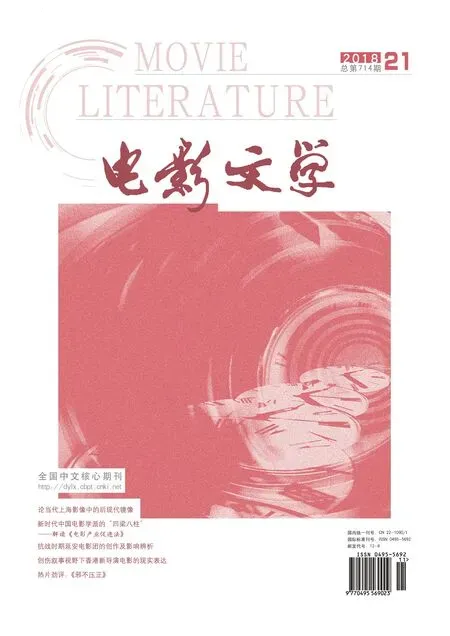大卫·芬奇电影的戏剧手法论
2018-11-14王银平
王银平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1150)
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电影学院派教育,以拍摄商业广告出道,却能够在踏入影坛后一次次贡献佳作,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另类电影风格,美国导演大卫·芬奇是好莱坞这个电影帝国中的一个独特存在。人们普遍意识到,大卫·芬奇是一名作者型的导演,但是与同样被称为作者型导演的昆汀·塔伦蒂诺、克里斯多弗·诺兰相比,人们又很难在“惊悚”之外,再找到属于大卫·芬奇的个人特色。而事实上,以戏剧手法来摄制电影,让电影呈现出一种舞台感,正是大卫·芬奇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电影对戏剧的出走与回归
电影与戏剧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舞台戏剧是电影艺术不可或缺的前身。这也是为何早年电影在诞生之初又名“影戏”的缘故。从电影内容而言,大量电影故事脱胎于戏剧剧本,而就创作者与接受者双方的意识而言,电影一度被认为是银幕对舞台表演的一种原封不动的再现。迄今为止,电影依然与戏剧有着诸多共同之处,如接受者对两种艺术的赏析都必须调动视听感官,剧场制造幻觉的诸元素,灯光、配乐、人物服装,各美术以及舞台调度等,实际在电影中也依然存在,并且同样服务于对观众幻觉的制造。
一般而言,在电影的创作中,电影与戏剧发生关系,通常有明暗两种形式。所谓“明”,即观众可以清晰地意识到戏剧的存在,这种电影对戏剧的接纳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即早期的舞台戏剧片,如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杂耍电影等;第二则是电影对戏剧名作的改编,如反复被搬上银幕,将原版故事融入各类时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第三则是将戏剧表演成分作为电影的一部分或叙事成分,如《雨中情》《爱乐之城》等电影中的歌舞,以及如《莎翁情史》《霸王别姬》等片中的戏中戏等,电影叙事中的人物命运与戏剧中的人物命运形成一种巧妙的映照。而“暗”式影剧关系,则是电影在拍摄中采用了戏剧手法,观众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虽然置身于电影院之中,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坐在剧院之中,欣赏一出舞台剧。而通常情况下,由于蒙太奇的存在,观众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
事实上,电影艺术已不可能如巴赞所提倡的抛弃蒙太奇,而纯粹使用定点镜头、长镜头完成叙事。蒙太奇在制造呼应、悬念、暗示和对比等艺术效果上,是电影表达的自身优势,它的存在也并不影响电影和现实之间建立关系。电影人也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将蒙太奇和戏剧手法结合起来,取长补短,这在早年的电影中就已出现。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基顿和卓别林在无声电影时期进行的实践,滑稽闹剧、杂耍歌舞剧等技巧被与故事情节熔铸为一体,基顿的绝技更是大放异彩,让观众忍俊不禁。观众得以在电影院中看到了更为集中,且富有故事性的杂耍表演。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基顿、卓别林将戏剧手段引入到银幕,本质上还是将电影当成一种先进的技术手段,这种技术手段能帮助其在舞台表演和艺术传播上有所突破。换言之,此时,电影还是为戏剧(舞台效果)服务的。而在大卫·芬奇的时代,一切则有所不同。电影不仅已经高度类型化甚至亚类型化,电影人对于镜头语言的探索也几乎达到极致,电影和戏剧的观众早已出现分流。此时崛起的大卫·芬奇属于以戏剧来为电影服务,在大批学院派导演和由广告或MV摄制转行电影业的导演们在尽可能放大电影特性时,大卫·芬奇却有意不进行这方面的炫技,甚至有过于克制之嫌,以让电影呈现出舞台剧式的观感。
二、以银幕为“舞台”
首先,大卫·芬奇有着对内景的执着偏爱。当下越来越多的导演倾向于拍摄大场面,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制造“奇观”,这是无可厚非的,导演的个人风格和能力也确实容易在这样的奇观之中显现出来,成为他人仿效或者解读的关键。而大卫·芬奇却极少拍摄大场面,他善于拍摄只有两个或三个人物,在一个室内空间中进行对话,从而完成信息的交代。以《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
,1999)为例,抽脂诊所的内景戏可以视为一幕戏,它恰好与之前的一幕内景戏,即杰克的教堂戏形成呼应。此处大量的信息依然全靠台词表达而出。杰克因为心灵空虚而到教会听其他人的倾诉,在参加了一个睾丸切除协会后,一个叫鲍勃的人在讲述完自己的故事以后拥抱了杰克。鲍勃曾经是一个健美先生,有过一个美好的家庭,但是现在他不仅破产离婚,两个孩子不肯接他的电话,最可悲的是因为八个月前切除睾丸,并接受了大量荷尔蒙治疗。鲍勃一边将杰克抱在自己的胸前一边哭诉:“他们又要给我做胸部抽脂手术了。”可以想象此时伪装病人的杰克心里受到了极大震撼。他每日忧郁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厌倦人生的真实原因,在教会杰克看到了比自己生活更惨的人,尤其是让他闻所未闻的男性胸部抽脂手术,因此他才会在后来精神分裂出泰勒以后,认为泰勒的肥皂脂肪来源是抽脂所得。杰克之所以会有着“泰勒”这一阳刚无比的人格想象,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男子气概并无信心,而与鲍勃等失去睾丸的男人的接触加重了他的恐惧。可以说,类似这样包含大量信息的内景戏在《搏击俱乐部》和其他大卫·芬奇电影中比比皆是,与之类似的还有如《异形3》(Alien
3,1992)、《战栗空间》(Panic
Room
,2002)等,可以说,大卫·芬奇的电影极为适合舞台式的移植。其次,大卫·芬奇有“锁住”导演之称,这形容的是大卫·芬奇对手持摄影(handheld)的厌恶,在大卫·芬奇的电影中,绝大多数的镜头都来自被稳稳置于脚架(或其他稳定器械)上的摄影机。《七宗罪》(Se
7en
,1995)堪称大卫·芬奇运用手持镜头最多的电影,也只使用了五个。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手持镜头大多集中运用于年轻警探米尔斯身上。尤其电影揭露最后一宗罪时的一组包括手持镜头在内的镜语设计是富含深意的。在电影的最后,米尔斯和沙摩塞两个警察在苦不堪言、极为压抑的工作后,终于得到了凶手杜·约翰的消息,于是开始了追捕。此时大卫·芬奇对米尔斯和沙摩塞的追摄是手持镜头,让观众高度紧张,在画面的剧烈晃动中,观众仿佛在跟随主人公一起跌跌撞撞地奔跑,能感受到主人公马上就能把凶手绳之以法,避免他继续杀人的兴奋心情。然而当镜头对准杜·约翰时,画面马上恢复稳定。这是因为杜·约翰是一切的设计者,包括此时急匆匆前来抓捕他的两个警察,也是他计划中的被操控者。虽然约翰跪在地上,手中无枪,但他胸有成竹:他杀死了米尔斯已经怀有身孕的爱妻翠西,犯下了“嫉妒”之罪,他会当面告诉米尔斯,甚至他已经把翠西的人头放在了一个盒子里带来,而米尔斯显然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会在一怒之下开枪打死约翰,这样一来,米尔斯也犯下“愤怒”原罪,而老警察沙摩塞则成为目睹米尔斯犯罪的证人。至此,约翰苦心孤诣设计的“七宗罪”才宣告落幕。包括此前两位警察的查案也完全是在跟着约翰故意给出的线索走,约翰为这一天已经计划了超过一年,最后让警方中计,心理势必是安稳而得意的。此处晃动镜头和固定镜头的对比,正是为了凸显警匪双方的对峙形势。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的画面都高度稳定,观众成为一个疏离的旁观者。众所周知,由于舞台的限制,戏剧艺术是无法制造手持镜头的,观众也就只能观看稳定的表演,而无法在视野的晃动中获得亲临现场的感受。这种旁观感正是大卫·芬奇想要达到的,他曾经表示,自己尽量地减低对摄影机的人为操控感,减低画面中的他人的参与感,以给观众制造一种“所见之事,注定发生”之感。第三,在剪辑上,大卫·芬奇尽量避免切进特写镜头。大卫·芬奇并非不拍摄特写镜头,但在成片中大卫·芬奇极少剪接进去。在一组镜头中,大卫·芬奇往往只会切入一两个特写,而越到后期,在《纸牌屋》等电视剧中,不难发现除了少数弗兰克·安德伍德的特写外,大卫·芬奇更是减少了特写镜头与观众见面的频率。原因在于,大卫·芬奇认为特写镜头对观众有一种提醒感,即电影主创以特写提醒观众某物或某人是重要的,这种提示是需要谨慎运用的。不难看出,和对手持镜头的态度一样,大卫·芬奇同样是想降低人为操控感,观众依然还是被设定在剧院中的观剧者位置之上,面对舞台的表演只能自己选择视线注意的方向,而难以就具体事物或人物面部的突然放大而得到特定的暗示。这样一来,大卫·芬奇也就达到了这样一种效果:他采用尽可能广的镜头呈现一个情况,画面提供的信息是多重的,这是典型的舞台幕布之前的表演方式。例如在《七宗罪》中警察局局长,沙摩塞和米尔斯的两次谈话,大卫·芬奇都极少给人物特写,在第二次谈话中,米尔斯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插入对话中的,但他依然出现在画面的中远景位置,观众能看到他对于局长和沙摩塞的态度。此时的场景仿佛不是经由剪辑处理后的成片,而是一幕正在上演的话剧,观众的观感成了“所见之事,正在发生”。
三、“舞台”背后
大卫·芬奇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我觉得人都是很变态的。我坚持这个观点。这就是我导演生涯的根基。”而只要对大卫·芬奇电影的题材稍作总结就不难发现,大卫·芬奇对于惊悚题材情有独钟,在把握这一题材时,大卫·芬奇能够更为自如。正如影史上的诸多惊悚大师,如罗曼·波兰斯基,弗朗西斯·科波拉等一样,电影成为大卫·芬奇为观众制造集体梦魇的一个法宝。也正是这种认为人皆有变态之处的看法,促使大卫·芬奇选择了上述戏剧手法。
在大卫·芬奇的电影世界中,人物离奇、恐怖的事件距离观众是遥远的,但是人性的种种丑陋之处其实又是离观众十分近的。就像在《七宗罪》中,沙摩塞对米尔斯表示,如果我们抓住了约翰,发现他是撒旦,那么反而这是好事,坏就坏在他不是撒旦而是一个普通人。大卫·芬奇要通过电影震撼观众的从来就不是各种暴力镜头,如《七宗罪》和《十二宫》中没有出现谋杀的具体过程等,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普通人能够变态、恶毒、自私到他人难以预料的地步。而人物所生活的环境之苦闷、压抑,也是观众其实每天生活在其中却很少意识到的,如《搏击俱乐部》中职业的毫无意义,《消失的爱人》中婚姻中的互相欺骗和伤害等,道德的微光是薄弱的,大卫·芬奇选择将这一切打造为“戏剧”并娓娓道来,强化观众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或猎奇者)身份,让观众与银幕中人若即若离,“场上搬演,场下指点”,从而思考自己注视对象的命运,以及自我的处境。无独有偶,只要对如拉斯·冯·提尔的《狗镇》等电影稍作留意,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戏剧手法。电影导演在要讲述一个阴暗的故事时,便以将电影舞台剧化的方式来操控观众的认知过程,让观众看到较为真实、多样的事物,人物较为常态化的动作,同时又用旁白来揭露人物心理,让观众自己生成画面的意义。
大卫·芬奇曾经表示:“大家知道你什么都有可能做得到。所以问题不在于‘你做什么’,而恰恰是‘你不做什么’!”在电影的造梦能力登峰造极,导演们能够几乎随心所欲地构建异类时空,或是能用各种镜头语言特点来为自己打造标签的今天,大卫·芬奇却保持了一种克制、冷静的态度,在拍摄中选择“做减法”,不以简单的视觉效果来刺激观众的眼球,让观众于不自觉间回归戏剧欣赏的状态,这是十分难得的。大卫·芬奇的这种对于舞台戏剧表现手法的套用,让观众尽可能地不注意到摄影机的存在,也是值得有意在惊悚题材上开拓的中国导演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