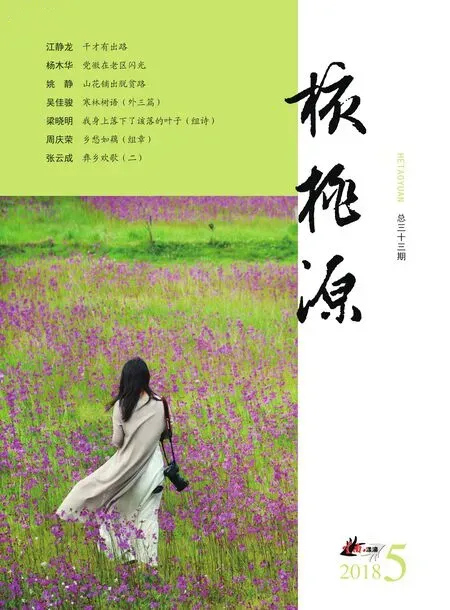我身上落下了该落的叶子(组诗)
2018-11-13梁晓明
梁晓明
优 势
我的优势是打开窗子
半夜我打开门让月亮进来
我和蚂蚁谈心,看小小苍蝇
用头撞击我的玻璃
我把天空隔离在外面
在世界地图上开除波浪
广场在一支笔下
在轰然鸣响的乐曲中
大幅度展开残酷的地界
我的身体和孤寂的菊花
在桌上保持清冷的思想
我繁衍一片田野
哺育棉花和孩子
点灯我撩开夜的衬衫
我仔细看清了黑暗的家乡
欢笑像落叶经不起冷风的一小点力量
漫 游
我身上落下了该落的叶子。
我手下长出了该长的语言 我歌唱
或者沉思 我漫游,
或者在梦境中将现实记述
我已经起飞 但飞翔得还不够
我低下头 我在褐色的泥土中将水份清洗
钟声不响,我的歌声不亮
正如一轮太阳使夜晚向往
我跟着一只鸟,我观察一群鹰
我在过去的传说中展开了翅膀
是告诉你的时候,我在说着故事
是繁盛的开端,我在倾听着寂静
好像是一种光 我在光中回想
在最大的风中我轻轻启动着双唇
没有字,没有让你领悟的通道
已经落下了叶子,但落得还不够
在应该生长的地方 我的飞翔在飞翔中静止。
书
书带着我离开木椅,门楣,书带着我飞
死亡与一件袈裟住在山上
我的回忆居住在影子倾斜的楼中
沿着黄昏衰老的人
向空中说出了姓名和一把灰
在诗中,我爱着一块布和蒙眼的走驴
我飞起或者跌落
总是在人类的碗筷之外
我低垂眼帘和时间并着肩在街上走
我将我的马献给光,将我珍藏的手
献给被黑夜禁锢的星星
给可怜的冬天一碗水
我在我细小的眼睛里坐下来,他里面有天空
我的灵魂是一棵树和一把土
我把自己疏忽在桌子上
灵魂带着我飞,他使我的脚离开大街
他带着早晨在每一个城头插秧
玻 璃
我把我的手掌放在玻璃的边刃上
我按下手掌
我把我的手掌顺着这条破边刃
深深往前推
刺骨锥心的疼痛, 我咬紧牙关
血,鲜红鲜红的血流下来
顺着破玻璃的边刃
我一直往前推我的手掌
我看着我的手掌在玻璃边刃上
缓缓不停地向前进
狠着心,我把我的手掌一推到底
手掌的肉分开了
白色的肉和白色的骨头
纯洁开始展开
各 人
你和我各人各拿各人的杯子
我们各人各喝各的茶
我们微笑相互
点头很高雅
我们很卫生
各人说各人的事情
各人数各人的手指
各人发表意见
各人带走意见
最后
我们各人各走各的路
在门口我们握手
各人看着各人的眼睛
下楼梯的时候
如果你先走
我向你挥手
说再来
如果我先走
你也挥手
说慢走
然后我们各人
各披各人的雨衣
如果下雨
我们各自逃走
大 雪
像心里的朋友一个个拉出来从空中落下
洁白、轻盈、柔软
各有风姿
令人心疼
飘飘斜斜的四处散落
有的丢在少年,有的忘在乡间
有的从指头上如烟缕散去
我跟船而去,在江上看雪
我以后的日子在江面上散开
正如雪,入水行走
悄无声息……
风 铃
我喜欢风铃
我喜欢风铃叮叮当当一片空荡的声音
我喜欢风铃左靠右晃屋檐下一种不稳定的身影
我喜欢风铃被斜阳照亮闲暇说话或干脆一言不发
我也喜欢暗中的风铃、门廊下紧张的风铃
宝塔上高挑寂寞
和孩子手中被拎着的风铃
路上的狗、沙漠上难看的骆驼颈项下倔强的风铃,
风沙越大,它说话越响
声音是它的命。
我喜欢风铃
我喜欢敲打宁静的风铃
坐在孤寂的家里,停下来和岁月相依相伴的风铃
应该听一点声音、应该有一挂风铃
应该有一些眼睛从风铃出发
或者与风铃结伴而行
无论我愿不愿意
无论我愿不愿意,天还是黑了下来,
它从门外黑进窗台,又从屋顶黑到了桌面,
它很快黑到了我的手指
我如果不开灯
我心里就会装满黑暗
我的心里已经黑暗,它挥着吞噬的小手
挤在眼睛边,它要走遍我的全身
它要在血液里扎根和发言
我要起身开灯,但我却丝纹不动
我看到黑暗降临大地
我不能幸免
遥远的星星自己发光
象一粒粒
自在的萤火虫
它越过时间,独自前行
直到与黑暗相敬如宾
想一想,觉得应该歌唱月亮
月亮翻山越海来到中国,它也去西方
它从小照着我的头顶,我长大
它依然照耀
它照耀广播分隔灯光
也照耀非洲和我的青瓦
在钢炮对峙两国相争的边境线
它依然优雅地
来往照耀
照耀谈判
握手后贴出来的布告
也照耀一个黑人向大海微笑
它照耀一个山东老汉面对城市
诅咒他的麦苗被污水损害
月亮在我写诗时照耀,我死后
它来看我,依然翻山越海
离开西方
看过我,它就呆一会东方
林中读书的少女
纯。而且美
而且知道有人看她
而更加骄傲地挺起小小的胸脯
让我在路边觉得好笑、可爱、这少女的情态
比少女本身更加迷人
少女可以读进书本里去,也可以读在
书的旁边、读在树林、飘带似的小河、一辆轿
车
也可以读在我这半老男人注意的眼光中
唉,少女,多可怜的年龄和身体
娇细的腰,未决堤的小丘和
疑狐未婚的心
少女纯白的皮肤让人心疼,而且她还读书
而且还在林中,而且还骄傲地觉得有人在看
哪怕我走了,她还骄傲地觉得
有下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