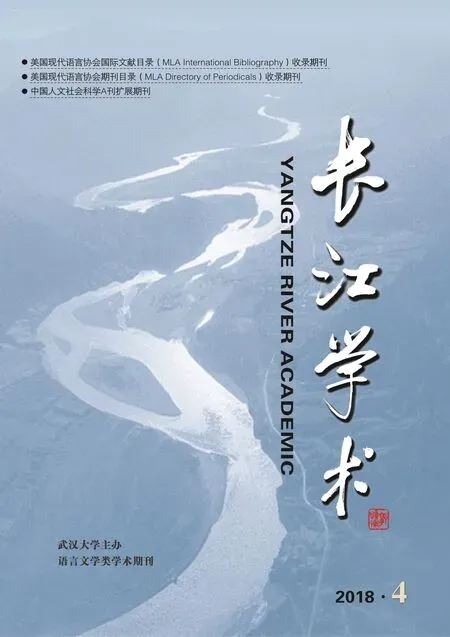江户时代异学者皆川淇园的文章学
2018-11-13张淘
张 淘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23)
一、皆川淇园其人与著作
日本江户时期开始兴起一股汉文学习创作的热潮,不仅翻刻中国的文章学著作,也催生了不少日人创作的文法书籍。荻生徂徕、伊藤东涯、皆川淇园三家于此用力最深,影响最大。关于前二者皆有不少论述,唯有对淇园的成就关注尚少。皆川淇园(1734—1807,名愿,字伯恭,又号有斐斋、筇斋、吞海子,通称文藏,京都人)是江户中后期的鸿儒,涉猎广泛,著述颇多,有对四书的“绎解”(集解)以及《老子绎解》《诗经绎解》等;易学方面有《易学开物》《易学阶梯抄》《易原》等;文学方面有《淇园诗集》《淇园文集》《六如淇园和歌题百绝》《三先生一夜百咏》《唐诗通解》《淇园诗话》等;史学方面有《迁史戻柁》等;医学方面译定过《补正医案类语》,文集中还有不少类似的为医书所作的序跋。门人弟子超过三千人。他提倡的学问称为开物学,即开名物之义,认为“《易》有开物之道,而其道要由文字声音乃可得入也”,从微观的视点出发,将语言与人类心理的关系解剖清楚。他追究古文文字及行文的内在倾向,在语言文字学方面有深厚造诣,有《太史公助字法》《左传助字法》《诗经助字法》《虚字解》《续虚字解》《助字详解》《实字解》等九种字书,与伊藤东涯并称为“近世两位优秀的汉字学者”。
他在文章学理论上的成就也不容忽视,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中云“淇园虽以经术自任,其说系一家私言,其所长却在文章上”。他留下了丰富的文章学资料,文章理论和技法主要见于《问学举要》《淇园文诀》等著述中,前者本是为批评朱熹的经学注释而作,但涉及不少文章理论,如同总纲领。后者原为日文,相当于文章技法的具体指导书。此外还有《习文录》《欧苏文弹》等作品是对古文大家的文章进行评注,是运用实例,可以对照参看。笔者从《问学举要》《淇园文诀》梳理出其文章学的主要观点,解释其中的一些观点和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他的其它著作中与文章学有关的内容,分析他对待文章的态度。
从学问而言,淇园反对朱子学,是一位异学者,开物学独树一帜,在当时甚至被人故意音讹为“怪物学”。从性格而言,他特立独行,放荡不羁,广濑淡窗《儒林评》云:“皆川行状放荡”,“予友原士萠举人之说曰:皆川放达出于弄世,谢安东山携妓之类也”。他的文章学理论和批评也具有特异性,有许多生造的术语,理论颇有新创之处。淇园以前的江户儒者如荻生徂徕、伊藤东涯等大都对本国文章存在的“和臭”问题进行检讨,而《欧苏文弹》转向矛头对准中国历代古文的代表大家——一直以来被视为典范的欧阳修、苏洵、苏轼,江户后期斋藤正谦《拙堂文话》中评价:“近世有一种文章家,专覈字义,其解穿凿迂缪,不止王介甫《字说》。虽时有所得,至于篇章之法,懵乎不知,而高自标置,下视欧、苏以下,痛加雌黄,可谓妄矣。”大概便是指淇园。他的理论有时繁复而琐细,批评有时严苛而主观,甚至有些吹毛求疵和穿凿。不过也有不少中肯之处,为后世开启了重新诠释欧苏古文的可能性,或许能使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得到重新审视和评价。
二、《问学举要》《淇园文诀》中的文章学理论
《问学举要》中说:“凡学文之要,大略有六”,即立本、备资、慎征、辨宗、晰文理、审思。立本的“本”即是“笃志以成物于己者”,物是指六经之文,他强调“道者自修己之道,学者自长其智之学”,即不受世俗偏见的干扰,不生希世干誉之心,才能发现前说的谬误。他敢于对欧苏等古文权威进行挑战,也是出于这种思想。
淇园将写文章看成“立象”,出自《易·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认为凡物皆有纪、实、体、用、道,出自九筹,“象”可分为作者心中的象和受众通过阅读等体验获得的象。立象后有明界与暗界之分,“明界”是指众人可见的形体以外的事物,“暗界”是指体内或者心中等无法用肉眼看见的事物,而区分明界、暗界时便可以用“纪”“实”“体”“用”“道”。这些在他的《易原》《名畴》《诗经助字法》等著作中有详细解释,也可以套用来解释文理。他的经学、辞学、文章学是三位一体的,打破任何一方都会破坏整个体系。
以下从文章本体论、文法论、创作论、文体论等方面进行具体介绍:
(一)本体论:文者言辞也。
皆川淇园在《淇园文诀》中曾自述习文经历:年轻时最初并不愿成为文人,仅因父命难违,为此,他作文时随心所欲,只求让人读懂便可。十七八岁时写了一篇文章给朋友,被大加批判,由此发愤研究文章写法,尤其注意助词的使用,经过一年多时间,已经能够分辨出本邦人文章中的不足。可知字学是他文章学的出发点,也是核心内容,藤原资爱在《淇园文集序》中称“文者言辞也”,这也可作为淇园文章观的概括。
他在《问学举要·备资》中提出要精辨字义、略通其世、知古韵。他尤其强调要准确了解每一个字的含义并正确运用,否则会影响到整篇文章:“盖一字失义,累及全章。譬犹棋失一着,则全棋俱败。为文者亦然,一字不当,则全言皆涩。”他在批评文章时尤其注意字义,他认为古代许多名贤大儒往往以文义来解古书,这会导致文理错误。其子皆川允在《虚字解·凡例》中曾说:“家先生学发《周易》,明开物之法,因音寻义,瞭然象意,征以诸古籍之所用众字之辨,犹如皦日。”淇园精通《易》学,根据中国古代汉字假借的特点,又以音声相求,来解释各种虚字的含义。他认为《说文》等字书在释义时皆取诸近似而已,“率非真诠”,所以他提出的方法是“求之其声之象数者上也,求之其书之形状者其次也,又皆兼须多按古书使用之例,以参验其实”。他对于后人用古文写作持谨慎态度,也是由于怀疑汉以后文字已失去古义:“学者若欲用读汉以后文字之法,以为古文,则其误解者必多矣。”(《问学举要》)他对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文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订正出于这一观点。由于在经学上他主张汉儒传经可疑之说甚多,在文字上他认定从东汉以后开始,名物之类已经变得非常繁复了,后世许多儒者释字义只能采用“连熟”的方法,即若符合上下文意或者二字经常连用已成熟语,这给释义带来了很多的弊端,学习古文者若不直承三代之文,则容易用错字词。他认为古文与后世文的区别在于:“古之文其辞简,西汉以后之文其辞繁。简者之法精,精在其字,繁者之法粗,粗在其句。前贤乃未悟此字句精粗之有异。而其为古文,亦犹如为后世之文,是以其亦未尝不言循拟之为善。而说之成夫立意要旨之陋,乃莫之能自知。”(《问学举要》)因此他也批判明代的古文辞派,认为他们是刻意深其言迂其辞,而不出于欲尽其意的目的。
(二)文法论:晰文理十五事。
相对于字义,皆川淇园认为文理“因字义而成”,是比字义次要的因素,不过他也并非不注重文理,在《淇园文诀》中他强调文理是极其重要的,在方法探索上也颇多创造性理论,《问学举要》中更是特设“晰文理”一节,分为十五事,《文诀》中也有具体示例。他还运用到实际的批评活动中,如果将《欧苏文弹》与《问学举要·晰文理》的内容对照来看,许多难懂之处便会迎刃而解。以下分条列出此十五事,并对其与中国文章学的关系稍作阐释:
(1)言物各依其部界:他认为文章的目的在于“章物”,言物贵在有别,“凡其大小远近,动静恒遽,外内主客之属,并皆不得相混言。”根据淇园所举示例,这里的部界划分是根据上下文脉来确定句子当中的内部结构。明代曾鼎《文式》“论作文法”条中提到“文字一篇之中,须有数行整齐处。……上下、离合、聚散、前后、迟速、左右、彼我、远近、一二、次第……”皆讨论文脉逻辑,淇园对此加以简化整理,并有具体阐述和示例。
(2)冒、斜插、补添:冒指“欲言其委者先言其源”。此法或者源于陈绎曾《文章欧冶》中的抱题法,但强调叙述事情的原委,这在抱题法中是没有的内容。补添即“为接应上势先言其用,既复恐其物杂乱失其旨之所归,下因复明其物,是名补添”。此法接近归有光《文章指南》中的“前后相应则”,即“凡文章,前立数柱议论,后宜补应”,但归有光此书至江户后期才有和刻本,因此淇园受其直接影响可能性不大。斜插指“用冒若补添之法,以弥缝两言中间,而以成章者,是名斜插”,《淇园文诀》对此有诸多实例,未见他书有类似说法。
(3)分量广狭:指文中语辞的含意可广可狭,“大抵文中语意,系一人而言,则是为分量狭,系众人而言,则是为分量广”。因此同样的语辞,用在不同的位置,其义不同:“凡文之所措其辞,唯随其位所在,而其意乃成不同”。此说特异,不见前人有此说法。
(4)伏应含蓄:此条含义与中国文话中强调的“照应”与“含蓄”大体相同,但淇园的论述尤为详细具体,指出“譬若只言二三者,一乃为之原状。若先言一,则十乃为之终应,如十一乃为别起,不得为终应也。若先言一而次言三者,则二乃为之含蓄。若言一二者,则三为未起,未起则不得为含蓄也”,这并非简单的理论指导,而是在行文时可以作为具体指导方法。
(5)同字一律:他认为东周以前的文章,“一章之间,字同而叠出者,其旨必归于一律。一篇之间,句同而累见者,其意必会于一途”,战国以后文始多出奇谲,“然至其大段,决无前后别调者”。此法未见他书。
(6)增减展缩:此法强调行文以简要为主,一字增损皆有目的,“如或虽所经言,仍复称之者,其必亦语势或已不相接承。或外虽仍接,而今将欲别从其内举其情者也。诸如是之类,古文例皆改其辞端,别起其称”。此法与中国文话中的炼字法有相通之处,但又与文法逻辑有关。
(7)辞之略析:“略析”二字是淇园的发明:“文有略析者,其所略析文字,或伏在其上文,或伏在下文”。分为“略析”和“可略析”,有以原伏为略析者,又有以反对为略析者,此法最为复杂,亦不见有前人提及。
(8)言之顺逆:顺逆比较容易理解,“如曰大小上下者,是顺言也。如曰小大下上者,是逆言也”。但是淇园强调“凡顺言者,其情皆静,逆言者,其情皆动”,这点前代文话从未提及。
(9)意之向背:这是从文意的完整而言,“譬若先言一次言三者,其意自反求其二。是其意为背。若先言一次言二者,其意自趣其次之三,是其意为向。若先言三而不言一二者,则其所伏之一二,实乃若在三中,故其意仍不反求而趣其次之四,此名孤起,而其意亦为向”。亦未见前人提及。
(10)势之接承:“凡文势相接承,有以自接承者,有以敌接承者。自者仍不离其物事而言者是也,敌者以他物他事与前接应而言者是也”。以自接承者即按照纪、实、体、用、道的顺序,以敌接承者则要审前文虚实之势。此法与文法中的顺承逆承相比,更为复杂琐碎。
(11)虚实:这条论述“文字有虚实死活”,实活是指“万物就其所含灵而言”,实死是指“万物只就其体质而言”,虚指“凡物无本质只有其象”。“虚与实相依,则为之诸气色声味之属者,皆是虚死。宣之作动之用者,皆是虚活”。陈绎曾《文章欧冶·汉赋制》中有:“实体:体物之实形,如人之眉目手足,木之花叶根实,鸟兽之羽毛骨角,宫室之门墙栋宇也。惟天文〔惟〕题以声色字为实〔体〕。”“虚体:体物之虚象,如心意、声色、长短、动静之类是也。心意、声色为死虚体,长短、高下为半虚体,动静、飞走为〔活〕虚体”。《文章欧冶·诗谱·变》中也列出了“四字变”,即为虚、实、死、活。淇园应该是将这些概念进行统合改造之后提出的,并且引申出了文法规律:“大抵句头实者,其意内而其势泛。句脚实者,其意外而其势定”等。
(12)既正未:即既往之事、未来之事、正当之事:“既往为已定而静,未来为未定而动。”相当于语法当中的过去式、将来式、现在式。淇园关注到此点与训读有关,江户前期儒者贝原益轩的《点例》卷上就有“既往、见在、将来的テニハ(日语助词)例”条,并举出了《论语》语句作为示例。
(13)反语:即反问句。陈绎曾《文说》“造语法”中有“反语”条:“《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又曰‘爱之能勿劳乎?’与《尚书》‘俞哉!众非元后何戴?’此皆反其意而道,使人悠悠致思焉。”江户时代的穗积以贯《文法直截钞》中亦言及反语,不过未下定义。淇园的特别之处在于提出“反语有不用语助者”。
(14)篇章之旨:即篇、章、句皆有主旨。此条文话中较常见。
(15)拟议:“拟议”一词出自《周易·系辞上传》,“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明李攀龙曾据此倡导古文辞,徐师曾撰《文体明辨》刊行时,赵梦麟、顾尔行作序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拟议并加以论述,淇园则引申为:“文辞之变,千言万语,都不出于拟议之二法。拟者拟之其物之形容之谓,议者议之其道之变动之谓也。”
尽管淇园的文法论有一部分内容借用前人文话,但总体而言,仍然有许多是他自己的新创设,这些理论并不是孤立而空洞的,不仅皆引用经学著作中的句子作为示例,还应用到了具体的文章批评上,可谓系统而新颖。
(三)创作论:“心神的妙用”与“文字锁之貌付”。
至于作文之法,他在《淇园文诀》中提出了一种概念,即“文字锁之貌付”。此为作者自创术语,“貌付”大体相当于印象的意思,“文字锁”大体相当于文章间的逻辑联系。他与其他文章学家一样指出学习做文章关键在于宋代欧阳修所说的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并指出初学之人还要读多、解多、做多。因为文章中有“文字锁之貌付”,即作者在写文章时,神气会在心思考如何作辞时,不知不觉地产生出各种新奇的作辞条理来,神气在心中,会使作者对文章更加用心,也会使创作更顺利。这可以称为“心神的妙用”。而要达到这种心神的妙用,必须多读古书,熟记各种“文字之锁”,在开始写文章时,这些记忆中的古文“文字锁之貌付”便会在恰当的时候浮现在心中,引导笔尖如何书写。如果不具备足够的“心神的妙用”和“文字锁之貌付”,不管你有怎样的才能也是写不出文章来的,因此不得不多读。
然而,“心神的妙用”所能引导的结果不过是如音乐节拍那样,对待变化莫测的条理,也应该像古文的“貌付”那样,将那些熟记下来的文字的义理预先仔细地解读并且记住,直到完全掌握。若非如此,在神气引导作者创作时,所写出来的辞(锁的雏形)虽然与开始创作时的节拍是相合的,但是文中会出现很多与神理并不符合的节拍。而且仅靠这种方法进行创作的话,写出来的东西虽然与“貌付”相符,但与神理不合,由此便会产生许多“刷违”。
所谓“刷违”是指:或者用辞迂远、意理闇滞,或者言说不足、道理无聊,记述未闻的事情时大多写一些使人无法读懂的文字。如果能多解熟记,浮现出来的“貌付”自然会与其要写作的机宜和条理恰到好处地吻合。因此不可不多解。然而读和解终究只是内心的技法,写文章是要把心里的东西表达出来,二者会有出入和不同,因此如果不练习如何从内心抽出条理作出文辞,便无法下笔。要想顺畅地下笔,必须积累多读多解之功,但这好比足痿症者蓄杖,对写文章没有效果,因此必须多做。以上就是对初学之人来说非常关键的“三多”。
这里强调的“神气”概念是与他在《易原》等书中提出的哲学观念一致的,而古人认为心是思考的器官,“心之官则思”,所以“心神的妙用”是作者的主观意志对于创作的影响。“锁”的概念可能源自诗学中的“钩锁”,元代范梈《木天禁语·六关·七言律诗篇法》中有“数字连序,中断,钩锁连环”,文字之间并不是松散的关系,而是有着文脉在里头。从他对欧苏文章的批评,也能看出他多次强调此点。
他既重视主观精神的作用,也认为这是可以通过学习积累的。对于如何积累提出了各种实践方法。如先分类抄录古书,大约经过一年左右时间,便会自然记住很多“文字锁之貌付”。在创作时要始终在文中保持“意”的一贯,文章不仅是文字,还是反映心中事物的条理,心到则笔到,心不到则笔不到。
淇园认为初学作文之人应该从练习写尺牍入手,其次是记事文,记事文写不好的话,议论文也写不出来。这点与宋代吕居仁提出的议论文才是有用文字大相径庭。淇园之弟富士谷成章(字仲达,号北边,又号层城,出继富士谷氏)是一位和歌家,淇园受其影响,曾将记事文比作和歌里的四季杂歌,初学者易懂,将议论文比作和歌里的恋爱,初学者比较难懂。这些理论既强调语言受到思维影响,即主观化(subjectivity)特点,又重视经验在其中发生的作用,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创作思想。
(四)文体论。
当时江户儒者间有一股重视《史记》的风潮,淇园也认为初学作文者应以《史记》为宗,其他各类文章可分别参照。著有《史记助字法》二卷、《史迁戾柁》三卷。他以《史记》《汉书》之类正史作品为记事文里的“正文”,曾与好友清田儋叟(1719—1785,名绚,字君锦、元琰,又号孔雀楼主人)切磋文章作法,并称:“吾学攻于经,而君锦长于史,常获说而玩者,与事可喜者,必交出而互告,如贾之贸易以殖其货者。吾尝与论文谬相推奖以为无以间然矣。”二人在文章论方面经常互相沟通交流,淇园的文章学观点以经为本,重视《史记》。
关于俗语文,淇园认为《水浒传》和日本的《源平盛衰记》《太平记》一样都属于俗文体,特点是其中有许多琐细的与事实无关的描写。俗语小说虽然有许多语言鄙猥的地方,但也应该兼读,因为其中琐碎的描写能够如实地反映人的“鄙情”(即人的情感),玩味这些文字便会生出创作氛围,达到“精神的活用”。唐传奇则别有一种风味,属于雅文。而当时江户书肆出现的明代瞿佑《剪灯新话》《余话》和刚刚舶来的《聊斋志异》等则是模仿唐人小说而作的,虽然并非“正文体”,但却比俗文体更能学习到如何自由书写文章,学写传奇文体是学写“正文”的手段。江户前期,学习唐话(汉语,当时主要是南京话)的人多从读《水浒传》《通俗三国志》《西游记》等白话小说入门,被称为“小说家”或“稗官”。当时冈白驹、松室松峡、冈鸟冠山、朝枝玖珂、陶山南涛被人称为稗官五大家。到了后来,出现了一些虽然不懂唐话但仍然可以读懂白话文学的人,清田儋叟就被人称为小说通。淇园与儋叟从小一起泛读各类小说如《水浒传》《禅真逸史》等,称金圣叹评《水浒传》为天下才子必读书。享和二年(1802)60多岁时他为门人本城维芳刊行的《通俗平妖传》作序,其中记载了这些往事。淇园之弟富士谷成章也曾根据《石点头》创作翻案小说《白菊奇谈》。他们对待通俗白话小说的态度无疑影响了淇园的文体观,因此尽管他划分了正(雅)与俗,但是对俗语文绝对不是轻视的态度。
此外淇园认为四六文起自六朝,北周庾信别出机巧,使四六文体为之一变,唐人的四六多为庾体。有韵之文包括赋、颂、箴、铭、赞,大多是由散文演变而来。赋原来是像买卖往来书信式教科书那样的内容,逐渐追求文饰,司马相如等人创造了赋体,至唐则别出律赋体,平仄对句等的加入更增添了难度。颂有终篇同韵的,也有每四句换韵的,还有仿照《离骚》之辞的,这些有韵之文的用韵法都与《诗经》的用韵不同。序有用四六文书写的宴序,还有王勃《滕王阁序》等,从韩柳开始,用散文形式写作宴序送序开始盛行。而诏也分为四六和散文两种。此外他还关注各类文体的写作方法,如尺牍、记、墓铭等。文体之间的差别也是他批评的标准之一。
三、淇园的古文批评:《欧苏文弹》
淇园的手稿本《欧苏文弹》(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是对欧阳修、苏轼、苏洵文章进行批判和修正的著作,能够最直观地反映出其文章学的成就。“弹”字取自奏疏类中的“弹文”之名,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中有“弹文”条,这里意为弹劾过错之意。据《汉学者传记及著述集览》,淇园另有《物服文弹》,当是对荻生徂徕和服部南郭的文章进行弹劾的著作,可惜今已不传。
本书主旨亦在订正批评,涉及文章包括苏轼《三槐堂铭》《范增论》《留侯论》、欧阳修《纵囚论》《读李翱文》、苏洵《管仲论》共六篇,从编排未见明显逻辑次序来看,当非一时所作。稿本在删去的部分用方框标注,用红笔表示直接修改原文的地方。弹劾的内容和原因用日文以夹注的形式写在各句之后,有针对助词虚字的,也有根据行文逻辑、上下文照应关系、古文写法等进行订正的可与“晰文理十五事”对照参看。
欧阳修、苏轼、苏洵皆为宋代古文大家,文章为学文者必须熟读的典范。国内文人学者的批评多从文与道的角度出发,如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皇朝文鉴二·诰》中批评欧文:“余尝考次自秦汉至唐及本朝景祐以前词人,虽工拙特殊,而质实近情之意终犹未失。惟欧阳修欲驱诏令复古,始变旧体。”朱熹也曾说“苏文害正道”。金王若虚是最早对欧苏行文用词进行质疑之人,《文辨》中云:“欧公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五代史》论,曲折太过,往往支离嗟跌,或至涣散而不收。助词虚字,亦多不惬。如《吴越世家论》尤甚也。”“欧公多错下‘其’字……”“东坡用‘矣’字有不妥者”等等。
淇园少年时期曾因当时盛行李王古文辞,一段时间内务为模拟其体,后心悟其非,以为“古文唯韩柳为近乎醇矣,次则欧苏二家而已”,便与儋叟一起校订《欧阳文忠公文集》,但从《欧苏文弹》中他称欧氏不知古文省字之法,语势多有不顺之处,又认为“宋人文中此类名目无理之处甚多”等语来看,至少某一时期他仍然对欧苏文存在偏见,而他大刀阔斧的修改显然是最严厉的批判。
这种批判出自淇园的古文观,他认为“古文只是古人之言语耳”,学习者应追溯直承上古三代之文。东汉以后语义发生变化,后人学习古文必须精通上古三代的作品:“精识字义。而以多读古书,则古文之法自在其中矣。后世所称文法者,率多皮相之语,不足采也。”韩柳复古,既追求“辞”亦追求“气”,故其文自然气格高,其步骤古人之处颇多,从欧阳修开始,鄙弃辞趣,稍乏古气,其流文辞之弊在于后来他们的全篇结构上成了熟套,且唐宋八大家不知古文有略析等文法,故其文与古不同。
他认为苏轼天赋在欧阳修之上:“大抵欧辞多婉曲,旨尚隽永,而苏乃辞气宕逸,旨喜痛到。此二家之异也。然要之,苏天资俊迈,十倍于欧。”不过苏文也有缺点:“然朱晦庵乃尝讥苏文用字多疏漏,以余观之,实有如朱言。且以其行文之法论之,其奏议书疏之类,条达明畅,无可议者。至如其余辞体效古文者,其错辞先后相承之间,以其神理之不属者、强作缀缉者甚多。盖虽读惯古文而其解旨疏略之过也。此不唯苏,而欧亦不免有之,盖以古今言语繁简异势,虽其所含理自然不同而读者不知其辨,则以读之所可得粗略为其旨已尽故也耳。”可见他对欧苏的批判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古文。《欧苏文弹》是淇园古文理论的实际运用,并且体现了他对欧苏文章的看法,笔者拟在将来把其中的弹文翻译成中文,以介绍给中国读者。
四、探本溯源:皆川淇园文章学与古义学派
尽管淇园的古文理论与批评有许多特异之处,但他的批评方法和理论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前人经验。中村幸彦曾提到,“受古注学影响的学者当中最具独创性的就是皆川淇园。他将古典研究的基本置于言语,这点有可能是受徂徕古文辞的主张和伊藤东涯名物学与小学研究的影响。”伊藤东涯比淇园早出生60多年,二人同为京畿文化圈内的文人,皆为反对朱子学的儒者,在文学上皆为反古文辞派,从学脉上而言淇园是对古义学派的继承,如淇园的《名畴》六篇与东涯的《名物六帖》,皆解释儒学中的道德诸“名物”如“孝”“悌”“忠”“信”等字词的含义。从他的文章批评和理论上更可看出他与东涯古义学派之间存在的影响痕迹。
淇园锻炼弟子们的方法采用“射复文”的方式,此法乃起自东涯之父伊藤仁斋,东涯在《作文真诀》中早已介绍过这种方法,即:原文—译文—复文。东涯同样重视下字与语境的关系,他有许多字书存世,《东涯漫笔》卷上有云:“后世之词,与古不同,故文字之道,元明不及唐宋,唐宋不及秦汉,秦汉不及三代,……虽古今之变,如此其不同,而同是中国之辞,四方之语,与中国不同,各从土语,译以汉语,以日本之语,习中国之词,固隔一重。以今日之语,摸上世之词,亦隔一重。呜呼,日本人学古文字,亦难矣哉。然中国之言,一字各有其义,音训相须,其义易辨,不如四方之言,连合众音,成此一义也,且自汉以来诸儒注解、义解,最是明悉,传之今日,无所迷惑。”《作文真诀》中云,“中原读书者训同而字异,盖、肇、俶、载、创,皆初也,而义则各异,咨询、谋略皆计也,而意皆不同。吾国读书者徒认训之或同而不察我之各殊,此用字之所以为难也。”这两种说法皆是承认汉字意义的古今之变,也是两人文章学的基本出发点。淇园将文章分为正(雅)与俗的区分方式与东涯在《操觚字诀》中的做法如出一辙。他们也都有具体的示例和学习书目,皆主张通过分类抄书的方式来学习。
不同之处在于,东涯的方法更为传统,而淇园在文理文法的探索上远远比东涯要深入得多。又如东涯之父伊藤仁斋认为文本于《尚书》,“文以诏奏论说为要,记序志传次之。尺牍之类,不足为文,赋骚及一切闲戏无益文字,皆不可作,甚害于道。叶水心曰:作文不关世教,虽工无益。此作文之律,看文之绳尺也。”而淇园则认为初学作文之人应该从练习写尺牍入手,并且不反对创作赋骚等文章。
淇园的文章学还有很多资料未开发,如《助字详解·总论》《习文录》等,有许多难题待解决,如他的理论究竟如何评价,是否与现代语言哲学有内在关联等,这些问题都有待学者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