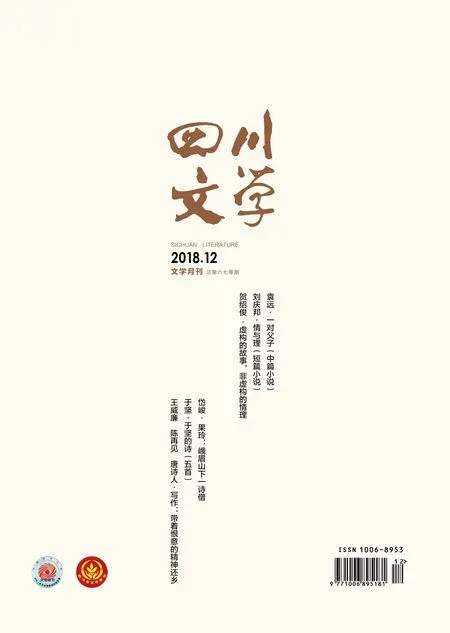情与理
2018-11-13
这一篇讲我亲叔叔的故事。
我爷爷奶奶一共有四个孩子,除了父亲、叔叔,还有大姑、二姑。大姑嫁到了蔡洼,二姑嫁到了洼张庄。您听听这村庄的名字,就知道我的两个姑姑嫁都到了“洼地”里。我们那里的人对蔡洼的评价是:蔡洼蔡洼,又菜又洼。姓蔡的蔡,怎么被说成了蔬菜的菜呢?当地人说一个人笨,或没本事,就用一个菜字概括,说那个人菜,菜死了,是个菜菇苔。村庄本来就洼,前面又加一个菜字,能有什么好呢!我大姑父被抓了壮丁,一去不回,杳无音信。我大姑到坑边砍柴火时伤了财主家的树根,被人家打了一顿。大姑一口气咽不下去,撇下两个孩子,年纪轻轻地就上吊死了。洼张庄被人编成了顺口溜:洼张庄,水趴趴,蛤蟆尿尿淹庄稼。二姑所嫁的丈夫是个做醋的,卖醋的。二姑父娶了二姑,又跟庄子里别的女人相好,着实让二姑吃了不少“醋”。两个姑姑的故事就不多说了,想起来还不够让我这个娘家侄子伤心的。再说,把姑姑写多了,就偏离了写叔叔的主题。
我叔叔曾当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赴朝鲜跟美国鬼子打过仗。听人说,说是志愿军,他磨磨叽叽并不愿意去。他说他没摸过枪,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枪放响,更不会打仗。动员他参军的村干部告诉他,放枪很容易,把枪的扳机一扣,枪嗵的一声就响了。不会打仗也没关系,上了战场就会了。干部说,当志愿军是很光荣的。不光他一个人光荣,全家人都沾光跟着光荣。叔叔说他不想光荣。咦,这样的态度就不对了,有些事情需要你光荣,你就得光荣,不想光荣也得光荣。叔叔这才说了实话,说出了他的担心,他说他要是死在战场上怎么办?这个问题嘛,上了战场,不一定就死。当然了,他如果为保卫国家而牺牲的话,那就更光荣了。
叔叔参军走后,我们家得到了一块长方形的金属牌子,上面的字是“军属光荣”。光荣的表现之一,是到过春节的时候,村里的青壮男人排成一队,集体给我们家的人拜年,对着我们的家门口三鞠躬。
叔叔是幸运的,他在朝鲜战场上经历了那么多枪林弹雨般的战斗,并没有把性命丢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停战协议一达成,他就活着回到了家乡。他不但活得很健壮,而且一点儿伤都没受。回到家乡的叔叔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叫退伍军人。
叔叔既然回来了,年龄也不算小了,那就找对象吧,结婚吧,成家吧。在叔叔外出当兵期间,我的奶奶,也就是叔叔的母亲,生病去世了。给叔叔张罗找对象的事,主要由我母亲负责。我父亲呢,开始筹集建筑材料,准备为叔叔另盖两间房子,作为叔叔结婚用的新房。之前我们家只有两间半北房,还有土地改革时从地主家分到的两间草房。那两间草房是坐东朝西的西屋,在另外一个地方,被父亲用作养牛的牲口屋。在我们家的两间半堂屋里,住着爷爷、父亲、母亲、大姐、二姐、我和妹妹,还支着锅灶,实在没有了叔叔住的地方,叔叔只好临时住在牲口屋里,跟牛住在一起。
有媒人给叔叔介绍了邻村的姑娘,让叔叔去跟人家姑娘见面时,叔叔开始调皮捣蛋,显出诡异的一面。去见面嘛,相亲嘛,叔叔应该穿得好一些,周正一些。从部队退伍时,叔叔带回了不少东西,有皮帽子、皮大衣、棉军装、单军装、毛毯,还有搪瓷盆、搪瓷茶缸子等等。倘若叔叔穿一身军装去相亲,那不是显得很威武嘛,说不定一见面就会给人家一个好印象,相亲就会取得成功。然而,叔叔好像对相亲并不感兴趣,甚至还有一些抵触情绪,他说相什么亲,开玩笑!去相亲时,他不穿军装,也不穿什么好衣服,而是专拣有补丁的旧衣服穿。头上呢,还戴了一顶烂了边子、散了篾子的破帽壳子,把自己弄得像一个稻草人,或者说像一个叫花子。叔叔的不可理喻就在这里,谁都不知道他是咋想的。或许他觉得这样装扮很好玩,可以吓人家姑娘一跳。或许他内心充满自信,想通过这样的穿戴考验一下人家的姑娘,试试人家到底识不识金镶玉。反正叔叔的思维有些怪,有些不大正常,于情于理都不大正常。人家姑娘,还有姑娘的家人,可不愿意跟他玩这样的游戏,可不吃他这一套,人家认为他不太精,怀疑他是不是有点傻,是不是在战场上打仗见的死人太多了,精神受到了刺激。人家好好的姑娘,当然不会同意嫁给一个“稻草人”,姑娘的父母也不会同意将闺女嫁给一个“叫花子”,叔叔相了一次亲,又相了一次亲,都以失败而告终。
叔叔从来都不听爷爷的话,一直跟爷爷对着干,爷爷让他上东,他上西;爷爷让他打狗,他撵鸡,爷爷对他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我父亲作为叔叔的哥哥,虽说比叔叔大十来岁,叔叔也不愿跟我父亲合作。某些事情他当面答应了父亲,说好好好,一转脸仍是我行我素。应该说我母亲对叔叔的婚姻大事是很负责任的,可不知为什么,叔叔对我母亲像是不大认同,叔嫂之间的关系有些半生不熟。后来我想到,也许因为我母亲的娘家在外地,叔叔对我母亲就有些排斥。
两次相亲不成,叔叔又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就没人再给叔叔介绍对象了。有人甚至在背地里说,吊着他,让他一辈子拉寡汉。
夏天来了,紫色的楝树花开了,明黄的丝瓜花开了。这天上午,二姐正带着我在我们家的院子里玩,只见从院子外面来了一个妇女。我当年才两岁多,记性还不是很好,我隐约记得,那个妇女穿一身黑衣服,头上顶着黑毛巾,像传说中的老猴精。有些细节是二姐后来告诉我的。
“老猴精”问:听说你们庄从外面回来了一个退伍军人,他的家是在这里住吗?
二姐答:是呀,他是俺叔。
你叔娶新媳妇儿了吗?
还没有。
那我给你叔说一个吧。
你是谁?
我是东南严庄的,我给你叔说的那个闺女姓严,她爹的名字叫严老敬,我不知道她娘叫个啥。
二姐说:这个事儿你得跟俺家大人说,俺爹俺娘到西地里干活儿去了,我现在就去把他们喊回来。二姐说罢,拉上我的手,我们就一路小跑到西地里去了。父亲没回来,母亲回来了,“老猴精”由母亲接待,母亲就让二姐和我到一边玩去吧。
后来我才知道,“老猴精”给我叔介绍的对象名叫严凤兰,那个口称“我不知道她娘叫个啥”的“老猴精”正是严凤兰的亲娘。这个事情来得就有些奇怪,一个当亲娘的,跑到外庄,登门为自己的闺女找婆家,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般来说,就算急着给闺女找婆家,也应该托一个媒人去牵线哪,她为何要隐姓埋名亲自出马呢?她这种做法,按现在的说法,有些推销的性质。怎么,她的闺女推销不出去了,眼看要砸在手里了?难道她的闺女有什么毛病,是豁子还是麻子呢?是瞎子还是瘸子呢?原来,她的闺女曾经“销”出去过,“销”的对象还不错,是一个在镇上供销合作社当干部的人。那个干部把她的闺女试验性地使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她闺女好吃懒做,对自己的母亲也不好,就坚决地和她闺女离了婚,把她闺女退回其娘家去了。是货都怕退,一退就难免产生负面影响。“老猴精”大概真的怕闺女砸在自己手里,怕托了媒人,媒人不给她的闺女添好言,就亲自上台,去我们家上演了那么一出亲娘为亲闺女说媒的戏。
我叔叔这头儿呢,大概觉得玩游戏玩得差不多了,出怪相也出得差不多了,如果再把恶作剧做下去,有可能真的找不下老婆了,真的要拉寡汉了。及至见到严凤兰,叔叔见严凤兰眼睛大大的,眉毛黑黑的,辫子长长的,眼前一亮,感觉不错嘛,相当不错嘛!这样的严凤兰,如果穿上一件长裙子,恐怕比朝鲜的姑娘也不差吧!至于说严凤兰好吃懒做,这没什么嘛!谁不爱吃好吃的呢!谁不想少干活儿呢!叔叔的怪异再次表现出来,人家给他介绍的黄花闺女,她不认真对待,一个浑身穿黑衣服的“老猴精”,把一个被人休过的女人推销给他,他却点了头。
这时候,我们家里的大事情都是由父亲操办。爷爷逢集到街上听小戏,背集在村里找人为他念唱书,乐得享受清闲。而我父亲呢,是个曾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的人,也是遇事有成算的人,愿意把家里的事管起来。既然叔叔愿意娶严凤兰为妻,父亲就为叔叔定了结婚的日子,是在秋后。到那时,庄稼收完了,麦子种上了,天气凉快了,人们消停了,正好可以为叔叔举办婚礼。更重要的是,再过两三个月,父亲准备为叔叔盖的两间新房就可以落成。届时把新娘迎娶进新房里,岂不是两全其美!
然而,麦子刚刚收完,夏天还在盛头上,离秋后还差得很远,离叔叔第一次见到严凤兰也就十来天时间,严凤兰就迈开双脚,主动到我们村找叔叔来了。当然了,陪同严凤兰的人,也可以称为送亲的人,还是有一个的。这个人不是严凤兰的娘,是严凤兰的大弟弟。严凤兰的大弟弟背着一个用床单包成的包袱,就把他姐姐给叔叔送来了。他大概打听到了叔叔住在哪里,没把他姐姐送到我们家的堂屋,而是直接送到牲口屋里去了。
叔叔把严凤兰来到的消息对我母亲说了,母亲说:快让他们到堂屋里来吧,待在牲口屋里算咋回事!天快晌午了,我马上给他们做饭吃。
叔叔大概是“金屋藏娇”的意思,他说:我看在牲口屋里挺好的。这样吧,等你做好了饭,我给他们端过去。
母亲做的午饭是捞面条,做的菜是黄瓜拌荆芥。母亲把煮熟的面条在井拔凉水里一过,浇上蒜汁儿一拌,上面放上黄瓜菜,盛了堆尖一大碗,让叔叔给严凤兰的大弟弟端去。母亲特意跟叔叔交代说,严凤兰的大弟弟是送亲的人,是客人,这第一碗饭先让客人吃。叔叔说好的。
叔叔端着饭碗走出院子,刚转过墙角,他大概闻出面条的味道不错,停下脚步,竟自己先吃起来。他吃得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就把一大碗捞面条儿吃了下去。叔叔就是这样不讲规矩,不按规矩出牌。当他把空碗送到我母亲手里时,母亲有些怀疑,她说咦,吃得这么快!
叔叔笑了一下说:被我干掉了!
母亲不悦,说:他叔,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家里来了客人,这第一碗饭应该让客人先吃才对呀,这是最起码的规矩呀!
叔叔不笑了,说:什么客人不客人,规矩不规矩,谁先吃不是一样嘛!我吃完了,你再给他们盛就是了。
严凤兰的大弟弟吃过饭走了,严凤兰留下了。留下了,就算跟叔叔结婚了。因为没有举行婚礼,就没有放鞭炮,没有拜天地,没有撒喜糖,没有喝喜酒,一切的一切都省略了。
但是,计划中的两间新房还没有破土动工,总不能让一对新婚的新人跟那头黄牛住在一起吧。黄牛在屋里拉屎,在铺上撒尿,一点儿卫生都不讲,新娘怎么受得了呢?父亲赶紧把牛牵出来,把牛槽搬出来,把牛铺清理得干干净净。并弄来新土,撒上石灰,用板砖把地砸平砸实了,才让新郎新娘进去住。
叔叔结婚时间不长,就开始闹事。叔叔和婶子早上都睡懒觉,不下地干活。那时人民公社还没有成立,各家各户的地都是自家种。我们那里的种地人长期养成的习惯是,天不亮就起床,就顶着星光,踏着晨露,到地里干活,干一阵子活再回家吃早饭。母亲一大早就起来做早饭,做好早饭,把早饭盖在锅里,跟父亲一块儿下地干活,该锄地就锄地,该间苗儿就间苗儿。叔叔和婶子早上不下地干活,到了该吃早饭的时候,总应该到堂屋里跟全家人一块儿吃早饭吧?母亲派大姐去叔叔和婶子住的地方喊一次,又喊一次。叔叔还在床上没起来,他先说等一会儿,又说让我们先吃。等我们吃完了早饭,父亲母亲又下地干活去了,叔叔才出动了。他的办法是,脱下自己的汗褂子,把母亲蒸好的馍收拾收拾,统统收拾到汗褂子里,兜起来就走了。除了把馍兜走,他瞅见一只碗里有腌好的咸蒜薹,就连碗把咸蒜薹也端走了,到南边屋里和婶子一块儿吃。
我们那里的午饭,多是做汤面条,一做就是咕咕嘟嘟一大锅。馍可以用汗褂子兜走,汤面条又是汤又是水的,用汗褂子是兜不走的。加上汤面条做熟后,不能在锅里放太长的时间,时间一长面条儿就朽了。吃午饭的时候,叔叔和婶子总该按时到锅灶前端碗吧?不,有时吃午饭他们也迟迟不到位。不知大姐看到了什么,她不愿再去喊叔叔婶子吃饭,母亲让她去,她眉一皱,嘴一撅,好像很为难似的。有一天中午,母亲又是满身柴灰满头汗地做好了午饭,让谁去喊叔叔他们两口子吃饭呢?喊他们吃饭是必须的,他们按时吃或不按时吃,是他们的自由。而母亲没有不招呼他们的自由。如果不招呼他们,母亲就输理了。母亲极其讲道理,极其遵守道理,她宁可不自由,也不能输理。母亲正好看见邻家有一位四爷从村街上往南边走,就托四爷顺便喊一下叔叔和婶子,让他们回家吃饭。
不一会儿,四爷转回来了,四爷满脸讥笑地对母亲说:你们只管吃你们的,不要管他们两口子。大白天的就光着个屁股,连一点儿脸面都不顾。牲口不在那里了,我看他们两个快把自己变成牲口了。四爷说着,可能连四爷都觉得不好意思,四爷的脸膛一下子变得红通通的。
叔叔之所以如此表现,是想分家另过。想分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嫌我的父亲母亲生的孩子太多了。他们已经放出风来,说我们才不帮他们养那些孩娃子呢!村里人看出来了,闹分家是严凤兰的主意,叔叔点灯,严凤兰加油;叔叔在外边点火,严凤兰在后面煽风。
在关于分家的事情上,说来父亲的观念是传统的,也是保守的,他认为,越是弟兄们在一起,越是家里的人口多,越显得和睦,兴旺,幸福。他主张要稳定,不要折腾;要团结,不要分裂;要谦让,不要争吵。作为弟弟的哥哥,父亲想对叔叔有所照顾,不愿意让叔叔早早地分出去。知道的,是叔叔婶子想分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父亲把他们分出去的呢,这让父亲在面子上也不大容易接受。所以,父亲对叔叔的捣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见跟没看见一样,听见跟没听见一样,那是相当的宽容和息事。
父亲不会想到,他这样做无异于对叔叔的放纵,终于有一天,叔叔把事情推向了极端,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天,叔叔和婶子还是不按时回来吃午饭。我们都吃完了,叔叔才来了。我们家喂有一头半大的猪,母亲正用糠糠水水在一个瓦盆里给猪拌食。人可以不按时吃饭,如果不按时给猪喂食,猪会持续提抗议。抗议的办法就是不断哼哼,甚至大声叫唤。一般情况下,等全家人都吃完了饭,用刷碗刷锅水给猪拌食比较合适,刷碗刷锅水浑浑的,里面还会有一点咸味,猪比较爱吃。可是,叔叔婶子还没有吃饭,还有小半锅面条在锅里盛着,母亲不能刷锅。那头一点都不顾脸面的蠢猪叫得声嘶力竭,实在难听。没办法,母亲只好把一些饭碗先刷出来,用没什么内容的刷碗水给猪拌食。叔叔走进院子,二话不说,搬起那块磨镰磨刀用的石头,朝猪食盆子砸去。石头的块头不小,恐怕有二十多斤重。叔叔一下子把猪食盆子砸碎了,里边的猪食溅了母亲一身一脸。叔叔的这一示威性的举动,显然是冲着母亲来的,石头虽没有直接砸到母亲身上,仍然波及母亲。母亲吃惊不小,跟叔叔吵了起来。吵架是一个热闹,听见母亲和叔叔吵架,住在同一个大院里的人纷纷出来看热闹。从院口路过的人也驻足观看。叔叔用石头砸猪食盆,是一种情绪的发泄。而在对待叔叔的事情上,母亲已压抑很久了,也需要发泄,母亲说:我做给你吃,做给你喝,哪一点儿对不住你?你凭啥这样对待我?让大家评评理,你凭啥拿石头砸我!母亲叫着叔叔的小名,骂了叔叔:我看你就是一只喂不熟的混眼狗。
叔叔和母亲对着吵。
这时父亲站出来了,父亲没有批评叔叔,没有帮母亲说话,反而让母亲住口,不要再吵了。父亲说:你们这样吵,不怕人家看笑话吗?
母亲正在气头上,气得已经有些刹不住车,她连父亲一块儿吵,说叔叔这样不讲理,这样欺负人,都是父亲给惯坏的。
当着那么多围观的人,父亲面子上大概有些下不来,大概要显示一点什么,他做了一样不应该做的动作。他这个动作把母亲给惹了。须知母亲是个内心很要强的人,是不好惹的,父亲却把母亲给惹了。他竟然动手打了母亲。他打的是母亲的头,打得有些不管不顾,在打母亲时,母亲发髻上带的银簪子把他的手给扎破了。说到这里,我有必要把父亲和母亲的婚姻简单交代一下。爷爷奶奶给父亲找过一个童养媳,因父亲长期在外边当兵不回家,人家童养媳就走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在父亲所在部队驻防的地方,有人给当军官的父亲介绍了我母亲。母亲见父亲一身军装,头戴大盖帽,显得挺威武的,挺精神的,就同意了。母亲当年十九岁,说起年龄来,母亲说她是属牛的。父亲说,他也是属牛的。既然都是属牛的,父亲正好比母亲大一轮,也就是大十二岁。大一轮就大一轮吧,那年头兵荒马乱的,闺女家的处境都是危险的,能嫁人就赶快嫁人。跟父亲结婚后,母亲才知道,父亲不是属牛,而是属鸡,不是比母亲大十二岁,而是大十六岁。母亲认为父亲没说实话,气得哭了一场。在这个事情上,父亲自知理亏,对母亲一直心怀愧疚。母亲跟随父亲当了两年太太,在新乡生下我大姐后,就带着大姐到了我们老家。老家的贫穷大大出乎母亲的意料,除了房子八下里漏雨,连做饭用的铁锅都漏水。母亲强烈要求父亲退伍还乡,要是父亲不还乡,她就走人。父亲退伍回家后,对母亲十分呵护。农忙时哪怕家里只煮一枚咸鸭蛋,父亲也要把咸鸭蛋切开,悄悄分给母亲一半。平日里,父亲连一句重话都不对母亲说,这日为了蛮不讲理的叔叔,父亲一时失去了理智,竟对母亲动了巴掌。母亲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委屈,她指着父亲说:好哇,你竟敢打我,我不跟你过了,我走!母亲说罢,抱起刚八个月大的妹妹,就走了。母亲的意思是要回到她的娘家去。
父亲定是收回巴掌就后悔了。他比母亲大那么多,年龄差距跟两代人差不多,平常爱护母亲唯恐不及,他怎么能动手打母亲呢?把母亲带到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穷得连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母亲不但没弃他而去,还跟他同心协力,共建家园,他怎么舍得打母亲呢?父亲不能让母亲走。母亲的娘家在开封附近的尉氏县,离我们老家有好几百里,那时又不通汽车,母亲得走几天才能走回家呢!母亲身上没带钱,她路上吃什么呢?喝什么呢?怎么住店呢?父亲一定得尽快想办法把母亲拉回来。
叔叔见势不妙,悄悄溜走了。
父亲有什么办法呢?他有了新的队伍,他的队伍就是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可以随时听候他的调遣。他对大姐、二姐和我说:快,快去把你们的娘给我追回来!
我们当然都不愿意让母亲离开我们,大姐、二姐和我跑着向母亲追去。我们追到村北一里外的北小桥上,把抱着妹妹的母亲追到了。我们有的抱着母亲的腰,有的抱着母亲的胳膊,有的抱着母亲的腿,顿时哭成一团。我们的哭吓着了妹妹,妹妹哭得更厉害。见我们都哭了,母亲也哭了。母亲哪里舍得离开自己的孩子呢,哭过之后,母亲领着我们回家去了。
父亲维护团结的想法宣告失败,和叔叔分家势在必行。父亲郑重请了三爷和一个在乡里当干部的堂叔为分家的管事人,开始一五一十地为父亲和叔叔他们兄弟两个分家。管事人把我们家的土地、房屋、牲口、农具、家畜家禽和一应生活用品平均分成两部分,父亲和叔叔各得一半。我的意思是说,只有父亲和叔叔他们两个人才是分家的主体,父亲虽然有妻子和四个子女,可我们好像只是父亲的附带部分,连一点儿参与分家的资格都没有。特别是我们姐弟四人,分家的主持者对我们是无视的,我们连一只碗和一双筷子都分不到。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家的家业,大部分是爷爷弟兄四个分家时分到的,是从太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的,可是,主持者在分家时,把爷爷也排除在外,爷爷一点份额都没有。爷爷明明还活着,他的两个儿子把东西分得干干净净,爷爷靠什么生活呢?三爷和堂叔给爷爷的出路是,让爷爷轮流到他的两个儿子家吃住,一个月一轮换,或半年一轮换。之所以不给爷爷留生活资料,是不好衡量留多少合适,也不知道留给哪个儿子合适。一下子把家产分干净,也是我们那里分家的惯例,免得留后遗症,免得老人去世后再二次分家。管事人明明知道,分家后爷爷不会到叔叔家去吃去住,因为叔叔视爷爷为敌人,父子俩一直是反贴门神不对脸,到一块儿就干架,可他们还是要这么分。父亲也清楚,爷爷一定会选择继续跟他生活在一起。父亲作为爷爷的长子,他自愿承担起奉养爷爷的责任,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他绝不会对爷爷有半点儿不孝。
叔叔闹分家的事,大概刺激了我的记忆,给我留下了一些印象。一个人对童年往事留下的印象,回忆起来必须有线索、抓手或细节,我的抓手是一只竹耙子。竹耙子是排列在一起的竹钩子,是我们那里每家必具的一种农具。这种农具像是农人延长的手臂和手指,麦收时可用来搂麦穗,搂麦叶,秋凉时可以到树下搂树叶。我们家的竹耙子是父亲一次赶三月三庙会时买回来的,母亲用过,大姐、二姐也用过。然而在分家时,竹耙子却分给了叔叔。这表明,分家分得很细,一砖一石、一草一木、一鸡一毛等,都被列入了分家的清单。母亲不想让叔叔把耙子拿走,不想日后看见耙子在叔叔的老婆手里拉来拉去,母亲怎么办呢?她想到了我,试试我能不能在保卫耙子方面发挥一点作用。母亲悄悄安排我说:等你叔来拿耙子的时候,你就说耙子是你的,别让他拿走。他就是硬要拿,你就哭,使劲哭!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有些重大,我说耙子是我的,这个我会说,但母亲让我哭,可能有一定难度。我从来没拉过耙子,对耙子一点儿感情都没有,我怀疑自己到时候能不能哭出来。结果我表现得还行,跟母亲配合得不错,没让母亲失望。记得我当时正睡在堂屋当门爷爷睡的小床上,小床里侧是用高粱秆编制的箔篱子,那只耙子就在箔篱子上方挂着。当叔叔来取耙子时,我就嚷起来,说耙子是我的,我还要玩呢,不许拿走,不许把我的耙子拿走!嚷着嚷着,我就哭了起来。哭是有惯性的,我一哭就有些收不住,哭得泪水横飞,嘴咧得像小瓢儿一样。母亲定是看出我有哭的潜力和能力,利用耙子的事情把我哭的潜力挖掘出来,把我哭的能力发挥出来。
我的大哭把父亲惊动了,把爷爷惊动了,把主持分家的堂叔也惊动了。须知父亲四十多岁了才有了我这第一个儿子,爷爷六十多岁了才有了他的第一个亲孙子,可以说我是穷人家的娇孩子,他们对我是很重视的。母亲利用的正是他们对我的重视,才让我配合她完成留住耙子的任务。母亲没安排大姐哭,也没安排二姐哭,母亲知道,大姐二姐怎么哭都没用,都不可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只有我的哭才是有效的。父亲除了让我别哭了,他倒不好说什么。爷爷不干了,站出来制止叔叔取走耙子,爷爷叫着我的小名,说我都哭成这样了,你怎么还好意思把耙子拿走!叔叔历来和爷爷对着干,爷爷不让他干什么,他偏要干什么。叔叔说,耙子分给了他,他就有权利把耙子拿走。三爷听见我的哭声过来了,三爷不但叫了叔叔的小名,还在小名前面加了一个小字,三爷说:不就是一只耙子嘛,你跟小孩子争什么!你今天要是敢把耙子拿走,我就用耙子拍你,跟拍一只蝇子一样!
叔叔的眼皮啪嗒了好几下,才放弃了取走耙子。他走的时候没有空手,把一架新窗棂子扛在肩上扛走了。两间新房没有盖成,父亲预备下的建房材料都分给了叔叔。除了窗棂子,还有梁、檩、椽子,以及苫房用的淮草等。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兄弟们在一起,不见得稳定,分裂了,就稳定了。一家人分成两家人之后,各家干各家的活,各家吃各家的饭,各家睡各家的觉,一天到晚谁都看不见谁,就不会生气了,也不会吵架了。父亲和叔叔原本是同根生,分家以后,他们像是由一棵树分成了两棵树,一棵栽在村北,一棵栽在村南,各自守着自己的位置,树干不相碰,连枝叶都不接触。母亲和婶子呢,也像一个是河水,一个是井水,我吃我的河水,你打你的井水,河水井水两不串,两不犯。大人之间这样如同陌路,难免影响到我们小孩子。在村子里,二姐带着我,我们可以随便到别人家去玩。可是,我们从不到叔叔家去玩。我们一看到他们家的房子,像看到一块危险的禁地,赶紧就躲开了。在村街上走,我们看见别的叔叔,会叫一声,看见别的婶子,也会叫一声。而一旦碰见我们的亲叔叔或亲婶子迎面走来,我们不理他们,他们也不理我们,脸一扭,或眼皮一塌,就过去了,看见跟没看见一样。不,看见跟没看见不一样,一看见他们,我们心里顿生别扭,别扭得似乎连心口都堵了。我们和叔叔家就是这样,根系上越近,关系上越是远;血脉上越是亲,感情越是疏。后来叔叔和婶子生了孩子,我们也不跟他们的孩子在一块儿玩。
1960年夏天,我们的父亲去世了。父亲去世时,父亲母亲已经有了六个孩子,大的才十几岁,小的才几个月。父亲的去世,对于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来说,像是天也塌了,地也陷了。我们狠哭,狠哭,哭得天也昏了,地也暗了。
听见我们的哭声,村里众多的叔叔婶子们纷纷到我们家看望我们,劝慰我们,并帮助我们办理父亲的丧事。在这个时候,父亲唯一的一个亲弟弟,也是我们唯一的亲叔叔,应该摒弃前嫌,到我们家看一下吧。倘若叔叔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去看望我们,我想我们会感动的。就算叔叔不愿搭理母亲和她的孩子们,他总该和他一娘同胞的亲哥哥最后告别一下吧。我父亲一直很爱护他,从没做过半点伤害他的事,他对父亲有什么可记恨的呢?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于情想不到的是,于理想不到的是,叔叔没去看我们,没去跟父亲告别,直到我们把父亲埋到老坟地里,我们的叔叔,他——他——他,连个面都没露。请相信我,我说的都是实话。要不是我的亲身经历,要是我不说,谁都不会相信,我竟然会有这样一位叔叔。天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爷爷的悲哀,在于活着的儿子对他不孝,而对他百般孝敬的儿子却先他而去。爷爷一直以父亲为骄傲,为依靠,父亲的去世,对爷爷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就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秋天,我爷爷也去世了。爷爷去世的前一天午后,我亲眼看见一只在我们那里被称为夜猫子的猫头鹰,驾着一股凉风,悄无声息地飞到我们家去了。猫头鹰的爪子抓在我们家中堂画的画轴上,两只张着的翅膀扶着墙,回过头来,两只大眼睛在骨碌骨碌转动,像是在搜寻什么。我刚要找一根高粱秆子把猫头鹰赶走,猫头鹰大概看出了我的动机,鬼魅一样飞走了。我从小就听大人说过,猫头鹰如果到谁家,谁家里是要死人的。病重的爷爷在屋当门的小床上躺着,已经不能吃饭。猫头鹰飞到我们家,是不是预示着爷爷要死呢?我把看到猫头鹰的事跟当队长的堂叔说了,堂叔吵了我,要我不要胡说。我知道堂叔对猫头鹰进宅的事是忌讳的,他越是不让我说,我越是担心爷爷会死。爷爷很喜欢我,我小的时候,他愿意把我揣在怀里赶集,给我买白馍吃。他去别人家请人家念唱书,也愿意带上我,让我给他捋胡子。我不想让爷爷死。
有经验的母亲开始征求爷爷的意见,看看爷爷还有什么最后的嘱咐,最后的要求。爷爷的要求是,要把他的藏书都放到他的棺材里去,他要用那些书枕头。母亲答应了,说他的书都给他带走。母亲问爷爷,要不要把叔叔喊来,跟他说说话,叔叔毕竟是爷爷的二儿子嘛!爷爷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的态度坚决而明确:不要跟他说,我不想看见他!我权当没有他这个儿子!
堂叔还是把爷爷病危的消息通知了叔叔。堂叔的意思,是让叔叔尽一尽当儿子的最后的义务。按我们那里由来已久的规矩,父母去世后,给父母送葬时,扛柳幡和摔恼盆的任务须由死者的儿子承担。爷爷的长子去世了,自然应该由叔叔顶上去代替执行。叔叔来到爷爷病床前,脸上似乎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笑意,他好像早就预料到爷爷会有这一天,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探头把爷爷看了看,没有喊爹,没有问爷爷的病情,对爷爷没说任何安慰的话,上来就说:你以前不是很厉害吗,现在不厉害了吧!
爷爷的手在发抖,爷爷对叔叔闭上了眼睛。
叔叔说:我说你不会做生意,做一次生意赔一次,你过去不愿承认,现在应该承认了吧!
爷爷的一只手抬了一下,像是要给叔叔指一下,让叔叔走。可是,爷爷像是已经没力气把手抬高,只抬起一点点,就掉落下去。
叔叔像是要对爷爷的一生来一个总结,他说:反正你的红旗从来没有插到过敌人的阵地上,你从来没取得过胜利,都是失败。
母亲听不下去了,对叔叔说:咱爹都病成这样了,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你这不是故意气他嘛!
叔叔冲母亲把眼一瞪:我说这些怎么了,我说的都是实话。
当天夜间,在门外阵阵秋风中,我们的爷爷就与世长辞。
随后在埋葬爷爷的过程中,叔叔又做出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我不得不略记几句。四个壮年男人在我们家的老坟地里为爷爷打好了墓坑,按照礼仪的规定,我们家的人须到墓坑前给打墓坑的人送去一些吃的。这是慰劳人家的意思,也是整个葬礼的组成部分和程序之一。程序规定,要给每个打墓坑的人送两个白馍,馍里要夹肉。程序规定,盛食品的容器不能用别的东西,只能用白柳条编制的五升斗。程序还规定,斗口上必须覆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能是笼布,不能是毛巾,也不能是木盖子,只能是盖斗馍。盖斗馍跟白馍一样,也是用小麦面蒸成的,只不过它是圆形的,面积大到得能盖住五升斗的斗口。我敢肯定,这些程序的规定都是有来历的,有讲究的,可惜我缺乏研究,不懂其中的含义,说不出所以然来。我看见了母亲蒸出的盖斗馍,我估计,蒸一个盖斗馍恐怕要使用相当于六个馍的面粉。盖斗馍暄腾腾的,样子有些像过年时蒸的枣山。两者的区别在于,枣山上镶嵌红枣儿,盖斗馍上什么都不镶。我吃过白馍和枣山,却从没有吃过盖斗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我们才能吃到白面做成的东西。在给爷爷办丧事期间,我们可以尝到盖斗馍的味道了。
给打墓坑的人送食品,三爷是指派叔叔去的。这也是叔叔应完成的任务之一。
叔叔倒是把食品给打墓坑的人送到了,可是,当叔叔抱着空斗和盖斗馍往回走的时候,走到半路,他大概闻到盖斗馍的麦香,前后看看无人,就拐进坑边的一片芦苇丛里,对着大面积的盖斗馍大吃大嚼起来。那么大一张盖斗馍,就算叔叔扯开肚皮吃,也吃不完。他大概觉得盖斗馍的味道确实不错,就把吃剩下的部分掰巴掰巴,掰成一块一块,放进五升斗里,拿回自己家,给他的老婆孩子吃去了。这就是我的叔叔,在有些事情上,他总是很有创造力,总能做出一些反常的、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听母亲多次说过,叔叔从小就不听话,行为就有些乖张。奶奶管不住他,就托四爷管教他。四爷也没什么有效的办法,他的办法就是打人。四爷趁叔叔不注意,或者在某个地方睡着了,走过去二话不说,操起硕大的铜烟袋锅子,在叔叔的光头上梆梆梆就敲那么几下子,把叔叔的头敲得很快就鼓起了几个枣核样的疙瘩。母亲的看法是,叔叔是生生被四爷打傻的。
爷爷已被放进棺材里。
叔叔拎着空斗回到了我们家。
谁家蒸的盖斗馍,应该由谁家的人吃,而且人人有份儿,平均分着吃。母亲一看盖斗馍没有了,马上问叔叔:盖斗馍呢?
叔叔没有任何不好意思,说盖斗馍被他吃掉了。
母亲不相信,说那么大一张盖斗馍,你怎么吃得完呢?
叔叔撒了谎,说他饿了,就吃完了。
这太不像话了,太不讲道理了,太不顾脸面了,怎么能这样呢?母亲向三爷告了叔叔的状,让三爷把叔叔管一管。
三爷也很生气,脱下自己的鞋,就要用鞋底子去抽叔叔。叔叔管不住自己的嘴,三爷准备抽一抽他的嘴巴子,让他的嘴长点儿记性。
叔叔不会让三爷抽到,见三叔要抽他,他拔腿就跑。他相信,三爷年纪大了,腿脚老了,是追不上他的。他并不跑远,回头见与三爷拉开了距离,三爷果真追不上他,他就停下了,样子似有些挑衅,仿佛在说:来呀,你追我呀,看看咱俩谁跑得过谁!三爷举着鞋底子再追他,他再跑。如此三番五次,弄得叔侄俩像做游戏一样,直到叔叔跑到了村外,三爷都没能追上他。
叔叔躲起来了,拒绝继续参加爷爷的葬礼。一切都准备好了,白花花的送葬人跪了一院子,主持葬礼的人都要喊起棺了,仍不见叔叔露面。这怎么办?爷爷的儿子不来,谁扛柳幡呢?谁摔恼盆呢?三爷和堂叔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再等那个不孝的叔叔了,由我母亲扛幡,摔盆。这事在我们那里说起来真是天大的笑话,死者的二儿子明明还活着,而死者葬礼的大旗却要由死者的大儿媳来扛。死者身后明明有男丁,死者葬礼的大旗却要由一个妇道人家来扛。母亲定是意识到她责任重大,同时难免想起我父亲,要是我父亲还活着,哪里会把她推到前台呢?于是母亲哭得非常痛心,非常非常痛心,她哭得几乎瘫倒在地,拉都拉不起来。
爷爷去世后,我们家和叔叔家更疏远了。每当想起还有一个叔叔,我都感觉有些出乎意料似的。对了,我想起来了,叔叔家和我们家相联系的,还有一盘石磨。在分家时,别的东西都分清了,只有这盘石磨没有分。往上追溯,这盘石磨属于大爷爷家和我爷爷家共同所有,共同使用。到了父亲和叔叔们这一辈,石磨仍是共同财产。这就是说,石磨有大爷爷的儿子堂叔一份,父亲和叔叔没有权利分配这盘石磨。再说石磨也不好分,如果拆开分给东家一扇,西家一扇,石磨就失去了使用价值。倘若把石磨整体性地分给一家,那别的人家怎么磨粮食呢?父亲生前在我们家的堂屋对面盖了一间南屋,那盘石磨就支在我们家的南屋里。叔叔家也要把粮食磨成面,叔叔推磨只能到我们家的灶屋兼磨坊里去推。我注意到,不管是夏天外面下着大雨,还是冬天下着大雪,推磨都是叔叔一个人推,婶子从来不帮他推。我们家推磨,差不多是全家人一齐上。叔叔推磨,从始至终都是他一个人。夏天他光着膀子,赤着脚,一个人就把磨推得呼呼的。石磨的上扇与下扇犬牙交错,粒粮不饶人,推起来是很沉的。这说明当过兵的叔叔还是有一把子力气的,推起磨来也是有耐心的。
叔叔和婶子的关系并不好,他们一天一小打,三天一大闹,日子基本上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我怎么会看到叔叔打婶子呢,因为他们的“战事”只是在家里进行还不够,还把“战火”烧到村街上去了。有一回,我看见叔叔在村街上把婶子打得披头散发,头破血流,仍不罢手。叔叔大概是推磨推惯了,他像抓磨棍一样抓住婶子的脚脖子,在地上推起磨来。他把“磨”快速推了一圈儿又一圈儿,一边推一边骂婶子。不知叔叔从哪里学来的骂法,他的骂极具个人特色,我们村的人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骂人,他骂的是:我操你的黑娘气,我就不信战胜不了你!
由于叔叔和婶子在村里人际关系恶劣,不管叔叔怎么揍婶子,怎么把婶子在硬地上推得团团转,村里没有一个人上前劝架。村里人愿意远看,也愿意近观,人们微笑着,都是看笑话的表情,都是欣赏的表情。婶子被男人推得肯定不好受,她肯定希望能有人站出来,制止一下叔叔野蛮的“推磨”行为。然而那些看“推磨”的男人和女人们才不会帮婶子说话呢,他们希望叔叔持续地把“磨”推下去,能把婶子身上的“面粉”或“豆浆”推出来才好呢!既然没人劝架,他们自己燃起的“战火”,最后还得靠自己熄灭。
叔叔的故事写到这里,已经不算短了,我回头看了一下,似乎已超出我通常写一个短篇小说的篇幅。通常写短篇,我一般写八九千字,超过万字的短篇就很少。这个短篇写到这里,一万四千字都多了,我还要不要继续写下去呢?真正有意思有分量的故事还在后头呢,激烈的矛盾冲突还没有写到呢,不继续写可是太可惜了。跟二姐说起叔叔的故事,二姐说他的故事太多了,写一部长篇小说都使不完材料。那么就请读者朋友们付出一点耐心,允许我把这篇小说写完整。我不会把它写成长篇,也不会把它写成中篇,字数还是控制在一篇短篇的字数范围内。但我也不会为“适履”而“削足”。
说话就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大革命当然有大运动,一开始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堪称是大运动。之后还有一系列的小运动,小运动包括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文革”到来时,我正读初中二年级,我是这些运动的见证者,或者说是直接参与者。我知道,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还有讲用、全家红等更细化的运动。何为讲用呢?当时的说法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你活学了,活用了,还要讲出来,讲给大家听,这就叫讲用。何谓全家红呢?一家人当中,只有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那称不上全家红。全家人都是积极分子,才称得上全家红。比如说吧,我二姐已经是大队、公社、县里和地区四级学毛著积极分子,她一个人红,只能是个人红,不能算是全家红。在二姐的带动下,我们全家都红了,才算是全家红。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全家红竟然落到了我们全家人的头上。而且是全公社唯一一家全家红。后来我才知道,哪个公社都必须有全家红,这是县革命委员会交给公社革命委员会的政治任务,如果哪个公社挑不出全家红来,就是没有完成政治任务。当时天天讲突出政治和政治挂帅,完不成政治任务可不行,各公社千方百计也要完成政治任务。
当公社把我们家定为全家红时,我深感意外,心里难免有些忐忑不安。村里有的人在背地里说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是历史反革命,公社让我们当全家红,把我们推到风口浪尖上,那些人心里怎么能平衡呢,这不是明摆着让人挑刺嘛,遭人嫉妒嘛!如果替公社领导想想,他们要在公社范围内挑一个全家红,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条件是,全家每一个人都得会讲用。讲用说的可不是普通的家常话,家常话谁都会说,猫呀,狗呀,吃饭了,睡觉了,可以张嘴就来,看见什么说什么。讲用者先要背诵毛主席语录,先要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再开始讲用。讲用的内容必须符合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讲用的话是一些字话,政治话,甚至是抽象的话。这样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能说。特别是一些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一句这样在台面上说的话。我曾在村里当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有一段时间,我和别的辅导员按照上级要求,在村口设卡,凡是出村去干活儿的社员,必须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如果不背,就不能出工挣工分。所背的语录,一般来说是比较短的,如: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还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别看语录这么短,让一些婶子背语录难得很,比让她们过鬼门关都难。为了能帮有的婶子度过这一关,放他们下地挣工分,我只好在设卡处临时教婶子。我像教一只小鸟儿一样,掰着小鸟儿的嘴教语录。我想有的婶子就算是一只小鸟儿,我教上十遍八遍,她也应该能学会吧。可有的笨婶子不是牙咬了舌头,就是舌头咬了牙,死活都学不会。有的婶子鹦鹉学舌时倒是能学下来,可你让她背一遍时,她一放下舌头就忘了,干瞪眼说不出话来。这样的婶子们,让她们登台去讲用,那是不可能的。而我母亲虽说也不识字,但她有着很强的记忆力,一段毛主席语录,她听三遍五遍就记住了。母亲能连着背好几段语录呢。我大姐、二姐更不用说,她们都上过三年小学,可以读整本儿的毛主席著作。当时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功夫。大姐、二姐真的称得上千遍万遍下功夫,她们不仅会背很多条毛主席语录,把称为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都背得滚瓜烂熟。我们家的大多数成员都具备学习的能力和讲用的条件,公社在挑选全家红时,就把我们家选中了。设想一下,要是我父亲还活着,出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全家红是绝对不会让我们当的。别说当全家红了,不被说成全家黑就算不错。因为父亲不存在了,他的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似乎暂时可以忽略不计。让我们当全家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荣誉,同时也具有政治任务的性质。政治压倒一切,当然很厉害。对于公社交下来的政治任务,我们不能有半点儿犹豫,半点儿推辞,只有接受的份儿,服从的份儿。
当了全家红,为了便于接受训练和到下面的大队讲用,我们全家住到公社去了,跟公社干部在一个食堂吃饭。公社每月发给我们每个人十五块钱生活费,我们每天都能吃到白馍和炒菜,生活真是好到天上去了。我们不用风里雨里下地干活了,按公社要求,生产队却要给母亲、大姐、二姐和我一天不落地记工分,计满分。
这样一来,我们村有的人坐不住了,睡不着了,他们开始互相串联,煽风点火。凭什么?凭什么?他们家的人凭什么吃好的喝好的?凭什么领公家的钱?凭什么给他们记满分?这太不公平了,太不合理了!说来村里真是有高人,高人的手段真够绝的,他们不但说服了村里的干部,还把我叔叔动员起来了。他们定是认真研究过了,认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自家人打自家人才最能打到痛处,才最有力量。他们说叔叔当过志愿军战士,是革命派。我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官,是反动派。只有革命派站出来,才能打败反动派。我们家的人不是在讲用吗,他们撺掇我叔叔也出来讲用,也斗私批修。通过叔叔的讲用,正好可以和我们家唱对台戏。现在想想,那真是一场闹剧啊,真是比荒诞还荒诞啊!不知他们在背后下了多么大的导演功夫,不知他们许给了叔叔什么样的利益,反正叔叔还真的把对台戏唱成了。叔叔不但在我们村讲用,还到全大队的社员大会上讲用。叔叔背诵的毛主席语录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一开讲就向自己家的人发起攻击。他说我爷爷不务正业,热衷于听封资修一类的唱书。他说我父亲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往家里寄的钱都是银圆。他揭发我母亲当过反动军官的随军太太,是隐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在斗私批修阶段,他主要讲自己怎样利用在部队学到的本领,在夜色的掩护下偷东西。他爬到高树上,偷过别人家挂在树杈上的玉米串子。在打麦场上,他趁看场的人都睡着了,以匍匐前进的战法接近麦堆,以裤子作口袋,偷生产队的麦子。叔叔的讲用,赢得了听众热烈的掌声。
说心里话,我并不愿意让我们家当全家红,自己也非常不愿意讲用,每次讲用内心都别扭得很,都老大不高兴。为此,一位公社干部找我谈过话,曾严肃警告我: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回想起来,我当时对讲用运动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并不知道那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是自欺欺人和对群众的愚弄。我只是凭直觉感觉到,我讲的并不是自己想说的话,并不是真话,而是大话,套话,是别人要我说的话,是符合潮流的话。这有点像吃东西,吃东西是人的一种本能,说话也是人的一种本能。看见不好吃的东西,我们会不爱吃,对于自己不想说的话呢,本能上也不爱说。
我还想过,村里有的人反对我们当全家红,并抬出叔叔当枪使,和我们作对,是不是代表一种民意呢?他们的做法是不是更接近正义?或者说更接近真理呢?其实不是,根本不是。他们也没有那样高的思想水平,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还是出于狭隘的私利,出于人性中的嫉妒之心。
叔叔出来打横炮,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二姐。此前,公社已准备让二姐在供销社里当营业员,吃商品粮,连参加工作的表格都填过了。叔叔那么一胡闹,上级就要对二姐重新进行政审。政审者到县里和地区查找我父亲的档案,虽没有查到证据证明我父亲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二姐参加工作的事儿还是被否定了。这是二姐跳出农门往上走的唯一一次机会,这个机会如果能够落实,凭着二姐的心劲和智慧,说不定会有很好的前程。然而叔叔却把二姐的前程毁掉了,一辈子的前程都毁掉了。这是二姐心上的一个痛点,每每忆及此事,二姐都痛惜不已。至于我自己所受到的不利影响,我就不说了。
叔叔把他的侄女和侄子们害成这样,他还能怎样呢?还能怎样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跟我们这些失去父亲的孩子过不去呢?有一天下午,我听一个堂哥说,叔叔生病了,拉肚子拉得快不行了。婶子不管叔叔,像是在等叔叔死。听到这个消息,不知动了哪根弦,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带叔叔去看看病,利用亲情感化一下叔叔呢?我真的找了一辆架子车,把叔叔拉到大队卫生所去了。我经常去大队开会,还参加过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跟大队卫生所的年轻医生比较熟悉。医生马上给叔叔打了消炎针,接着又给叔叔输了两瓶水,叔叔的命就保住了。连婶子也不得不承认,要不是我把叔叔拉到卫生所去看病,叔叔就活不成了。我这样做,把叔叔感化了没有呢?他是不是有所回心转意呢?没有,叔叔对我们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我去煤矿参加工作离开家之后,叔叔竟变本加厉,攻到我们家里去了。我没有亲身经历叔叔的攻击,一些情况是弟弟后来对我讲的。叔叔在夜间潜入我们家的院子,爬到我们家门前一棵高高的椿树上,将一杆红旗绑到了椿树枝头的最高处。叔叔的用意显而易见,他套用的是战场经验,谁把敌人的阵地攻下来,并把标志胜利的红旗插到阵地的制高点,阵地就属于谁。
母亲早上一开门,就看到了椿树枝头飘扬的红旗,同时看到婶子带领她的孩子们堵到了我们家的门口。婶子倒没有冲母亲和弟弟喊什么口号,但她提出的要求跟喊口号的性质差不多,他要求重新分家。她的几个孩子也跟着要求:分家,分家,分家!
家早就分得一清二楚,连一分一厘未分配的东西都没有,现在又要分哪门子的家呢?母亲当然不答应,跟婶子吵了起来。身体已经强壮的弟弟,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保卫母亲和家庭的责任,他以一夫当关的勇气,把婶子一家赶走了。
婶子的要求没有得逞,就到村干部那里去吵闹。婶子还向村干部告状,说我弟弟打了她,打了他儿子。
让人不能理解的是,村干部让我母亲破费点儿钱,堵堵叔叔和婶子的嘴,权当买个安宁吧。
母亲问:为什么?
村干部的解释一点儿都不让人信服,村干部说:你大儿子在外面当工人,能挣工资,你们家的日子比他们家的日子好过嘛!
说来说去,几经周折,母亲还是极不情愿地拿出了一百二十块钱,通过村干部给了叔叔。
这个钱不是我给母亲寄的,是母亲和妹妹喂了一头猪,妹妹天天下地割草,把猪喂了一年多,才卖了一百二十多块钱。母亲等于把她和妹妹辛辛苦苦喂猪挣的钱几乎全部给了叔叔。
我回家探亲时,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我越想越觉得悲哀,竟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嚎啕大哭起来。
我的哭把院子里的人都惊动了,他们不知道我为何这样痛心。有人说我是心疼钱,有人说我是心疼母亲,还有人说是父亲的魂附在我的身体上了。他们的说法只能让我悲上加悲,痛上加痛,哭得更厉害。
谁能知道我为何哭得如此悲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