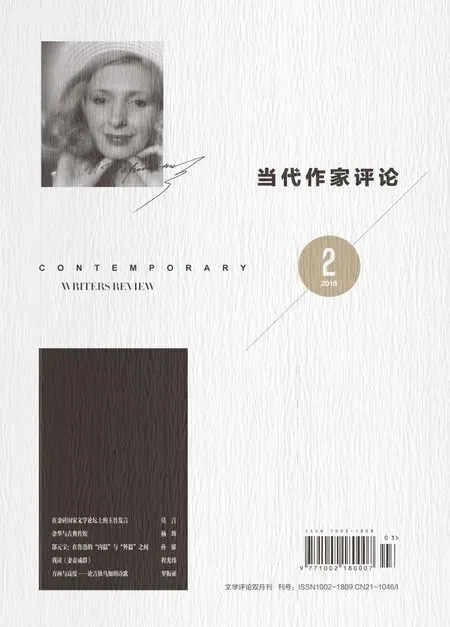重塑经验、想象和时代
2018-11-13印度美瑞杜拉嘉戈MridulaGarg
〔印度〕美瑞杜拉·嘉戈(Mridula Garg)
姜 肖 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你们让我来谈谈“新时代,新经验,新想象”和金砖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我想,文学非“新”而不可为,换言之,如果文学不能把“旧”重塑为“新”,那么文学便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用梵语“波罗迦耶 布罗崴什”(Parkaya pravesh)来解释,文学即是你的灵魂或无意识突入另一个肉身或者意识中。
但“波罗迦耶 布罗崴什”又不仅仅意味着遵循他者的规范,更多意味着借此生成新的个体。文学书写“自我”,“自我”与我们共在。有时,在眨眼的一瞬间,我们会发现,意识中那个遥不可及的个体,恰恰就是我们自己,而这便是冥冥中存在的另一个自我。这也正是我们创造文学或者艺术的初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征服了时间,让它恣意流逝,又归于无常,或称之为永恒变换。这就是我的小说《无常》的含义。万物皆变换,过去或现在终属无常。我们在某一个时代写就的文字,也许会在很久以后的某个时空中脱胎为真实,至少对我的许多小说而言是如此。
同时,文学存在于“边缘”。“边缘”意味着时间与空间的向心离散,它并不是一个单一而固化的实体。在边缘的内部,又存在着许多无形的边缘,充满生命力地繁衍生息。边缘的存在意味着分歧,而分歧是文学和社会变革的动脉。尽管边缘往往受“中心”牵制,但至少边缘是可见的。然而,不幸的是,当我们试图弥合边缘,让每个个体都宣称自己是中心时,这种强大的复仇行为恰恰在创造另一些边缘的同时,将我们自己推离了边缘,让我们身处的边缘不复可见。
实质上,恰恰是当我们处于众多隐性边缘的簇拥之中时,我们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文学和艺术,惟其如此,我们才得以摆脱那些建立在文学与社会之间的重重屏障,在边缘之间自由徜徉。当然,当我们身处边缘时,往往感受到巨大的压迫,我以为,压迫感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有益的,但是这种压迫感不应缘于偏见,也不应期待仁慈,更不应期待怜悯,我们期待的是一视同仁。任何文学都应该得到同样的珍视,尽管这绝非易事。悲哀的是,对于那些在边缘徘徊的人们而言,他们往往必须不断坚持证明,尽管自己被边缘化了,但是自己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这正应成为此次金砖国家文学论坛的主要议题之一:未来,这样的“自我证明”将不必存在。在巴西、印度、南非、中国、俄罗斯的文学中,难道还缺少足够的例子来证明,这些创作正在把西欧文学和美国白人文学,或是那些居于中心位置的文学推向边缘吗?
每个作家与生俱来的使命,就是使那些被边缘化的文学成为读者心目中的中心。让读者们决定读什么,怎样的文学将被传唱,怎样的文学将被时代遗忘。当然,这种选择也没有恒定的准则,顺时而变,那些被遗忘的文字也有可能会涅槃重生,颠覆昔日的偶像。文学无暇顾及他者,除非认可“边缘”是文学的核心。但这种认可绝非来自于强权,而是那些处于边缘的作家们,其才华远胜于那些自持为中心的人们。毕竟,究竟何谓边缘,又何谓中心,这取决于每个人的视角。从边缘的侧面观察,视野就会变得更为宽广,若给边缘更多的空间,边缘便会不断拓宽,最终你会发现,边缘不断扩展直至占据所有,中心的比重则所剩无几。
我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对作家这个特殊身份的认识,可以说:“解构我所有的经验、感情和感知。无论我在创作中谈什么,我也可能马上否认,因为选择何其多样,已知的或未知的,真实的、有经验的或想象的,这些都与我刚刚所写、所言、所经历的如出一辙。”
这就是文学:体验另一种自我;包容创造和变革中的异同。毋庸置疑,边缘不仅仅生发于根系,而且应时而变。一旦我们根系已定,便会坦然迎接任何变换。我们应该认识到,艺术与文学的根系越深广,便会越发表现出同一性。也正是缘此,身处边缘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更有可能带着他们的创作走向世界文学和艺术的中心。这就是我对于文学“多样性”的信念,毕竟,文学本非天成之实体。向金砖国家文学致敬!向文学多样性和“波罗迦耶 布罗崴什”精神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