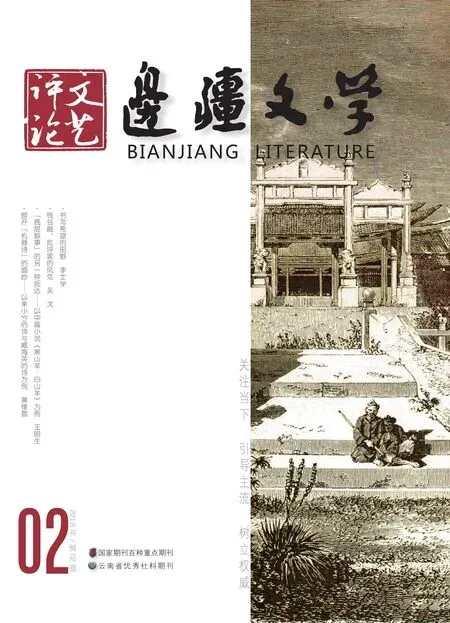后现代戏剧的叙事视角与不确定性
2018-11-12严程莹
严程莹
如果说我们把戏剧性理解为观众兴趣的建立与保持,那么,传统戏剧的戏剧性主要是以悬念为表征的冲突论,现代派戏剧是以变形为表征的怪诞论,那么,后现代派戏剧的戏剧性则是以含混为表征的不确定论。同样属于后现代派戏剧,荒诞派戏剧的不确定性是由非逻辑化的表达引起的,剧作家参与其中的痕迹较重,是剧作家故意不交代或自我否定式的交代。叙事戏剧在表达上是逻辑化的,不确定性主要依托叙事人的身份特点和视角差异来形成,是由人物引发的,与作者基本无关。一般情况下,后现代戏剧利用叙事人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来制造不确定,形成戏剧性。
一、病态人物造成的不确定性
病态人物担任叙事人物,有可能将情节和意义引向一种不确定状态。情人眼里出西施,因为他们的偏执、疯狂,他们眼中的世界也相应地呈现出病态特征,从而完成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性表达。谢弗《马》中的狄萨特、《上帝的宠儿》中萨利埃里都是不正常的人,都是心智不健全的人,他们视角之下的世界必然扭曲变形。狄萨特由于缺乏艾伦那样的勇气,因此他对这个少年充满了好奇和同情,甚至还有一丝崇拜。萨利埃里是一个心有妒忌之火的小人,在他眼中,莫扎特当然处处显示出不落俗套的出格之举。
这里还可以提到德国剧作家魏斯的剧作。1963年魏斯创作了全名为《由马尔基德萨德导演的夏郎东疯人院病人上演的迫害与残杀马拉》,也选取了一群病态人物作为叙述人。马拉与萨德历史上确有其人,马拉是个激进的革命者,萨德是个虚无主义者。萨德是马拉葬礼的主持者,此人喜欢写一些散文和戏剧,后来他被关进了夏郎东疯人院,在那里他给一些病人排戏。萨德的这段经历启发了魏斯,萨德如果排演马拉被刺是什么效果呢。于是,一出别出心裁的新戏剧就这样诞生了。《马拉/萨德》表现的是1808年在巴黎近郊的夏亨顿精神病院里,一群疯子在演出。戏里的故事讲的是发生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中的一起政治谋杀,即马拉被刺。在这部戏剧中,萨德出面邀请疯人院的疯子排演马拉之死的故事,他自己充当导演。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马拉由疯子扮演,马拉的革命言论成了疯言疯语,萨德观点与此针锋相对,却是在排戏,萨德是在想象中与马拉进行思想交锋。马拉的话被疯人说着,观众如何能信,萨德振振有词,却是对着一群疯子大发感慨,言语的有效性何在。
疯子的语汇使导演拥有了一种特殊的自由,因此布鲁克在导演这出戏时认为,“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你实际上说什么都可以。在疯人之中,你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你可以说极为危险和疯癫的事。总之,可以说一切的事,而同时你又可以说些极力想人们愿意听的政治上蛊惑人心的事。”演员们时而扮演痴傻癫狂的疯子,时而扮演暴民、贵族、革命者,舞台上呈现出来的是一片杂乱、喧闹。既有咏叹调式的大段台词,又有诙谐、滑稽的语言处理。既有中国戏曲写意的形体动作,又有荒诞式的表演手法。剧中还有杂技、歌舞、梦呓,并充满了随意性,这是一出非常复杂的戏。严肃与嬉闹、高贵与庸俗、精致与粗糙对立交错。剧本的意义就在这种怪诞的空间里变得不确定,是疯子把历史史实歪曲了,还是历史本身就是由疯子创造的,谁也不知道,萨德的行为无疑是一场闹剧。
二、回忆造成的不确定性
常人的记忆总是飘忽不定,难以确切,特别是一些年代久远的事情,我们的回忆显得更加的不可靠。所以马克·柯里认为,“自我叙事的可靠性有赖于叙事者与所叙内容之间在时间上的距离,但如果叙事要使人相信,就得牺牲叙事的自我意识表现出来的天真。”叙事体戏剧的剧作家也有这样的实践。
《皇家太阳猎队》中的人物都是真实的,历史上的皮萨罗远征军不过一百六十多人,而阿塔华坡的印加帝国却有六百万人口,而且皮萨罗是个拜金主义者、淘金人,并不是什么精神文明的追求者,皮萨罗一收到印加王国的赎金,就杀掉了作为人质的阿塔华坡。但这个事件却是由一个虚构的人物讲述出来的,本身就值得怀疑。同时,在这部剧作中,谢弗还改变了皮萨罗到达南美的动机,属于有意歪曲历史,殖民者皮萨罗不远万里来到南美,不是为了寻求黄金而是为了寻求信仰。作者将目光投向了非历史的神性世界和精神家园,皮萨罗在印加找到了信仰,又丢失了信仰。找到信仰后,他脱去了冷漠的外壳、洗涤了玩世不恭的心,再造了灵魂。印加王朝不死的神话在剧中只是一个背影,一个搭建戏剧情节的平台。剧中的老马丁既是此行的幸存者、亲历者,又是故事的叙述者,少年马丁是当年跟随西班牙征服者首领皮萨罗作战的传令兵,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少年马丁带着我们走进历史事件,老年马丁又把观众拉回到现实中来,过去与现在就这样交织在我们面前,他们相互补充,有时又相互抵触。当少年马丁从剧情中走出成为老年马丁时,他就是布莱希特所说的“车祸目击者”,向我们讲述过去发生的事,可惜他已经老态龙钟,往日的记忆逐渐腐蚀,只留下了一些断断续续,甚至根本不可靠的记忆碎片。
所有人都像凝固了似的。
老年马丁:死的尘土,它就在我们的鼻子里。令人恐惧的感觉来得这么快,像一场瘟疫一样。(众人都转过头来。)所有的人都挤在广场周围的建筑物中。(众人都站了起来)他们站在那里,浑身发抖,随地大小便。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所有人都处在绝对静止状态。)五个小时过去了,印第安人的营地里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的军营也鸦雀无声。一百六十个人,全副盔甲,骑兵已上了战马,步兵整装待命,大家都站在死一般的寂静中等待。
皮萨罗:要坚持下去,听着,你们是上帝,要鼓足勇气,不要眨眼睛,不要吵闹。
老年马丁:七个小时过去了。
皮萨罗:不要动,不要动,你们要自己管住自己。孩子们,你们不再是农夫了,你们的机会来。抓住它,别把它放走。
老年马丁:九个小时过去了,十个小时过去了。大家都感觉到寒冷在浸透着我们的躯体。
皮萨罗:(悄声地)派他去,派他去,派他去。
老年马丁:夜风嗖嗖,恐惧感油然而生。神父的手臂也失去了效力。
皮萨罗:太阳正慢慢地落下去。
老年马丁:没有人看一下自己身旁的人。后来,夜的阴影朝我们扑来。
少年马丁:他们来啦,瞧,他们下山了。
德索托:有多少人?
少年马丁:有几百人,先生。
整个剧情都操近代在老年马丁的手中,他带领着观众回到从前那段时光,他所承担的功能正是把观众从过去带回到现在,而少年马丁的表演却又让观众从现在回到过去,他们一近一远,穿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英国的斯托帕德创作的《戏谑》也是如此,它的叙述人是图书馆的一名老管理员卡尔,由他回忆查拉、列宁和乔伊斯在一起的日子。可惜这个老管理员记忆力衰退,带给我们的是一段残缺不全的往事。
三、视角差异造成的不确定性
在叙事人的设置上,我们说存在一种分裂式的视角,就是由两个以上的叙事人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同一件事情,或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去叙述同一件事,他们的视角可能会因为各自的秉性差异造成一种不确定感。也就是说,传统戏剧中叙述视角的统一性被叙事人物的多重性破坏了,就连旁观式和固定式视角也因为过于强调独断和单一而被彻底颠覆了、解构了。
在《安道尔》中,整个十二场戏可以看作是“众人眼中的安德利”,每场戏都把不同人物与安德利的接触作为重点,从而构成了安德利生活的一个个片断的组接,场与场之间相对独立,单独存在。但就整个剧情来看,却又保持着整体情节走势的向前发展,即安德利一步步走向死亡。也就是说,场与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具有视角的统一性,更多地表现为平行关系。这种情节发展的非连贯性特征,与叙事体戏剧不追求情节的完整性相关。但对于弗里施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按照布莱希特的理论行事,而是对其进行了某种改造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剧作就整体情节来说也是完整的,但场与场之间缺乏布莱希特式的递进关系,而表现为一种平行关系,可以说,他走在传统戏剧体戏剧与叙事体戏剧的中间道路上。在这部剧作中,安德利死了,但每一个人都声明不对这件事负责,那么,究竟谁应该对安德利的死负责呢,弗里施并没有给出答案,只是理智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让观众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得出结论。观众一边看戏一边思考,从而把自己从安德利之死的悲伤中解脱出来,将关注的焦点更多地放在致死原因的分析上。
海纳·米勒《任务》中至少出现了四个叙述人,从而形成四个叙事文本。第一个叙述文本是剧本刚开始时格隆狄写的信,这是以格隆狄的视角进行的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他和其他两位战友的情况,水兵与安东尼的对白是对那份信的补充。第二个叙述文本出现在第一幕与第二幕之间,是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描述我们初到牙买加时的情况,它虽然在叙述人称上与第一幕相似,都是第一人称,但它已经变为复数,可见这个视角就不再个人性的了,而是扩大了的视角。这一幕中三个人的讨论和伪装身份的场面是对第二叙述文本的戏剧性展示。第三个叙述文本是第三幕与第四幕之间,这个叙述文本相对较长,也是第一人称叙述,但叙述者不是剧中人,也不是全知全能的旁观式视角,而是一个身份不明的现代欧洲人,他叙述的内容也似乎与剧情无关,但这个叙述的经历和心态与狄波逊十分相似,他们都对一个不存在的任务产生怀疑和绝望,这实际上是第三幕叙述内容的隐喻。第四个叙述文本是第四幕之后,是第三人称有限制的叙述,以剧中象征性人物即第一情人对狄波逊的引诱及背叛革命为主要内容,这一幕的叙述内容是这个叙述文本的延伸。可以看出,这四个叙述文本的角度和限度各不相同,从而使各个段落成为相对独立的叙述片断,叙述角度的统一性被取消了,这些异质化的片断被拼贴在一起,具有拼贴戏剧的特征,体现了后现代艺术以破碎形式对抗破碎世界的艺术态度。德国威尔什说:“后现代艺术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世界知觉方式的改变。世界不再是统一的,意义单一明晰的,而是破碎的,混乱的,无法认识的。”也就是说,布莱希特的插曲式片断由于叙述角度的内在统一仍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海纳·米勒的叙事片断由于叙述角度的频繁变动,内在的统一性也取消了,场与场之间完全是异质的。打个比方,他们的剧作都是一个由碎片重新拼贴而成的整体,布莱希特的花瓶的碎片来自于原先同一个完整的花瓶,而海纳·米勒的花瓶的碎片却分别来自于原先几个完全不同的花瓶,这些花瓶不是同一个型号,甚至不是同一窑或同一时间烧制的。
《哥本哈根》试图解开物理大师海森堡1941年去哥本哈根拜访老师玻尔所留下的历史谜团。海森堡、玻尔及玛格丽特的亡魂重聚在一起,谈论1941年的战争,谈论哥本哈根9月的一个雨夜,挪威滑雪场的比赛,纳粹德国的核反应堆,同盟国正在研制的原子弹;谈论量子、粒子、铀裂变和测不准原理,谈论贝多芬、巴赫的钢琴曲;谈论战争期间个人为国家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原子弹爆炸后城市里狼藉扭曲的尸体。原子弹的研制和爆炸使两位物理大师深陷精神地狱,他们背负道义的重压难以解脱。因为房间里被安装窃听器,他们的谈话无法展开也无法深入。这次神秘的会见对以后的原子弹研究和制造,对以后的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海森堡到底跟玻尔说了什么,他们的亡魂无法说清楚。他们在寻找、回忆、思辨,不断回到前生,回到往昔,求证他们想要的答案。“哥本哈根会见”被三个幽灵演绎了四次,但每一次都提出不同的可能性。他们不断地重回1941年的傍晚,面对当年的困惑,但结果总是陷于迷雾,直到最后都没能找到确切的答案。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如何面对这个道德的两难选择:国家抑或良知。战后三十年,海森堡作为一名曾帮助纳粹从事核研究的科学家,他的命运是悲惨的,陷入了数不清的辩解和解释中,可是需要辩解的仅仅是海森堡一人吗?波尔这个真正在制造原子弹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面对当年无辜百姓受害的局面,能够仅仅逃到战争受难方的外衣里,逃脱良知的责问吗?于是剧中人物一次沦入到自我辩解的怪圈中,连灵魂都无法逃脱。而这一次次辩解,一次次“让我们再来一遍”,追寻当晚的真相,却如同海森堡发现的测不准原理那样,永远无法达到事实的临界点。在每一次的事实重演中,我们都看到了两人谈论了许多话题,再一点点地靠近那个不能触碰的往事之痛。但是每一次的事实重演都不是事实,而展现了科学家对一些古老命题的思考:关于爱,关于良知,关于国家,关于真理,关于人性,关于父子。
总之,以这些病态人物或老人为代表,当代叙事制造了一种不可靠的信息。“当代叙事理论普遍认定这样一个思想,即叙事只是构筑了关于事件的一种说法,而不是描述了它们的真实状况;叙事是施为的而不是陈述的,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与传统戏剧叙事相反,后现代戏剧叙事只陈述对事件的一种看法,而不是还原事件本身。因此,这是一种极具自我意识的叙述。
【注释】
[1] [英]斯泰恩《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三),第743页,刘国彬等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
[2] [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第130页,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柳鸣九主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第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4] [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第130页,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