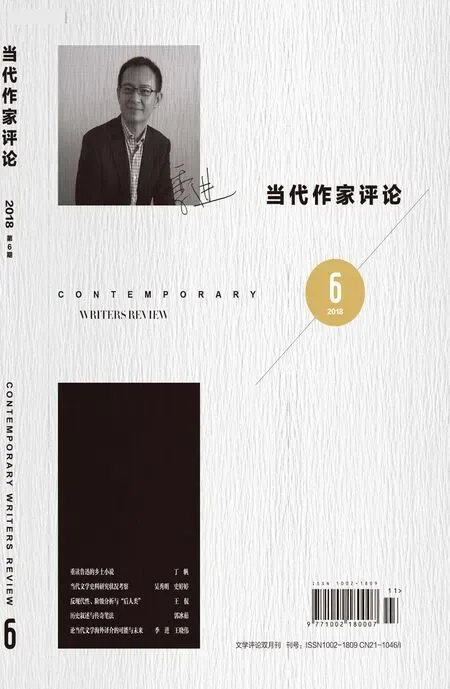经验的光晕与小说的指纹
——论陈河小说创作
2018-11-12梁豪
梁 豪
一
自古而来,文学的诗性与生活的世俗性便是一对欢喜冤家,彼此相生相克。一类作家的写作将琐碎的世俗经验视作羁绊,欲以“自由人”的心境和身份重拟文学的经验,此类写作放达空灵,纵横驰策间,常有意外之喜。另一类作家的写作痴缠于世俗的声色,与生活保持黏腻的暧昧,文学脱胎于生活,它是生活的直系子嗣,能在人群中唤起血缘的感动。陈河的创作当归后者,这位哆啦A梦般口袋里塞满各色素材的华人作家,用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叩开文学的惊奇之门:万物迥然相异,然万物与我为一。梳理、清洗生活现场的痕迹,勘察、发掘适合文学的道具和布景,运算出世人共通的情感品质,这是陈河的小说哲学,也是他的生活哲学。写作及其前期的介入姿态(观察、悬想、资料搜集)是陈河的生活日常,而生活则随时准备为这位经验的信徒奉上灵感的琼浆。
记忆对于写作者而言,特别是在其早期写作中,无疑是最稳妥也最浓烈的灵感来源。但在陈河这里,记忆的保鲜期之长,附加值之丰沛,在作家中并不多见。陈河的小说大致可归分两类,一类是从个人经验出发的现实小说,将人物投放在与亲身经历紧密关涉的特殊时局或异质情境中,状描他们身在其中的意外、惊叹和调整,比如《红白黑》《布偶》《西尼罗症》《猹》《黑白电影的城市》《南方兵营》等;一类是从资料素材出发的史类小说,重在资料的收集、消化和反刍,以期查缺补遗,唤醒被历史主潮的滚滚尘嚣遮蔽的“小众”史料,比如《沙捞越战事》《外苏河之战》《甲骨时光》《怡保之夜》等。不管是哪一类小说,都不难发现记忆在陈河创作中的神圣地位。记忆投注于自身,成了个人的命运流转;投注于外界,便是历史纷杂的回声。
对不同记忆的熔铸,构成了陈河小说错落有致的时间观。不同记忆的形态和气息,引诱读者前去淘掘故事的谜案,在曲折回环的时间迷宫中,感受晕眩的快感。“红二代”女邻居远赴法兰西,意外客死他乡,当有一天陈河自己踏上巴黎的街道,这则信息和女邻居的形象突然从纷杂的记忆中跃出;常年在阿尔巴尼亚经商生活的陈河,在经营中餐馆时接触到贩卖人口的“蛇头”,从他们口中获知诸多内部消息,消息连同他们的形象一并成为写作的养料;这些片段和细节,又与青少年时代的“文革”经验互相激活。最终,散落的经验碎片聚为一缕青烟,从记忆的瓶口腾出,化身小说《红白黑》(原名《致命的远行》)的骨骼。不论是在创作谈还是在访谈中,陈河都不讳言自己作品与过往经历的“过从甚密”。记忆或经长时延宕,终而抽芽成枝,幻化为文学;或一瞬情定,如箭离弦,洋洋洒洒,自成文章。
在余华那里,记忆意味着能让读者怦然心动的恍然如故,是时间、作品(作家经验)和读者经验如同日食般的三点一线时刻。而在韩少功看来,文学对记忆的召唤,应当不失其真,也即明确“记忆书写者的责任”,这种观点无外“修辞立诚”文学观的历史顺沿。在陈河的记忆书写中,记忆的力量,一来比感同身受所诱发的“瞬间的怦然”更为持恒;二来记忆的价值,更在于抵近内心深处那团“模糊的光芒”,它是作家梳顺情感、消化生活、讲述故事的自我需要。陈河自况,“写作其实就是写作者不断地给自己的内心图景做自画像”,小说最终指向某种内倾性的可能,某种偶然的存在与激荡。昆德拉说:“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记忆并不对真理负责,只对心灵负责。
在《猹》《西尼罗症》《水边的舞鞋》等域外华人家庭生活小说中,陈河调动去国前的生活逻辑与国外生活逻辑之间的反差,呈现不同价值观念的对峙和博弈。这种“认知的时差”作为晚近的记忆,被陈河记录下来,复活为小说。此外,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文艺作品,作为年少的回忆,常常在不同小说的叙述中客串登场,温故而知新,小说的肉身因此增添了岁月的沧桑与厚重。
《黑白电影的城市》以阿尔巴尼亚吉诺卡斯特城为故事发起的原点,商战和情爱故事、街垒的暴乱与战火、阿尔巴尼亚革命电影《宁死不屈》的剧情、电影女主角米拉的雄姿英发、城市少女雕像背后的二战典故,不同年轮的记忆彼此敞开、应和、交锋,流变的时间将城市空间彻底解放,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在记忆的重构中获得比现实更加饱满、深邃的活力。在陈河的小说里,历史的偶然塑造了诗性的必然,主体的认知挽救了历史的虚无。在《沙捞越战事》《外苏河之战》等海外抗战小说中,陈河以文学的语言为钩网,去打捞那些历史鲜为人知的远洋沉船,或为陈列纪念,或为“为了忘却的记念”。
从小说记忆的地理脉络观之,不断远行的陈河既非游客,也不是作为后至者的永久居民,他始终是一个暂居者,或者说,一个深度体验者。他带回的不是花哨的纪念品,也不是傲慢与偏见,而是客观之真和经验之真彼此调和的文本实在,一种发自肺腑的感喟。不盲目趋新,也不刻意做旧,是其所是,自成记忆的文学,或是文学的记忆。而当下,正是通往记忆深处的第一道驿口。
当记忆配着自身的光环,从脑海幽暗的景深中款款踱来之时,陈河凝视它,书写它,不放过任何一个看似微小的细节,他在与它对话,娓娓述来,不怯场,也不虚张声势。记忆在这样的时刻毫无设防,如江流汩汩而来,浇灌、浸透、拥抱着这位最熟悉的陌生人。富恩特斯曾表示,需要许多人的生活来构成一个人物。而在陈河这里,是许多种不同的经历和体验浓缩为一个人物,这个人物体内储蓄的能量与张力,丝毫不输前者。
这是陈河在与自己对话,是很多个“我”在对话。爱德华·卡尔说,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在自我的生命历程中,对话的目的是为了不遗忘,同时也还希望能从看似故旧的记忆中,寻获未来寄存在过去某个角落里的礼物。榴炮营连队子弟兵,汽车运输公司干部,地方青年作家,贩售抗生素的阿尔巴尼亚华商,被劫持者,教堂纺织厂保全工,加拿大新移民,域外抗战史发烧友……不同身份、时段和处境的陈河,他们常常共处一堂,在那个“庞大而复杂的小说王国”里,他们谈笑风生,场面温馨而热烈。
二
从对世俗世界的认知层面看,陈河小说大量主人公都可视作精神上的年少者。他们正如童话里径直拆穿成人世界谎言的少年。他们的懵懂与无辜,加剧了谎言的可恶。《去斯可比之路》中,不论是对待事业还是感情,段小海都显得天真冲动,他的身上散发着少年的可爱与真诚。去往斯可比之路,是上帝赐给这位童真者的圆梦之旅。幸福短暂易逝,如梦如幻,因此弥足珍贵。但在更为漫长的现实生活中,他只能是那个所有朋友里唯一仍穿行在危险地带的人,一位没有追随者的摩西。他近乎无可避免地成为被绑架者,绑架他的既是塔利班组织,也是这个对不愿长大的彼得·潘们缺乏包容与怜爱的时代,是人类对于纯真期的选择性遗忘。类似的人物还有,《沙捞越战事》里对自我的身世和战争的危险均缺乏足够体悟的周天化,他至死都是一个少年郎,有着永远耗不完的能量和永远解不尽的困惑;《夜巡》里对于时代盲目的沸腾浑然不觉且深陷其中的治安联防队青年镇球,他一心要缉拿的对象——既是革命政治的敌人,也是自我情欲的敌人——俨然一具无主的幽灵。
除去天真的少年,堕落的年少者形象同样成为小说精神年少者系列里的另一族裔。小说《红白黑》中对妻子、对外部世界都知之甚少的卡车司机谢青,他的堕落正是始于自己的成人化。《义乌之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查理(杜子岩),在他身上兼具革命臆想症患者、留洋知识精英、疯狂资本家等多重身份,“斜杠青年”背后是其精神的分裂,这种分裂的终极表现形态是一个耽溺在革命英雄幻梦里的流氓有产者。“资本”构筑起他的“游戏”“人生”,这注定是一场零和的游戏,一段异想天开的人生,杜子岩成为他亲手创造的乌托邦世界里的“头号玩家”。没有理性的自制,也没有外部的电击,“网瘾少年”无法自拔。
如此这般无知无畏的年少者,他们无形中也扮演着来者不善的闯入者角色。在各种貌合神离的群体中,闯入者的现身不仅格格不入,而且极易引发群体内部的混乱和恐慌。闯入者及其“危害”在《猹》和《西尼罗症》中,变身为动物及其带来的灾疫。《西尼罗症》里携带致命病毒的死鸟带来的怖惧,和《猹》里浣熊家族对一个华裔家庭造成的惊扰,它们从一个健康问题或说生活问题,最终演变为人的精神困局。究其根本,症结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体内部之间深重的猜忌和怀疑。赢得安全感,是人类尤其在步入现代社会以后,一场堪称永久性的非暴力战争。许多当局者并未意识到斗争的紧迫和情势的严峻,他们的自大盲目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那些屡屡错失挽救危局良机的主人公,正是当中的代表性面孔,这些面孔具有世界属性。在他们自负而又脆弱的精神世界里,闯入者无处不在。
陈河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对第一人称可谓情有独钟。根本的原因或许不在于“我”在叙述上的大开广角,甚至也不在于“我”在读者接受心理上的身临其境,而是人称作为叙述者的重要化身,“我”所带来的熟悉感和安全感,是一位将贴身的世俗经验奉为想象终极源流的作家,激活自我叙述自信与叙事节奏的必要仪式。陈河小说擅从主体视阈发轫,以主体的感受和经历作为发声的喉咙与丹田。第一人称“我”无疑是最经济便捷的途径,毕竟,水中之月,总是无限接近天上蟾宫。这也是为何,当与并不谙熟的经验正面交手时,小说的“声音”容易跑调。在《我是一只小小鸟》中,由于对青年留学生的生活状态尤其是精神状态所知浅显,作者只能凭借臆测去弥补主体经验缺失造成的盲点,由此引发的忸怩也就不足为怪。
人称问题,或者说视角问题,在中篇《布偶》与长篇《布偶》这对有着扩写的亲缘关系的小说中可以见出明显的端倪。中篇主人公“我”,在长篇中被替换成一位叫吕莫丘的小官员子弟。“我”的隐身并不意味着“我”的离场,一方面,“我”戴上了吕莫丘的面具,仍以意外闯入者的身份,混杂在教堂纺织厂和裴家舞会的人群中,他站在舞台中央,接受他人的检视,感知自己的心跳;一方面,“我”已然金蝉脱壳,走到了观众的身后,更加自由地调度着场内人物的情感投放、衔接走位、灯光音效。是走进观众的视线,还是藏身幕后,这完全取决于作者的客观需要,出于一个作家对不同审美间距效果的研判。而始终不变的,是陈河对自身经验如化学家之于化学试剂般痴迷的调试与高度的信赖。
第一人称并不必然意味着独语或独奏,它完全可以养成从一种声音中幻化出诸多面孔和不同心路。殊异的街道市声、民俗风情与驳杂的情感欲望互相盘错,它们从陈河行文的“一种声音”里幻化而来,隐然有“口技”的效果。声音碎裂为诸种响动,“一齐凑发,众妙毕备”,终而“抚尺一下,群响毕绝”。这位东瓯善口技者最精彩的时刻,是那“抚尺一下,群响毕绝”。陈河的主观经验并未使其丧失一种超然物外的克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陈河在小说里,顺利实现了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观化,两者相敬如宾,安然和谐。
因此,陈河的小说既不过分感伤,也不残暴或飞扬,纵是书写凶杀,如《女孩和三文鱼》中小女孩的横遭不测和凶手的浮出水面,作者也以周全的思虑,撑破逞凶扬善的单一向度。所谓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这种情感状态,既不黑色,也不哥特,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悲悯,凛冽中透着温情。在这方面,许多中国作家常常比西方作家更为“西化”。而这恰恰是陈河这位“出口转内销”的华人作家难能可贵之处。他始终知道我是谁,我何以至此,又将何以浪迹。
陈河的小说,纵使书写历史与异域,也似水之下流,烟之上寻,自然而然,不令人感到绝然的陌生与疏离,恍如在异乡遇见阔别多年的知己,在无数的生疏和唏嘘里,透露出永恒的亲昵。在陈河笔下,作者和叙述者的关系非常亲密,这种亲密最终也感染到读者。那些有感而发的身体经验与心灵经验,那些小说里的“我”,从中国走向世界,从历史步入当下,在巴尔干半岛动荡的局势、东南亚的蕉风椰雨和万湖雪国漫长的冬季里浸没,他们在作家的笔端集结、整合、动员,最终兵分多路,带着自身的温度抵达读者的意识深处。
这位自称“伪装成商人”的作家,凭借商人身份壮游四海,远行者必有故事,在不断获得想象性资源的同时,陈河也在物质上为自己赢得“当一个职业作家的条件”。且不论这是否是一种精明的自视,陈河的“伪装术”绝不仅仅体现在货币贸易体系中的“以假乱真”,而同样昭显在其对生活何以反哺小说一事上的如鱼得水。以讲故事为原始要义的小说,本质上正是一门精于“伪装”的艺术。在陈河这里,小说的一大意义是对讲故事这一古老内涵的再发现。缘情与言志的诉求,伪装在故事的迷彩里,与现实之我融为一体,等待痴迷的读者识别和侦破。陈河小说的“伪装术”之所以让人称道,在于他知道“真”在哪儿,“实”在哪儿,也就能裕如地加以伪饰,终而逼真、仿真,如在身侧,似在前日。
加拿大的三文鱼、臭鼬、国会议员选举、万圣节的南瓜是属于陈河的,阿尔巴尼亚的枪林弹雨、无花果树下的少女雕像和街上曼妙的女郎是陈河的,巴黎的拱廊街和咖啡馆也是陈河的。对陌生事物及其无规则运动予以熟悉化、节律化,而非任诞的变形,万般物象皆生共振。加拿大街区的浣熊可与江南沙地上的猹发生微妙的对接,阿尔巴尼亚街头丰腴的女人同样可以跟故乡打铁铺抡大锤的妇女产生联想性互动。陈河俨然资深向导,凭借国产的肉身、镜头和麦克风,携领我们驶出公海,抵达不同的彼岸。他与读者一道,在世界各处辗转历险,感受异域的风情与人情,品味“时间流逝的美感”。这种化身向导、共同亲历的处理方式,顺利避免了“仿真即失真”可能给小说造成的损伤。要知道,对陌生人事谬托知己,正是令许多小说家出尽洋相的苦主。而陈河以文中人“卖出破绽”的办法,让小说的叙事扶摇直上,牢牢占据着入情入理的审美高地。
三
在《讲故事的人》中,本雅明谈及优秀小说家理应兼顾编年史家的宗教意向和讲故事者的世俗理念,他们与历史学家截然不同。历史学家努力对讲述的事件加以解说,而叙事者聚焦于表述事件本身。记忆在当中扮演缪斯女神的角色,是完美叙事天赋的源泉。陈河正是朝着这个趋向,重新树立起小说讲故事的传统。
他的小说往往以人物被动的遭遇而非主动的求变,把人从单向度的局面(不论是资本神话还是情欲迷局)里解救出来。在林林总总却近乎必然的失意行动中,身心俱疲的主人公们与读者一道,悖谬性地获得了关于情感、物质、生命、历史、人生的“渐进的顿悟”。我们率先感知到经验撩人的气息,或者说,经验率先造成了知觉系统的战栗。由经验出发,我们不难发现陈河对“叙事”的执念。地理的铺展、时间的回溯,更多是为了壮大“叙事”自身的权威和盛名。陈河打造的小说世界,是一片带有追忆性质的故事天堂。在那里,陈河精心酿造着想象与纪实的混合物,重构个人的记忆和梦境,找寻宏观的时代表情与微观的个人宇宙之间微妙的衔接点。
詹姆斯·伍德在评价福楼拜的创作时,赞叹其小说“表现出高超的观察能力;它能保持一种不感情用事的沉稳,像个好男仆一样知道何时从多余的评论中抽身而退;它对善恶保持中立;它发掘真相,即使会令我们厌恶”。这种评价放诸陈河的小说创作,想必同样不算过誉。
在《南方兵营》里,因为榴弹炮营夜间训练时的一次失误,导致村里一位非同族孤儿意外身亡。在负责调停的李特派员眼中,小孩之死与一头耕牛的失踪、鱼塘里鱼被咬死等事件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比不上自己的编制问题。处理过程的轻易,让连队的方凤泉深感意外,他同样困惑的是村里人竟没有对此示以愤怒。一直在书写军营生活的小说,最后落笔在小孩出殡时的场景,小说写到那个秋日早晨的天际、云团、风、杜鹃花、斜坡上的刈稻者、远山尖顶的积雪和一只飞旋的鹰。出殡队伍里的方凤泉感觉自己如在梦境,但他又分明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若是联系到方凤泉本人是一个生命随时可能终结的白血病患者,这种对生命之轻与重的情景交互呈现,便会迸发出异常汹涌的内力。生命本身的脆弱和生命价值的单薄,构成了小说最真实也最平凡的震惊体验。
陈河小说本质是一种呈现的美学,而非寓言或讽喻的美学。它是一株植物,关注的重心永远在泥地之下,在于自身何以稳定地活着,而非园艺师的绿篱剪挥向何处。无意造型的深意,并不代表就能独善其身,当高度景观化与园艺化的作品蔚然成风、大行其道之际,审美疲劳的赏鉴者精明的目光,便在不断搜寻那些野蛮生长的植被。摩拳擦掌的批评者,汲汲于在陈河的小说中发现“远取譬”般的寄意,在“意义”这条扑朔迷离的道路上策马扬鞭。这种论述并无贬义,相反,当意义追寻的队伍渐行渐远之时,正是小说获得某种批评向度上的成功的瞬间。小说以自身的谜和魅,度己之余,亦在度人。那些熠熠闪光的奖杯和证书即为物证。
不同个体、民族的成长史所塑造的文化性格,在故事棱镜的折射下,呈现出多彩的光晕,它们之间相似性的魅力,与彼此的差异性相得益彰。这是一幅多样动态的立体图景。陈河力图把充斥着神谕色彩的说教和讽喻推挡在文本之外。他更信赖“讲述”本身赐予一位文字手艺人的神圣感甚或神秘感,而非借由逻辑学、历史学和作文术的阶梯爬上小说教堂的穹顶,绘制关于远古和未来的精神图腾。这正是陈河小说通俗,却不一定易懂的原因。这种意象传递方式的好处在于,作者的创作态度显得格外诚恳、谦卑,读者想象的自由或说权限和追随的意愿或说诱惑,因此变得更为宽松、炽烈。
严谨的结构让位(并非舍弃)于故事情节的漂游,个人的经验和历史的言说成为使叙述之河充盈生气的动物、植物与矿物。陈河小说呈现的是一些并不整饬的情节板块,这是一种多中心的开放结构。这些板块之间同样存在某种柔软的秩序,这是属于故事的液态的秩序,因此,毫无疑问,它也是小说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体系下,故事的终结只是某种全新的开始,因为流动永不止歇。
周天化最终殉身那片弥漫着硝烟的热带丛林,《沙捞越战事》最后写道:“如果要寻找他(周天化)有没有血脉留在丛林里,通过DNA技术完全可以做到。但是不会有人去做这件事的,因为周天化只是一个普通的华裔二战士兵。”小说以周天化牺牲后的惨淡境遇,唤起生者对生命的敬畏和对逝者的缅怀。本雅明说,小说的意义不在教诲,而在向我们描绘某种命运。这种命运“借助烈焰而燃尽,给予我们从自身命运中无法获得的温暖。吸引读者去读小说的是这么一个愿望:以读到的某人的死来暖和自己寒战的生命”。周天化之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已然获得的和尚须行动去争求的暖。
许多作家处理不好结局,原因在于他们无从消弭小说与故事之间看似完美的合作伙伴关系背后,那古老而深刻的敌意——注重形式和文体的小说家意识到故事先天畸形造成的肌体无力,注重剧情细节的小说家感受到结构图纸不清导致的空间压力——最终,敌意在最后环节演变为敌对。但在陈河这里,小说和故事的敌意消失了,他不是以技术手段为二者赢得崭新的和谐,而是直接取缔矛盾,越过敌意,让小说止于未止处,从而出奇制胜。把叙述问题降格为风格问题,这确实是陈河小说的应对之道。又或者,这是一位对现实素材与切身经验忠心耿耿的作家,理应获得的意外回报。
帕慕克精辟地谈到过,小说的艺术在于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自己,使读者认为你在讲述他人;或者以独特的方式讲述他人,使读者认为你自己曾经历过他们的故事。独特之为独特,应当包含一种文学层面的人为的泥泞和蓄意的蜿蜒。陈河小说常给人直接、干净、顺滑之感,不论是语感声调,还是讲述的方式和节奏,就小说的诗性而言,似乎遗漏了一点必要的停留与耽搁。科斯托拉尼·德若在小说《夜神科尔内尔》中有那么一句话:“诗里的月亮,总被涂上颜色,卖俏又造作,但仍比真实的要漂亮许多。”如何为小说涂上一抹别致的颜色,这是顺滑的经验性写作值得思考的地方。
帕慕克所谓的独特,让我想到拉什迪所说的魔法。拉什迪讲:“小说是想象力的家园。想象力必须由记忆与知识来喂养,但是它必须对小说施加自己的魔法,否则你的书就会平淡无味、了无生气。”陈河小说不缺魔法,缺的是对魔法更进一着的冒险。这种冒险可能迎来的收获是,小说既能释放经验的光晕,也能呈现光晕的色散、变形和位移,还可将经验封印入瓶。
在那段连环礼炮般对福楼拜的溢美之词最后,詹姆斯·伍德如此说道:“而作者印在一切之上的指纹,悖论般既有迹可循又无影无踪。”这的确是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幻术。在陈河的小说中,我们不难窥见作家遗留在字里行间上的指纹,它们意味着生命的独一无二、神迹和激荡。当有一日,这些指纹能够悖论般无影无踪之时,陈河势必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