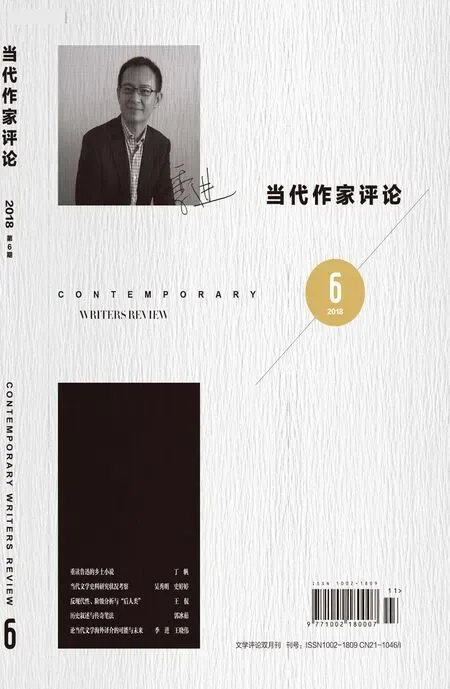迟子建小说中的“生成—动物”研究
2018-11-12刘阳扬
刘阳扬
以动物为中心表现自然生态是迟子建小说的一大特色,讨论迟子建小说的动物性,也成为探讨其文学世界的重要突破口。但是,评论界对其小说中的动物叙事研究,往往集中在生态美学的范畴之内,通过考察分析迟子建小说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从而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如果依照德勒兹的“生成—动物”观点来看,上述的表述方法依然存在着将人与动物进行二元对立的预设态度。在德勒兹看来,“生成动物不是存在或拥有,不是要达到动物的某种状态(力量或天真),也不是要变成动物。生成动物是对动物运动、动物感知、动物生成的一种感觉”。刻板的等级划分囿于理性、逻辑的规则制约,不自觉地遮蔽了生命中的差异性因素。而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应该是超越界限、相互“生成”的混沌关系,因此,在迟子建的动物世界里,对人性的批评与反思可能并非其最为关键的内容,而人与动物的相互感知和“生成”,以及共同的越界、逃逸,乃至游牧,或许是其小说更具理性哲思的部分。
一、德勒兹:“生成”与“生成—动物”
“生成”概念是德勒兹哲学的重要内涵,这一概念是基于其“块茎”(Rhizome)思维而产生的。“块茎”模式与“树状”模式相对应,“块茎”无中心、无规则,而“树状”具有中心化的特征。“块茎”思维意在打破人们长久以来遵循的惯有思维方式,否定秩序和逻辑,呈现旁枝逸出、任意组合、变化延伸和异质结合的特征。德勒兹和加塔利将“块茎”视为反权威、反中心的象征,“块茎是无结构、开放性的,构成‘多元性的入口、出口和自己的逃逸线’。这种逃逸线(反对固定的原点)是典型的反中心或‘游牧’思维的体现,与柏拉图以来主导西方思想的‘树状逻辑’恰成对照”。根据“块茎”思想,各种力量开始不断蔓延,并重新组合和“生成”。“生成”的性质是“分子”的,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克分子”。“克分子”通过二元对立的规则将社会进行排序和划分,形成种族、性别、阶级的对立,而“生成”则是要克服这种对立,越过克分子的限制而重新组合。
“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是德勒兹“生成”理念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这一概念的描述和阐释体现出他们二人反对中心化、系统化的哲学思想,“我们相信生成—动物的存在——它是极为特殊的,渗透着、带动着人类,既作用于人,也同样作用于动物”。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生成—动物”通过集群的传染产生变化,传染活动与集群中的异常者有关。当集群中出现异常者时,“解域”点开始出现,欲望就有可能从现存的、固定的疆域中解放出来,产生生成和流变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和集群中的异常者由于相互之间的吸引力而释放出分子微粒,从而形成断块和联盟,“生成—动物”随之发展起来。“动物”与德勒兹的“生成”理念发生关联,使得一种新的看待人与动物的视角诞生了。这种视角打破了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思想,摆脱了原有的屏障和边界,使人与动物的关系开始具有多种可能性。
德勒兹和加塔利区分了描述动物的三种方式,首先,在弗洛伊德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描述中他们看到了动物描述的第一种方式,即一种个体化的、俄狄浦斯式的动物。弗洛伊德曾经描述儿童汉斯看到马的情形,将马解读为父亲的替代、欲望的替代,并运用幼童所具有的俄狄浦斯情节,将小汉斯与马之间的关系简化为其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这种解释将人与动物间的关系变形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人类置于中心地位,而将动物置于从属位置。德勒兹并不同意弗洛伊德的阐释,因此他重新解释了弗洛伊德的例子,“小汉斯的马不是再现性的,而是情状性的。它不是某个物种中的一员,而是某种机器的配置之中的一个要素或一个个体:驮马——公共汽车——街道。它为一系列能动的或被动的情状所界定,在它构成为其一部分的个体化配置的背景之中”。德勒兹认为,小汉斯的马并不是一种俄狄浦斯式的动物,也不是父亲的替代;相反,小汉斯与马之间形成了一种“生成—动物”的模式。动物的第二种存在方式是从属于分类或国家,具有特征或属性。荣格关于“原型”的描述将动物视为此种存在。如果说弗洛伊德的动物存在于个体幼年的记忆之中,那么荣格的动物则存在于一种“集体无意识”之中。以上两种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将动物解释为俄狄浦斯式的或国家式的,对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这些精神分析学家,“将动物视作一种冲动的样本或一种对于亲代的再现。他们没有看到一种生成—动物的现实性,没有看到冲动自身就是情状,它不再现任何东西。除了配置自身,没有别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德勒兹和加塔利观点中的第三种动物开始显现,那是一种凶恶的、集群的动物。当所有动物可能是一个集群的时候,动物本身的多样性开始变得更加难以察觉。这种多样性以情状、力量或是缠卷的方式体现出来,将动物带入一种“生成”之中。显而易见,德勒兹偏向于用集群来解释动物存在方式,集群不存在中心,而是以松散的结合体方式互相影响和传染,并带动了各式各样的“生成”。
二、集群:突破传统偏见的一种可能性
德勒兹和加塔利曾以卡夫卡的小说为例,挑战现代主义关于卡夫卡的传统看法。他们认为,卡夫卡的小说与西方传统思想中的树状结构迥然不同,呈现出“块茎”的状态,具有不断延伸、复杂多变的逃逸性质。一些评论者用精神分析学上的俄狄浦斯情节解读卡夫卡作品,实际上是一种越界、夸大的解读方式。其实,卡夫卡小说中的动物表现出一种“生成”状态,如歌唱家约瑟芬,她在耗子似的集群中属于异常者:“时而处于一个外在于群体的位置,时而又滑入、迷失于集群的集体性陈述的异常性之中”。约瑟芬一边歌唱,一边观察耗子式的听众们,而耗子们对音乐的不理解使约瑟芬成为一种少数的、异常的存在。在德勒兹的理解中,异常者促使集群进行传染,从而实现“生成”。实际上,德勒兹和加塔利对卡夫卡小说的关注早已开始,他们曾在《被夸大了的俄狄浦斯情节》中强调卡夫卡小说的“生成—动物”内涵:“对于‘恶魔性力量’的不幸,有一种生成动物的答案:宁可成为甲虫,成为狗,成为猴子,‘转过头离开’,也不低头继续做一个官僚主义者,检察官,审判者或被审判者。”
在迟子建的《逝川》中,泪鱼就呈现出集群性的存在方式,在每年的九月底十月初,泪鱼成群结队地从逝川的上游哭着游下来。当地的渔民们在与泪鱼集群的共生状态中,掌握了与泪鱼交流的方式。他们在夜晚捕捞泪鱼,将其放在木盆中,“安慰它们,一遍遍祈祷般地说着‘好了,别哭了;好了,别哭了;好了,别哭了……’从逝川被打捞上来的泪鱼果然就不哭了,它们在岸上的木盆中游来游去,仿佛得到了意外的温暖,心安理得了”。次日凌晨,人们将泪鱼放回逝川,泪鱼便不会再发出呜咽的哭声。人与泪鱼通过交流实现了集群的互动,相互释放分子实现“生成”,摆脱“克分子”状态的束缚。渔妇吉喜善于捕鱼和编织渔网,“她在火爆的太阳下织,也在如水的月光下织,有时织着织着就睡在渔网旁了,网雪亮地环绕着她,犹如兜着一条美人鱼”。在与鱼的互动中,吉喜也通过逃逸线穿越了与鱼之间的界限,从而实现了生命的释放。
如果说《逝川》中的泪鱼是善良、美好的集群,那么《白雪乌鸦》中的乌鸦,则是更具有多元意义的种群。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解读,乌鸦仅仅是鸟类的一种,并没有囊括多种意义,甚至在西方和中国的古代传说中,乌鸦还经常被视为一种具有智慧和神性的鸟类。但是通常情况下,尤其是民间传统中,人们却对乌鸦有着深刻的偏见。因为通体乌黑、声音刺耳、食用腐肉,乌鸦的出现常被看成一种不吉利的征兆。在中国古代民间传说以及古典文学作品中,乌鸦常常与萧索、败亡、不祥的景象联系在一起。因此,当乌鸦进入文学领域之后,已经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乌鸦,而成为不祥的承载物。这样的乌鸦是一种“克分子”的动物,长期承受着人的憎恶与嫌弃,处于失语的状态。人们通过对乌鸦的命名以及意义建构,将乌鸦塑造成丑陋、阴暗、不祥的“克分子”形象,从而反衬人本身形象的高大与完满。不过,在《白雪乌鸦》里,乌鸦却开始以一种不同的面貌出现。它们只是一群普通的鸟类,常常成群结队地停在树上,像成熟的果实一般压弯了树枝,如果人们洒下一把谷子,乌鸦就会纷纷落地啄食。小说中的翟芳桂就并不讨厌乌鸦,甚至有些爱乌鸦,在她眼中,乌鸦的黑色外衣永不过时,它粗哑的叫声也带有人间烟火之气。翟芳桂喜欢乌鸦,将其视为朋友,并且用愤怒和诅咒来对待毒死乌鸦的纪永和。《白雪乌鸦》对乌鸦的另类描述,打破了民间传统中关于乌鸦的既定观点,人与乌鸦之间实现了一种德勒兹意义上的“生成”关系。
三、巫师:临界点与“生成”的边缘
德勒兹将解域视为“生成”所必须的条件,即将欲望从某种固定的模式之中释放出来,走向流动状态。“解域就是‘某人(物)’离开界域的运动。它是逃逸线的运作。”在解域线上往往有异常者存在,它与其他元素结盟,并且引导“生成”行为的延伸和发展。占据异常者位置的常常是巫师,因为他们喜欢来往于森林和村庄的边缘,游走在各个部落和村庄之间,天生处在边界的位置,“我们会说,生成—动物正是巫术的专长,因为:(1)它意味着与一个魔鬼相结盟的原初关联;(2)这个魔鬼发挥着一个动物集群的边界的功用,而通过传染,人进入这个集群或在其中进行生成”。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萨满占据了解域线上的异常者位置。当姐姐列娜生病的时候,母亲请来尼都萨满跳神,一只灰色的驯鹿仔代替列娜去一个黑暗的世界了。驯鹿是森林中有灵性的生灵,也是鄂温克人的好伙伴,它们性情温顺,以集群的形式与鄂温克人共生。萨满在两个群体的边界之间,引导着人与动物相互传染,当萨满通过跳神,调换了姐姐和小驯鹿的命运时,实际上一种“生成”关系已经形成。在这种秘密的生成力量之下,已经建立起来的人与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界限被打破,驯鹿成为一种具有个性尊严的生命,人也在这种情况下反叛了社会文明的规定。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论述中,“人类学,神话和民间故事提供了人类广泛存在的生成—动物的证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生成—动物的过程通常与边缘的社会群体或运动有关”。可以看出,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少数族裔和少数人群的关注恰恰印证了德勒兹的观点。除了迟子建,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小说中也常能见到萨满形象。他笔下的萨满,除了具有神性,动物性也是其不能忽略的特质。当萨满为了远离游客而躲进山洞的时候,“他躺在树洞里,晒着暖融融的阳光,嘴里嚼着陈年松籽,野熊一般悠闲自在……他这样做的本意是什么?这是一时的迷狂,还是对骚动人群的逃避?我至今仍记得,他从幽暗的树洞中投射过来的目光——那真是一头困兽的迷惘和无奈”。刘庆201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唇典》也讨论了萨满在神性、动物性以及人性之间交错复杂的关系。关于萨满教徒之于“生成—动物”的意义,德勒兹在《千高原》里有所提及,他认为,“生成—动物”需要依靠动物精神,如鸟的精神、豹子的精神,这种精神隐藏在实体内部,在着魔的情形下更容易表现出来,而“萨满教徒、武士、猎人的权力组织脆弱而不稳定,但正因为它们通过实体性、动物性和植物性而运作,反倒变得更为具有精神性”。因而,更加接近神灵的教徒,往往因与动物的精神更加贴合而具有了“生成”的可能性。实际上,早在《伪满洲国》里,迟子建就开始探索萨满教对少数族裔文化的影响,这也恰恰符合德勒兹思想中的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内容,即“生成少数”。“生成”理论认为,所有的生成都是生成少数。如果说多数指的是占据统治地位的集群,那么少数则需要突破多数的统治地位,在历史和传统的桎梏中突围。因而,迟子建文本中的“生成—动物”线索,与“生成少数”的理念相互联系、相互交织,成为德勒兹和加塔利“生成”理念的有力注脚。
《鸭如花》里的鸭群同样是一群拥有主动感受的动物。它们喜欢浅浅的河滩以及淤泥中的虫子,同时还对花朵有感情,“它们有喜欢野花的,就用鸭嘴抚弄草滩上的花。它们不太喜欢那一片片的小黄花,大约以为自己的嘴就是和它一个颜色,见多不怪了。它们喜欢的是茸嘟嘟的紫色马莲花和球形的粉色带着浓密黑点的花”。鸭子能够主动感知主人徐五婆的气息,在听见主人的脚步时,就会抖着翅膀叫起来,对主人表示欢迎,当徐五婆没有按时到来的时候,鸭群静静地在草坡上等待着她的到来,仿佛一片美丽的光影。在小说中,鸭群是有感知、有智慧的集群,而帮人办丧事的冥婆子徐五婆,处于人间与冥界之间,扮演了近似于巫师的角色。当冥婆子处于鸭群边缘的时候,就能够与鸭子相互感知和“生成”,“她特别想挨只鸭子地亲吻它们一遍,可它们已经团团簇簇地围聚在她周围。它们毛茸茸的身体触着她的腿,终于使她抑制不住地哭了起来”。在徐五婆与鸭群的相互“生成”中,诞生了悲悯而又温暖的情调,这种情调在逃犯被枪毙的时候达到了高潮。一只鸭子站在逃犯的坟头,仿佛一朵飘摇的花,植物被引入了人与动物相互“生成”的秩序之中,形成了缓缓流动却又不可名状的奇妙氛围。
四、“无器官身体”作为“生成”场所
“生成—动物”并不意味着模仿动物或成为动物,也不是和动物实现同一,“生成”的重要性并不在结果,而在过程,在于“从(我们所拥有的)形式、(我们所是的)主体、(我们所具有的)器官或(我们所实现的)功能出发,从中释放出粒子,在这些粒子之间建立起动与静、快与慢的关系”。当人与动物遭遇之后,如果出现了某个特殊情境,令人受其影响并沉浸其中,人就有可能获取动物身上的某些粒子,从而形成新的聚合体。同时,容易受到动物粒子影响的个体,往往会具有“无器官身体”的性质,这种个体容易在孩童群体或是精神病群体之中出现。德勒兹理论视域中的“无器官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是一种欲望的内在领域,是“不同系谱学文化符号刻录的最初空白载体”,这一载体与机器所代表的规则之间具有明显的冲突:“机器的每一次耦合,每一次机器的生产、运行的任何声音,对于无器官的身体来说都变得无法忍受”。“无器官身体”剔除了约定俗成的规则,是不可分割的混乱的集合体,同时也是“生成”发生的重要场所。
在迟子建的小说里,人与动物发生交汇,并在“无器官身体”中实现“生成”的情境并不鲜见。在《雾月牛栏》里,宝坠就很喜欢和牛在一起,不仅喂牛,还和牛进行交谈,甚至和牛睡在一起。宝坠在人的集群中是一个异常者,他失去了部分的意识,成为一个弱智儿童。这样一来,宝坠的身体开始不受习俗和理性的控制,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了“无器官身体”。宝坠愿意和牛相处,并非是成为牛,而是掌握了与牛交流的语言,并且在这种交流中,脱离了克分子状态,消解了自己和牛之间的界限。人与牛遭遇的那个决定性瞬间,或许就发生在宝坠每天两次解梅花扣的过程之中,“他每次在解和结梅花扣的时候都怦然心动,仿佛这个瞬间曾发生过什么重大事情,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什么,一如他听到牛的反刍声努力回忆却仍终无所获一样”。当母牛花脸产下小牛卷耳的时候,与牛进行交流的已经不仅仅是宝坠。母亲和雪儿也天天逗弄卷耳,就连死去的继父也在梦境中极力与卷耳达成和解。雾月出生的卷耳第一次看见阳光,它小心翼翼地缩着身子走路,生怕自己的蹄子踩碎了阳光,它的一部分在阳光之下与人形成了交互和生成,人与动物间的等级观念也随之打破。小说《稻草人》中的儿童生荒,也是一个热爱自然动物的孩子。他讨厌麦地里树立的稻草人而喜爱被稻草人所吓退的鸟群。其实,故事里的鸟群并不迷人,“它们耸着身子朝塔尖飞去,身子全是蒿草的颜色,嘴巴是黑色的,并不是十分美丽的鸟”。但就是这样的一群有着黑色嘴巴的鸟,却让生荒十分喜爱,甚至不惜烧毁稻草人来挽留离开的鸟群。在热爱鸟群的过程中,生荒也吸收了鸟群释放的分子,从而出现“生成”鸟的状态,“像一只雏鸟一样轻盈地走下去了”。当舅舅表示再也不扎稻草人的时候,生荒对鸟群的喜爱打破了人与鸟之间的截然分界,两者实现了互动与融合。
迟子建的文学世界中,人与动物互相“生成”的同时,人与人之间却充满了隔阂和对立。《酒鬼的鱼鹰》里,鱼鹰与刘年、寒波也存在相互交流、相互依存的关系,当刘年前往酒馆喝酒的时候,鱼鹰“突然飞上了柜台,它张开了翅膀,似乎在欢迎刘年的到来”,不仅如此,它还使得一直找寒波麻烦的婆婆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小说进行到这里,鱼鹰似乎具有了自主性,它不再依附于人而存在,而是体现出自己的智慧。但是,小说的最后,人与鱼鹰之间的“生成”似乎失败了,鱼鹰最终被税务局局长投入冰柜准备制成标本。但是,“生成”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延续下来,因为受到鱼鹰感染的儿童王小牛目睹了这一幕以后,总是怕冷、打寒战。生病的王小牛和弱智的宝坠类似,都是一种“无器官身体”,他们摒弃了传统习俗与政治规约的束缚,成为欲望、感受、心理状态的复杂混合体,同时也是“生成”的处所。因而,王小牛与获得了主体性的鱼鹰具有相同感受,也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生成”的状态。类似的儿童形象还有《原野上的羊群》里的芦苇。作为一个几个月大、尚未具有意识的婴儿,芦苇符合德勒兹“无器官身体”的表述,他在被领养之后依然保持着和原生家庭无法割断的联系,这种联系就通过羊群来表达。芦苇的生父十分想念被领养的儿子,希望他能够回家看看羊群和家人,婴儿芦苇经过与羊群的互动出现了与羊相似的成分,“穿着一套雪白的毛衣毛裤,神情活泼,像只淘气的小羔羊”。通过观察和感受羊群,婴儿芦苇不仅打破了人与羊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消弭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使得人们之间达成了宽恕和谅解。在《罗索河瘟疫》里,弱智儿童领条在埋葬死狗的途中偶然发现了哥哥的杀人行为,但是哥哥却以他是弱智为借口否认了这一行为。当受到否认和压抑的领条发现家中的另一只狗也因为瘟疫而死亡时,他自己的一部分也随着狗的死亡而远去,他最终决定跳入河中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迟子建笔下,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总是温馨而美好的,反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充斥着更多黑暗、丑陋和负面的成分,作者通过对这些关系的描绘向我们提供了更多人性反思的维度以及深入思考的可能性。
五、《候鸟的勇敢》: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多层次表达
迟子建最新的小说《候鸟的勇敢》是其迄今为止的中篇小说中最长的一部,其中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表达也较其他中短篇小说有了更为完整的呈现。小说中人与动物的关系实现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表现。其一,从整体上将人与候鸟进行类比,把冬天离开瓦城避寒,春夏回到瓦城消暑的富裕人群比作候鸟,从动物性的角度解释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其二,将人的想法加于候鸟身上,一时将其视为好逸恶劳的孬种,一时又将其看成神话的主角和正义的使者。其三,侧重描写了管护站张黑脸与东方白鹳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第一、第二个层面上,人与候鸟尚未形成深层的互动关系,在第三层面上,人开始与候鸟产生关联并最终相互影响和“生成”。瓦城的权贵邱老和庄如来疑似因为禽流感而死去,而起因被传为食用了管护站站长周铁牙偷猎的野鸭。瓦城人素来忌惮周家和庄家的势力,他们的死亡使得百姓们将传播病毒的候鸟视为正义的使者,虽然他们此前因为候鸟怕冷又怕热而对其嗤之以鼻。候鸟的迁徙自有其生理规律,但瓦城人却按照自己的想法赋予候鸟多重意义。候鸟原本被认为是贪图享乐、好逸恶劳之徒,但是,当其被疑为携带致命病毒的时候,人们对它们的看法发生了剧烈的转变。一方面,人们因为死去的是权贵阶层而赋予候鸟“扶贫济困、匡扶正义”的旗帜性意义;另一方面,瓦城的“候鸟人”原本是百姓羡慕的对象,现在却常受到歧视和鄙夷。无论是将人与候鸟进行简单的类比,还是按照人的想法随意更改候鸟的性质,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些行为体现的正是人与动物的不对等关系:动物被视为人的从属,不得不接受被肆意评判的命运。然而,迟子建所做的这些前期的描写仅仅是一种铺垫,为了引入小说更为重要的层次——即张黑脸与东方白鹳之间的关系。张黑脸曾经是一名扑火队员,在一次灭火中失去意识,在白鹳的庇护下得以生还,但从此失去了部分记忆,变得痴傻愚钝。张黑脸类似于迟子建小说中屡屡出现的弱智儿童,可以被视为一种“无器官身体”,这样一来,流动与“生成”的可能性就存在于张黑脸与候鸟之间。张黑脸沉默寡言,不善与人交往,但是却亲近候鸟。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理论认为动物以集群的形式存在,他们的思考集中于构想一种不依赖于血缘的繁衍和生成:“我们将(流行病的)传播与血缘关系对立起来,将传染与遗传对立起来,将(通过传染而进行的)移居与有性繁殖和生殖对立起来。集群——无论是人类的还是动物的集群通过传染、传播、战场和灾难而得以增殖。”保护站的候鸟以集群的方式集体存在,而禽流感(或者说是误诊的禽流感)为其走向逃逸和生成提供了潜在的路径。张黑脸在和白鹳的交往中,渐渐从愚痴的状态中走出来,并与娘娘庙里思凡的尼姑德秀产生了爱情。一个是木讷愚笨的管护员、一个是心如死灰的尼姑,两人竟然同时恢复了人的自然性情,挣脱了传统与等级的桎梏,这一切有赖于借住在娘娘庙的白鹳的感染和“生成”。禁忌的爱情给了张黑脸和德秀别样的刺激,对惩罚的担忧反而使得他们之间的爱恋更为疯狂。冬天即将来临,候鸟纷纷南迁,但是受伤的雄性白鹳却无法追随族群的步伐,它的雌性伴侣也久久徘徊不愿离去。当它们终于在暴风雪中丧生的时候,张黑脸和德秀也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等同,他们埋葬了死去的白鹳,如同埋葬自己一般,“当他们抬白鹳入坑时,那十指流出的鲜血,滴到它们身上,白羽仿佛落了梅花,它们就带着这鲜艳的殓衣,归于尘土了”。故事最后,葬完东方白鹳的张黑脸与德秀在黑暗中寻找归途而不得,“他们很想找点光亮,做方向的参照物,可是天阴着,望不见北斗星;更没有哪一处人间灯火,可做他们的路标”。放弃人间灯火的指引,或是被人间所放弃,张黑脸和德秀的未来显得灰暗而缺乏希望,他们“在获得混沌幸福的时刻,却找不到来时的路”。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张黑脸、德秀与东方白鹳之间形成了真正的“生成”,人与动物之间的鸿沟终于消除,两者走向了平等和自由。
结
语
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生成”哲学“说到底是一种关于越界的哲学,关于逃逸的哲学,关于圈定界限,然后再跨越界限的哲学”,而在此基础上的“生成—动物”则是“关于感知和生成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生成”理论对文学的阐释注入了活力,有利于重新观察中国当代的文学实践。迟子建的小说中充满了对自然的礼赞、对动物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展现以及对宗教、巫术、哲学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思考,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德勒兹笔下的“生成”关系。她小说中的动物以集群的形式生存和繁殖,并与人类发生着互动关系。而人类则在日常生活、移居迁徙等活动中,通过人群中异常者的引导,不断地触碰逃逸线,不断地解域,以“块茎”方式实现了“生成—动物”。在这种集群的互动关系中,动物摆脱了人类曾经附加在它们身上的负面评价,逃离了文化限制,具有了感知能力,并通过不断地传染和生成增强了自身力量。与此同时,人类也突破了与动物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人与动物开始向对方靠近,实现了理想的游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