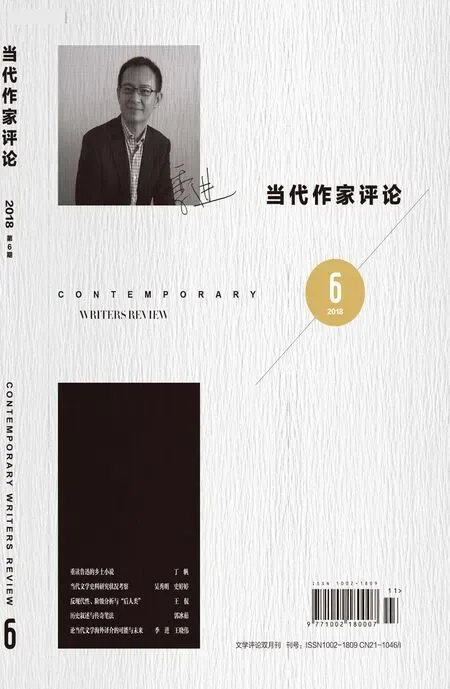当代乌托邦小说的叙事困境
——以长篇小说《山河入梦》《人境》《巫师简史》为例
2018-11-12卓今
卓 今
当代乌托邦小说,试图对未来社会做科学系统的制度构建,涉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许多艰难的问题。这一类型的文本,作者意图很强,总体来说它的社会文化性价值比艺术性价值更突出。《山河入梦》(2012)、《人境》(2016)、《巫师简史》(2015)三部小说都在实践层面探索一种可能性。他们不同于早期的乌托邦文本,不仅有系统的、完整的制度设计,还与当下社会发生种种勾连。三部小说代表了三种阶段的理想社会。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担忧的同时,在制度探索和精神向度上却表现出积极的一面。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形态变成了现实制度,从一国道路走向多国道路。早期乌托邦或世外桃源的思想资源也证明了人类理性可以主导未来。
一
社会改良者对社会主义试验的冲动从未停止,他们的理想是要超越现行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设想进入纯粹的或者较为高级的社会主义模式之后,所展开的种种想象。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即是从普遍规律和哲学层面进行的较为系统阐述。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仍然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社会的变革,全球格局的变化,尤其是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实际上对这一制度的顺利实现,带来机遇和挑战。机遇是大数据平台下,市场可以被调控,更有利于计划经济和财产公有。人工智能可以替换一部分低端劳动力,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最大化地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基因技术可能解决疾病和生理难题。带来的挑战是,它们对不同阶级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斯拉沃热·齐泽克曾担忧,一个潜在危险可能是掌握财富和权力的人利用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操纵和奴役低阶层的人。不排除出现新的阶级矛盾、贫富悬殊等问题。
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表面看起来,一个是先验的,一个是经验的,在主客关系上似乎也存在一种对立的形式。实践者的办法是躲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元对立的矛盾,理性扎根于质料之中,但又必须基于形而上的设计,主体应当回到作为自我解释的现实环境,并且具有建构世界功能的主体性那里,而不必拘泥于偶然性,类似于亨利希的后形而上。空想社会主义文本往往都是非时间性的。在空间上也采取一般性描述,虚构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地理位置。没有实践,只有绝对真理是不会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对所有这些人(空想社会主义者,作者注)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自古以来的乌托邦文本都有它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在无力改变社会现实的情况下,乌托邦可以赋予历史一种观念意义上的远景。可以肯定,一种对比框架之下的乌托邦叙事,具有标杆性的意义,现实社会制度与标杆之间的差距恰好是人性向上的动力。与纯粹的实践性和现实性相比,它有一种自由和超越的气质。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有少数几位作家对体制和社会形态进行过深入思考,他们把构筑乌托邦当作一种巨大的乐趣和挑战,小心维护着这一份理想,却又不敢真正豁出去,常常面临一种叙事悖论,不得不在红色共产主义乌托邦想象与灰色自由主义乌托邦冲动之间做出选择,也有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恩格斯曾提醒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要“把各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当代乌托邦小说中的社会主义实验场所大都是封闭的、孤立的,对融入全球化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与现代经济运行规则保持一定的距离,对高科技心存戒备。当代乌托邦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一个强悍的改革者,仁爱博学、理想主义,靠人格魅力号召民众。实验场所体量小,一般都是以村庄为单元,容易被周边环境影响,一旦主动与外界合作,很快被瓦解。因此,他们有一种本能的反资本、反市场、反全球化的态度。发展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全球化也是历史的选择,如何在两者之间达成一致?当代乌托邦小说都未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后还是免不了被各种外在因素击得粉碎。格非在《山河入梦》中,塑造了一位铁腕人物郭从年,他苦心经营的花家舍,在“江南三部曲”的下部《春尽江南》中解体,在资本和人欲的冲击下变成了娱乐场所。除了体制,花家舍的田园景观符合人们对世外桃源的所有想象。与郭从年对应的是怀有自由主义乌托邦理想的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他的普济水库的乌托邦设计,被认为“头脑发热”,加上失误,最后被降职处分。刘继明在《人境》中抠出一小块理想主义园地,做过大公司董事长助理的马垃,公司破产,替老板坐了七年牢,获释后把长江边上的一个叫神皇洲的村庄作为理想社会的实验场地。最后,跨国大公司的买办与县里官员勾结,以洪水的名义让神皇洲的“同心社”全部搬迁。这里洪水像是一个隐喻,资本洪流的摧毁力量超出了自然洪水。于怀岸的《巫师简史》严格地说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社会主义因素,是一个古代桃花源的升级版。隐蔽在湘西大山里的“猫庄”,巫师兼族长的赵天明从父亲手里接管了猫庄,按照祖制经营。赵天明的建设性恰好体现在毁灭性上,这个躲过无数灾难的世外桃源,从晚清开始,衰败的势头不可阻挡,同盟会、土匪、革命党、红二六军团、抗日、土地改革、湘西剿匪等一轮一轮的冲击,猫庄不再是世外桃源。拥有法力、能与神沟通的巫师赵天明在这样的大动荡中落败,最后还是吃了枪子儿。猫庄与红色革命后的新制度有内在的一致性,没有地主、不用“土改”,追求自由和平等,但在精神层次和终极目标上存在根本性分歧。
三部小说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在高纯度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样本的周围,存在着各种不确定因素。对样本进行强力干涉的因素,有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有外来的制度冲击,有不同体制下的资本挟裹,有新兴的科技力量,有来自人本身的思想难题,还有战争、革命、文明冲突等。三个文本趋向一致,单纯样本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被同化和消灭。同世界主义、国家消亡理论一样,需要大环境支持。面对这种种困难,如何构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科学制度,并将这一制度稳步向前推进,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热衷于乌托邦小说的作家们。
二
怎样消除剥削压迫、消除不平等,人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人该过怎样的生活,如何才能达到人之完美。人类理想社会形态雏形,东方和西方两种文明的大思想家孔子和柏拉图对此都有过深刻的思考。尽管他们没有考虑经济因素对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影响,但都注意到了理想社会必须和谐有序。
空想社会主义与乌托邦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英文为utopian socialism,准确的译法为乌托邦社会主义。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书名几经更换。恩格斯在1892年英文版导言说,“根据我的朋友保尔·法拉格(现在是法国众议院里尔市的议员)的要求,我曾把这本书(即《反杜林论》,作者注)中的三章编成一本小册子,由他译成法文,于1880年出版。”恩格斯所说的1880年在巴黎印的单行本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空想社会主义”对应的是socialism utopioue。1892年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其中空想对应的是utopian。“‘空想’这种中文译法,在清末民初报刊上即出现过,是从日本转译来的。辛亥革命后,国内的一些报刊陆续开始直接译载恩格斯的著作。1912年5—7月,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第1、2、5、6、8期上,以《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为题,连载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空想社会主义文本”与“乌托邦小说”在内涵和外延上并无多大差异。从使用频率来看,在马克思主义及社会制度研究中侧重使用空想社会主义文本,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常用乌托邦小说。事实上两种用法也没有严格的规定。
乌托邦小说常常是作家的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实验基地。中国知识分子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描述的这种热情和痴迷,究其原因有很深厚的思想根基。中国当代乌托邦小说有两个思想来源,第一个思想来源是孔子的大同思想,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内在的线索,小说文体不同时期的变体,每一种变体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乌托邦成分,如文人笔记小说、章回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等。另一个思想来源自柏拉图之后,17世纪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乌托邦的一个侧面或者一个支流,最终汇入乌托邦的河流)。
自有孔孟的大同社会理想之后,一直以来都有不同形式不同手法的理想社会的探索和想象,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历代文人笔记小说遇仙、修真式的谵妄。《镜花缘》直接从制度入手的颠覆性描述,以此表达女权主义和扶助弱者的理想。晚清、民国的大量无政府主义思潮和空想社会主义文本。中国文化中一直有一股乌托邦潜流,孔子的大同社会理想影响了后世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陶渊明在《桃花源诗》里有理想化的说明,他对现行政治体制表示不满和苛责,只有在“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这样一个没有苛政赋税的前提下,才有“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这样的理想化图景。《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给世人呈现了一个结果,内在地包含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古代文人笔记小说也有很多空想成分,但文人笔记小说缺乏对集体或者某个利益共同体的整体构想,通过志人志怪的形式,侧重个人化的理想状态的描述,成仙、遁世、长寿、奇遇,向往潇洒俊逸的高士、名士风度。大量笔记小说甚至包括猎艳、暴富等低俗的幻想。无论是哪种境遇,都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都表示出对现有的制度的认可和顺从,属道家文化的支脉,与古希腊的伊壁鸠鲁、斯多葛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处,都主张逃离现实,遁入自我内心。其积极意义是表示出对强权的不合作态度。这一脉络承袭下来,直到唐代的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都没有多大的改变。真正从制度上反思的乌托邦文本当数清代小说家李汝珍的《镜花缘》,虽然对制度的探索近乎荒诞,但超越了一种纯粹的空想。《镜花缘》表现对弱势群体的极大同情,直接从制度入手改变政策结构上的不平等问题,想象中的女权社会,对人情风俗匡正,以此来“正人心,宜风雅”。
与中国的桃花源想象形成对比的是欧洲17世纪中叶三个托马斯的空想社会形态的制度设计,他们同样也给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思想资源。托马斯·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文本《乌托邦》(1516),因为这个文本的巨大影响,后世有关各种空想或虚拟的事件都拿乌托邦作比喻。《乌托邦》没有人物塑造,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文人笔记小说。该文本通过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描述某个地方的一个神奇的国度,这个地方财产公有,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穿统一制服,吃公共食堂,选官用人通过公共选举。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超越了所有现实存在的国家。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与《乌托邦》体裁类似,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太阳城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地方,虽然它内部还有奴隶(没有实现人人平等),与周边国家常有战争(作为异端被孤立),外交上也有尔虞我诈(人格的两重性),但已经对现实有巨大的超越。托马斯·闵采尔,这位精通古文学的神学博士,没有像上述两位托马斯留下空想社会主义文本,但他把想法贯彻在实践之中,一生致力于人人平等的伟大事业。三位托马斯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意义非凡,作为一种思潮,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走过近五百年的历史。“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运动到制度,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不断演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8世纪后期,又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社会主义的推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他们三个人有过高度的评价。“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
晚清和民国的乌托邦文本吸收了中西两种资源,蔡元培就认为《石头记》为清康熙朝之政治小说,他自创《新年梦》(1904)也是带有一种制度幻想的“清光绪政治小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陈天华的《狮子吼》(1905)等作品与古代乌托邦文本相比,除了理想品格,更难能可贵的是实践品格,“我们看到,‘新中国乌托邦’的图景在十年后、半个世纪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令人十分感叹其合理性与预示性。”在经过一轮轮的革命实验之后,五四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与无政府主义兴盛,毛泽东同蔡和森,恽代英与林育南,他们都有过理想新村的精心设计,精英知识分子尤其信仰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脱离历史条件地鼓吹立即废除一切形式的强权和国家,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空想。”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如沈从文、废名等则反身寻觅古代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反而是那些经历各种尝试的改革者,最终找到正途。如毛泽东、蔡和森等。
与描述美好未来的乌托邦小说相对应的还有反乌托邦小说,反乌托邦(Dystopia)(或叫“敌托邦”或“废托邦”)通常指充满丑恶与不幸之地。比较典型的有《美丽新世界》《动物农场》《我们》。反乌托邦描述的社会,表面上和平,内在其实是一个大脓包,强权政治、阶级矛盾、资源紧缺、高犯罪率等,是一个看不到未来的社会。科幻类的反乌托邦小说则表现人类受制于人工智能,或物质文明侵害精神文明,人类被高度发达的科技捆绑从而失去了自由。中国当代反乌托邦小说篇目十分有限。阎连科的《受活》(2003)本意是构筑一个残疾人的乐园,圆全人(即正常人)要想过受活庄天堂般的日子,除非把自己弄残,否则无法领受这个村庄所包含的真正的幸福含义。受活庄经历了革命、社会主义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运动和社会变革之后,受活庄的精神领袖和实际上的管理者茅枝婆,她的最大的理想就是带领受活庄人返回过去三不管的时代,去寻找“各种自家田土,不被他人管束的悠闲自在、丰衣足食的日子”。经过现代性洗礼的受活庄想回到古代桃花源式的乌托邦显然是不可能了。《受活》的意义在于传统乌托邦与现代乌托邦缠斗过程中,各种乌托邦尽显所能但都以失败告终,宣告乌托邦的不可能性,与《美丽新世界》《动物农场》《我们》等反乌托邦小说一样,对未来表达了同样的焦虑。
《山河入梦》《人境》《巫师简史》它们各自提供了一种方式或者一种思想类型。它们已经不同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文本,不仅有系统的、完整的制度设计,还进入实际操作层面。三个文本代表了三种阶段的理想社会。这三部小说,虽然结果令人遗憾地滑向了反面,甚至与反乌托邦类型小说有暗通款曲之意,但从制度探索和精神向度追求上有积极的意义,都是出于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的美好展望。为什么在作者意图与目的非常明确的情况下,文本反映出来的现实,或者给读者传达的信息却是另外一番情景?作者有可能陷入一种维姆萨特所说的“意图谬误”,或者是阐释者出现了一种“强制阐释”现象,抑或二者混合纠缠。中国文学中的桃花源情结(或乌托邦理想),往往是在对现实不满意的情况下的幻想。区分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主要看作者是站在哪个逻辑起点上,如果站在社会现实的对立面,从当时社会现状相反的方向去构想,就会带有强烈地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在这种虚构的理想社会形态中,政治、国家机器都有原罪,只有脱离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运行规则、行政组织等各个社会必要条件,才是真正的自由。而现代社会与古代农业社会的桃花源式的乌托邦不能兼容,设造一个靠道德自律、没有法律、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真诚纯朴、安逸和谐、无为而治的“净土”。作家在单纯美好意愿的推动下陷入一种叙事的悖论。
三
为什么《山河入梦》中谭功达和郭从年都以失败告终?他们代表了自由意志的两端,谭功达所以引发灾难代表了自由意志的极端放纵。郭从年代表自由意志的极端控制,导致民众自我异化,所以花家舍的共产主义实验田难以为继。作品表现的积极意义是对两种极端形式的忧思与警示。人追求自由,但需要警惕的是,极端会导致邪恶。郭从年的出场是从聂竹风给谭功达的一封介绍信说起的,因谭功达受处分“发配”到花家舍做“巡视员”(他的实验田是整个梅城县)。信中说,郭从年原是三十八军的一名副师长,林彪手下赫赫有名的悍将之一,从东北嫩江一直打到海南岛,“善权谋”、“性格怪僻”,喜欢恶作剧,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军,都是在笑声中死的。十年前他拒绝了林彪要他入空军的命令,一个人回到花家舍做起了“山大王”。谭功达进入花家舍,就看到一幅别出心裁的标语“花家舍欢迎您”,字是在长满菖蒲的湖里用浮标拼成的。村子里的住户都是粉墙黛瓦,格式、装饰、庭院都一模一样。每天晚上有节目表演,财产都是公社所有,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拿着同样的镰刀去收割紫云英,宽宽的帽沿底下的脸也是同样的表情。让谭功达纳闷的是“为什么这里的人都显得郁郁不欢”?当谭功达提出给他分配一项工作,工作人员告诉他,花家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从不向任何人派任何工作,而是由每个人自己决定去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在这方面,每一个公社社员都享有完全的自由”。没有规章制度、没有行政命令、甚至没有领导。花家舍的社员不是被动地应付上级指派的任务,而是依照花家舍未来可能的样子忘我地工作。每个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培养出奇妙而伟大的直觉,事实上既不会误工,也不会窝工,每个工作所需要的劳动力一个也不会多,一个也不会少。“按劳计酬”、“民主评分制度”、“道德自律委员会”,还有一些非常抽象的机构。除了工厂、农田和桑树林等基本生产场地,学校、医院,各种公共设施都是免费的。还有一个神秘的机构:101。他们接下来的计划是推山填湖,增加稻谷产量。每个人心底无私,胸怀坦荡,反倒是谭功达这个外来人“太多心”。公社所有社员都不知道书记郭从年长什么样,他很低调,可能就在人群当中,也许见过面、握过手。他究竟长什么样子,人们还是忍不住发挥丰富的想象力,花家舍流行着各种版本的传说,有的说他一头银发披挂在肩头,皮肤嫩得像婴儿,有的说他坐在轮椅上。也有谣传郭从年三年前就得肺结核去世了,公社方面出于特殊考虑隐瞒死讯,秘不发丧。一个儿童团员告诉谭功达,在花家舍每个人都是郭从年。让谭功达没有想到的是,天天与他打交道的向阳招待所那位身上有股猪粪臭味的驼背八斤就是郭从年。花家舍除了云遮雾绕般的神秘,谭功达不得不感叹郭从年的才华和智慧,生活在这里的人的确不会有什么烦恼。当然也不是完全能做到人人平等,还有很多匪夷所思的怪事情。谭功达来这里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嫉妒心,出于在梅城建人民公社失败的愤恨,他要到花家舍现有的体制中找出弊端,就在他快要离开时也没找到。然而问题终于暴露出来,姚佩佩(谭功达的心爱的人)因命案亡命天涯与谭功达通信扯出了线索。“铁匦制”就是花家舍的软肋,郭从年通过“铁匦制”管制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举报成风,收发的信件都要过101之手,并复制一份(手抄)存档。“人性原则”就是“好奇心原则”,人永远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即使人的所有愿望都得到满足,但人的好奇心仍然会受到煎熬。郭从年早就预感到了花家舍将被人的欲望击垮。一对日本夫妇参观花家舍后,决定回去生一个孩子,郭从年给他们的孩子取名“光”。
《人境》中的神皇洲比花家舍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它不仅涉及到资本主义理念与社会主义信仰的斗争,还有跨国资本与本土农业的博弈,过度开发与生态主义的对抗,民间与官方的对立。中共十六大以后,东北和华北出现了成百上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马垃所在的神皇洲地处长江边上。合作社取名“同心社”,主打产品是“同心生态大米”。一开始规模很小,只有五户:谷雨一家(谷雨在大工厂打工被机器切了手指),胡嫂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胡嫂的丈夫在城里建筑工地上从十几层楼掉下来摔死),留守老人曹广进和老伴(儿子儿媳在武汉打工),孤儿小拐子(小拐子的爹在小煤窑冒顶时没来得及逃出来,小拐子的娘从煤老板那领了几万块跟耍魔术的江湖艺人私奔了),马垃(单身,坐过牢)。除了马垃,都是村里的困难户。马垃的同心村几乎集中了“矜、寡、孤、独、废疾”,符合孔子大同社会对弱者的扶持、人人平等的理想。马垃莫名其妙坐了七年牢,但他有经营大公司的经验,从小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作品滋养长大,怀有共产主义梦想。马垃的哥哥就是一位抢救公共财产牺牲的烈士。马垃对同心社的制度设计有很强的操作性,一开始就主动融入市场,他认为棉花和小麦的价格由全国乃至国际市场定价,而水稻自己有定价权,不同产品价格相差很大,这些年生态大米很吃香。他们去湖南农科院买到了袁隆平新培育出来的“南优2611”。生产、销售,一切都很顺利。神皇洲有两家合作社,另一家是种粮大户赵广富,他集拢一些强壮能干的农户组成一个合作社。赵广富的女婿是一家跨国公司的亚洲区代表,沿河县楚风集团就是这家跨国公司的控股企业,生产除草剂草甘膦。头两年,赵广富的合作社生产的抗虫棉大获丰收,市场价格也好。马垃提醒他们,印度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很多棉农自杀,他们种的都是抗虫棉,抗虫棉的种子价格和化肥需求量节节攀升,而棉花价格却大幅下跌,棉农辛苦一年,反倒欠一大笔货款。种子、农药、化肥都被外国人控制,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李海军(跨国公司亚洲代表、赵广富的女婿,马垃的老师)不客气地打断他,“你脑子要换一换,什么中国外国,现在都全球化了……”马垃的合作社一开始就处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矛盾冲突之中,他积极融入全球化这个大市场之后,一方面要维护本土文化传统和共产主义价值观念体系,一方面要抵抗全球化大潮跨国公司和美国经济文化的侵蚀和操控。最后,赵广富的合作社走上印度棉农的老路,马垃的同心合作社被官商勾结的跨国公司以洪水的名义灭掉。
《巫师简史》里的酉北县位于湘西。陈统领大办工厂,湘西十县自治,治下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整个湘西安定和谐。这是猫庄的大环境。猫庄是个富裕寨子,红军“土改”工作队来猫庄,打算揪出一两个恶霸地主,激发老百姓的情绪,然后把田地分到每个人。只有他们分到了田地,才会有人踊跃报名参军。可是,猫庄人告诉工作队,猫庄人没有地契,地契只是一张纸,猫庄人的契约都在心里装着。工作队的领导周正国意识到这是个特别的地方,他在其他地方的一切工作方法在猫庄都失效了。不仅各种条例在猫庄没有对应,他的慷慨激昂的演讲得到的是集体的沉默。人群没有躁动,没有跟着他振臂高呼。猫庄没有地主,猫庄人人有田地、有饭吃、有衣穿、没有欺压。周正国想揪出一个田地相对数量比较多的人做典型也失败了,因为猫庄人的田地都是按人头分的,每人一亩六分水田,二亩八分旱地,五亩四分坡地。每十年重新分一次田地。族长身上也找不出催租逼税、欺男霸女的恶行,这就尴尬了。一说到征兵,台下的猫庄人哄地一下就散了。但给苏维埃的钱粮布鞋却又悉数上缴,让工作组找不到革猫庄命的借口。猫庄显然过于理想化,主要是制度问题,一是只取传统中合理的成分。对有些致命的问题视而不见。孔子的大同社会开启了中国人的德治梦想,他删改六经,奠定了“尧舜德治禅让”的心灵根基,以至于后来者对未来制度的设计过于简单化,避开重大而艰难的经济难题和精神难题。在儒家礼制德治的框架之下,往往会忽视人的自由和平等。猫庄的土地问题与经济制度是脱节的,土地均分初步解决生产力适应生产关系问题,但这里头有许多块垒没有化开,对于男女平等、人的自由、人格成长完善、价值判断、理想追求等方面的回答显得无力。彭武芬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女孩,过目不忘,却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她只能站在学堂门外旁听。赵长梅因诞下私生子,被族规处以私刑,夺去年轻的生命。自私、贪婪、邪恶的族长弟弟赵天文却混得顺风顺水,猫庄的族规和私刑失去普遍意义。作者通过这些例子反证了只有德治没有法治的后果。瓦解猫庄的力量看上去是战争和动乱,年轻人有的参加红军、有的参了国军、有的变成了土匪。有些是被迫的,大部分是自愿的,实际上他的制度没有了凝聚力和向心力。年轻人要追求另一种生活,要去另一个世界,要生活自由、婚姻自主,挣脱族规和神规的双重枷锁。
四
当代中国作家对于乌托邦小说的建构一直持极为谨慎的态度,很多人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律视为“无法实现”的社会制度,以及前面提到的反乌托邦小说的火上浇油,使得乌托邦具有贬义的意味。再加上乌托邦小说是一个科学系统的制度构建,在意识形态领域涉及许多艰难和敏感的话题。然而,新世纪前后全球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对新旧制度(包括西式民主)批判声一浪高过一浪,有生命力的社会改造方案却仍然稀少,构建一种预见性的没有弊端的社会制度是有难度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是将“乌托邦”与“科学”对应起来进行分析的,也是为了说明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和他自己倡导的社会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恩格斯明确地界定:“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曼海姆对乌托邦界定很明确:“一种思想状况如果与它所处的现实状况不一致,则这种思想状况就是乌托邦。”它仅仅是一个客观描述。
乌托邦小说的作者意图很强,阐释者的立场也很明显。社会文化性价值比艺术性价值更突出。《山河入梦》的花家舍几乎到了一种比较高级的社会主义形态,或者是已经一脚迈进了共产主义门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劳动分工废除后的状况有如下描写:“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这一景象在花家舍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实现过程看作历史的、发展中的过程和运动。《山河入梦》在社会外在形态上基本达到了共产主义标准,但他们面临一个更艰难的问题——人的意识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真正完成之后进入共产主义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答案留给了未来。《人境》面临的是资本暴力和政治不合作,“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由于市场的不确定因素,生产者始终被产品或者剩余产品钳制。《资本论》里的著名公式,W=C+V+M(即商品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其中M剩余价值是资本形式的呈现,在现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环境下,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操控M。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对社会生产资料并没有主导权,外来资本可以通过非正常手段任意霸占。而可变资本即劳动力也被外力支配,不具有完全自主意识。他们既没有资本主义的市场优势,又没有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此,他们还很难达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人境》还涉及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力量对体制的控制将使体制陷入危险或覆灭的可能。私有制与公有制如何保持一个恰当的比例?这个答案也留给了未来。《巫师简史》面临的制度本身重大改革问题。作者有一个理想在里头,他想超越人性(假定人性趋于完美),超越制度(假定制度不需要在社会进步过程中不断升级改进),完成一个纯粹自然形成的大同社会的想象。认同德治方式是一种值得期待的方式(假定这种不需要法治的方式更完美更高级)。族长虽然也要动用家法和族规,但须凭族长的个人威望得以实现。可以省掉一笔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费用。德治强于法治的制度存在一个人才选拔制度的困境,“选贤任能”的机制如何进行?如何避开“人性的结构性伪善”?许多历史进程其实是由技术进步触发的,这在工业化信息化之后体现得更为明显。制度结构上缺少一种社会力量、科技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平衡。
结
语
三部小说都有极强的现实感,在实践性上具有某种警示意义。《山河入梦》和《人境》最后都是毁于资本主义洪流,《巫师简史》的猫庄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桃花源”毁灭在真实的社会主义之中。中国当代乌托邦小说在体制上有一定的反思能力,对社会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有预测,包括对这些问题的深刻的忧虑。但往往对社会发展规律缺乏一种宏阔的视角,对人类终极目标和理念缺少整体的把握,对某些探索性的改革缺乏理解和同情,并且对中国目前的制度选择以及其历史性和必然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人类未来图景的描述上,反而丢失了古代作家的想象力传统。过于经世致用的观念导致小说失去了乌托邦应有的超越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