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里的书房
2018-11-08陆俊文
○陆俊文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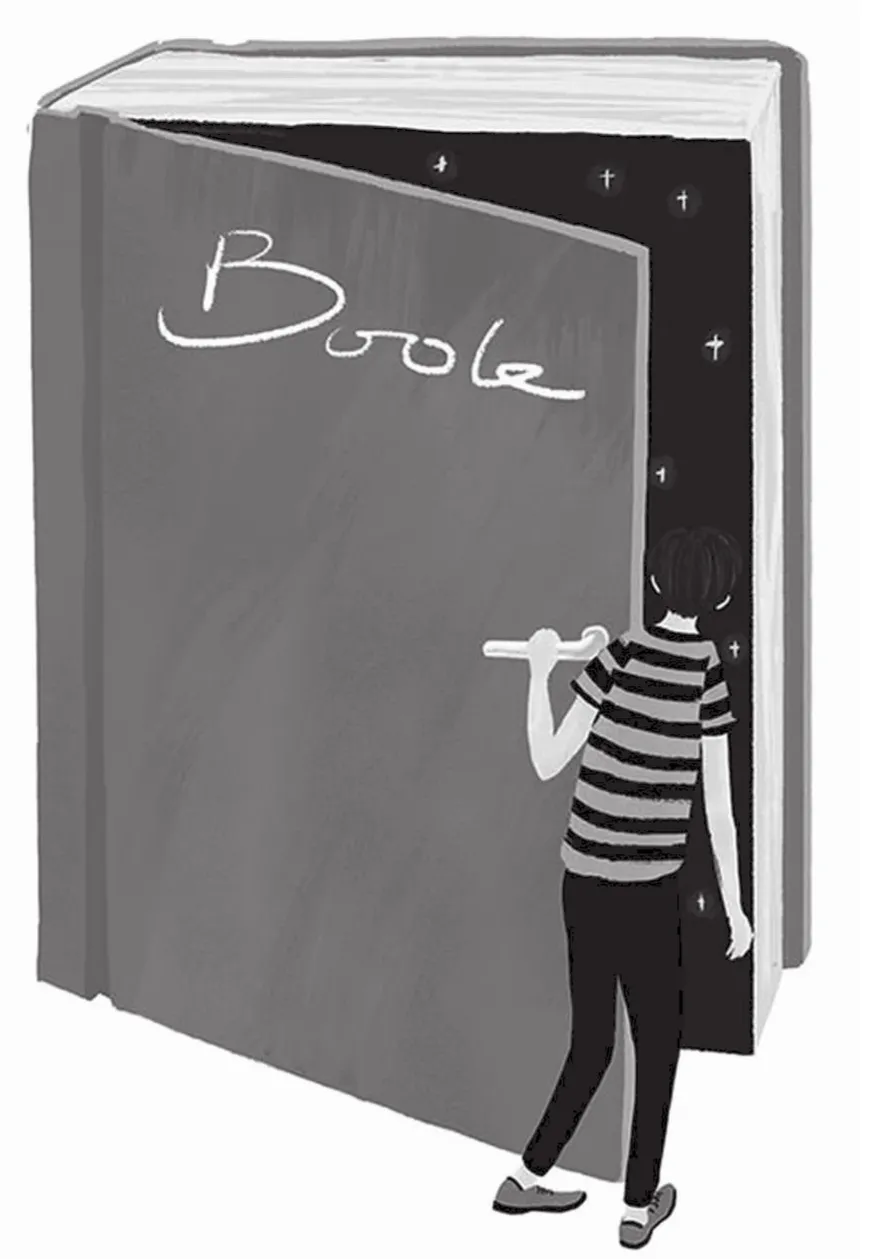
我在小城里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学校的大门每周只有周日下午两点半才会开。到了六点半,班主任就开始在教室里点人数,缺席者名字会被写在黑板的右侧,迟到者则要站在门口等待老师训话。每周日的这四个小时对我来说太宝贵了,以至于我常常在周六就开始盘算这段时间要怎么度过。周日午休时,我更是辗转难眠,生怕自己睡过头。所以,我常常躺在床上盯着枕边的闹钟看,快到点了,我就“嗖”一下跳起来,赶在学校大门打开的第一时间冲出去。
但我常常在冲出去后又不知所措,只好在小城的街市里兜兜转转。街市很短,水果摊和文具店我都逛遍了,甚至连路人我都熟悉得不得了。于是,这短短的四个小时逐渐变得刻板而因循守旧起来。我让三轮车车夫把我拉到附近的书店,买完习题和参考书后我就囫囵吞枣地把那些“不务正业”的书翻来翻去,遇到喜欢的就买下来。直到熬过四点半,我才依依不舍地移步离开,往那条熟悉的旧街道走去。行人们都各自奔波着,我心想:难道这就是我的青春吗?我灰头土脸地回家洗澡、吃饭,然后掐着表坐颠簸的三轮车回到学校。
2
校园小得即使天色暗了下来,人们也寻觅不到藏身之处。最令我讨厌的是,隔壁理科班那个多管闲事的班主任。我曾经几度被他从寝室里揪出来,和室友们并排站在大太阳底下暴晒,或者在寒冬的夜晚被罚绕着球场转圈跑。他总是仰起他高傲的下巴蔑视我,而理由又总是那么荒谬——午休、晚休时间都不能看书。
我们是十个人住一间寝室,走道狭窄得甚至不能并排站两个人,锈迹斑斑的铁床脆生生的,仿佛随时都会被压弯或折断一般,让人心惊胆战。重要的是门边还有两扇窗户,巡视的老师走过时,里面的动静能看得一清二楚。学校中午十二点下课,十二点半午休,铃声一响,整栋楼就像是中了邪一般,从方才的欢腾声中戛然而止。老师们每天都来查房,他们扫视着床上床下,甚至连房间里有几只蜘蛛、几只蟑螂都熟稔于心,可唯独有一个地方他们看不到,也管不了,那就是每间寝室的厕所。
这个阴暗、潮湿、逼仄,而且味道不怎么好闻的空间,成了我们每天争夺的战场。每个人都会手不释卷地带一本书蹲在这个小角落里,从看第一行字开始就不停地有人小声催促:“你好了没?轮到我了!”大家你争我抢、唇枪舌剑,每讲一句话前都要仰头观察是否隔墙有耳。
而我总是等他们都累得睡着了,才悄悄地抱着书蹲在厕所里翻看。那个年纪看的书多而杂,我有时候沉迷于故事的曲折,有时候又感叹于作者文笔的优美。我在那间滴答漏水的厕所里,用了两周才看完王安忆的《长恨歌》,而王小波的书则时常让我破涕为笑,《黄金时代》我读了好几遍,《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让我忍俊不禁。那个时候,我最中意的作家是郁达夫和太宰治,我不仅反复阅读他们的小说,还不由自主地模仿那种叙述的笔调,把人生过得昏天黑地。
3
我开始上瘾一般买书,然后躲在厕所里看,这个闭塞、阴暗的空间仿佛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书房。晚上十点半寝室熄灯,而唯有厕所可以亮着灯。昏黄的灯光映照在纸张上,叫人愈发迷离。
有时夜里失眠,或是被噩梦惊醒时,我都会悄然从枕边取一本书,蹑手蹑脚地爬下床,躲进厕所。困顿或是难过的情绪会在这里烟消云散。我怕厕所的灯光太亮影响舍友休息,便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月光或是走廊彻夜不熄的灯光,抱膝蹲地在深夜里读。
这狭窄的空间让我有足够的安全感,红白砖块砌起的高墙将我与外界隔绝,有绵绵的青苔痕,有斑驳的砖墙影,于是我在这里思考青春和人生。
在那段岁月里,我把吃饭的钱都省下来买书,那些书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而来,我将它们一一带进我的“书房”,和我共度一个中午或是临睡前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