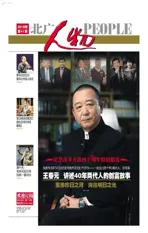贾平凹谈文学:要写出中国人状态
2018-10-29
写得准确和得意也是我们常说的与神相遇的时候

10月7日,第125期文汇讲堂《让世界认识贾平凹》邀请德国著名汉学家、作家、德国波恩大学终身教授顾彬主讲 《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传播》,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贾平凹作回应主讲。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众议,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郜元宝,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多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彭青龙与顾彬展开圆桌对话。以下整理自贾平凹的演讲内容。
要挣脱业已成为习惯的文学观
当一个人被拉出来评头论足的时候,作为一个写作者感慨万千,确实感慨万千。表扬如同鼓掌和加油,批评如同教练指点,让我跑快点。
从上海交大一天半研讨会到今天下午文汇讲堂,我听了发言,有一些做了记录。大部分是肯定我的,受到肯定当然高兴,它让我能增加一些信心,就像比赛场上,鼓掌和加油的声音一多,就拼命地往前跑。当受到一些批评和被指出不足的时候,我也很高兴,让我有很多启发,就像田径赛场上,教练在旁边不停地指点着你的动作、节奏,使比赛者跑得更快一点。
更重要是从每一个人的讲话,看他是怎么思维的,看他对这个世界如何做判断、审美和思考,从而来影响激发自己内在能量,寻找我自己通往文学的出口。现在轮到我发言,想把自己这一两年常萦绕于心的问题,借这个机会再详细说说。
从一件往事谈起。十多年前我在西北大学带过文学写作研究生,有三年时间。在那三年里几乎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跟学生反复强调,怎样建立自己的文学观,努力挣脱业已成为习惯的那套固有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影响着我们的写作,同时也影响了我们的阅读。所以我一再强调,并从各个角度去讲要建立我们的文学观,也就是我们要明白文学的真正意义,我们的独立思考、我们的观察、我们的判断、我们的追求和想象。
我举这个例子,意思是干任何事情,一是要从大的方面、在根本的问题上有所明确了,解决了,然后别的事情才能解决。比如我写作的技术的问题都是这样慢慢来解决的。我们常说一级是一级水平这句话,就是说村长面对的是一个村,乡长面对的是一个乡,县长面对的是一个县,省长面对的是一个省,总理面对的是一个国,面对的问题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一样。在文学写作上,一直要盯着文学写作的态势,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整个文学是怎样一个大盘子,大盘子里装着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豆子,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永恒是什么,哪些是永恒,我们没有永恒的局面会怎样,我们又是如何没有永恒的。
努力从特殊走向普遍并反复递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作家写作,对世界文学,它是特殊的,是“这一个”。它的努力都是想着使自己能走向普遍的意义。这个普遍意义如同文明轴心国影响着全球或区域一样。作为特殊的“这一个”,当经过努力,差不多使自己有了普遍的意义,往往遇到了更高的文学标准,就将自己的普遍性又还原到了特殊性。我们现在讲从高原到高峰,也是一样道理,一直努力着,登到了一座山,以为是高峰了,可往前一看,前面的一座山更高。由特殊到普遍,再由普遍回到特殊,再由特殊到普遍,这样的过程是冲撞的、破裂的、痛苦的。但当了解了自己与更高的文学标准的关系,才能够分析、吸纳,融合、重新生成,以内在能量再次使自己的特殊变成普遍,如此反复递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写作才能大成。
小说的基本价值,或者说写作的理由,是表达人类生存的困境,并探讨复杂的人性,使人活得更美好。我们强调普遍性,就是要求写出所写的人与物的本性。本性是人类共知的,是自然散发的,彭青龙老师讲到是共同、共通,也是共识的。举个例子,当我们一群人乘坐一辆汽车去某一个地方旅游,早上十点的时候,我说肚子饿了,咱停车去路边店吃饭吧,全车人都不理睬,司机也不会把车停下来。而到了十二点,我说肚子饿了,咱停车去吃饭吧,大家就都响应,司机也会把车停下来,大家一块去了路边店吃饭。这就是说,凡是人都有饱了饿了的感觉,但吃过一顿饭后大致有个肚子再饿的时间,十点钟我的肚子饿了,那不是吃饭的节点,只是我一个人的肚子饿了,而十二点才是大家的肚子都饿了。小说写作写出一个人的饥饿感是不行的,要写出所有人的饥饿感。当然这取决于作家自己的见识,有能量还要有定力,也就是说你要能发现十二点时你饿了,大家都饿了,你还得有能力将这种集体饥饿感写出来。所以从这一点上讲,任何的作家都是在写自己,写作的过程就是发现和提升自己的过程。写得准确和得意也是我们常说的与神相遇的时候。
准确、真实地写出中国人状态
文学的普遍性就同文明的轴心化一样,它的外化就是文明的担纲者,这样来看我们当下的作品并没有影响别的国家的写作,我们对于世界文学还处于特殊性阶段。这就需要我们一是竭力增强自己的能量,提高自己的力量,以适应全世界的文学环境,二是超越地域、国家和民族,建立世界视野的想象力,以便安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对于现今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们、社会学家们都发表了很多的言论,他们认为虽然中国还没有在世界上处于中心的定位,但世界原有的秩序在失衡,在重新组合,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这种判断是对的,那么可以说真实、准确地写出中国现实社会,写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也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之所以在这里强调真实与准确两个词,是我们要警惕当下写作中迎合的东西,这种迎合有时是有意的,投机性的,有时候是不自觉的、引诱的和裹挟的。比如说迎合偏激、迎合娱乐消费等等。
当突破地域、民族、国家的视野看到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结构意义,然后再强调地域、国家、民族的存在,找准我们中国的位置,找着中国文学的位置,这是非常重要的寻找位置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寻找对手和镜子,干任何事情都得有对手,没有对手就得有镜子。位置没有找对,就可能产生无尽的烦恼,找对了,我们就相对自由了,就知道你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知道你应该坚持什么放弃什么。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递进循环中,越是要扩大文学视野越是要专注自我,这就是四海漂泊、守株待兔。
因为有中国国情的所在,因为中国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现实,中国当下文学中批评的元素非常多也非常强烈,这似乎成了中国当下文学的一个特点,而很久以来我们讲作品的深刻,总是以批评的强弱为尺度,这样就常常出现一些观念的写作。我们几乎习惯了作品中精英式的视角,但是中国文学会不会还有另外的写作呢?会不会还有另外的视角呢?20年前我与一位著名的电影摄像做过交流,他说作为电影摄像有两种,一种是极力要表现摄像的存在——其构图、其颜色、其情调、其节奏,当你在观看电影时,不断地能看到这里有摄像的存在,强调这是他的作品。另外一种,就是摄像完全消失,观看电影时,你忘了这是电影,这就是存在于天地间的一个真实。我是推崇后一种的。在我的认知里,凡是一个生命,在生命达到圆满的时候,他是精力充沛的、反应敏捷的、能吃能跑能干活的,浑身都感觉有一种气向外喷发,甚至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就像佛一样,头颈上有光圈。而一个生命不圆满,或者是病残,能让他干什么呢?这就是说作品把你所要写的人或物,写到位、写到本性,其就有了所谓象征意义、诗性,否则那只有人为的外在的强加,只是观念写作,是可能会一时取悦于世,但很快就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