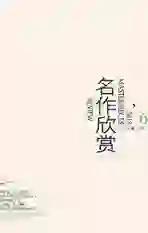双重特征的卑微者
2018-10-20胡鑫鑫王芳
胡鑫鑫 王芳
摘 要:卡夫卡在《城堡》中通过对女性头发、体型、服装、首饰等装饰性细节描写,展示了女性的卑微处境,她们既是K.追寻路上的同伴,也是引诱K.堕落的诱惑者,她们具有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性,承载着卡夫卡的多重思考。
关键词:卡夫卡 《城堡》 女性观
《城堡》是卡夫卡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主人公虽然是男性,但是其中大量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却在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的叙事功能。据笔者统计,《城堡》共写到十三位女性,根据体型外貌特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身材高大粗壮丰满,比如酒店老板娘黛嘉娜、巴纳巴斯的姐姐奥尔珈、酒店女侍佩碧等;另一类女性瘦小虚弱,有着忧郁的眼神,如弗丽达、汉斯母亲等。从外表看,两类女性前者偏重肉体,后者偏重精神,她们和K.以及城堡当局(权力)的关系也判然有别,对这些女性人物的刻画,显然反映出了卡夫卡多层面的女性想象,对这些女性人物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卡夫卡的女性观。下面本文就将从三个方面,来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物质女性:权力的附庸
卡夫卡写女人,极少采用肖像描写的手法,而是高度关注女性的头发、体型、服装、首饰等装饰性的细节。先说头发。相对于身体的其他器官而言,头发非常特别,它自身体长出,却没有任何感应器,不能传达任何感受,它的造型、颜色,更多的是产生一种视觉的效果,它更像是个体姿色、性格的象征性符号,正如学者汪民安所说:“头发是身体的资产而非身体的器官”,“不同的造型、不同的发式选择、不同的类别,都立体式地扩充着头发的意义。”{1}在《城堡》中,弗丽达“是个不太出众的小个子金发姑娘,带着忧伤的眸子和凹陷的脸颊”(城,27),客店老板娘的头发很浓,佩碧有一头又浓又密的金红的头发,并在头发上编了许多蝴蝶结和丝带。奥尔珈和阿玛莉亚姐妹、女教师吉莎、洗衣服的女人都有着一头金发。金发在西方文化中是性感的标志,爱神阿芙洛狄特就有一头漂亮的金发,在描述女性性吸引力方面,卡夫卡显然并不能免俗。传记材料显示,卡夫卡年少时,曾有一位金发法语家庭教师或法国女人促成了他的性觉醒,因此,金发是卡夫卡对异性形成的最初的也是最深刻的印象,《城堡》中如此之多的金发女人,正是K.这一点的绝佳注脚。这些金发女人中,大多数都高大、粗壮、丰满。客店老板娘珈黛娜是铁匠的女儿,身强力壮,她庞大的身躯能遮住屋里的光线;巴纳巴斯家的两姐妹又高又结实;吉莎有着结实而丰满的身体;佩碧有两条胖腿。这些丰满的肉体正如“熟肉铺子”一般,给人以无限的性幻想。
此外,《城堡》中的女性描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女性服装、佩饰的反复刻画,甚至不乏津津有味的探讨。参加庆祝会的阿玛丽娅白衬衣的胸前鼓着一道道花边,妈妈把所有的花边都帮她镶上了,姐姐奥尔珈也把借來的波西米亚红宝石项链戴在了她的脖子上。得到酒吧招待位置的佩碧在脖子上戴了一条直垂到领口开得很低的露胸短衫里的细项链,用眼花缭乱的蝴蝶结和丝带来打扮自己,她的女友更是拿出了最好的料子来帮她缝做衣服。“当时大家多喜欢这件新做的衣服,它好像是成功的保证,要是再补做一条腰带,对于未来的成功就毫无疑问了”。《城堡》中的这些女性,似乎都天然地倾向于谄媚权力,“女人和官员的关系……是很难断定的,或者不如说是很容易断定的。他们之间总会产生爱情……如果当官的看上了女人,女人就不能不爱他们;是的,她们在这之前就爱上他们了”(城,189)。漂亮衣服,繁杂的装饰花纹显然都是女性用来增加自身性吸引力的筹码。这些女性都精通诱惑术,并以接近权力为荣。在K.跟着奥尔珈去贵宾旅店时遇到弗丽达,“她在卖弄风情地拨弄着她那件剪裁得挺马虎的奶油色罩衫”(城,28),高傲的目光则显示出弗丽达作为城堡高级官员克拉姆情妇的虚荣与满足。客店老板娘那满柜子与老板娘身份不符、装饰繁杂、式样过时的衣服也暗示着老板娘曾经是城堡官员情妇的身份。
克劳斯·瓦根巴赫在其《卡夫卡传》中曾说:“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女性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描写成了妓女。”{2}在《城堡》中,这个判断无疑是适用的。阿玛丽娅凭借着精心的装饰赢得了索蒂尼的青睐,而男人们也都对佩碧的精心打扮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大家都抢着摸摸佩碧的鬈发……谁也抵挡不住这些鬈发和蝴蝶结的诱惑”{3}。连K.都不由自主地偷偷伸手抓住一个蝴蝶结,想把它解开。试图挽回家庭地位的奥尔珈则与克拉姆的侍从们整夜狂欢:“奥尔珈是舞蹈里的中心人物……舞越跳越快,叫喊声像喘气似的,越来越显出渴求的意味,越来越震耳欲聋,后来渐渐变成几乎像是一个人的声音了。”(城,30)“天亮了……奥尔珈虽然衣衫不整,头发散乱,但仍像昨晚一样活泼。”(城,33)
《城堡》中的女性社会地位都非常低,她们都承担着艰难的工作。有一部分女性虚弱疲乏,沉默寡言,眼神忧郁,尤其是几位母亲,在她们身上,肉体的诱惑力被大大削弱,尽管如此,她们同样对权力有着难以遏制的向往,和那些肉感的女性一样,都是男权的附庸。
二、精神女性:同伴与障碍
和酒店老板娘黛嘉娜、奥尔珈、佩碧等身材高大粗壮、精力充沛、欲望强烈,与做事功利性强的女性不同,弗丽达、阿玛丽娅、汉斯母亲等较为文雅,她们的眼神得到了卡夫卡的重点关注,这类女性精神色彩较浓。弗丽达具有不同于他人的眼神,“她的目光,她那流露着的神气却让人感到惊异。她的目光落在K.身上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目光似乎她已经办妥了与K.相关的几件事”(城,27)。这样的目光,如同黑暗中的光明,牢牢吸引了K.的注意。反叛者阿玛丽娅的“目光是冷冰冰的,清澈的,像往常一样一动不动的;她的目光往往不是直接盯着她观察的东西,总是带点儿苦闷的神气对它微微地斜睇着……这目光本身并不让人讨厌,它是矜持的,而且在深沉中蕴涵着正直”(城,128)。“她那忧郁的眼神——却高傲地对我们不屑一顾,我们几乎真的不受控制地要拜倒在她的面前了”(城,144)。“不同的就是她那冷漠又高傲的目光,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就被她的目光给震惊了”(城,157)。汉斯母亲,“躺在靠背椅上的女人像是泥雕木塑一般,甚至都不低头看一眼怀里的孩子,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屋顶”(城,9)。这些女性迥异于他人的眼神似乎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吸引着K.。
卡夫卡擅长用目光来反映人物的精神世界,《城堡》几乎每位女性的眼神都被写到了,但这几位女性的目光却因为与人类群体疏离(汉斯母亲甚至连怀中的孩子都不顾)而有某种属于城堡的属性,让K.能够一眼就认出她们来。从这一点来看,她们和K.是同一性质的人:她们不满足于现状与既成事实,渴望与城堡建立更为深刻、持久的关系。在卡夫卡笔下,这些女性甚至带有某种宗教色彩。汉斯母亲,来自城堡,苍白、虚弱,一出场似乎就笼罩在一束圣洁的光里,“在屋子的后墙上有一个很大的窗洞,这是墙上仅有的一个洞,一道雪一般的白光从窗洞外射进来,从那里透进来,显然是从院子里射来的。在角落的深处一个女人正疲倦地几乎躺在一张高靠背椅上,她几乎斜卧着,洞里透进来的白光,映得她的衣服像绸缎一样发亮”(城,9)。这是一副改写的圣母子图,圣母不再是传统油画中那种充满慈爱的形象,而是冷漠麻木,无所用心。弗丽达、阿玛丽娅眼神中也都有这种超凡脱俗的傲慢气质。
有意思的是,K.总是想方设法接近她们,试图利用她们达到接近城堡的目的,最终却正是因为她们而远离了城堡。K.接近弗丽达,是为了与克拉姆建立某种联系,但是当K.渴望见到的克拉姆就在房门背后,推开门就能见到时,他却因拥抱着弗丽达而失去了理智。“K.不停地想要摆脱这种状态,但根本做不到,他们在地上滚了几圈,砰的一声撞上了克拉姆的房门”(城,32)。原本作为K.与城堡的桥梁和引路人的弗丽达却在此时让K.彻底迷失,忘记了自己的最终诉求。这种情节设置让人想起圣·奥古斯丁所说的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物比女人的拥抱和肉体的结合更能使男人的心堕落。”{4}显然,在尘世之爱与永恒追寻之间,卡夫卡表现出了相当的矛盾性,他承认了女性对K.巨大的诱惑力量,同时也赋予了K.执着追寻的精神。
K.与这些具有城堡属性的女性具有某种精神上的契合,他借助她们一步步走近城堡,但是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对她们的爱恋,在性的迷醉中失去了接近城堡的机会,最终与克拉姆失之交臂,从这一方面来看,女性无疑成了男性实现最终诉求的阻碍。她们表面上为K.提供了帮助,实际上却都在分散K.的注意力,都在损耗K.的精力。“每当在故事进入高潮,在决定主人公命运的关键时刻,她们便出现,抓住主人公就往自己身上拉,她们一面给主人公制造种种麻烦,一面诈称自己在帮助他”{5}。卡夫卡笔下的女性就这样成为悖论的载体。
三、性欲不洁与死亡冲动
弗丽达和K.“他们互相拥抱在一起,她的娇体在K.的手里燃烧起来,他们滚在一起,失去了理智,K.不停地想要摆脱这种状态,但根本做不到,他们在地上滚了几圈,砰的一声撞上了克拉姆的房门,随后他们又躺在了洒落在地上的一小摊啤酒和粘在地板上的脏东西上。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俩像一个人似的呼吸着,两颗心像一颗心一样地跳动着。时间在流逝,K.不断感觉到,他迷了路,或者到了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到过的奇异国度,在那里连空气都与故乡的空气有着显著差异,在那里任何人都会被那种奇异感窒息而死的,这种奇异感是如此强大,如此诱惑,使你什么也干不了,只有继续往前走,继续迷失”(城,32)。《城堡》中的这段性描写,可能是文学史上最匪夷所思的性描写,它既给人男女交媾肮脏的感觉,又可以看成是男女完美融合的抒情段落,这种双重性和小说中女性群体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双重性是一体的。
卡夫卡是犹太人,熟悉犹太教的各种教派与教规,同时他又是归化了的中产阶级家庭,了解基督教的各种观念。犹太教中的一些禁欲的教派如库兰宗派认为婚姻中的性关系将导致宗教礼仪上的不洁,早期基督教著名教父德尔图良和奥古斯丁都对性欲持负面看法,认为女性要对男性的肉体堕落负最主要的责任。德尔图良认为女人是“邪恶之门”,奥古斯丁也认为“女人从一开始就是邪恶的,她是死亡之门,是毒蛇的信徒,是魔鬼的帮凶,是陷阱,是信徒们的灾星。她腐蚀圣徒,那危险的面孔使那些就快要成为天使的人功败垂成”{6}。卡夫卡显然熟悉这些观念,《城堡》中的性爱描写,就隐含着这种性欲不洁甚至暗示着死亡的思想,性在某种意义上与死亡冲动颇为相似,弗丽达对K.说:“我向往着一座坟墓,一座又深又窄的坟墓;在那里我们俩像被钳子夹住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我把脸紧贴着你,你也把脸紧贴着我,谁也看不到我们。”(城,107)卡夫卡有自虐倾向,他在日记和笔记中为自己的死亡设计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残的快感往往和这种性的高潮有异曲同工之处。《城堡》中K.与弗丽达在激情中迷失,完全忘记了身处何处,身下的肮脏、柜台上坐着的两个助手,都被遗忘,也颇有墓中的况味,正如弗丽达所说,只有在坟墓中,才能真正不受干扰地相爱。
“文学、姑娘和死亡:弗朗茨卡夫卡就在这个三角中游戏人生,消耗人生。”{7}在《城堡》中,卡夫卡对女性进行了多层面的刻画,她们和K.一样卑微,急于获得权力的认可,是K.追寻路上的同伴,也是引诱K.堕落的诱惑者,她们具有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性,承载着卡夫卡的多重思考。
{1} 汪民安:《我們时代的头发》,见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2}{5} 〔德〕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周建明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第86页。
{3} 〔奥〕卡夫卡:《城堡》,魏晓亮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页。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为了行文简洁,后文只随文标出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4} 〔美〕D·L·卡莫迪著,徐钧尧、宋立道译:《妇女与世界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
{6} 〔美〕詹姆斯·A·布伦德茨:《中世纪欧洲的法律、性和基督教社会》,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7} 方速林:《卡夫卡女性观》,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1] 方速林.卡夫卡女性观[D].湖南师范大学,2012.
[2] 李晓娟.卡夫卡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解读[D].南昌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