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地理学视野里的传统中国
——读韩茂莉《十里八邨: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
2018-10-16□
□
从家门到耕地的往返距离是十里,集市上的顾客来自周围八个乡村。从初生到暮年,从清晨到黄昏,一代代生命如水般回旋流转,这就是近代山西乡村中,许多人一生周而复始的历程。在中心地理论的描述中,人们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六边形里,遵循着内敛而精确的轨迹,而在青苗起伏的垄边地头,农人们也常在不经意间说起身边的世界:十里八村(邨)。
韩茂莉新著《十里八邨: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从地理视角解析近三个世纪以来的山西乡村社会,综合历史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等方法,研究民间基层管理、商业、祭祀、婚姻、水利社会等问题,论证“十里八村”实际是近代山西村民的有效认知范围和日常活动空间,集市交易带来的人际关系构成了各种社会活动的基础,揭示了出行半径与传统观念对农户生活的影响。在城市化疾速发展、我们日益疏离乡村的今天,这样一幅乡村社会图景将引我们频频回望。
朝暮之间的回归线
其实人们的耕作路程未必永远是十里,八村也常常是六七甚至十余个村庄。生活的半径随着高山河谷延伸,又在平原上变得短促而密集。但不变的是人们总行走在日出日落之间,如同飞鸟追寻着日光往复的痕迹。这也许是从洪荒时代沿袭而来的习惯,远古的人们迎着山峦后的晨光,采摘树梢的浆果,追逐林中的鸟兽,当暮色降临时,伴着虎豹远近起伏的低吼声,跨过村寨外流水潺潺的壕沟,走向月光下载歌载舞的篝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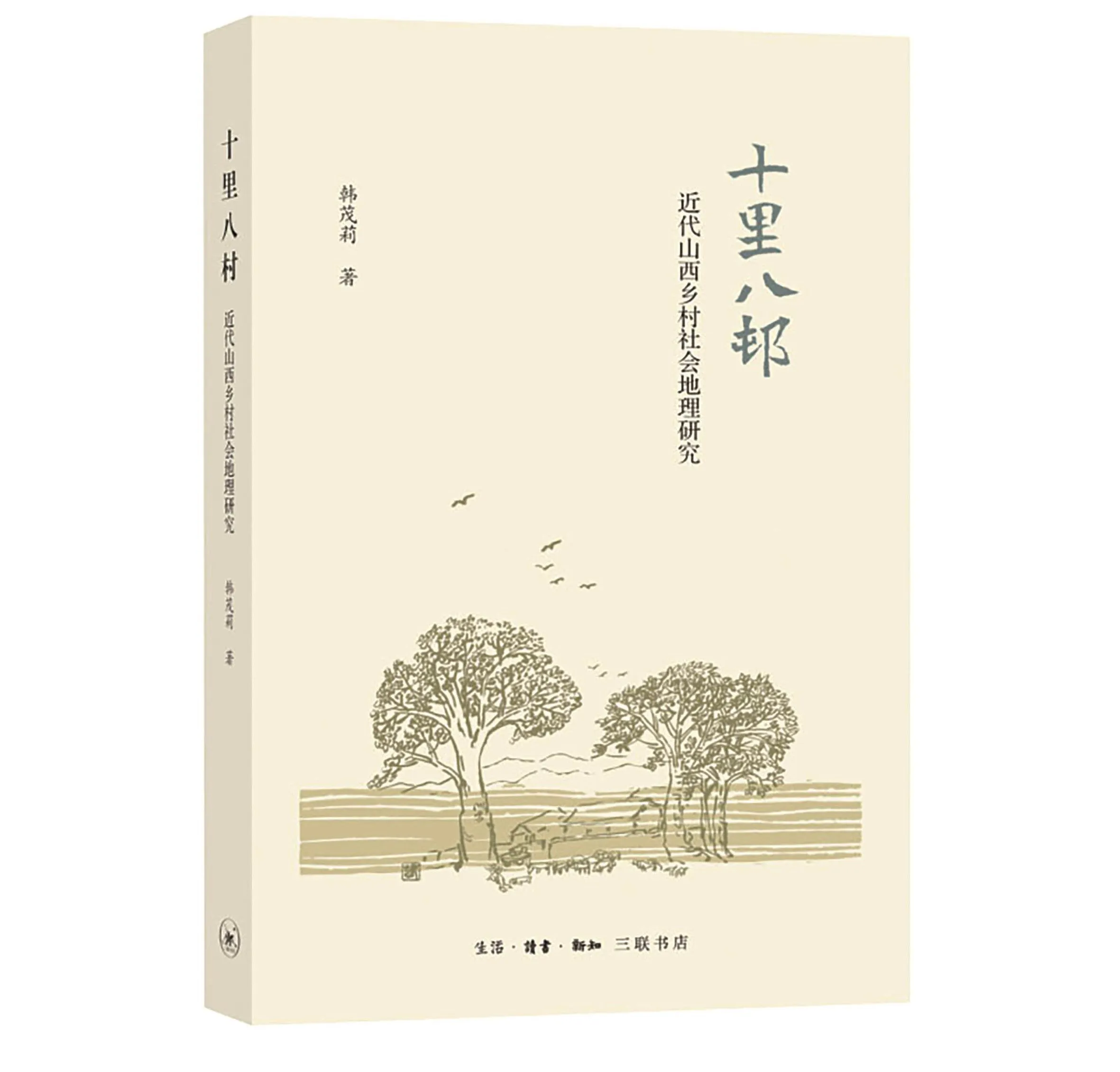
物换星移,时空变幻,后来人们修起城墙,天子坐上朝堂,普天之下裂土划境,逐渐确立起百里设县,一日往返的习惯。县令清晨出巡,视察辖境最边缘的河堤水堰,傍晚返回县衙,行程也在一日之间。又如朝行暮栖的驿站,间距也常是四十到六十里,人们前行的步伐迟速各异,却同样遵循着日升日落的轨迹。
常在白天往返于十里八村间的还有另一群人,他们被百姓称为“能人”,又在后世的书中被写作“精英”。他们不是朝廷命官,常因姓氏、地位和自身能力受到推选,权力范围通常只在十里之内,管辖村落的名字也不会写入官修的一统志,但他们的职责却和县令们一样,催粮收税,维护治安。前者是朝廷教化中天经地义的职责,后者是乡邻们近在咫尺的现实期待。在以农立国的时代里,被称为乡约、里长的精英们常是乡村中真正的权威。人们用血缘和姓氏织成乡间最细密而威严的权力,构成传统社会里自然而坚固的基石。
生活在集市中歌唱
以一日为往返界限的并非只有村落和县境,还有喧嚣的集市和庙会。连绵的群山改变了市场的间距,也影响了远近的田圃风光,人们在城郊种植不易储存的水果和蔬菜,在清晨采摘下新鲜的果实,匆匆进城入市,又在远处和山间种植五谷和耐寒作物,在高低不同的地带形成错落的风景。
道路永远是市场的生命,相交的路口总能汇合出无限商机。集市并非天天开放,也许是单日或双日,也许是初一和十五,最简陋的草棚茅店也会迎来熙攘的车马,人们在固定的日子奔向集市,如同飞鸟从四面八方向太阳飞翔。这是千年来中国乡村不变的风景,商业圈与社交圈合二为一,叫卖声中伴随着亲朋们久疏的问候,关于农具与籽种的攀谈里夹杂着有意无意的探究。人们在茶棚与饭铺里交换着奇闻轶事,关注着十里八村的每一场风吹草动,织成熟人社会里悄无声息的天罗地网。
这里是媒人与中介们大显身手的天地,道路上随时可能出现精心筹划的偶遇,琳琅货架掩不住秋波流转,马车外飘落又捡起的手帕上,绣着晨光中最先歌唱的鸟儿和春天里最初绽放的花朵。人们在戏台下结朋交友,在庙宇外暗定终身,他们把集市上听来的消息带回家,村头的杂货小店可能是下一场传言的起点。一代代乡土传奇从这里茁壮生长,河边浣衣的女子们在欢笑声中结束窃窃私语,抬眼望去,会看到远处青石桥上,回首又驻足凝视的少年。
守望在异乡的飞鸟
如同很多关于基层社会的研究一样,在看似繁琐的数据里,总能留下无数曾经鲜活的生命痕迹。他们耕种或是行商,居住在深山或旷野,家中有或多或少的田产,零落分布在村庄的不同方向。整个村落中可能只有一个姓氏,也可能有因婚嫁而来的外姓人,偶尔还会出现外省来的佣工,他们不携带家眷,仿佛从遥远树林飞来的鸟儿,在另一群人的故乡做着异乡人。
人多势众的大族往往支配一方天地,主宰着河水的流向与祭祀的内容。孤单的姓氏里可能埋藏着隐忍的故事与思乡的情绪,日常细碎的生活中,不同的衣食习惯,细微的口音差异,都可能造成无言的亲近或疏离。宗族构成了人们相互支撑的力量,却也会迎来分家析产,自立门户的日子,一代代生命开枝散叶,如同鸟儿栖息在不同的树梢,也改变了村落附近的田园景观。
神殿颂诗与英雄传说
栖息在树顶和低处的鸟儿也许永不会相遇,但当它们生活在同一高度时,总难避免纠葛的出现。想要和平相处,便只能各自退让,在一场场纷争与妥协间划出安全的生活界限。为了吸引客源,争夺开集日期的人们会把官司打到县衙甚至省城,而最后的解决结果,通常也只能用一四七和三六九的日子来区分。轮流开集是千古不易的良策,与捻阄一样公平而有效,但在另一些时候,人们的选择是另辟蹊径,开创一方新的天地。
村落里的人们祭祀着不同的神灵,如同集市选择不同的日子交易,一眼望去,可能是村东敬龙王,村西祭土地,村南拜玉皇,村北祀关羽。每座新建的庙宇都带来新的商机,每位新增的神灵都成为新的乡贤,他们与村民同在,像亲朋一样倾听人们的诉说,在香烟缭绕的诵经声里安抚尘世的悲欢离合。
有时人们无法平均分配数字,只能用激烈的方式解决纷争,像鸟儿振翅扑向对方,激荡起漫天飞羽。在遍布着江河沟壑的国度里,河流与水源随时可能变成战争或械斗的导火索,占据源头的村落拥有天然优势,下游的人们则难免大费周章。山西洪洞一座庙宇石碑上铭刻的故事里,人们的解决方式是向沸腾的油锅里投下十枚铜钱,能用手取出几枚,便拥有几分河水的使用权。一位年轻人徒手捞起七枚铜钱,在悲壮的情节里成为世代传颂的英雄,两地之间却械斗不止,以至断绝婚嫁,视若敌仇。学者们曾用治水视角解读中国早期的大一统历程,而在山西乡间因水而起的纷争中,或许会看到这种宏大历史的缩影。

这些风景出现在近世的山西,却又不限于这片时空。千年来的中国乡间,随处可见这样的人们,每天清晨,他们离开家门,前往几里之外的耕地,黄昏时分,伴着各自投林的飞鸟,返回家园。脚下的山峦与平原也许会换作河湖密布的水乡,官道上的车马也许会变成烟雨中的乌篷船,天南海北的人们祭祀着不同的神灵,买卖着各异的货物,社戏中吟唱着高亢或低回的曲调,锣鼓与丝弦中却讲述着同样的悲喜与期盼。
繁衍生息的人们换了一代又一代,黄尘路上印下稍纵即逝的脚印,直到轰鸣的汽笛划破平静的天际,工业时代滚滚而来,辘轳在喑哑的声音中汲起井水,清凉又带着黄土气息的风里,依然回旋着千年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