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ke Ricci
2018-10-16陈湘墨
文|陈湘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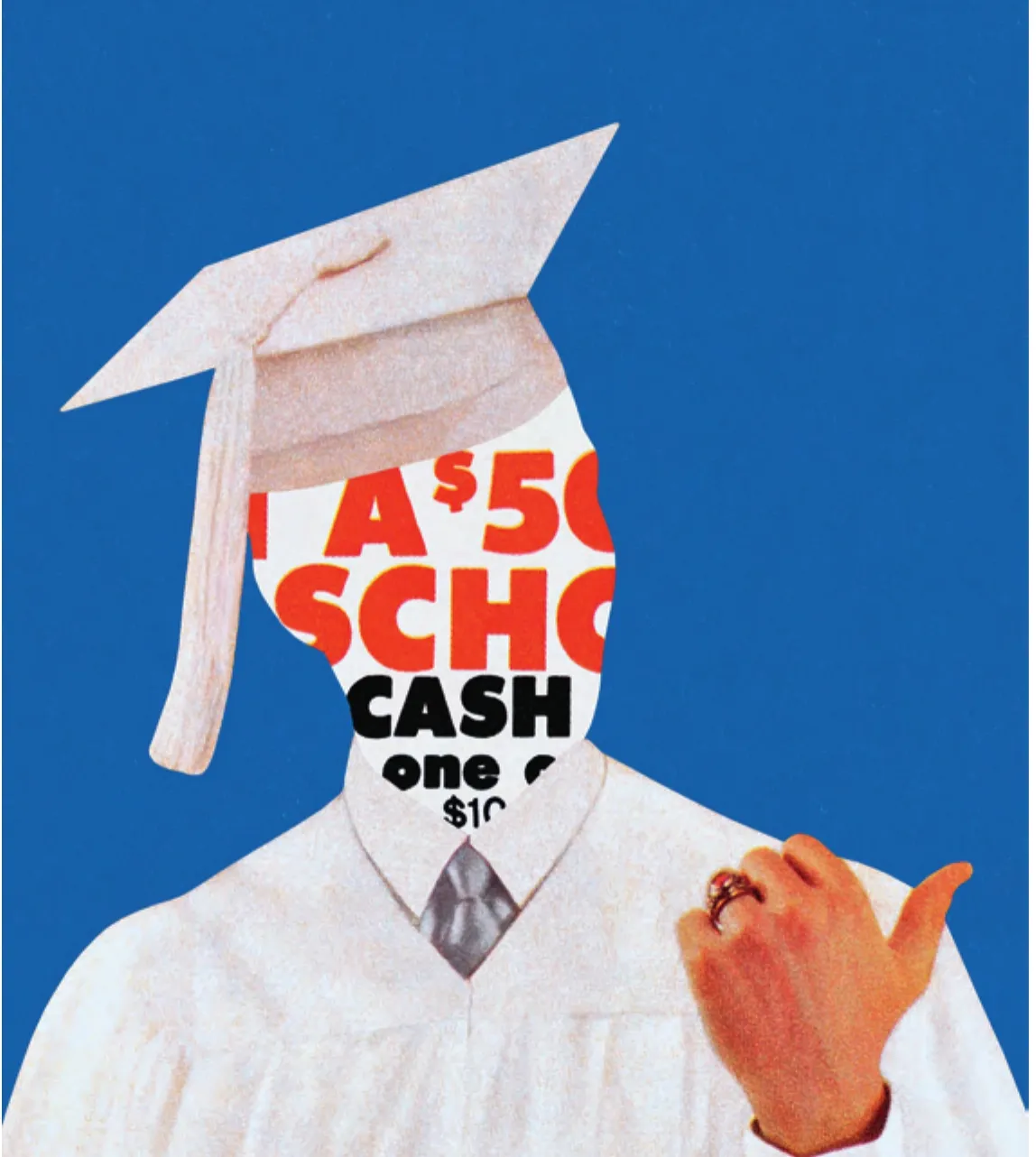
一
“What's your name,sir?”
这就是我对Jake Ricci最初的记忆。
我们学校要求大一学生都必须上一门叫“大学英语”的通识课。因为学生基数大,所以我们被分成了几十个小班,每个英语老师负责三四个班,我的老师就是Jake Ricci。Jake是个美国人,宽额头,高鼻梁,下巴到耳根长着密密的胡茬,头发像落了秋霜一样灰白。
第一堂课上,我正好坐在第一排,自然成了他讲课时举例的对象。他先询问我的名字:“What's your name,sir?”他的发问让我心中一颤,因为他用了“sir(先生)”这个词。刹那间,我有一种清晰的疏离感—我不知道我已经是可以被称呼“先生”的年龄了。
“Mark。”我说。
二
我逐渐意识到高中英语和香港这边大学英语之间的差距。当然,从高中走向大学,对英语的要求提升是必然的,但我感受到的是断层一般的差距。从交际性信件到看图说话,再到针对学术文章的Annotated Bibliography(文献注释,简称AB),这种断层让我无所适从。
我自认为英语不算很差,但AB成绩发下来的那天,Jake那成堆的纠错让我吃了一惊。我感觉有必要跟他面谈一下,于是用邮件约好时间后就去了。他的办公室在旧校OEE10层1007。他瞥了一眼在门口有些局促的我,然后立刻把目光扫回面前的电脑屏幕上,并招呼我拿把椅子坐下。
这是我和他第一次单独见面。那天我们谈了很久,我似乎是把每个地方都问到了,但这让我觉得思维清晰之余,仍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挫败感。我在AB里犯的绝大多数错误,都是因为我的遣词造句与英语本身的表达习惯不合。这甚至很难说是错误,只是别扭而已,但是这类问题无法举一反三—语言是经验主义,知道就是知道,如此而已。
第二次作业Argumentative Essay(议论文,简称AE)要求我们根据题目选择立场,从给定的三篇学术文章中提取论据,完成文章。然而,这次的成绩比AB还差—现实给了我贵族式的自尊一记重击,我情急之下又去预约面谈。
“这个例子太过绝对了,你要注意。”Jake指着我文章中的某处说道。
“但这是您给的学术文章里的例子啊!”
“并不是说我给的文章都是好的。”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他也用淡蓝色的眼睛看着我:“如果要我给那个作者打分,我不会给高分。”
“那您为什么还要把这篇文章给我们呢?”
“我想看的是你们整合信息的能力。通过自己的判断,你们究竟能将这三篇文章的价值挖掘到什么程度。”
他的这番话对我触动很大,也让我内心生出些许敬意。我一直对质疑学术文章这件事抱有一种畏惧,但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质疑貌似需要雄厚的本钱,但其本质是独立思考的权利。若说质疑需要勇气,那近乎说吃饭需要鼓励,睡觉需要助威。
“你关心自己的成绩是件好事,但是我感觉你过于紧张了,得放松放松。你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光顾着找女朋友呢。”Jake冷不丁抖出一个包袱,接着自己笑了起来。
三
我从学校的公告墙上偶然得知,学校要组织一场英语小故事创作比赛,有点儿动心。但是转念一想,编故事并不是我的强项,于是心里又打起鼓来。
有一次英语课前我跟Jake闲聊时谈到了这个比赛,他问我参不参加,我摇摇头,说:“应该不会参加,我没有写小说的经验。”
“又不是小说,只是小故事而已。”
“那也肯定需要编故事的技巧吧。”
“我给你一个建议,‘show,not tell’(故事要展示,而不是讲述)。”
后来我还真在Brooks写的《故事力学》里找到了完全一样的观点。我兴奋地把这本书带到课堂上给他看,他笑着点头。
“我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本,有什么灵感就写下来。”Jake向我传授他的经验。
正在我犹豫要不要参加小故事创作比赛的时候,英国语言文学系的前辈向我推荐了诗歌创作比赛,于是这就成了压倒前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之后某个清晨的英语课,我正好第一个到了教室,Jake突然问起我有没有决定参加小故事创作比赛。
“就像上次说的,不参加了,不过明年也许会尝试的。”
“我就是问问,看你有没有改变主意。”Jake靠在讲台上,右脚插在左脚外边,漫不经心地喝着咖啡。我看着他这副模样,想起他有一次自白:“我可不是早晨很有干劲儿的那种人。”
四
大一下学期去上Jake的课时,我有意早到了一些。让我惊喜的是Jake到的比我还早。他坐在教室外面的凳子上看手机,一见我来了,立马打了声招呼:“嘿,Mark,你今天看起来轻松多了!”
“那不是多亏您没fail掉我上学期的英语嘛。”
“你怎么会fail呢?哦,对你来说,fail就是B吧……”
“上学期期末的时候,我没写完参考文献列表考试就结束了,我保守估计都只是C了。”
我也是在这次谈话中知道,我们是Jake带的最后一届学生了。这学期结束后,他就会回美国再读一个硕士。
“您为什么不读博士呢?”
“读博士太累了,而且,很多机构只是看博士的名号,其实他们招聘的那些人很难说真的配得上博士的头衔。”他淡淡的回答让我有些惊讶。
“那您为什么来香港教书呢?”
“赚钱。”仍然是无所谓的语气。
我本以为这学期我可以真如他所说“放松一些”,但是在面对ARP(Argumentative Research Paper,研究性论文)时,我仍然焦头烂额。有一次找Jake面谈的时候,我甚至一路跟着他去7-11买三明治。
“你只要把自己想写的写清楚就好。你找我这么多次,我感觉你只是想要得到能让我开心的答案。”他一手抓着三明治,几根胡萝卜丝从面包夹缝里伸了出来。他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欣赏,但也没有埋怨的意思。
“这倒不完全是……我的论题有关中国内地的教育,可我自己就是它的一个产物。”选择这个论题,多半是出自我对自己曾经身处的教育体系积攒的怨言,但我没有考虑其棘手程度。我以为离那个教育体系远一些,我就仿佛拥有了可以批评它的力量。可到头来发现,我接受的教育就是我的影子,我不仅看不清它的全貌,甚至它还会影响我看待其他事物的眼光。
“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Jake突然笑了,“与英语无关,这门课就是要让你们思考,独立且清晰地思考。我很高兴你做出这种挣扎。”
Jake确实也给我提了一些方向上的具体建议,但那是我唯一一次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也正是那篇ARP的成文以及公开报告,让我从他那里得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分数。
五
“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给Jake办个欢送会什么的?”我跟Bella(同为内地学生,一直跟我竞争Jake的头号粉丝,不过基本都是她赢—好些关于Jake的事还是她告诉我的)说。
“好啊。唉,虽然名义上只是暂时的离别,但感觉却像永别一样,可能是因为真的很久都见不到了吧。”
“还好我存了他的照片。”
“偷拍?”
“是上学期小故事创作比赛的时候照的,虽然我没参加比赛,但我参加了颁奖仪式,没想到他还在上面演讲呢!”
“他是组织者啊。”
我一下子愣了,思绪疯狂地回溯到那个清晨的英语课前。我说也许明年会尝试参加这个比赛,但我当时既不知道他是组织者,也不知道明年他就不在这里了。Jake向我们宣布他不再任教是在第二学期的一节课上,他并没有伤感的意思,至少没有表露出来。他说我们让他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我回美国之后大概会休息几个月,跟我老爹一起。我家还有农场呢。”后来我从Bella口中得知,Jake的家乡在匹兹堡。
最后一节课上,Jake站在讲台上扫视我们。他的语气没有变化,就像以往的每节课一样。他说:“我告诉你们最后一件事—words mean things(文字必有所旨)。”
我写了一首诗,打算送给Jake。Bella一眼就看出我要送诗给Jake的意图,不过她没有猜到这首诗是用中文写的,她知道Jake不懂中文。然而,我并不是为了让他读懂才写这首诗的,而是为了表明一种确实的身份—words mean things,仅此而已。
六
我、Bella、Jade等几个和Jake关系特别好的人想请他一起吃饭,因为担心会有Conflict of interest(利益冲突)的问题,于是,我们决定在期末出成绩之后再约。
我们约在黄大仙的牛八涮涮锅专门店,进店的时候,Jake已经到了,远远就看到他坐在椅子上向我们招手。
席间我们谈了很多事情,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透过小巧火锅冒出的蒸汽,Jake向我发问:“你是想做一位阐释世间道理的人呢,还是想做一位描述它们的呈现方式的人?”他貌似是让我在哲人和诗人之间做个选择。
“后者。”
“果不其然。”
这顿饭本来是我们请客,但饭后Jake拿出信用卡,说:“这就算是我给你们最后的招待吧。”
“我们以后到了美国,去哪里可以找到您呢?”
“在一个农场里。”Jake诙谐地回答。
后记
在李作权大道上有一家矮矮的太平洋咖啡店,店门大敞着。有时候,会有一两只麻雀飞进去在桌子间绕圈,或是在冷柜前的木地板上跳来跳去,啄食面包屑和午后闲散的时光。我曾在这儿偶遇Jake。
他没坐在店内,而是坐在店外黑色的椅子上。他戴着墨镜,双手摊开搭在椅背上,灰色的短袖被撑出一种优美的弧度,有种广告模特的感觉。
“您怎么在这儿?”
“我在等着上11:30的课。”
“您等我买个Croissant(羊角面包)再来跟您聊……我这个发音没错吧?”
他点了点头。
“Croissant是个法语词吧?”
“是的。”
我从店里出来,拉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他给我讲了一个笑话,可惜我没听懂。
“我打算用中文写一篇有关您的回忆录。”
“一定给文章起个酷点儿的名字。”
“以后我会去美国留学,有时间就去看您。”
“可以啊。”
“不过说起来,适应那边的学习生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
“Mark,I don't worry about you.”
“What do you mean?”
“You can take care of yourse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