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与反思鸠摩罗什汉译《中论颂》里龙树的两个“两难论证”与“一切皆空”之论证
2018-10-13赵东明
赵东明
一、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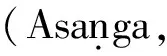

二、探析与反思鸠摩罗什汉译《中论颂》里龙树的两个“两难论证”

(一)以《中论颂·观去来品》论证“不去”为例
鸠摩罗什汉译龙树《中论颂》第二章《观去来品》关于“不去”的论证,偈颂如下:

在这个论证式中,龙树质问论敌[注]按照前后文脉络看,龙树《中论颂》的论敌应该是指佛教“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主张“三世实有”的学者。其他如龙树《回诤论》(Vigraha-vyāvartanī)中的敌论,一般认为是指“正理学派”(Nyāyika),也可能是指佛教内部的实在论者,如“说一切有部”的学者。不同于学界的既有观点,Chr. Lindtner主张《回诤论》的论敌应是阿毘达磨论者,其证据是敌论多使用佛教词汇。(Chr. Lindtner, Nāgārjuniana: Studies in the Writings and Philosophy of Nāgārjun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2, pp.70-71, note, 110.)。:你所谓的“去”是指“已去”,还是“未去”?论敌不论回答“已去”还是“未去”,都将陷入一种困境,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难论证”。龙树的辩驳论敌确实很高明、精彩,问题是其辩论的对手(即论敌、外道)能够认同吗?
1.龙树使用相同语词存在“歧义”以质疑论敌
在上述“两难论证”里,龙树非常精彩地对“去”这一个名言概念,提出不同的定义(即有着“歧义”)来质疑论敌,也就是将一般日常语境定义与使用的“去”这一词汇,区分成“已去”与“未去”这二个概念。可见,龙树在此处对相同语词的使用是存在着“歧义”的。因此上述这个“两难论证”,其辩论的对手可能完全无法认同甚至拒绝回答[注]龙树除使用“两难论证”式辩破其辩论的对手外,还常使用“比量”论证式以及“归纳论证”。也许龙树其实并不认同完全固定形式的逻辑系统(因完全固定化即有所谓的“自性”见),而不是完全拒斥类似西方形式逻辑比量的使用。当然,因为龙树在陈那之前,所以他也不是使用陈那所建立的新因明三支比量。(杨惠南:《龙树与中观哲学》,前揭书,第257—269页。)。
其实,论敌可以这样回答: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说例如“我明天要去上海”这样的话,如果龙树还要问“去”这一词汇是指“已去”或是“未去”,那么日常生活还有世俗约定俗成且可以作为互相沟通的名言、概念或语言吗?在同一语词存在“歧义”时,我们还能够彼此进行对话与讨论吗?显然,龙树的这个问题其实精彩在运用名言、概念的“歧义”,制造让论敌陷落入两难而无法回答的困境之中。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其辩论的对手没有必要回答龙树的这个因运用语词存在“歧义”而难以回答的两难诘问。
2.龙树似乎对“胜义谛”与“世俗谛”的区分存在不同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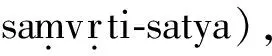
另外,如果龙树确实严格地区分“胜义谛”(paramārtha-satya,第一义谛)与“世俗谛”这两个层次,那么“世俗谛”存在着来、去的运动现象,应该也是龙树所承许的。但若“世俗谛”承许来、去的运动,却又在这里将“胜义谛”的不来、不去,拉到“世俗谛”的层面来谈论,并且反驳论敌的日常认知及语言使用,那么显然龙树可能对“胜义谛”与“世俗谛”的区分存在不同标准,这同样让人感到困惑。
由以上讨论可知,龙树论证“不去”的这个“两难论证”,其实还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是无法让其辩论对手完全认同的论证,甚至还可能导致论敌拒绝回答与对话。
3.西方学界对龙树《中论颂·观去来品》的论证的讨论
以上的讨论与解释,是基于鸠摩罗什汉译的龙树《中论颂》第二章《观去来品》。关于《观去来品》的研究,在西方佛学研究界算是个热门议题,比较新近的是2012年丹·阿诺德(Dan Arnold)的《龙树反运动论证的迷惑无知:另一观点看〈中论颂〉第二章》一文[注]Dan Arnold, “The Deceptive Simplicity of Nāgārjuna’s Arguments Against Motion: Another Look at Mūlamadhyamakakārikā Chapter 2”, in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2012, vol. 40, pp.553-591.。在此文,他提到一些前人的相关学术研究,这里顺道稍微谈及一下。
一些现代诠释者认为龙树这个有名的论证及其扩展的论证,按照传统字面述说,被当作是类似于“芝诺誖论”(Zeno’s Paradoxes)[注]See Mark Siderits & J. D. O’Brien, “Zeno and Nāgārjuna on motion”, in Philosophy East & West, 26(3), 1976, pp.281-299; I. W. Mabbet, “Nāgārjuna and Zeno on motion”, in Philosophy East & West, 34(4), 1984, pp.401-420;B. Galloway, “Notes on Nāgārjuna and Zeno on motion”, in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0, 1987, pp.81-87.。在适当地找出龙树论证的此种数学特征方面,单尼尔·英格尔斯(Daniel Ingalls)认为其数学论证的形式源自典型的古希腊哲学传统,即在语言学与文法学的分析上,呈现出对古印度哲学家而言的知识典范的统治。[注]D. H. H. Ingalls, “The comparison of India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in Journal of Oriental Research, Madras, 22, 1954, pp.1-11.相对于此,卡马雷士瓦·巴达恰雅(Kamaleswar Bhattacharya)则指出,在经常被引用的《中论颂》中,龙树的论证采用的不是数学的几何学预设前提,而比较像是梵文文法的预设前提。相对于上述这些支持重建当代的数学论证方式的主张者们,巴达恰雅强烈主张“承认龙树与月称之论证的梵文文法学基础是错误者,已经承担了许多不精确说法与朦胧晦涩的责任”[注]See Kamaleswar Bhattacharya, “Nāgārjuna arguments against motion: Their grammatical basis”, in A. L. Basham, et al. (Eds.), Corpus of Indian studies: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Gaurinath Sastri, Calcutta: Sanskrit Pustak Bhandar, 1980, pp.85-95; “The grammatical basis of Nāgārjuna’s arguments: Some further Considerations”, in Indological Taurenensia, 1980-1981, pp.8-9,35-43; “Nāgārjuna’s arguments against motion”, in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8, 1985, pp.7-15; “Back to Nāgārjuna and grammar”, in Adyar Library Bulletin, 1994-1995, pp.58-59,178-189.。
比较晚近的研究,例如珍·威斯特霍夫(Jan Westerhoff)则在《中论颂》此章节中,区分了三类不同类型的论证。为详细阐述此说,他有效地识别出巴达恰雅分析作为功能的一些相同点,将之取代为“性质缺乏论证”(property-absence arguments)和“性质迭加论证”(property-reduplication arguments)[注]Jan Westerhoff, Chapter 6: “Motion”, in Nāgārjuna’s Madhyamaka: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29-152.。在此种诠释中,龙树的论证被理解为一般就条件而言是性质的实体化(就像是“成为运动的起因”being an agent of motion)。克劳斯·欧特家(Claus Oetke)对威斯特霍夫此种诠释提出挑战。他使用当代的概念工具来说明,如“休姆问题原则,也就是我们若要区分事物的不同,必须设想他们一者独立于另一者”[注]“the Humean principle that for things to be distinct we must be able to conceive of them independently of one another.”,《中论颂》第二章应解释成“给予一个论证形式的例子,如此可以应用到主题(subject-matters)的多样性”[注]“give an example of a form of arguments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a variety of subject-matters.”。他的论点是,所有龙树《中论颂》第二章的论证都应被理解为具有建立“一个形而上学宗旨”(a metaphysical tenet)的“最高目标”(overriding goal)[注]Claus Oetke, “Two investigations on the Madhyamakakārikās and the Vigrahavyāvartanī”, in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39, 2011, pp.245-325.。
从以上介绍可知龙树此论证被西方佛学界理解、解释与讨论的复杂性。或许,正如丹·阿诺德的论文标题所示,龙树《中论颂·观去来品》的论证似乎仍存在许多迷惑无知(Deceptive Simplicity)。
(二)以《中论颂·观法品》破除“(神)我”的论证为例
鸠摩罗什汉译龙树《中论颂》第十八章《观法品》关于破除“(神)我”的论证,偈颂是:


1.龙树自己认许的语词,其辩论的对手不一定能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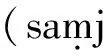
需要注意的是,鸠摩罗什在汉译青目《中论释》时,仅仅将梵文“ātman”一词翻译成“神”字[注]鸠摩罗什所翻译的青目《中论释》是这样注释龙树上面这段文偈颂的:“有人说神,应有二种:1、若五阴即是神;2、若离五阴有神。”“1、若五阴是神者,神则生灭相。如偈中说:若神是五阴,即是生灭相。何以故?生已坏败故,以生灭相故,五阴是无常,如五阴无常,生灭二法亦是无常。何以故?生灭亦生已坏败,故无常。神若是五阴,五阴无常故,神亦应无常生灭相,但是事不然。2、若离五阴有神,神即无五阴相。如偈中说:若神异五阴,则非五阴相,而离五阴更无有法。若离五阴有法者,以何相何法而有?若谓神如虚空离五阴而有者,是亦不然。何以故?《破六种品》中已破,虚空无有法名为虚空。”(黑体字及1、2等数字为笔者所加。CBETA, T30, no.1564, 24a15-27)需要补充的是,佛教对外道教派(印度主张有“(神)我”教派等)的质疑是“离五阴更无有法。若离五阴有法者,以何相何法而有?”但这些教派显然认为“(神)我”是离于五阴的,而且认为不需套用佛教的解释来说明(如五阴)。因此,佛教(在这里是龙树、青目)这样的质难,笔者认为外道是不太会认同的。。这里的“神”字不是指大自在天、毘纽天、梵天等“天神”,而是指人内心中永恒不变的“灵魂”或“自我”。 笔者以为,此处的论证在某种程度可延伸成反对大自在天、毘纽天、梵天等存在的佛教式的“反上帝存在论证”。严格来说,这其实是反对“灵魂”、“自我”(ātman,“阿特曼”)存在的一种“反(神)我存在论证”,所以这里不能对鸠摩罗什翻译的“神”字有所误解。
问题是,龙树的辩论对手一厢情愿存在如佛教这样的观点吗?显然,外道的立场应该是:“(神)我”超越佛教所谓“五阴”(五蕴)的定义!因此,龙树在这里以自己认许的语词(“五阴”或“五蕴”),强加在他人所不认许的语词(“五阴”或“五蕴”)上,可能会导致辩论对手并不能真正认同。因为论敌、外道显然不认为一切法不能超出“五阴”(五蕴),至少他们认为“(神)我”就是超出于“五阴”(五蕴)之外!所以,龙树这个破除“(神)我”的“两难论证”式,其辩论对手应该是无法接受、甚至拒绝回答与对话的。
2.论敌或外道可以选择不回答龙树的两难质疑
按照龙树的思维逻辑(如果龙树有的话),不只是如上两难的论证型式,即便加上将“(神)我”说成是与“五阴”的关系为“亦是亦异”或“非是非异”,连同之上的“是”、“异”的所谓穷尽一切论证的“四句论破”型式,论敌或外道显然无论如何回答,都会陷入错谬的困境之中。问题是,为什么论敌或外道非得要顺应龙树这样的思维逻辑呢(如果龙树有固定思维逻辑的话)?当他们发现龙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在质疑与诘难他们的命题或主张,他们还需要与龙树进行理性的对话和讨论吗?显然,论敌没必要理会龙树的诘难,像傻子一样地落入龙树所设下的“两难论证”陷阱。

三、探析与反思龙树关于“一切皆空”的论证
在鸠摩罗什汉译的龙树《中论颂·观四谛品》第二十四记载着关于“一切皆空”的偈颂:

这个偈颂有别于龙树经常使用的“两难论证”式,而是基于经验上观察的知识而推论出的“归纳论证”(induction或inductive argument)式。龙树的意思应该是:在我们经验范围内,观察到的每一法(事物)即一切法(事物),没有一法(事物)不是从“因缘和合”(意思是“空”)而产生的(偈颂“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所以每一法(事物)即一切法(事物),没有一法(事物)不是“空”(意思是“因缘和合”)的(偈颂“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但是,仔细思考就会发现,上述论证是一个什么也没有说明的“套套逻辑”(tautology),即“同义反复的重言式命题或表述”。龙树此处在其思维模式中所提出的“一切皆空”,是一个不会错误的“恒真句”,因而在哲学论证上会显得没有意义。
(一)龙树的论证其实是一种“套套逻辑”
根据龙树的说法,“空”的意思是“因缘和合”。例如,同样在《中论颂·观四谛品》提到的偈颂:“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空)。”(CBETA, T30, no.1564, 33b11-12)因此,上述“归纳论证”式的偈颂可以写成:
因为〔经验上的〕每一法(没有不是)→因缘和合(空)(“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
所以〔经验上的〕每一法(没有不是)→空(因缘和合)(“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
可见,这个论证就像说“没有白雪不是白的”或“没有四足动物不是四只脚”一样,是一个“套套逻辑”。它只是将重义的概念反复再说一次而已,属于“恒真句”(即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错的),因而从某种角度而言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明。
这里,龙树的论证似乎要说明的是一个属于“常识哲学”的知识,即(经验范围内观察到的)一切事物,没有事物不是从“因缘和合”(“空”)产生的,所以(经验范围内观察到的)一切事物,没有事物不是“空”(“因缘和合”)的。这属于“恒真句”,大概不会有人反驳。龙树的辩论对手虽然也可能认同这点,但他们应该还会认为:虽然每一事物(法)在我们经验观察到的常识知识上都是“因缘和合”(“空”)的,但是它们在最终极意义上却不是由“因缘和合”(“空”)而产生的,而是有一个例如大自在天、毘纽天、梵天甚至上帝(基督教观点)、真主安拉(伊斯兰教观点)的超经验的、永恒不变之神的存在,创造了这些我们经验观察上“因缘和合”(“空”)的事物。这才是真正导致龙树的辩论对手不能认同龙树“一切皆空”(一切皆“因缘和合”)的观点的原因,因为他们显然认为大自在天、毘纽天、梵天甚或上帝、真主安拉并不是“因缘和合”(“空”)的!
(二)“一切皆空”是一个“全称命题”吗?
根据英国培根(Francis Bacon)的说法,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三段论式逻辑,是一种“演绎论证”(deduction或deductive argument),而“演绎论证”其实并无法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归纳论证”才可以,因此培根认为这是一种“新工具”,也是近代科学采取的研究方法之一。这里的问题是,龙树上面的“归纳论证”可以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上述偈颂实际是一个经验常识:(经验内的)一切事物,没有事物不是从“因缘和合”(“空”)而产生的;所以〔经验内的〕一切事物,没有事物不是“空”(“因缘和合”)的。这是同义反复的重言式命题表述,就是龙树的“一切皆空”(一切皆“因缘和合”)。
这暂且置之不论,我们先借用龙树经常使用的“两难论证”式,来尝试质疑上述“一切皆空”的命题。我们可以反问龙树:“请问你这里所说的‘一切皆空’,是一个‘全称命题’吗?”无论龙树回答是或不是,都要面对两难,因为这很容易造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1.龙树可能犯了“全称性”指称的错误

若我宗有者,我则是有过;我宗无物故,如是不得过。(CBETA, T32, no.1631, 14a29-b1)[注]此句的梵文偈颂是:yadi kācana pratijā syānme tata me |nāsti ca mama pratijā tasmānnaivāsti me || 29 || 英文译句是:“If I had any proposition(pratijā), then this would be mine, I have, however, no proposition(nāsti ca mama pratijā). Therefore, there is no defet that is mine(tasmān naivāsti me ” 以上梵文原文与英译参见:Kamaleswar Bhattacharya(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Sanskrit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The Dialectical Method of Nāgārjuna(Vigraha-vyāvartanī), Text critically edited by E. H. Johnston and Arnold Kunst,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78, p.61, 113.
就龙树而言,“一切皆空”显然不是一个“命题”(“宗”)。问题在于,“一切皆空”(“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这句话,仍然是一个“全称性”的表述或说明(不管它是否是个“命题”或“宗”)。这里龙树的说法其实犯了“全称性”指称错误,因为其立论的基础是站在“经验观察范围内”的“一切”,即(经验内的)每一事物,没有事物不是从“因缘和合”(“空”)而产生的。因此,这里的“全称”词“一切”,前面要加入“在经验观察范围内的”才是合理的。例如,“一切乌鸦都是黑色的”(不管它是否是个“命题”或“宗”),这样的表述或话语在世俗约定俗成的范围内并没有问题。如果龙树“一切皆空”的意思也是在世俗约定俗成的定义上而言,则会产生如下所说第二点问题,因为“空”并不如“黑色”这个语词般,是世俗约定俗成的日常语词。
严格而言,当我们说“一切乌鸦都是黑色的”时,科学家会指正说“除了白子和少数的特例”之外的“一切乌鸦都是黑色的”。所以要特别注意,这里所谓的“一切”含有“或然率”(probability)的错谬问题。换言之,即使龙树认为“一切皆空”不是一个“命题”或“宗”,但他仍然犯了“全称性”指称的问题。这句“一切皆空”,其中的全称词“一切”要加上“(在经验观察范围内的)一切”才是比较妥当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我们的经验观察范围,实际上是无法观察到所有的“一切”经验的;另一方面,要是我们观察到有些经验不是“因缘和合”的(即便我们现在观察不到),那“一切皆空”就有问题了。所以,这里的“一切皆空”(事物没有不是“一切皆空”“因缘和合”的),显然在论证上多少会有让人产生疑惑。而且,这种经验观察进路的哲学体系,也是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者所不能认同的。他们认为有些知识是经验达不到或不从经验而来的,正如笛卡儿(René Descartes)所说的,上帝赐与我们人类心灵内在的理性之光或自然之光即是。
2.龙树的“空”是任何世俗上约定俗成的语词概念吗?
假设龙树的“一切皆空”不是一个“全称命题”,甚至根本不是任何的“命题”或主张(“宗”),而是世俗约定俗成的表述或说明即“假名”(prajapti),只是为了让我们理解万物实际的情形而有的“方便施设”。龙树的意思应该是:在(在经验观察范围内的)“一切”的众多万法、事物,没有不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这是龙树的“空”的意义,而且是世俗约定俗成的一种表述,即“假名”施设的。龙树在此要表述的是,“空”就是“缘起”,就是“因缘和合”,就是远离有、无二边的“中道”之义。这是龙树在《中论颂观·四谛品》提到的“三是偈”或“三谛偈”[注]此汉译偈颂出现三个“是”字,故被称为“三是偈”;又因天台智者大师智顗依据此偈颂而有“三谛”之说,故又被称为“三谛偈”。傅伟勋认为智顗的“三谛”思想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吴汝钧(NG-Yu-Kwan)则认为智顗将《中论》此“三是偈”解读成“三谛”之说,在对比《中论》梵文原文后,可知不符合梵文偈颂的仅有“二谛”的涵义:“由这首偈颂发展出三观、三谛思想,是基于《中论》的汉译者鸠摩罗什(Kumārajīva)的错误翻译而来……智顗不懂梵文,自然不读原偈,只读鸠摩罗什的汉译……智顗的误读而发展出三谛、三观,自有它两者的价值在,更可以说是智顗对中观学的二谛说的创造性发展、开拓。但从哲学史、思想史方面看,龙树只持二谛说……不是持三谛说。”(傅伟勋:《从中观的二谛中道到后中观的台贤二宗思想对立——兼论中国天台的特质与思维限制》,《中华佛学学报》第10期,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1997年,第385页;NG-Yu-Kwan, T’ien-t’ai Buddhism and Early Mādhyamika, Honolulu: Ten-dai Institute of Hawaii/Buddhist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p.30-31;吴汝钧:《佛教的当代判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1年,第474页。):
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CBETA, T30, no.1564, 33b11-12)
这里仍会产生一个问题:“空”作为一个表述语词、词汇、概念、名言或语词的“假名”,其实并不是任何世俗约定俗成的日常词汇,而是一个佛教的专门术语。不信仰佛教的印度外道在这里必然质疑,“空”是佛教或龙树自己发明的表述语词、词汇、名言或概念(“假名”),根本就不是任何世俗约定俗成的表述语词、词汇、名言或概念。所以龙树的辩论对手或者一般人,其实应该不太能知道龙树说的“空”到底是在表达什么。如果龙树回应说理解了世俗名言的缘起性与其约定俗成的意义后,自然能了解什么是“空”,那么,龙树的辩论对手在理解了龙树的表述语词后,或许还是不知道龙树这个“空”是哪个地方或国家、地区所使用的世俗约定俗成的词汇或名言。“空”一词毕竟是佛教或龙树在自己的脉络体系下成立的专门术语、表述词汇,而不是任何世俗约定而成的名言、语词。
所以问题并不是论敌、外道不了解“空”的意义,或着龙树说的缘起、“因缘和合”之义,而是龙树自己体系的专门术语、表述词汇到底真正说了什么?他究竟想表述或者否定什么呢?[注]关于龙树的“空”究竟指什么,可参见杨惠南的《龙树的“空”》《“空”否定了什么?》《龙树〈回诤论〉中的“空”之研究》。(杨惠南:《龙树与中观哲学》,前揭书,第67—89、161—182、183—232页)。龙树有真正达到想要表达的目的吗?这应该是我们要再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四、结 语
综合上述的论述可知,对鸠摩罗什汉译《中论颂》里龙树的一些论证,需要更深入的理解与反思,才能对汉译青目《中论释》里关于反“神(我)”(意指灵魂或自我)存在的论证有进一步认识。这是印度佛学在哲学与理性上精彩的思辩与论证,也是龙树的思辩智慧的展现。但是,龙树的“两难论证”以及关于“一切皆空”的论证,在理性思辩上可能存在某些值得商榷的问题[注]林镇国认为:“龙树显然区分‘积极性论证’(positive argument/ evidentialist argument)和‘否定性论证’(negative argument/ non-evidentialist argument)二种,批评前者而采取后者。”(林镇国:《空性与方法:跨文化佛教哲学十四论》,台北:政大出版社,2012年,第4页。),而且龙树的论敌或外道完全有理由用同样的方式,不去回应龙树的两难质疑,甚至四句论破的质疑。

笔者的用意,绝不是挑剔或反驳龙树或青目中观哲学的理性思辩与论证,而是认为:一方面,在理性对话上,龙树的“两难论证”方式,由于破斥论敌、外道太过,可能会导致不同哲学教派之间理性对话与互相理解的不可能和终结,所以笔者倾向于支持与认同使用陈那的宗、因、喻三支比量论证方式,作为理性沟通的桥梁与工具;另一方面,宗教的论述常常有“理性”与“信仰”之间的辩证张力,多少会表现出“信仰”高于“理性”的倾向,例如基督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信仰的理性主义”[注]参考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64页。的神学观点,因而,或许可以说龙树、青目、鸠摩罗什等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应该也有自身某种“信仰”高于“理性”的倾向。
此外,若将时空场景回到6世纪的中国,中国佛教天台宗开创者智顗(538-597)自称传承龙树学,结合北方的止观之学与南方的佛教义学,创造出号称“教观双美”“止观双运”,判摄东流一代圣教,建立“五时八教”教判论,并将之组织成“三谛圆融”,而提出终穷究竟极说“一念三千” 的理论。同样在公元6世纪,中国天台佛学与印度龙树之后的中观学,不论是“中观应成派”还是“中观自续派”(Svātantrik,自起派、自立论证派),在哲学论证与理性思辩上却是相去甚远。从此,中国佛学因中国人重圆融的思想特征[注]中村元曾说:“中国人常有以圆来表现完整的东西之倾向。例如说,圣人之心是圆的。汉译佛教经典时,原语本是‘完整底’‘无缺底’这种抽象意味,中国人皆译之为‘圆满’。‘一切具备’(Sampad)也译为‘圆满’。一切诸法,即一切事物的真实本性,玄奘三藏及属于其系统的学者译为‘圆的实性’,圆字全属附加的。天台或华严的哲学,以事物之完全相即为‘圆融’,及至中国判教成立时,遂称佛教中最完全的教说为‘圆教’。以圆形为完整性之表征,乃中国之独自的思维形式。印度人不以圆形(Vrtta)为特别之意义。”([日]中村元:《中国人之思维方法》,徐复观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第67页。),使谈玄说妙的形上学、本体论大为流行,因而削弱了印度佛学中精彩的哲学思辩与理性论证。这大谈本体与现象(理、事)的圆融与无碍,既是中国佛学的特色,又是其与中国哲学的相似之处。至此,印度佛学中极具精彩思辩与论证的知识论(量论)、逻辑学(因明)与语言哲学,在中国逐渐地被大谈圆融与无碍的形上学所取代。如印顺(1906-2005)所言,大量地谈论形而上之“涅盘智”,而却不再花功夫讨论缘起之“法住智”[注]印顺:“这里,觉得佛教中,每有一种错误的倾向,就是不求法住智,而但求涅盘智。”印顺在此虽然没有明言他是指“中国佛学”,但据笔者推测应该差不多。(印顺:《成佛之道》,台北:正闻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的“中国佛学”[注]对此,林镇国说:“当宗教土壤不同时,对中国佛教徒来说,因宗教而引生的哲学论辩便不再是迫切的问题。在印度,因明量论最盛之时,也就是宗教派别之间争论最厉害的时代。在中国,面对宗派的对立,判教则成为解决哲学冲突的方法。判教与因明成为区分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的根本标记。”(林镇国:《空性与方法:跨文化佛教哲学十四论》,前揭书,第14—15页。),从“印度佛学”过渡到“中国佛学”,这种思想转变的缘由值得吾人进一步更深入地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