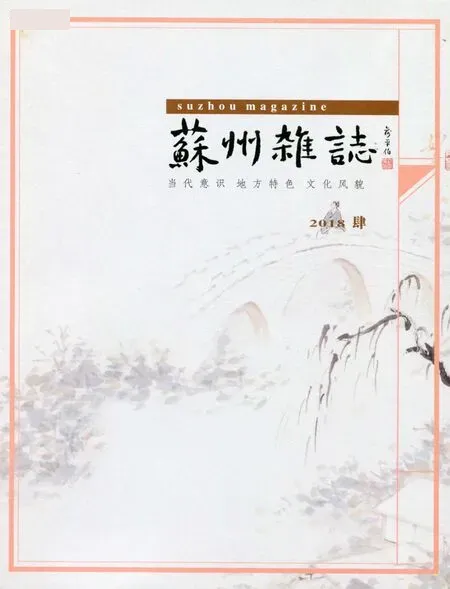我与运河
2018-09-29

上塘河头
亦 然
新邻居入住前,要我拟个园名,好刻在门楣上。我想了想,他家在运河边,正好面对枫桥,想像夜深人静的时候,是能够听到船家说话和拍岸水声的,就建议四个字:枕涛山房。枕涛是应景,山房是虚晃一枪。后来,和邻居的邻居家客人一起吃早茶,客人表示异议,他嚷着说,山在哪里?我一时语塞。好在说的是“山房”,没说“房山”。
再写下去就疑似开发商广告:上塘河头枫桥边,还有寒山古寺、唐塔、铁铃关、大运河,古寺古桥古塔古关古河,如果后面再横一座山,那就更妙了。
上塘河头,我喜欢这里。
大运河是姑苏城的母亲河。大运河有三条脐带通向姑苏城,从北向南依次是山塘河、上塘河、胥江。胥江这条脐带还连着太湖。太湖是苏州的生母,大运河是苏州的养母。
站在上塘河头遥想当年,这三条河大约是有分工的。游人画舫无疑喜欢经虎丘山下从山塘河一路逶迤入城,沿河风光宜人啊。官人官船更宜由胥江隆重入城,接官厅及其配套设施都在那一带,顺理成章。而进进出出的货船从上塘河入城比较便捷,据我猜想,城内平江河两侧的众多粮仓与上塘河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
然而,世事无常,上塘河的航道重任显然早已卸去。往前推二三十年这地方颇为荒冷,当年的航拍照片显示,这里只有弃用的两排房舍,两片水塘,后面傍河有个规模不大的化工厂。
这里有个老名字叫娘娘浜,因为过去有个娘娘庙。娘娘庙是为上塘河的风波而建的,航船由运河折向东,经上塘河过上津桥、下津桥入护城河进城,遇上风高水急就有危险,不少船家就倾覆在这里,以至需要有个娘娘庙于此蹲点禳灾。现在这个地名已被人们彻底忘却了。
上塘河头的对岸却多了个新地名江枫洲,是一片与寒山寺隔河相望的新景区,即便不是假日,那里也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最热闹当数每年除夕之夜,世界各地的人和一百单八记钟声一齐赶往寒山寺,辞旧迎新的仪式总是有趣的。
是啊,化工厂撤了,造纸厂搬了,河水清了,上塘河美了,大运河新篇章里,上塘河头是一张弹眼落睛的插图。
曾经策划过苏州最牛的“走三桥”活动,上塘河头三座桥:枫桥、江村桥、江枫桥,还有比这更牛的么?
上塘河头,涛声依旧,却已是风华翻新了。
那个地方
戴 来
前些年,外地来朋友,我一般会把他们领到平江路去,至于他们想不想看,我不管,反正总归要去到一个地方尽尽地主之谊。
去平江路是有道理的,我对他们说,那里是历史文化街区,那里有河道,有小桥,有寺观,有祠堂,有园林,那里街巷幽深,粉墙黛瓦,人家尽枕河,是最有苏州味道的地方,简而言之,那里有名有实。我说得像是导游词。和外地朋友一起逛平江路,我一不小心就找到了导游的感觉。
通常我会带大家从平江路的南端进去,先让他们看看街口那块南宋《平江图》的石碑。就像上学时老师布置我们隔夜做预习一样,有个直观的印象。对照《平江图》,一目了然,如今的平江河道、街巷和桥梁位置基本没变,依然延续着唐宋时期的一河一街、水陆并行的格局。平江路在当年是主干道,如果把姑苏城看做一个人的体循环,平江路相当于她的主动脉,从南往北,路两侧分布着的众多小巷,不妨就看作是平江路的毛细血管吧;粗粗细细的血管里流淌着太多历史遗存和人文典故。我一路讲过去,直说得口干舌燥,最后找个临河的地方坐下来喝茶。当然,中途我一定会指一下丁香巷。我十四岁之前就生活在巷子尽头的40号里。难道这才是我带朋友去那里的初衷?
丁香巷走到头就是与平江路平行的仓街。仓街一带曾是苏州明清时期的仓储中心和漕运集散地,通过平江路东西走向的大柳枝巷河、胡厢使巷河、大新桥巷河等河道与大运河(东环城河)直接贯通。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大运河苏州古城段的遗产点。
早七八年前,平江路还没有这么闹忙,更多的外地游客还跟着导游旗在山塘街上东张西望。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忙是一种生活常态,大人在河边洗衣服涮拖把,在井旁淘米洗菜,路上有拖着板车送煤球的,自行车铃声脆得像点心店里刚捞出油锅的馓子。大人都在忙生活,但忙而不闹,有烟火气,却还是清静的。闹忙是轧出来的,比如轧神仙,一年就一次,是约好了一起轧闹忙的,那不是生活常态,所以不烦人。
这几年,平江路真是轧,不过外地朋友来苏州我还是愿意把他们带到平江路去,反正总归要去一个地方尽尽地主之谊,顺带便亦或许是处心积虑地指一下丁香巷。
运河之水清兮
小 海
文友聚会,聊到大运河。一个说,我家就在河边住;一个说你住河东,我住河西。我心里想,本人也曾在运河边住过的。听他们这般争着抢着表白,我生生把到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好在我有早年的诗歌为证:
我怀抱沉默的女儿来到阳台上
发现运河的气味已经改变
风将波浪推向更遥远的波浪
说话的牛群和运河堤岸上传出的狗吠
时光在马厩中养马——群星灿烂
(《沉默的女儿》,写于1994年9月)
那时,女儿出生才刚好一个月,我们住三元三村的一处顶楼,邻近大运河和寒山寺。燠热的晚上,把她的小摇篮移到阳台边,吹吹运河上刮来的风。当时,运河边的华盛造纸厂还没搬迁,污水就排放到运河里,以致河边总有股子腥臭味。风向变了,才嗅闻不出。
紧攥这点记忆,好像生怕被别人抢走了大运河似的。大家都亲近这条河。你就明白了,大运河和一座古城,以及与这城里人的关系(我不敢说气质甚至命运之类的大话)有多么密切了。
如今,我的工作单位就在运河索山大桥东堍。午休时间,我喜欢到大运河边新铺设的人行步道上散步一圈。运河上依然有舟楫往来,偶尔还会看到押船人牵着狗立在舱门口,穿越桥洞,随着马达声渐行渐远。
我也和同事一起,专门去看过南面不远处的横塘古驿站。
横塘驿站,地处大运河与胥江交汇处,原是水陆驿站,为古代传递官府文书以及往来官吏中途歇宿之所。驿站目前仅余亭子一间,楼、庑、台等已不可见。亭子是原驿站大门,属于清代建筑。驿亭南面石柱上刻有对联一副:“客到烹茶旅舍权当东道,灯悬待月邮亭云映胥江”,为清同治十三年六月所题。边上有彩云桥,原本东西跨越运河,后因大运河拓宽,1992年迁建胥江,与驿亭相守。
关于横塘的诗歌真的是太多了,当然也和运河苏州段大有关系。横塘,几乎成了烟雨江南的代指。因为横塘为古代交通要冲,南往北来的客人在此折柳话别,正如南宋诗人范成大《横塘》一诗所说的:“南浦春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想想,还有哪些古代诗人吟咏过它?
凌波不过横塘路。
但目送、芳尘去。
锦瑟华年谁与度?
月桥花院,琐窗朱户,
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
彩笔新题断肠句。
试问闲情都几许?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
梅子黄时雨。
(贺铸《青玉案》)
贺铸笔下的横塘路,引发多少唏嘘感叹。他也因此获得“贺梅子”的称谓。可见,苏州,对诗人不薄。
横塘,后来变为一种出身,令人刻骨铭心。明袁宏道《横塘渡》杂言诗中说:“横塘渡,临水步。郎西来,妾东去。——妾家住虹桥,朱门十字路。认取辛夷花,莫过杨梅树。”吴梅村《圆圆曲》中“冲冠一怒为红颜”“一代红妆照汗青”的陈圆圆,即使误入风尘,也要“验明正身”,一般地作这番标榜:“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其实,让人们念兹在兹的横塘,更可能是“少年一段风流事,只有佳人独自知”。
在明代李流芳《横塘》一文中,横塘的地理概念有了落实:“去胥门九里,有村曰横塘,山夷水旷,溪桥映带村落间,颇不乏致。予每过此,觉城市渐远,湖山可亲,意思豁然,风日亦为清朗。”(见李流芳《江南卧游册题词》)

今天,伫立于周边高楼林立的横塘驿站边,你会恍惚,不知你和古代诗人,到底是谁生错了时代。
不错,古代的苏州大运河,我们只能通过方志和流传下来的诗词来感知、追忆。古往今来,运河在姑苏城区也几经改道,它不仅承载了王朝一统的漕运历史,也承载着诗词歌赋等流动的传奇;它不仅是披在古老中华帝国身上的文化绶带,也是挂在姑苏人颈项上熠熠生辉的鲜活珠琏。
运河之水清兮。对运河边长大的孩子们来说,无论走多远,无论看过多少大江大海,当回到故乡时,也顺带看一眼这条河吧。
古道,黄昏
汤海山
古代的运河边,黄昏是繁忙的,许多船准备泊岸,行者驻足四顾,寻店投宿。纤夫想歇脚,乘客想上岸大快朵颐。运河的纤夫,不像长江边赤身裸体的黝黑汉子,可能是美丽的宫女,也可能是高贵的官员,船上坐的可能是皇帝,也可能是丞相、尚书。皇帝巡游江南,一般不带皇后贵妃,最初开河的皇帝,就是游幸娱乐的心思。猎艳,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沿河大大小小的行宫里,各地官员、商人物色的美女,歌舞与声色俱绝。
那时候,要看漂亮的女人,就去运河边,她们像云一样飘在河上,像花一样种在岸边。运河的黄昏,夕阳西下,美人玉立,暗香疏影,神秘,迷幻,美丽,多少心在晚风中动。
官船,民船,商船,载人和运物的各种船,从苏州往南(杭州方向)大约半天多辰光,到吴江城南的九里石塘,就看见了西边的太湖,心情顿时舒缓。纤夫们更是欢喜,他们走上长长的青石纤道,步履轻快流畅。
这是隋修运河(苏杭江南河)段最好的塘路,又称松陵路,往南是八坼、胜墩、平望。荆歌出过一句上联:平望胜墩高八坼(尺),至今无人对下联。从松陵到平望的一段运河,有极其复杂的历史,曾经是运河史上最糟糕的河段。勾沉这段旧史,已经困难,与松江的变迁有关,大概来说,松陵、平望河段,在更古老的时候,隋汉秦或更早时期,是古松江水域。最初的土河堤,便叫松江堤、吴江岸。
那时,太湖没有东岸,湖水漶漫,形成大约廿里宽阔的水道,直接浩浩荡荡流向东海。这条吴地最阔最长的水流,就叫吴江,也唤松江,现在称吴淞江。之后泥沙淤积,江水渐窄渐浅,到隋唐宋初,江南的运河,已经舟船相衔,这一段却无堤无岸,仍与太湖、松江混在一起。水苍茫,一片白。“一片白”,是这片水的名字。
南来北往的人、马、车,到了松江两岸,便被这片水阻挡。南来的不说,北往,从苏州乃至苏州之北、北之北,到越地、到杭州,必须渡水。当年,吴越之间艰难、漫长拉锯战的原因,是这片水。吴越决战,就在这片水上定局。
《吴地记》说,“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泽”。笠泽不像江名,我怀疑,似是太湖之东、运河之西、松江之头这一片水的雅称。古松江是吴越的界河,吴越王钱镠割吴地、越地各半,置吴江县,南北两岸才归于一统。
后来,水面越来越窄,古松江朝北萎缩,平望离太湖、松江渐远。然后,松江到了八坼之北,就这样一点点移过去。沼泽、河荡、浅滩逐渐扩大,地形日趋复杂。或已有早期的围水成圩。但唐宋人到此,仍需摆渡。
如果遇到风雨,要在岸边的驿站、客栈、酒家等待,也许一两天,也许一旬半月。等渡船从渺茫的彼岸摇过来,或摇到彼岸去。做官、经商、旅游、访友、流放……商人怕等,流放的官员、文人,却巴不得有风雨,耽搁了,好看好吃。此处水景甚美,风物尤佳。观吴水、赏吴音、看吴娘,吴娘多卖鱼,最好的鱼是鲈鱼。吃各种水生美味。鱼虾水鲜之外,还有莼菜、茭白、菱角、茨菰。
许多人等渡船的时候,写泊松江诗。大多是黄昏的景致和心情。他们到江岸,大抵正是黄昏时分。江边的黄昏,也是最有风情的时候。即使不是黄昏,为了湖色、鲈鱼、吴娘,也要歇下来。古代的人,不急着赶路,唐诗宋词一半是在路上写出来的。写唐诗宋词三百的一半人,在吴江写了诗词。吃喝玩乐,吟诗作画,都从黄昏开始。现在我遥想这片已经不存在的水域时,也多是古代黄昏的想象。

宋朝庆历年间,长江边造岳阳楼的时候,吴江的运河边,也出现两大著名的工程,一个是前朝“堤松江为路”,也就是在松江里筑了一道土堤,作为运河的岸路,但并不很实用,水患即溃,于是增石驳砌护坡。此时古松江经过无数次折腾,左冲右突,在浅滩、沼泽中,开辟了另一条落北流向的主流,剩下的支流便于收拾。另一个工程,是垂虹桥建成,站在塘路上,可以看见垂虹桥,看见穿过桥下的松江,水势依然鲸波鳌浪。
虽然是泥塘路,总算正式将运河与太湖隔开,实现南北通岸。不过土质疏松,古松江的残流,得着太湖洪水的支持,冲垮它易如反掌。元朝泰定二年,垂虹桥易木为石,白石重砌,过了廿一年,至正六年,又一次浩大的工程,重修塘路,用巨大青石筑岸铺路,“九里石塘”始出。明清吴江的形胜和繁华盛名,与此一石塘、一石桥大有关系。我困惑的是,它们居然是黑暗蒙元黄昏时期的产物,仅仅廿年后,蒙古人的统治就谢幕了。
有年夏夜,我坐在运河岸边,石塘的一处桥头,等苏州开往杭州的夜航船。船一直没有来。午夜时,我从桥上跳落河去,一入水,顿觉深不可测,寒气入骨,且有漩涡缠绕,差点遇险。惊恐、迷茫之际,我感到奇怪,运河岸边不应该这么深。
旧载,松陵南运河边,有甘泉,陆羽品为天下第四泉,泉边修一桥,名甘泉桥或第四桥,宋人有咏泉诗,“松江第四桥,风雨不可过。下有百尺蛟,蜿蜒枕桥卧。窟宅居要津,口腹长饥饿。”推测甘泉,应在我的落水之处或附近。也许我遇上的是古龙潭的暗流。
姜白石携小红过垂虹桥,“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尽过完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松陵路”就是吴江石塘古道,“十四桥”的另一个版本,是“第四桥”,即甘泉桥。过垂虹桥之后,在船上,吹箫低唱至曲尽,倒是与从垂虹桥到甘泉桥的时间近似。
倪云林也有一首甘泉诗:“松陵第四桥前水,风急犹须贮一瓢。热火烹茶歌白纻,怒涛翻雪少停桡。”
甘泉,烹茶,于石塘的烟水往事里冒出来。我问朋友圈,可有人和我合作,在古纤道上,甘泉遗址,开家第四泉茶馆?一个朋友笑了,这样吆喝,不怕泄露商业秘密嘛?我说,接待文朋诗友的茶馆,古风残照,瘦马枯藤,一般人开不出来。
梦魂长在枫桥西
郁岚
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最喜欢家乡的哪一处,我只能自说自话了,忆江南,最忆是枫桥。据说张继“枫桥夜泊”里面的“江枫渔火对愁眠”之江枫,指的是两座桥:寒山寺照壁前的江村桥和偏北的枫桥,江村桥我没走过,或许走过,也已经忘了,我心中只有枫桥。
我生在苏州长在苏州,从未长时间离开过家乡苏州,但对身处其中的环境,内心里却总有过客般的疏离感,身在苏州,却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隐隐约约的思乡情绪不时来袭,而十里地之外的枫桥,常常是我想念的对象。其实我脑海中的枫桥并不清晰,只是一团情绪,朦朦胧胧。音乐最易引发乡愁也最抚慰乡愁,前一段时间聆听了苏州市民族管弦乐团在会议中心剧场首演的《烟雨枫桥》,音乐的旋律中枫桥忽远忽近,时而清晰成杨明义的画,时而又在风声雨声中隐去。我能想到的枫桥仅仅是某一年的某一天,爸爸背驼着我穿过铁铃关深深的门洞走上枫桥的石阶,妈妈走在旁边,时不时伸手拉一下我渐渐往上缩起的裤腿……当时我那么小,懵懵懂懂,谁曾想,那一刻却成了我的乡愁。
长大以后,我知道了托着这份乡愁的盘子十分厚重。
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贯通苏州环城河,枫桥横跨的上塘河是大运河经过苏州的咽喉,枫桥原名封桥,是扼锁运河之意,它曾经如此重要,既是城池防卫的要塞,又是迎来送往的惜别之地,因为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诗而名扬天外。之于我,枫桥是沟通白马涧的桥梁。因为我和白马涧是有渊源的。年轻的苏州人和新苏州人也许都不知道,那时候从古城去白马涧只有从枫桥这一条路走,走过枫桥,走过田间小道,翻过谢宴岭才能抵达。白马涧是一个四面环山的村落,妈妈怀着我的时候正在白马涧下放劳动,我是呼吸着白马涧的山林清气成形的,所以父母给我起名岚。字典上说,岚是山林里的雾气,但有毒。自身带点毒好啊,百毒难侵。
八十年代另辟的大运河新河道将枫桥与白马涧隔开了,在枫桥西边形成了一个美轮美奂的洲,这是从摄影家航拍的镜头里看到的。我再也没有去过。
余光中的乡愁是一枚邮票,一个暗伤,一份遗憾;我的乡愁是一个不想惊动的梦,一道颤颤的微光,是一份成全。
借用晏几道的词义,梦魂长在枫桥西。
我还运河一首诗
胡兵想

悠悠千载的古运河,四十多年前成就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远方。
如今人到中年,每当孤独时分,我都会选择回忆来打发寂寞时光,在岁月的长河里,总有一些往事,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全国恢复高考的前一年,一九七七年的春节过后,我们辍学回乡的几个花季少年,眼看着一个个家庭成份比我们好的同学,身挎着书包行走在去镇区读高中的路上,我们怅然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悲愤中让我想起了中学课本里诗人林升的一句诗:直把杭州当汴州,我把这一刻的想法与伙伴们沟通了一下,没想到立马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
翌日,东方的启明星还在沉睡,我们男女五个同学就聚集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准备出发了。等我们徒步从偏远的乡村来到吴江运河码头,我们才知晓苏杭班只有在夜间载客营运,傍晚的时候才经过这里。我们一行只好在运河边的饭店,每人来了一份盖浇饭。然后,大家坐在运河码头的河埠上,各自怀想着自己的心事,目送着大运河里的船只南来北往……
傍晚时分,一声清越的汽笛,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运河的尽头,此刻,苏杭大客轮乘着沉沉暮色,仿佛就像一艘远载着游人去达彼岸的诺亚方舟,徐徐前来。
此时,在吴江运河码头上船的游人并不是很多,后来我们在坐船时有一个插曲,休息大厅里一个老人会教魔术,收二角钱教别人一个魔术。他看到我们几个学生模样的少年到来,立马找上我们,只要我们给他买两盒方便面,他会免费教我们每人几个魔术,我们商量了片刻,欣然答应了老人的要求,我们各自努力地学着魔术,一张张神态生动。表情鲜活的笑脸,仿佛把辍学的忧伤已经忘在了身后。我为老人在小卖部买回了两盒方便面,独自一人来到了客轮的船头,晚风稍带凉意,回想自己离家这短短的十几个小时的经历,我开始了人生第一次思考,我思考这次远行的初衷,不能因为学几个魔术而沾沾自喜,让这点喜悦麻痹了我的初心。我想社会应该是一个大熔炉,不能是一个大染缸。我不能学杂耍,更不能像船仓里那个老者,虚度这一生好年华。

苏杭班是在第二天的日出三竿,才到达西湖边的运河码头。我们步行半小时后见到了课本里的西湖: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突然,断桥边随风传来了一曲《二泉映月》,这首充满对命运抗争的二胡曲,在一个盲人的手指间遥遥传来,瞬间,我竟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人间的悲痛原来可以用这种形式呻吟与倾诉,藏在心中的风云,可以用音乐来寄托,用乐章来诠释命运中的苦乐年华。
归途,游罢孤山,我在灵隐寺买回了一把二胡。后来,就是这把二胡让我考上了菀坪乡文化中心宣传队,再后来又成长为宣传队的负责人和文艺工厂的厂长。
那次远行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见证了祖国的山河之美。一周后,我们同样乘夜航班归来,船到姑苏城外的澹台湖边,一声长长的汽笛,把我从梦中唤醒。我披衣临窗,眼前的宝带桥在缥缈的晨雾中如长虹般卧在运河与澹台湖的交汇处,碧波荡漾的澹台湖背靠着美丽的七子山,远山近水,宜人景色美不胜收。我欣然命笔,临窗深情地写下一首运河小诗,当年虽然没有发表,以此表达内心对祖国山河的爱恋,但是,那些美好的感觉总是在我心头萦绕。借这次苏州作协和《苏州杂志》联合举办行走运河的机会,我想把这首在我內心沉睡了四十多年的小诗,还给运河,其中我这样写道:/无论你匍匐在苏北平原/还是行吟在江南水乡/在你奔忙的波影里/我看到的总是蓝天与白云/终于在一个不知名有着晨雾的早上/多情的澹台人/把五十三孔的长笛/挪到了你的唇上。

我印象中的运河
殷秀红
说起运河,2013年一次偶尔的机会,吴江文联邀请老舍的儿子舒乙老师来吴江作运河讲座。我第一次听到有关运河主题的讲座,一切都是那么新奇,让我联想起小时候喜欢和小伙伴往太浦河桥上赶,看大轮船。一条条看似没有尽头的船只,逶迤慢行,承载着多少希望,一点点地驶向彼岸。那是我对运河最初的朦胧感觉。
吴江,因舒乙老师的到来,打开了运河的窗口。他幽默风趣的叙述,一路的运河趣事,让我回去迫不及待地购买了他的著作《疼爱与思考》,过了一把瘾。
次年,机会又来了。在四月天,春暖花开,面朝大海的季节。民文组织我们一队人赴杭州采风。第一站,就是参观京杭运河文化主题博物馆,领略了“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迷人风情。知晓了,自隋唐大运河的疏凿始,“东南名郡”遍地开花,繁荣昌盛,留下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的瑰宝,如杭州张小泉剪刀、苏州桃花坞年画、无锡泥人等等。
因运河,历史的长河,也涌现出了不少风云人物,从隋炀帝杨广至清代陈潢、勒辅等等,他们都是运河的先驱者、开采者、有功之臣。有人把大运河誉为“大地史诗”那是再贴切不过了,因大运河和长城一样,是在中华大地上书写的一个大大的“人”字,中华几千年的灿烂文化的大串联,就如同珍珠般熠熠生辉,与日月同辉。
如果说,拱宸桥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那么我们不能忽略了身边的运河。我的家乡苏州吴江,在2014年春天,接到了运河的喜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遗名录,其中苏州运河遗产包括四条运河古道和七个点段。七个点段分别为:山塘历史文化街区、虎丘云岩寺塔、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全晋会馆、盘门、宝带桥、吴江运河古纤道。原来家乡还有这么多运河遗存,为之骄傲!
家乡有运河,自有运河专家在,他们是我们运河的守护神。2014年杭州采风,我认识了一位运河专家张卫荣,他从事航道管理十多年,有一肚皮的运河文化掌故,信手拈来,如鸭子坝的来历,河伯和水神,九里石塘的发现抢救等等。择日,我准备登门拜访听他讲故事,好听的故事,不容错过呵。
张老师实地先带我去了松陵三里桥,那里是运河重要地段。坐定他又和我说了一则运河的传说,那是他听老父说的,关于周家溪的故事。
据传有一个叫周天官的官员,有一天他向皇上辞行告老回乡。皇上说,有一天朕想你了,就派人打面红旗来请你。如果朕想杀你了,就打一面白旗来。周天官急忙回家,请了一位风水先生,帮他找一块风水宝地建宅。风水先生寻遍江南,选定了周家溪这地方。周天官看着甚好,准备安享晚年。
哪想风水先生过于卖命,眼睛都找瞎了。周天官为表感恩,挽留风水先生在他家住下,每天好酒好菜相待。
一天,周家一丫鬟杀鸡待风水先生,不曾想半死的鸡在地上扑腾几下,滚到了粪池里。丫鬟又惊又怕,没法子,还是将鸡从粪池里捞上来,洗干净,煮了给风水先生吃。次日,她问风水先生,鸡汤好喝吗?风水先生连声赞好。丫鬟人实在,将昨天的事说与风水先生听。那还了得!风水先生恼羞成怒,想自己竭尽全力为你家主子找风水宝地,眼睛都弄瞎了。你们周家倒好,这样待我,实在是太气人啦!
一怒之下,他跑出了周家溪,奔到桃源南面的大运河太师桥上,大声喊道:“乌镇北栅头,有天无日头。”人们听到桥头有一个瞎子在大声喊,都好奇围拢过来问他。风水先生说出了原委,并说乌镇这地方再也出不了大官了,因为好风水都流到周家溪了。
人们就问他了,怎样破风水?他说办法有的,说这条河像一条龙,这里是龙头,你们准备十栲栳缝衣针,在某月某日某时辰将它从太师桥上倒下去。再派人到东边白龙潭的地方观察,如看到潭里有血沫泛起,那就说明风水破了。人们照此办法,果然奏效。
话说皇上,有一天真的心血来潮想他的爱臣周天官了,准备请他到京城叙旧。根据两人的约定,传旨扛一面红旗请他过去。钦差到达周家溪口,传话周天官接旨。他却派管家先到门口一探究竟,旗子是红还是白?
管家慌慌张张地跌进来,说看到的旗子是白色。周天官大惊失色,想自己大限已到,皇帝要你死,你不得不死。他吩咐手下人赶紧带着金银细软逃命去吧,而他和老婆双双自缢而死。外面的钦差奇怪,在外等了老半天,不见周天官出门接旨,就闯进门一看,发现周天官夫妇已自杀,底下人也全逃命去了。他不得不快马加鞭回京城向皇上禀告,皇上闻听这样的奇事,心有愧疚,派人给周天官修了坟墓。
其实,皇上是承诺了约定,确实也派人送了红旗,那么怎么看到的是白旗呢?原来,古代交通不便,经运河路上的风吹雨打、日晒,到达周天官家已是由红泛白,变白旗了。遇到管家脑子又简单,一急,报了白旗,真正叫不分青红皂白,出了这么大的乱子,酿成了千古遗恨,追悔莫及!
说到这里,张卫荣老师坦言,解放以来,交通部门非常重视对运河的整治和管理。以前从平望市河到莺脰湖沿嘉兴塘至王江泾。新运河改道后从草荡、澜溪塘到乌镇、练市、塘栖至杭州三堡船闸。后来又对苏南运河,即瓜泾口至鸭子坝四级航道整治,成为第一条国家级文明样板航道。如今,运河三级航道也已整治结束,可承载1000吨级单船通过。再也不受“风涛冲击,日夜无休”的肆虐摧残。不久,我们又能看到元代诗人萨都拉“桥上青山桥下水,世人几曾见风波”,清代诗人查慎行“两岸菰蒲闻笑语,人家只隔轻烟”他们所描述的运河好风景啦!
苏杭班
陶文瑜
傍晚5点左右,苏杭班从苏州出发,夏天白昼更长一点,天色擦黑光景,苏杭班经过宝带桥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在宝带桥上走动,从前以为宝带桥就是运河上的一件摆设,苏杭班上的乘客,从船舱的窗户中向外看,古代泊在水上。
轮船码头在人民桥堍,苏杭班是苏州至杭州的轮渡,轮船从苏州出发,差不多的时间,另一艘轮船也从杭州向苏州驶来。好像是一天早晚两班,但我一直记着傍晚的班次,也没有在早上乘坐过。
应该就是白娘子的故事,那时候的苏州人心目中,觉得杭州是浪漫的城市,西湖是和爱情有关的风景。正好距离苏州不远,时间和经济上都紧凑,所以新人都去杭州。大部分是办好喜酒,利用婚假旅行,也有生活节简的人家,也不摆喜酒了,就散一下喜糖,新人去一趟杭州,那时候称之为旅行结婚。
苏州到杭州也通火车,当时要节外生枝似地绕一下上海,轮船价格节省,而且晚上的时间原本是用来睡觉的,所以绝大一批苏州人都是选择苏杭班,苏杭班见证了无数苏州人夫唱妇随的开始。
我是很小年纪就知道苏杭班了,十一二岁,差不多是三年级吧,有一天我们班一位姓蒋的同学兴冲冲来学校向老师递请假条,然后赶来教室,告诉所有的同学,他父母要离婚了,他们要带他去杭州玩呢。大家羡慕地望着他,心想:自己的父母怎么不离婚呢。
我的第一次苏杭班也不是甜蜜的圆满,那时候我本质上十分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功课也落后,谈一个女朋友是班级里的学习委员呢,我们约好了去杭州,下午三四点钟,女朋友来电话了,说是她父母不许她和我一道出门。她父母和我们学校的老师认识,知道我功课不行,以为我很渣男。傍晚5点多,我独自一个去搭乘苏杭班。
甜蜜和快乐或者孤独和失落,随着苏杭班沿着运河缓缓的流水而平静舒缓,甚至美好起来了。仿佛从前的古人。从前的古人去外地探个朋友或者做趟生意,基本上很多天是赶在路上的,他们驾一叶扁舟在水上飘飘荡荡,四周的山山水水出落得跟公园似的好看,而他们仿佛是闲来无事,上公园里来游玩的。现在从苏州到杭州,上了高速公路,差不多花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吧。
从前的日子不怎么心急火燎,从前的古人似乎也是有的是时间。现在好几百里的路,一会儿工夫就很不在话下地到了,却也没见我们生出多少空闲来。我们的世界,是没日没夜地日新月异,然后呢,建设得越快,就越是要建设,发展得越快,就更要发展了。
我是要说苏杭班的,一下子生出这么多闲话,可能是到了想当年的年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