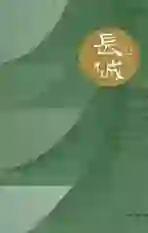儿时的电影
2018-09-24张映勤
张映勤
一
现在,生活的变化实在是日新月异,新元素层出不穷,同时也在淘汰着一些旧事物。大众传媒像闪电一般瞬息万变,有些东西我们还来不及多看它一眼,就随着岁月的河流匆匆而过,只留下了一些残存的记忆。就拿看电影来说,前些年还时兴光碟,花几块钱买张影碟,放到电脑、DVD机上观看。时间不长,手机、电脑、“挨拍的”就全国普及,想看什么影片,上网一搜即得,躺着坐着,怎么舒服怎么看。当然,还有那些舒适豪华的电影院,成了年轻人约会消闲的场所。
恋人们钻电影院,你以为单是为了去看电影?错了,人家享受的是那里幽暗的环境,别致的情调,增加彼此依偎亲密接触的机会。不信,你把灯光调亮了,看看里面还剩几个观众?难怪有的电影院要增设情侣座、包厢座之类的设施,没有这些,我敢说,电影院的上座率一定会大受影响。
在我的印象中,最早看電影并不是在电影院,而是在露天的操场上。那是在“文革”初期,我还没有上学,我们家附近有一所中学,学校隔上十天半个月就在操场免费放一场电影,美其名曰:进行宣传教育。放露天电影的时候是我们孩子们的节日,届时,街坊四邻奔走相告,人们欢天喜地,带上板凳、马扎,早早地坐在操场等着。看着体操台前支好的幕布,我心里纳闷,这人是怎么在上面动的?电影,实在是太神奇了。
电影快到放映时,操场上挤得人山人海,密不透风,来晚了的观众有爬在后边篮球架上的,有骑在墙头上的,黑压压一片,那场面用宋丹丹的话说:“那是相当的壮观!”
当时的四大中外名片——《地道战》《地雷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我看的都是露天电影,而且看了不知多少遍。里面的许多台词,整段整段的,当时我都能背得滚瓜烂熟,人物的一个动作、一个细节,记得清清楚楚。演到列宁的卫士瓦西里和自己的老婆对话,银幕里的人物还没说话,我们就说出了台词:“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后来我寻思,就凭咱这么好的记性,愣没考上“清华”“北大”,或是混个硕士、博士什么的,全是因为小时候“用脑过度”的缘故吧。后悔呀,少年不是不努力,只因儿时爱看戏。
露天电影的主要阵地是在农村,城市里有影剧院,场地也有限,除了一些大型企业机关和学校定期放映,露天电影在城市生活中不是太普遍。人们喜欢看露天电影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省钱,一些单位作为福利为职工免费放映。坐在电影院里自然舒服,但得花钱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贫困时期,一两毛钱人们都得掂量着花。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我们住的楼房震损严重,政府安置我们临时搬到南开大学的操场住了一年多,房子是临时搭建的防震棚。那时的大学还没有恢复高考,学生基本上都是外地的工农兵学员。学校为了丰富学生生活,每到周末晚上都在小操场上放映电影。操场上没有门,几个路口处由教职工把守着。学生老师三三两两地涌向操场,拿出工作证、学生证就可以进场,我们这些外来居民的孩子只能眼巴巴地在路口等着,一面苦苦央求管理人员放我们进去,一面寻找着机会溜进操场。毕竟孩子太多了,查证的人员大多铁面无私。里面已经开演了,我们在外面听着声音,踮着脚,伸着脖子,隐隐约约看见少一半的画面,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直到电影开场好长时间,管理人员撤了,我们这才跑到里面。当然,好的位置没有了,站在黑压压的人群后面,我们踩着小板凳仰着头看完下半场。
后来学校开始对外卖票了,五分钱一张。偶尔我也破费一次,买一张票,大摇大摆地进场。当然得早早地进去抢占有利地形,好不容易花钱消费,就得叫它物有所值。
印象中在南大操场看的最后一场露天电影是供批判用的《反击》,这部所谓的阴谋电影因“四人帮”的倒台而夭折,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反击》都无出色之处,除了记住主演是于洋之外,其它已概无印象。
搬出临建棚以后,改革开放40年了,我再也没看过露天电影,但那种热闹的情景铭心刻骨,至今难忘。
二
说到小时候的电影,就不能不提当年的幻灯。这种影视形式,恐怕30岁以下的青少年都没有见过,也不知道什么叫幻灯。这东西现在基本没有了,名字却还保留着。多年以前,有一天孩子玩我的手机,在拍照功能里看到“幻灯片放映”一栏,孩子问我,什么是幻灯片?还真一下子把我问住了。
我们小时候看过不少幻灯片,在电影放映之前,一般要先放幻灯,内容大多是宣传政治口号、法律常识、科普知识或新片预告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带有情节的专题幻灯片。它是当年除了电影之外,广为观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幻灯,利用强烈的光线和透镜装置,把玻璃片上的文字与图画映射在银幕上供观众欣赏。电影在正式开演之前,观众陆陆续续进入场内,这时候放映一段幻灯片,既可以宣传一些相关的知识,又能起到静场的作用。
幻灯的底片不像电影胶片,它是一张一张画好的,投射到银幕上的画面也是固定不动的,就像一幅幅彩色的连环画页面,配置一些简单的文字说明。
改革开放之前,虽然人们生活条件差,但在城市里,看电影的机会比现在要多得多。没有那么多的报纸杂志书籍,没有那么多的歌厅舞厅餐厅,更没有什么电视电脑手机,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相当单调,唯一可以选择的大概只有看电影了。尽管影片的品种有限,但看电影还是人们当时最大的精神享受。放幻灯作为电影的前奏,人们是再熟悉不过了。
我看的幻灯片,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在电影院,而是在邻居家里。
四十年前,我们家楼上住着一家知识分子,父母都在大学教书,他们二十岁出头的儿子酷爱电器,自己用零件攒了一台幻灯机。有时候这位邻居大哥在家里放映幻灯片,我们几个小孩儿聚在一起观看,片子有的是商店里买的,有的是自己制作的。屏幕就是他们家的一面墙。幻灯片的内容早就忘记了,想必没有什么吸引人的情节,无非是一幅幅画面打在雪白的墙上,但我们对这位邻居大哥充满了崇敬、赞佩,他几乎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幻灯机,当时在我们眼里,无疑就是深不可测的高科技,几个零件拼凑在一起就能让它照出彩色的画面,实在是太神奇、太了不起了。这台幻灯机不仅让我们大开眼界,对电器知识充满了幻想和渴望,而且也对拥有知识的文化人倍加尊重。果然这位邻居大哥不同凡俗,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当年就考取了一所重点大学。
现在看起来,幻灯确是技术含量比较低的设施,内容简单,画面死板,但在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当年,也曾风行一时,带给人们一定的精神享受。
三
上世纪70年代,人们的文艺生活异常单调,但比较而言,电影市场还算火爆,一有新电影公映,场场爆满。原因无它,物以稀为贵,可供人们观看的片子太少。“文革”前十几年拍摄的老影片,统统成为“封资修”作品横遭禁演。国外影片,即使是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审查严格,引进的数量也不多。而国产片的生产几乎停滞。据有关方面统计,从“文革”爆发的1966年到1973年,中国竟没有拍摄一部故事片,泱泱大国,数亿观众,可供观看的影片寥寥无几。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文化市场才逐渐松动,看电影还是我们当时最大的精神享受,当时除了新拍的一些國产片《青松岭》《战洪图》《闪闪的红星》《创业》《车轮滚滚》《海霞》《春苗》《决裂》等等,还有重拍的几部经典老片,像《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等等。
重拍的老影片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根据《三进山城》重拍的《侦察兵》,王心刚用雪白的手套潇洒地往敌军炮兵阵地的炮口上一抹,蔑视地瞥着蒋军团长,拖着长腔道:“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那动作、那神态、那声调绝对是帅呆了,酷毙了。从小到大,咱就从未追过什么星,无论是歌星、影星,新星、老星,但要让我说出平生曾经喜欢过的男演员,也就属当时的王心刚了。
当年的许多影片,品种有限,有的同一部片子,我们反复看过多次。尤其是到了寒暑假,电影院放映学生优惠场,五分钱一张票。我们几个同学结伴看电影,成了假期必不可少的节目。
相对来讲,国外影片更受观众欢迎,当年还没有对外开放,放映的基本上都是和咱们关系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像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地下游击队》;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巴不什卡历险记》《爆炸》;朝鲜的《卖花姑娘》《看不见的战线》《一个护士的故事》《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以及几部越南影片。
这些外国影片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中有些精彩的台词,我们都能倒背如流,许多情节让人记忆犹新,留下深刻的印象。像《宁死不屈》里游击队员见面时的暗语“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成了当时孩子们时常挂在嘴边的流行语;电影中的插曲“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敌人的末日将要来临,我们的祖国将要获得自由解放……”,几乎每一个看过的年轻人都熟烂于心。
当年外国影片的重头戏是朝鲜电影,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卖花姑娘》,这部影片让中国观众流尽了眼泪。记得当时人们都说,看《卖花姑娘》时必须带着手绢擦眼泪,人物悲惨的命运,演员动情的表演,让你止不住泪流满面。我当时虽然没流什么泪,但也曾经哽咽难过。周围不少的观众,尤其是一些女士,痛哭失声,悲痛欲绝,场内的哭声此起彼伏。除了影片煽情感人之外,当年中国人的善良单纯可见一斑。
给我印象较深的还有一部越南的影片《森林之火》,印象深是因为那部影片的效果实在太差,从头到尾都是夜间戏,黑洞洞的,看完影片,一头雾水,弄不清演的是什么,只记住了一句台词:“天灵灵、地灵灵,妖魔鬼怪快离开。”
改革开放之前的电影,人们用一句顺口溜来概括:“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顺口溜编得朗朗上口,形象生动,基本上总结出这些影片的特点。
在当年萧条的中国电影市场中,国外影片始终极受观众青睐。“文革”结束后,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拉开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序幕。欧、美、日等国外影片开始逐渐引进中国市场,当年,只要放映新进的国外电影,电影院一定是人满为患,一票难求。届时,影院门口经常有等富余票的观众和倒腾票的贩子。记得1978年,栗原小卷主演的日本电影《望乡》,因为描写了当年妓女阿崎婆卖春的经历,一经放映,立刻轰动一时,电影票票价被炒到十倍以上,即使这样,有的观众还是拿着钱买不到票,有的人站在影院门口手拿一瓶白酒换票,而那时的白酒是凭本供应的紧俏商品,只有年节每户才供应一瓶。
70年代末大量引进的这些译制片,成为观众窥视世界的重要窗口,当时电影市场的火爆程度现在想起来真让人不可思议。有的影院为了增加票房,甚至开设了通宵电影。大概是在1979年冬天,因为转年要备战高考,我们好长时间没看电影了,到了寒假,我们几个同学约好了到一家比较远的影院去看一场通宵电影,印象中有卓别林的两部喜剧默片《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和美国科幻大片《超人》等。晚上十点开演,第一部看得认认真真,聚精会神,到了后两部头昏眼花,脑袋发木,电影演的什么情节稀里糊涂,有的同学困得不行,干脆坐在那睡着了,我算是硬着头皮坚持到最后,但也是半睡半醒的状态。等到早上五点多散场,天还没亮,外面竟然下起了雪,我们顶着寒风,踩着积雪,说说笑笑地去吃早点。那是我平生看过的唯一一场通宵电影。近四十年过去了,电影院连同那一片平房区早已荡然无存,但当年看电影的情景都深深地记在我们心里。
这以后,电影市场开始逐渐解禁,国内国外的好影片数不胜数,旧片复映,外片引进,看的多了,印象反倒不如以前,如果再啰嗦下去,怕有流水账之嫌,不说也罢。
这几年,生活真是今非昔比,丰富多彩,人们再也不必为看电影勒紧裤腰带了。有了网络,看电影也不必非进电影院了,线上线下,一网打尽,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可以观看,露天电影更是在城市中绝迹了。可是在电影院看电影和在家里看电脑、看手机绝对是两回事,根本没法比,就像喝惯了高度的“二锅头”,你非给人家上啤酒,都是酒呀,那味道可差老鼻子了。当年的《泰坦尼克号》,多么煽情的一部大片,我最早先看的光盘,竟然毫无感觉。后来轮到影片上演了,坐在电影院里才感受到那种心灵的震撼,人家把煽情的手段用到了极致,那么大的场面,那么多的投入,在电视上绝对看不出那种效果。
看电影,我记忆最深的还是小时候看的那些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