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科幻小说《古蜀》的审美特质①
2018-09-18丁卓
丁 卓
《古蜀》是中国“新生代”科幻作家王晋康推出的转型之作,作品依托中国神话故事,构建了一个瑰丽的历史科幻世界,展示出作者对传统文化和现代精神的新思考。《古蜀》的审美特质,来源于人物型构和多重文化意蕴。
《古蜀》的三种人物型构
《古蜀》结合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原型,通过建构三种人物类型展开情节,形成小说的审美形式。
神救人的女娲型构
在小说中,天神是拯救力量的人格化,共同发挥着“女娲救人”的作用。这些“女娲”型的天神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高位格神,包括西王母、羲和等,是解救人类的终极存在;第二类是中位格神,包括有强大法力并能变化外形的金凤和朱雀;第三类是低位格神,既有刚被西王母点化的鱼凫、神界的信使青鸟,也有奇异灵兽麒麟、白虎和羊龙等,它们法力有限,充当辅助者。尽管三类神都与人类相亲相爱,关注凡间疾苦,但在《古蜀》世界中,神界自身存在上下级关系,神和人也存在等级分别,呈现出理想化秩序下高低有别的级别秩序。这种秩序最鲜明地表现在昆仑意象上。《古蜀》的诸神都住在昆仑山,昆仑山上有神的宫殿,同时生长着“不死树”,从“不死树”派生出来的神药或蟠桃,有起死回生或长生不老的功效。在昆仑神话体系中,昆仑既代表世界之源,也是太阳西沉之所,既是万物本源,又是黑暗之渊。以上这些都意味着昆仑象征着赐予新生和吞噬生命的双重特性,因此,昆仑是天庭和地府的结合体,成为“天地之脐”,体现了生死平衡的哲学意味。然而,昆仑还是那个昆仑,但神仙已不是那些神仙。《古蜀》并未把中国神话中的神原封不动地搬进故事中来。在形态和内质上,古蜀世界的昆仑诸神已经与中国传统神话的神拉开了距离。
第一,从形态上看,古蜀世界的神在生存态度和外在形体上都是积极正面的,符合人伦标准,这与中外远古诸神都有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和乱伦滥交倾向的设定不同。在古蜀世界中,神的形体与凡人保持一致,神的生存态度与人类别无两样,比如主神西王母,已经褪去了古代传说中“蓬发戴胜”“虎齿豹尾”的装扮,以及善啸、居于洞穴的原始面貌,变成衣着华丽、金玉环佩的青春少妇。神话中的西王母,最早见于《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以后经汉晋文人改造定型,一直到明清逐渐演化至今,由早期的中国西北部族女酋长,到后来的黄帝后妃或东王公之妻,再到天宫仙女之母,她的象征意义不断发生变化,并拥有掌管生死、代表太阴、主管刑罚或女神之祖等一系列职能。《古蜀》中西王母的诸多职能被扬弃,保留了拯救世人的功能,形成了“新西王母”的人物形象,而远古神话中淫逸、暴力的遗风则被涤荡殆尽。
第二,从内质上看,古蜀世界的神与凡人有共同的精神追求,表现出高度的情感认同。普通的凡人无法找到并登顶昆仑,他们在诸神面前是面临生死的生灵,然而人间德才兼备的仁主或建功立业的伟人,有资格被西王母点化为神,这明显是受到修身为佛或羽化成仙的佛道观念影响,但古蜀世界中却显露出更鲜明的民族寻根意识。受到点化成神的鱼凫,是多位蜀民祖先的合体,包括教民养蚕的蚕丛和引领迁徙的柏濩,这说明古蜀世界有意识地把像鱼凫这样的蜀地先祖,解读为开拓进取、创始更新的人性力量的代表,彰显中华文化根脉中奋发图强的民族品性,并暗示这种薪火相传的文明特质对当代社会的巨大影响。
与基督教“道成肉身”相反,古蜀世界遵循的是中国神话里“肉身成神”的传统原则,神不是虚无缥缈的外界权威,而是从凡间升天的人类最强者。在这样的封神原则下,古蜀诸神已非天外飞仙,而是来自人间对喜乐和疾苦的全知全能者。相对于希伯来《妥拉》中动辄惩罚信众的亚卫、古希腊史诗中淫浪暴躁的主神宙斯、日耳曼神话中暴力好斗的奥丁,古蜀世界的西王母的个性特征是慈爱、柔情、宽容、理智,与外显的雍容华贵、恬淡从容气质相统一。而中国古代的女神羲和,被改造成男性神祇,作为西王母的丈夫,幽默善良,不拘小节,勤勉地驾着太阳车与贤妻巡游世界。更有金凤和朱雀,活泼灵动,向往爱情,宽以待人,全然没有因为蜀王杜宇偷窥她们在天池沐浴,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阿尔忒弥斯对待阿克特翁那样,将他变成麋鹿任由猎犬撕成粉碎。整体而言,一方面,古蜀世界的神被改造重塑为人类的保护神,如同慈母一样细心地关注人世苍生的变化。另一方面,由神圣之爱包裹的是人间情爱的内核,既有西王母和羲和追求的夫妻恩爱,也有金凤和朱雀追求的青春恋爱。杜宇和鳖灵之所以分别与金凤和朱雀结为夫妇,正是因为这两对情侣在理想、能力、思想和情感等诸多层面的高度统一,从而酝酿了人神结合的爱情神话。
由此可见,古蜀世界中的“女娲”们,不仅有救济苍生的行为,还有与民众同乐共苦的情怀。在神圣之爱和人间情爱的双重滋润下,《古蜀》中的神成为人间一切美好理想的化身,丰富了中国古代神话“神救人”原型的内涵。古蜀诸神在生存态度、外在形体、精神追求和情感观念上与人类的高度一致,使他们不仅从物质层面救助凡人,同时实现了对人精神与情感的拯救。
人爱人的大禹型构
《古蜀》在凡人世界中,歌颂了建立功业的凡人,重点刻画了鳖灵的经略之才、巴王廪君的扩土之力、娥灵的复仇之志。
首先,鳖灵的经略之才。鳖灵和妹妹娥灵是楚国王族后裔,隐居于民间,过着田园牧歌的生活,但鳖灵欲实现自己的鲲鹏之志。鳖灵对自然的态度是发掘其中的矿藏,打造人类所必需的器具。由此可见,鳖灵在观念中有强烈的入世倾向,他到了蜀国后,向蜀王杜宇献宝玉和竹简,展示自身的才华可为蜀国带来富强国运和文字开化,最终赢得蜀国君臣的一致好感,担当治理洪水的重任,并在千难万险中砥砺前行,即使妹妹娥灵被巴王廪君抢走也没有阻碍他完成为民造福的大业。在这里,《古蜀》并不是要像《浮士德》那样突出神对主人公的考验,而是要展现鳖灵的爱民情怀,这是中国古今无数精英人物的共性。鳖灵经略之才的基础是他富有理智的人格,而这种人格在王晋康的科幻小说中屡见不鲜,从《亚当回归》里的王亚当和钱人杰,《天火》里的林天声与“我”,到《水星播种》里的陈义哲和洪其炎,《新安魂曲》中的谢小东、狄小星和周涵宇,再到《与吾同在》中的姜元善和严小晨,这些人物富有传奇色彩,具有奉献精神。
其次,巴王廪君的扩土之力。巴王代表武力进取,是蜀国的对立面,雄强好胜的他意欲征服蜀地,开疆扩土,严重威胁到蜀国的安全和利益。但是,巴王廪君并不是邪恶势力的代表,他开辟疆土的愿望,正是华夏民族世代生息的前提。回到历史考古中我们发现,巴蜀大地的先民,最初是戈人,随后新的部族为避周朝追杀而从北方迁入,击败戈人后,形成比较强大的蜀人部落和巫臷部落。巴人原本从属于巫臷,后来兴盛起来便取而代之,成为有实力与蜀人对抗的强大部族。原始社会充满部落间残酷的生存竞争,胜者存活,败者湮没。展现荒蛮时代的古蜀世界亦不排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实际上是王晋康“低烈度纵火”的翻版。因此,巴王廪君及其发动的侵蜀战争是必然的,他死后化身为白虎重返人间,就是《古蜀》对他所代表的血性和进取心的肯定。
最后,娥灵的复仇之志。鳖灵的经略之才和廪君的扩土之力,都是民族发展的必由之途,但楚蜀合流与巴国扩张也是民族关系中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又集中体现在娥灵身上。娥灵希望自己和兄长都能功成名就,但在她遇到廪君后,被这个与兄长截然不同的异性吸引,春情萌动。欲望的本质是匮乏,娥灵内心缺乏的是安全感和权力欲,而这些都在她成为巴国王后时得以充盈。《古蜀》中娥灵本质上是善良的,但她被安置在鳖灵和廪君之间,既是鳖灵的妹妹,又是廪君的妻子,既是蜀国的臣民,又是巴国的王后,因此巴蜀的冲突造成了娥灵的悲剧,她的存在也加剧了巴蜀的矛盾。在此条件下,娥灵以复仇为己任,要求巴军上下披戴“万年孝”,为巴王报仇雪恨。万年孝代表对耻辱的铭记,娥灵只有恢复巴王的功业,才能获得安全感和权力欲的满足。因此,她把扩土之力和经略之才合二为一,鳖灵和廪君的人格特质在这个女性形象身上得到完美融合。
尽管鳖灵、廪君和娥灵特质不同,却共同诠释了中国神话的另一原型:人爱人,即部落领袖对他人的爱。娥灵和巴王廪君突出的是个体间的爱情。娥灵爱廪君,忠贞不渝,即使廪君身死,化身为白虎,娥灵仍对其不改初心;相应地,廪君也珍爱娥灵,为求娶娥灵,他答应除娥灵以外不近其他女色。夫妻双方相濡以沫,并诞下爱情结晶。廪君和娥灵的爱情是对大禹和涂山氏爱情的改写,鳖灵治水就更显露出对大禹治水故事的仿写。如果廪君和娥灵凸显的是两情相悦的个人爱情,那么鳖灵就是对民众的博爱。
由上可以说,一方面,鳖灵、廪君、娥灵的人物型构,围绕爱人展开,尽管爱人的方式和结果不同,但其仁者爱人的本质固定不变,这是《古蜀》对大禹爱人的故事重塑的结果。另一方面,一个大禹的故事被演化为三个青年男女的恩怨情仇,在战争情节和家族叙事的催化下扩展了故事容量,不仅探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爱情和事业的悖论,同时也凸显兄妹情和夫妻爱的抉择、血缘亲情与个人雄心的矛盾、家族利益和国家关系的冲突。因此,《古蜀》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的内心境遇,从中国传统神话出发,挖掘出更具现代意义的多元人性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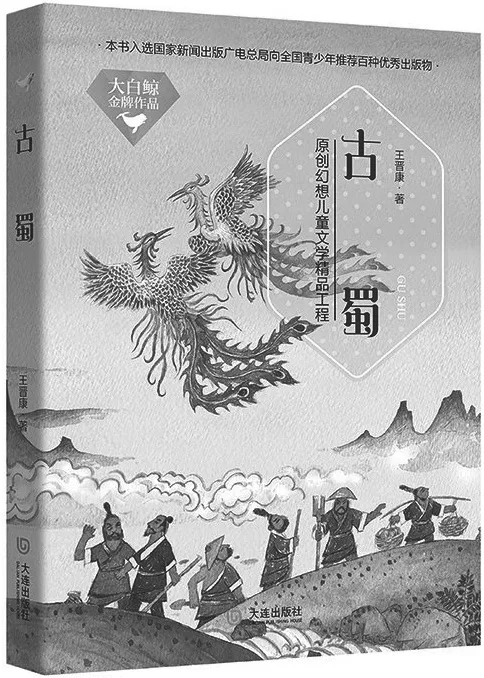
图1 《古蜀》(大连出版社,2017年7月)
为超越的价值型构
《古蜀》中杜宇喜好艺术,对治国毫无兴趣,在得知鳖灵欲发动政变后,杜宇主动禅位,并将亲手打造的箭杆鱼鸟纹王冠献给鳖灵。杜宇和鳖灵君臣易位的情节,是《古蜀》对中国神话传说中杜宇让贤的改写,并进一步突出了杜宇面对权谋的艺术之华。
如同巴蜀战争,低烈度冲突也发生在蜀国国内,鳖灵政变,非由己出,主要因巫咸等权臣极力倡导而成。巫咸在《古蜀》中不是秦桧、贾似道、魏忠贤一类恶势力的代表,而是治国知识分子的化身,是鳖灵品质的扩展。中国古典文化有臣为君死、精忠报国的传统,但也盛行“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的观念,突破了唯皇族正宗的血统论,适应了新时代变化演进的需要,体现出永恒运动、发展向前的朴素唯物史观,因而具有进步意义。然而,《古蜀》没有因为弘扬社会发展进步,就忽略进步所付出的代价:鳖灵问鼎权力之巅,背弃了杜宇当初的知遇之恩,禅位后的杜宇失去了权力、朝臣,甚至没有人身自由,陷入担惊受怕、朝不保夕的绝望之境。
古蜀世界不是瑰丽的田园诗,而是权力斗争的角斗场。人的欲望带来进步,也引发悲剧,《古蜀》没有回避进步的代价,但又极力避免剧变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和毁灭。用政变显示现实的不完美、非人道和无理性作为杜宇追求艺术理想、走向超越的反衬和铺垫,他彰显的艺术才华更弥足珍贵。然而,杜宇的艺术之华不是单纯的个人赏玩,与鳖灵和巫咸们相比,杜宇在政治争斗中保护了内心高洁,展现了他人生价值的三个侧面:
第一,杜宇因艺术享有天神赞誉。杜宇亲手制造的大部分工艺品都是祭神的礼器,洒脱奇绝,超凡脱俗,与中原祭器厚重稳健的风格截然相反,获得神界西王母等诸神的喜爱和赞赏,也为娥灵和妹姬等凡人钦羡。神赞赏他的作品,实际上就是对他所代表的民众敬神行为的赞许,由此可见,艺术不仅是凡间才华的展露,而且沟通天地,成为人与神交流的方式。杜宇是这种方式的集大成者,并为民众赢得了福佑。
第二,杜宇因艺术赢得人神爱情。金凤对杜宇的爱情,正是受到他过人的艺术天赋的吸引。杜宇因艺术而成为与神最近的人类,他打造的太阳神鸟器照耀天空,灵动大地;他制作的青铜纵目面具,象征人类窥探宇宙奥秘和终极真理。应该说,杜宇身上有南陈后主陈叔宝、南唐“词帝”李煜、北宋徽宗赵佶等亡国之君的影子,但他又和那些玩物丧志、仁德尽失的皇帝不一样,杜宇的艺术之华浓缩的是华夏文明五千年的艺术哲思,他能忘我地探求世界元初真理,同时又保持一份轻松幽默和从容淡雅。因此,与鳖灵、巴王和娥灵身上弥漫的沉重艰辛不同,杜宇的艺术之华折射的是人本真的自然光辉。
第三,杜宇因艺术得以超越人间。杜宇禅位后,化为杜鹃与金凤变成的凤凰比翼齐飞,彻底归隐于山林。在这里,杜宇的结局又和西王母提升昆仑山离开人间世界相呼应,纯真的艺术和神界的神秘必然因为人类物质力量的过快增长受到损害,但离开人间不是寂灭或自毁,而是以另一种形态存在于人的精神之中。古蜀世界众神离开人世,成为远古神秘的回声,为人类今天的定位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营养。如果鳖灵是儒家入世的代表,那么杜宇则是孤守艺术、最后超越凡尘的典范,古蜀世界为出世的老庄哲学留置了足够的审美空间,杜宇化鹃后“不如归去”的声声鸣诉,分明是向保有艺术之华和追求精神家园的人们发出的呼吁,因而有积极向上的意义,他已占有一切又不留恋一切的境界,真正体现了佛家“四大皆空”的真谛。
总之,古蜀世界揉进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儒道释观念,塑造了以杜宇为首的开明君臣,重点突出杜宇以艺术之华超越人世的历程,同时印证了包含广博的中国传统文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古蜀》的三层文化意蕴
通过三种人物型构,《古蜀》实现了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改写和重塑,编织出中国现代神话故事。王晋康试图在历史科幻小说中建立理想化秩序,这是为现代社会过度的工具理性造成的人类生存困境寻找解脱之路,也是对缺少理想和秩序的社会状态的深刻忧思。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小说的审美内涵,体现在三层文化意蕴中。
古蜀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间接把握
《古蜀》的深层目的是对神话化的中华历史重新进行编码,进而对现实进行解读。古蜀世界形成山崇拜、玉崇拜、石崇拜、鬼崇拜、虎崇拜、鱼崇拜、鸟崇拜七大崇拜体系,古蜀人以尊崇自然、敬拜神明的方式认识世界,丰富的崇拜对象和万物有灵的精神信仰既表明古蜀人内心的充盈,又反衬出现代人因过度追求物质享受造成的精神困境,突出了宗教信仰、人际和谐和古典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古蜀世界是艺术变形后的中国现实,在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把握中凝结着作者对中国未来的期盼。
古蜀世界是人类心灵家园的精神象征
《古蜀》塑造的一系列人神形象,形成人物型构体系,丰富地展现了完美人性的多元内涵,表达了对祖先和复活的永久期待。祖先是对自然和社会力量的人格化,也是华夏文明的根基。只要祖先形象永无止歇,人就对复活永葆期待,民族机体也将生生不息。但是,《古蜀》并不是对中国神话的复写,而是对华夏文明的综合,古蜀世界的祖先不仅是原始先民的护佑力量,也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化身。入世与出世,进取和超脱,和谐与圆融,具体地呈现在不同的人物身上。古蜀世界推崇的祖先信仰与传统精神,尝试通过跨越时代的对话,表现了对远古文明的追忆和珍爱,体现出古今合一的信念,这就是现代意义上人的心灵家园。古蜀世界尤其指明了人类的心灵家园必须在艺术之华的光晕中来营建完成。《古蜀》通过刻画杜宇对艺术所表现出来的浑然忘我,以个性化的方式凝聚了仁者爱人、舍生取义、大道无形、自然而然、六道轮回、四大皆空等诸多华夏文化因素,这是作品在用中国声音对理想化秩序发出的最强音。
古蜀世界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与转换
《古蜀》的创作离不开中国传统神话和文化的营养积淀,但它是面向当代对传统进行的重塑。在整合不同体系神话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意识重构神话文本,编织出符合现代人审美要求和欣赏习惯的新神话,真正能使读者在“进入一部文本时,他不仅感到作品内发生的事仿佛在他自己身上发生,而且他还在那种本来与他无关紧要的‘别人’的经验形式中,看到他自己的无意识的想象和忧虑……通过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打开一条交流的道路,阅读还起着一种巨大的‘治疗’的作用”。可以说,《古蜀》是以现代思维整合了华夏文明多元的精神命脉,形成以人物型构为审美形式、以理想化的秩序为审美主题的稳定结构,在古蜀世界对现代社会的观照下,又让这一结构中的所有组成部分不断从现实中获得新的生机。《古蜀》这样的古今转换方式,实质就是双向阐发,不仅用今天的意识光照传统的经典,也用古代的声音讲述当代的故事,更在天马行空般瑰丽的想象中对中外文明精髓进行融汇创新。从这个层面讲,《古蜀》以神话为皮相而以科学理性为骨,是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创新典范。
王晋康的《古蜀》跨越了时空,在现实与历史、当下和神话、文本外与文本内等方面实现了不同意识之间的对话,这其实是古老的华夏文明在当代中国再次勃兴的表现。在立足于后工业化时代的背景下,中国文学创作必须在跨越学科视域中改变思维方式,重视历史科幻文学的创作优势,从广博的中外传统文化中萃取素材,整合重塑成想象力丰富的幻想篇章,以审美的方式展现人类共有的精神理想,实现不同民族和时代之间的交会对接,而这种交会对接最有活力的形式,就是从讲述现代的新神话入手,这也是《古蜀》在跨越时空进行对话时所鲜明体现的。因此,《古蜀》为历史科幻小说进一步健康发展树立了三个标准:其一,通过回归神话来反思现代社会的弊病,并塑造一种新的乌托邦理想;其二,通过发掘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人际关系,提供认识世界的新视角,并寻获新的审美体验;其三,预警社会灾患并减少新的灾变带来的破坏力。在作品的结尾,古蜀世界和现实世界连接在一起,形成历史和现代的交相辉映、科幻与现实的有机统一,隐喻对理想化秩序的希望就隐藏在现代生活中,这既是这部作品思想价值的最高展现,也是其审美特质的最后升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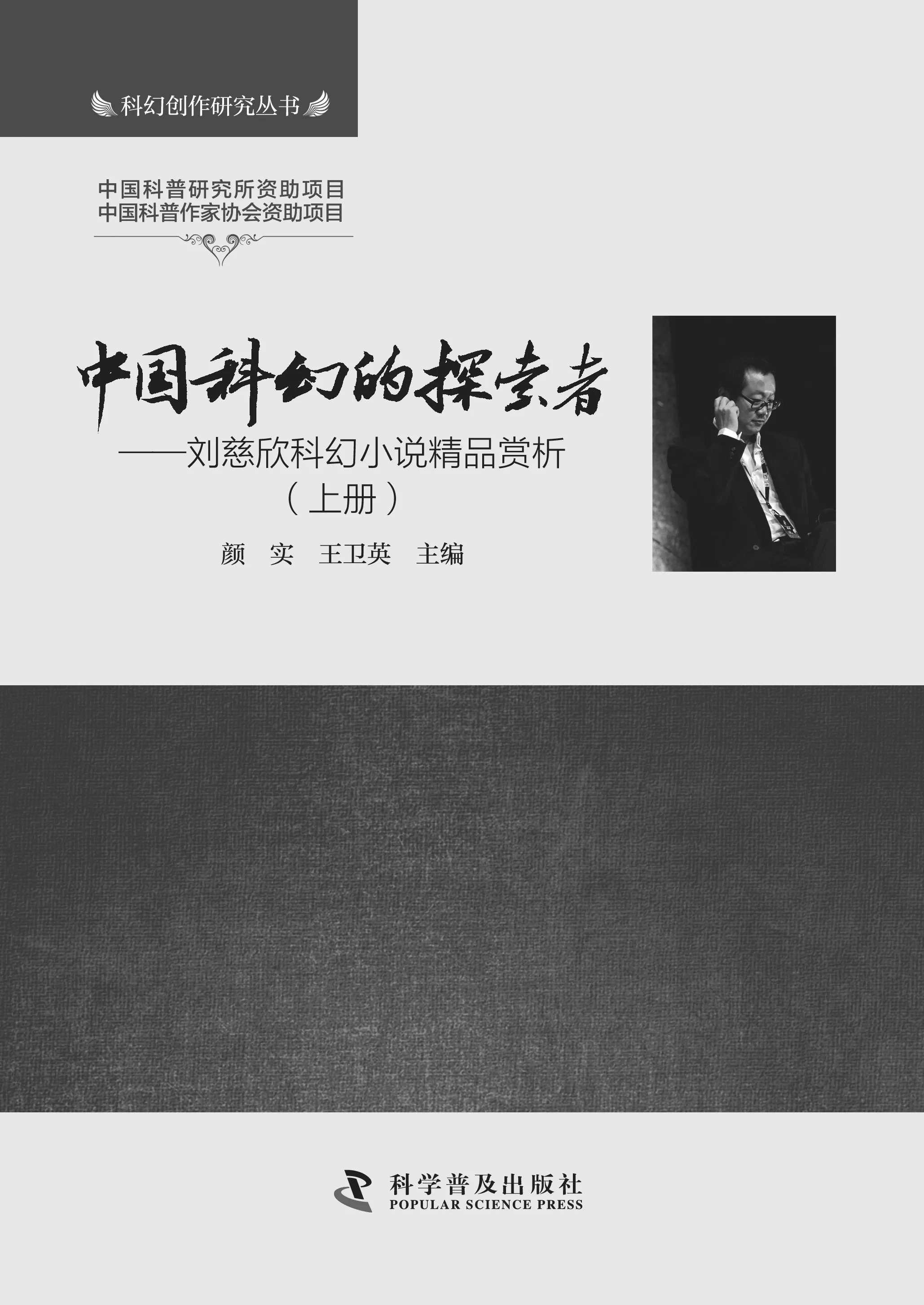
《中国科幻的探索者——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赏析》颜 实 王卫英 主编科学普及出版社,2018年6月
本书首先对刘慈欣的作品进行梳理,遴选了40篇(部)科幻精品(选录作品基本涵盖其所有的短中长篇小说),然后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深度赏析,凸显刘慈欣小说的创作特色和风格,挖掘其科学文化内涵和文学审美价值,为科幻作家的创作提供理论支持,为科幻的深入研究搭建理论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