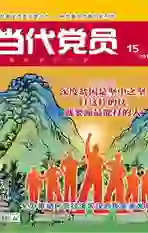心理学在祝乐村派上了用场
2018-09-10王小运
王小运
打好脱贫攻坚战,群众工作是基础。我是学心理学专业的,来到城口县鸡鸣乡祝乐村任第一书记,原以为心理学没有用武之地,但是,一件事情改变了我这个想法。
在最初的贫困户动态调整中,我们坚持按照标准严格执行。在这个地方,多年的扶贫让部分人滋生了“等靠要”思想。因此,部分没有评议上建卡贫困户的人心里不那么痛快。其中,有一户村民叫李自均,祝乐村4组人,之前一直在外务工,年近40岁才找了一个老婆。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的老婆,祁某。
在动态调整评议结束后,我和副乡长、村主任组成工作队,一起去没有评议上建卡贫困户的村民家走访,解释相关政策。当天,我们走了13户,晚上6点多才到祁某家里,又冷又饿,解释了半小时后,便下山吃飯了。可能是解释的时间不够,又或者是我们的解释没能让祁某满意,第二天下午,祁某给我打电话,说要找我谈谈。
那天,祁某带着她三岁半的小孩来到我的办公室,看起来有点凶,我猜想应该是为了贫困户调整的事情而来。于是,我赶紧去旁边找了一个苹果和两个小蛋糕给她女儿吃。她看见我对她小孩这么友好,气也消了一半(运用心理学上感同身受的方法,我是一个四岁半孩子的父亲,以这种角色进入谈话,效果更佳)。
在与祁某的谈话中,我更多的是听,让她倾诉,当然也解释了扶贫的各项政策。倾听中,我了解到祁某的真实困境:李自均家的房子属于危房,之前自己改造了房屋,因政策发生变化,他家没能拿到相应的房屋改造补贴。李自均的女儿在屋前意外受伤,面部受伤严重,未来三年植皮美容还得花至少30万元。当时,因为过度担忧和劳累,祁某肚子里两个月大的孩子流产了。这一年,家庭的种种变故让祁某充满担心、焦虑,她无法疏解这种情绪,并将其发泄到干部身上,因此对我们常常表现出抵触态度,去年还曾把以前的第一书记关在屋里不让走。
对于祁某,我首先采取了倾听,建立了信任关系后,用自我暴露的方式,说了我自己的故事,缓和了她的攻击态度。同时,对于其一些不合理的想法进行疏导,引导其发现正能量,而不是纠结在过去的不幸当中。
三个半小时后,祁某带着孩子满意地离开办公室。事后我发现,祁某没那么纠结了,也不再充满攻击性了。
我常听村里的干部说,基层工作最难的还是做人的思想工作。在基层待了一年,我也遇到过群众的不少矛盾和怨言:他们有的是因为没享受到有关政策,有的是因为利益协调不到位……这些问题,我想每个第一书记都碰到过。开始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也一头雾水。后来,我用专业所长,发现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其实也没那么难。
心理学最直接最管用的法子就是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具体到扶贫工作上来,就是能够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了解贫困户到底在想什么,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注重群众的利益诉求。比如,在一次走访中,我发现一对双胞胎留守儿童和我的小孩年龄相近,于是拍了照片发给家里人。晚上,女儿给我打电话,用稚嫩的声音问我:“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听到女儿的声音,我平静的心不再平静,想到了白天遇到的留守儿童。尽管在城口乡下,但我每月还能回去一两次,而这些小孩的父母长年在外务工,完全不能陪伴他们成长。那晚,我夜不能寐,心情十分沉重。第二天,我立即对全村133名留守儿童展开调研,并呼吁帮扶单位重庆邮电大学的师生积极献爱心,让133个“心愿清单”全部得到满足。这一次小小的尝试,也得到了村民的极大认可。
现在,我深深地感觉到,只要有人的地方,心理学就会有用武之地。对于农民而言,很多时候就是利益分配问题,但是只要政策执行不偏不倚,老百姓还是会理解的。对基层干部来说,要做好说服工作,必须是因人而异,针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根本点是建立信任,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说问题,在政策范围内,寻找最大公约数,最后问题往往能够得到圆满解决。
(作者系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团总支书记、城口县鸡鸣乡祝乐村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