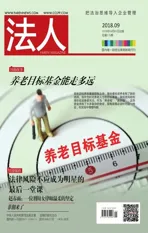没有人该成为现实的旁观者
2018-09-10法人徐若风
文 《法人》特约撰稿 徐若风
从2015年金棕榈颁发给《流浪的迪潘》(法国)起,短短四年内已经有包括《我是布莱克》(英国)和《小偷家族》(日本)三部电影,以“底层无血缘亲情”的故事来探讨社会现实问题,从而在戛纳获得大奖。显然,这是一个值得被关注的现象。
《小偷家族》这部电影,是目前是枝裕和电影序列中构成最为复杂与矛盾的作品,他本人也言及:“这10年来他所思考的东西,都放进了这部作品当中。”从表层出发,这是一部《无人知晓》《如父如子》式的,底层群像在各方驱动后的“多元家庭重组”情节剧,描绘了一个靠犯罪才能维系亲人关系的家庭,在面对社会直视时的轰然坍塌。而对它继续深入探讨,则会发现这部电影,代表的是一场对传统家庭与社会现实等多个观念角度上的反观。
血缘之外的羁绊
《小偷家族》的创作基点,源自一家谎报亲人没有去世,继续骗取养老金的社会新闻。是枝裕和就这起新闻事件,展开对当下日本社会、家庭的思考。一个“法外之地”,该如何被赋予情感的温度?一个社会新闻的背后,究竟纠缠着什么样的羁绊?《小偷家族》对这些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问题进行发问。
倘若说国内观众“熟悉的是枝裕和”,是从《海街日记》《比海更深》这类作品中所显露出温暖与爱意的导演。那么,《小偷家族》则显然与它们都有着一道界限,它更像是枝裕和用这层“家庭剧拍法”的包裹后,对自我早期电影的一次回归(《距离》《无人知晓》),又是对《第三次杀人》的延续。人们常习惯于用“家庭”来概括枝裕和的一系列作品主题,却会忘掉导演本质上并不是在讨论这个字眼,而是它背后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关系。
在影片发展的前段,是枝裕和将用克制的笔法构建了这个不寻常的家庭,亲情与血缘、法理与情感的辩证关系由此展开。
电影始于一场偷盗,在一个东京的冬日,善于窃取财物、成日游手好闲的父亲柴田治带着儿子祥太在超市搜刮偷盗家人的日常用品,随后在回家路上捡来了小女孩由里,把她带回了家。因为由里的原生家庭对她进行虐待,一家人最终选择把她留了下来,但这在日本的法律上实则是犯下了“诱拐罪”。
这个家残存在一个破旧平房里,还住着年迈的奶奶柴田初枝,柴田治的妻子柴田信代,以及“信代的妹妹”亚纪。他们依赖“养老金”过活,当这笔钱不够用时,就会各自找活做——偷窃、临时工,甚至是在风俗店中表演。就是在这个看似“贫民窟奇情”的情节人物设定中,是枝裕和将六位家庭成员间真挚的情感和暧昧的身份、内心的秘密和惊悚的欺骗交织在了一起。当结局揭晓,我们会发现所有人互相之间都没有血缘关系。
和前些年由陈可辛导演的《亲爱的》相似,人与人的关系即便在血缘之外,也能获得延续的可能。在缺少情感联结的社会里,偷得一点爱,便能继续努力地活下去。“偷窃”,不仅为这家人维持了生活的日常,还成了他们互相之间结识的关键。在机缘巧合的相遇里,亲人间的感情借由冲突而产生。
在电影中,这个家庭便是一个“多元家庭”的缩影。表面上看,他们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但实际上无人因血缘而相连。每个角色都离开了原生家庭,他们的重组来自于个人意愿,类似于一份无形之中的契约,靠情感来造就。
是枝裕和希望利用“生下孩子就成为父母了吗?”“无法选择的亲人和自己选择的羁绊孰重孰轻?”这些社会话题抛带出更深层次的探讨。其实,这些话题远不止于聚焦“血缘”这一概念本身,更重要的,是直指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
在现代社会下,家庭意味着什么?只有法律意义上的关系才是牢固的吗?当一个家庭无法提供温饱,无法提供安全,甚至无法提供身份之时,它又因什么而存在?
社会关照的真相
“岛国根性”是《小偷家族》的导演是枝裕和对日本社会所想要着重做出的反思。他认为,“由于自身不成熟,个体对笼罩整个群体的(在外界看来只能称之为暴力的)单一价值观不加批评、随波逐流,并沉湎在如此便能心安理得的错觉当中”。
作为旁观者,大多数人也许难以对这样一起法律事件做到感同身受,对新闻的阅读往往会停在信息量上便浅尝辄止,无法意识到这背后发生的真相所谓何物。

柴田治与信代两位主角,代表的便是日本经济历次低迷后的东京社会底层的中年人们——日雇劳动者。他们按日结账、获得工钱,收入低且劳动环境恶劣,无法获得工伤保险和社会保障等劳动保护。信代在奶奶过世后提议将她掩埋,不申报死亡或举办葬礼,很大的原因便是为了能够继续冒领养老金。这么做看似耸人听闻,实际上在日本却是“常见现象”,不少家庭铤而走险,隐瞒老人离世的消息,甚至处理掉老人的尸体——2010年,日本全国调查“百岁老人是否真的在世”活动,仅在兵库县一个地方,便发现了1万多名老人其实早已去世,但仍由家属冒领养老金。
而一家人居住的破落的家宅,在东京常常会被当作危房,多已被政府以低价“游说拆迁”。在电影中,每个角色都没有独处的房间,孩子们只能在拥挤的柜子中睡觉、学习。在这个家庭组成之前,他们都曾有各自的居所——亚纪是奶奶的前夫在重组家庭后的孙女,从奶奶的探访里,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原生家庭显然是中产阶层;由里最后回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身边,再洁净的公寓都在陡然之间变得阴冷、无趣。
以上的种种设定,都显示出了电影对现实投射的残酷一面。但同时,是枝裕和在处理这些社会话题的时候,又采取了非常不一样的角度。他是一位擅长从自我生命体验中提取创作元素的电影导演,对真相的揭露也往往不止一面。
哪怕现实残损,情感却能在荫翳里透出光亮,在角落里被无声传递。人与人之间产生共鸣的经历,为这部作品带来了举重若轻的力量,让它变成了一个汇聚记忆的场所——信代发现小女孩由里身上有和她一样的烫伤印痕;在之后燃烧她的衣服时也紧紧抱着,透露出曾有过的类似经历。亚纪与4号先生的首次谈话,言及的是由里如何爱惜新买的泳衣,自己也曾如此;而这场看似奇妙的露水情缘,其实早就在信代的人生中上演过了。
同样,在《小偷家族》最后的离别时刻,多重的反转与落幕,经由前期大量的铺陈,达到了堪称是“深水炸弹”的效果:信代面对审讯时无言以对而又无法自持的恸哭,告诉祥太身世时看透一切的微笑;柴田治与儿子祥太最后一次在雪夜戏耍、堆雪人;祥太告诉柴田治真相后,在车上回头用默语道了一句“爸爸”。一切都在决绝的沉重中,带着无法被轻易言说的复杂的温暖,在瞬间倾泻出了磅礴的情感。他们的生命交叠,在这一刻分崩离析,却又仿佛更紧密了。
这部电影,看似是以虚构的方式,来演绎特定的真实新闻事件,实则是利用环境空间与一年时间线的流动,将生活流的叙事运转起来,让观众体验他们被抓前的日常生活。于是乎,这些“被遗弃”的角色,无论是被父母遗弃、还是被社会遗弃,他们首先都不是作为冷冰冰的“罪犯”身份,而是以鲜活的个体来存活,相偎相依、互相取暖。
通过如此的刻画方式,令电影对现实的关照,迈入更为普遍的情境之中,从而引发更为广泛的共鸣。“违法”“犯罪”这类字眼,往往连带着的是“法不容情”,却在这部电影中被唤起了温度。换言之,真相需要被凝视,更需要被经历与体验。是枝裕和所想要描绘的,是“只有平凡人生活的、有点肮脏的世界,忽然变得美好的瞬间”。
没有人该成为现实的旁观者——这就是《小偷家族》与它的导演是枝裕和,在面对现实时所采取的发声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