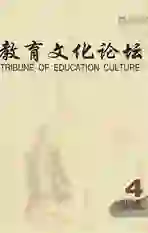教育如何影响人们的品牌消费态度
2018-09-10林小莉孙伦轩
林小莉 孙伦轩
摘 要: 高品质的消费旨趣是人们接受学校教育的非货币收益之一,也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心理基础。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与人们的品牌消费态度偏好呈显著正相关,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连接两者的重要机制。教育程度对品牌消费态度的影响仅在高中以上水平的群体中存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累积性。这为我们基于学校教育的政策供给来扩大居民消费提供了新的线索。
关键词: 教育程度;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品牌消费态度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8)04-0097-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8.04.020
一、问题提出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区间,当消费旺盛经济增长率就高,消费不足,经济增长率就会滑落。[1]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新时期政府工作的核心关注点之一。一般情况下,消费态度作为一种内在的行为倾向,它直接影响和决定消费者的行为。因此,培养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积极消费态度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基础。在政府可利用的長效政策工具中,学校教育是培养消费态度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无论是对物质消费力还是精神消费力的提高,学校教育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改善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进而扩大和改善人们的消费需求。[3]通过教育来提升内嵌于人身体之中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态度,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善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4]
作为一种非货币收益,教育的消费收益研究在学界非常悠久。亚当·斯密、凯恩斯以及舒尔茨分别在不同程度上提及教育对消费行为的影响。[5][6][7]然而,大量研究都源于西方国家,国内的相关实证研究还不多见。中国作为经济增长最为快速、消费结构更新最为剧烈的国家应该得到应有的关注。消费行为学认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上升,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越来越依赖于商品品牌所带来的心理情感满足以及品味体现。[8]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实证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提升了人们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并显著影响了人们的品牌消费态度。这一发现初步印证了上述猜想,证实了学校教育对于人们消费态度和观念的影响,也为新时期基于教育供给来扩大消费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
(一)学校教育与居民消费
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等人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指出教育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培养经济发展所需人才的生产功能。舒尔茨还认为,所有这些研究都忽略了教育的消费性价值,教育总是创造一种消费资本的形式,这种资本具有改善学生日后生活中的消费爱好和消费质量的特征。[7]在国内,尹世杰较早在观念层面上指出学校教育对消费观的影响。他认为,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而这有赖于教育,有赖于学校对健康文明消费观念的传播。[2]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一般就越能理性决定自己的消费行为,从而去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9]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城镇居民在消费决策技能、商品识别技能、商品的使用和维护技能以及消费维权技能都存在较大差异,教育对消费技能起着决定性作用。[10]受教育程度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以及消费方式等方面的相关关系相继被发现。[3]消费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最关键因素,收入只是其基础条件,而教育在这中间起到了引导的作用,教育传授给人们消费技能,培养人们良好的消费习惯,教会人们如何去科学合理地消费。[11]消费者的行为很大程度都是后天习得的,人们通过学习获得绝大部分的态度、价值观、品位、行为偏好。[12]个人受教育程度背景实际上作为一种潜意识因素影响了其日常消费行为。由此我们形成假设: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越具有品牌消费意识。
(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作用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人们对所处阶层的主观感受,它使得人们形成对社会、人生的不同认知层次和心理。[13]消费建构阶级是西方学者关于消费和阶层认同研究的一条主线,即认为消费行为本身可以作为界定社会阶层的标准之一。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对“地位群体”的定义。他指出,“地位群体”是根据其货物消费的原则来划分,表现为生活方式的特殊形式。[14]1899年,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描述了成功的工商业精英们表现出来的炫耀性消费,这种消费行为是有闲阶级地位和尊荣的社会标志。[15]布迪厄在《区隔》一书中谈到,消费是一种区分手段,可以用来确立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消费行为、生活风格在成为一种“惯习”后就具有预先标志等级的功能。
在国内,消费被认为是社群划分的一个维度,同一社会阶层的人的消费方式趋向同质。他们的生活方式相互影响,在能表现他们社会阶层归属的消费行为上具有一致性。[16]消费与认同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事实,认同支配消费,消费又是认同的显现,在阶层认同中消费起着重要的作用。[17]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更能体现人们的自我期望以及与其他群体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感。[18]当基本的物质消费所带给人的幸福感逐渐淡化时,品牌消费更能够给予消费者一种文化附加值,使其感受到相应的身份、地位、荣誉以及自信,提升消费者效用。相对于西方消费者,中国消费者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更倾向于使用商品品牌的象征性价值消费来构建自己在社会中的阶层和地位。[19]由此我们形成假设: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个体越具有品牌消费意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资本和文化技术资本呈现出的较大相关性,使得教育成为改变个体经济资本的有效手段。[20]1967年布劳和邓肯提出经典的地位获得模型进一步证实,无论是居于调节作用还是地位传递,教育对个体地位获得的重要性。[21]功能主义者认为,个体通过教育而获得的技能水平是社会分层的关键维度。同样在现代社会中,教育不仅仅是一种资源,同时也作为一种重要的地位获得机制,与社会阶层的结构以及社会流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22]因此,学校教育不仅可以通过直接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与消费技能来影响消费态度,还可以通过提升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而改变他们的消费品味和旨趣。[23]人们所受的教育、职业、财产、收入水平均影响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其需求和消费模式也不一样。[24]由此我们形成假设: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以及假设在控制住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以后,受教育程度对品牌态度的积极影响会减弱。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 年度调查项目。CGSS 2010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并且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大量实证研究。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方案,调查点覆盖中国大陆的全部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调查对象为 17岁以上的中国居民。CGSS 2010 调查数据总样本量为11783。剔除了在重要变量上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进入各分析模型的实际样本量为9001。
(二)变量选取
1.因变量
本研究使用品牌消费态度作为因变量。借鉴李颖晖(2014)的做法,使用CGSS2010中的五道问题进行测量,例如“买东西应该讲究实用,是不是名牌不重要”以及“我周围的人有名牌货,我也得有”等,受访者在5点量表上依次评价他们对四道题的同意程度,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指标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7,达到了测量学上的可接受水平。
2.自变量
受教育年限。將受教育水平赋值为受教育年限:没受过任何教育=0年;小学=5年;初中=9年;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12年;大学专科=15年;大学本科=16年,研究生及以上=19年。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教育阶段的影响差异,我们构建了教育水平的虚拟变量:没受过任何教育=0,小学=1,初中=2,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3,高等教育(大学专科及以上)=4。
3.中介变量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为了呈现结果的稳健性,使用三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即当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十年前社会经济地位和十年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问题为:“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十年前/十年后在哪个等级上?”每个问题的回答选项: “1分”代表最底层,“10分”代表最顶层,被调查者在1-10分内给自己打分,进而形成一个1-10的连续变量。
4.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户口、年龄、民族、政治身份、收入、自评健康和自评经济等。相关变量的具体操作以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三)研究步骤与模型设计
上述公式中,Y代表居民的品牌消费态度,X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M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方程(1)代表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品牌消费态度的总影响,方程(2)代表居民受教育程度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方程(3)代表受教育通过中介变量对居民品牌消费态度的影响。模型中所有被解释变量均为连续变量,采用OLS进行多元回归。考虑到减少篇幅以及步骤调整的合理性,我们首先呈现方程(2)的结果,然后共同呈现方程(1)和方程(3)的结果。
四、实证结果
(一)教育程度对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按照研究步骤,我们首先检验了教育对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表2所示,分为教育年限模型和教育级别模型。在教育年限模型中,受教育年限对人们的当前社会经济地位(B=0.0285,P<0.001)、10年前社会经济地位(B=0.0622,P<0.001)、10年后社会经济地位(B=0.0261,P<0.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人们的受教育年限越长,越倾向于认为自己占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教育级别模型中,随着个体的受教育级别越高,个体的自评社会经济地位也整体趋高。具体来看,在以“当前社会经济地位”为因变量的模型中,相对于文盲群体,受教育水平为小学(B=0.125,P<0.05)、初中(B=0.147,P<0.05)、高中(B=0.254,P<0.001)以及大学及以上(B=0490,P<0001)的个体均认为自己占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且影响的系数呈梯级增长,说明教育可能发挥较为线性的积极影响。在以“10年前社会经济地位”和“10年后社会经济地位”为因变量的模型中,我们也观测到类似的趋势。因此,综合两个模型的结果可以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的三种自评社会经济地位都越高,假设3得到验证。这与既有的研究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教育程度高者在社会中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25]
(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教育与品牌消费间的中介作用
表3呈现了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在个体受教育年限和品牌消费态度间的中介作用。模型1显示,受教育年限对人们的品牌消费态度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B=0.0082,P<0.001),假设1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2—模型4分别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当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十年前社会经济地位和十年后社会经济地位。结果显示,个体自评的当前社会经济地位(B=0.0443,P<0.001)、10年前社会经济地位(B=0.0218,P<0.001)、10年后社会经济地位(B=0.0311,P<0.001)均对品牌消费态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2也得到支持。与此同时,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从模型的R方来看,加入中介变量后的模型解释力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强,说明三个维度的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均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中介作用,假设4得到验证。模型5是将所有变量均纳入的全模型,结果显示,当前社会经济地位(B=0.0325,P<0.001)和10年后社会经济地位(B=0.0117,P<0.05)的影响仍然显著,10年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不再显著,且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下降,说明受教育年限可能主要是通过当前社会经济地位、10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产生影响。相比较过去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人们的当前自感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对未来的地位预期更能影响消费行为中的品牌偏好。
表4呈现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不同受教育级别和品牌消费态度间的中介作用。模型6显示,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高中(B=0.0633,P<0.05)、大学及以上(B=0.166,P<0.001)的教育对品牌消费态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初中以及小学的教育并未对品牌消费态度产生显著影响。这个结果说明教育对品牌消费态度的影响具有累积性和阶段性。
模型7-模型9在模型6的基础上加入三个维度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结果表明,当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B=0.0437,P<0.001)、10年前社會经济地位(B=0.0220,P<0.001)、以及10年后社会经济地位(B=0.0304,P<0.001)显著影响居民品牌消费态度。纵观模型7-模型10,发现加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以后,高中水平的教育对品牌消费态度的影响不再显著,这说明自社会经济地位在高中教育和品牌消费态度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大学及以上水平的教育的影响仍然显著,但系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说明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这些发现进一步支持了假设1、假设2和假设4。高学历人群有着较好的人力资本积累,具备货币支付能力的同时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较易形成地位群体和阶级认同感,进而形成象征高品质的品牌消费态度。
五、结论与讨论
“教育改变命运”的观点深刻阐述了教育对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的重要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给我们带来的文化资本不仅有学业资本的积累,更有品位资本的上升。[26]相较于学业资本,品位资本更能体现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文化趣味、消费方式等方面的区别。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研究发现,教育对人们的品牌消费态度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影响仅在高中以上水平的受教育群体中存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累积性。通过机制分析进一步发现,学校教育除了可以直接培养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态度,还可以通过提升人们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进而影响到人们的品牌消费态度。
消费社会学家认为,人们会通过有意识的消费行为来维持、整合一种群体的认同感,使自己成为心理上认同的某种阶层或群体。无论是物质消费还是文化消费,往往都被人们当成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人们通过对不同商品符号的消费来保持自己的个性,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维持了群体的特征。我们的研究证明,学校教育提升了人们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进而促使人们形成更有品质的消费态度。教育产生了一种明显的知识成层现象引发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文化资本的再分配,使新的阶级或阶层产生。品牌消费在心理层面成为某一阶层的必需品,其符号价值要远远超过它的使用价值。高学历群体受过长期的教育和文化的熏陶,具备了享受品牌消费效用的两个重要保障条件:高收入的生产能力以及享受高质量生活品味的能力,因而在消费态度中显示出了较强的品牌偏好。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以期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与改进。例如,本研究使用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虽然具备一定信效度且被广泛使用,但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个体主观判断的影响,期望未来的研究使用更为客观的指标进行测量。此外,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是一个截面数据,对内生性以及异质性问题的控制是一个难题。为了更好的揭示教育程度与品牌消费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需要未来研究使用动态追踪调查数据以及自然实验等方法进行更为严格的讨论。
参考文献:
[1] 刘东皇,谢忠秋,李向东.中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5(22).
[2] 尹世杰.消费力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3] 张学敏,何酉宁.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影响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6(3).
[4] 张学敏,陈星.教育:为何与消费疏离[J].教育研究,2016(5).
[5] 亚当·斯密著,唐日松等译. 国富论[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6]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 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8] 王宁,杨燕青.中国人的面子观对品牌购买行为的影响——性别的调节作用[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5,45(22).
[9] 钱智勇.对教育收益的经济学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8(3).
[10] 张学敏,田曼.受教育程度对城镇居民消费技能的影响研究[J].消费经济,2009(3).
[11] 王冰.教育的消费性价值——研究“伊斯特林悖论”的新思路[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2(3).
[12] 冯丹.高学历者受教育程度与消费行为的相关性分析[D].重庆:西南大学,2008.
[13] 徐淑一,王宁宁.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居民自感健康[J].统计研究,2015,(3).
[14]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5]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6] 彭华民.消费社会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
[17] 王宁.消费与认同——对消费社会学的一个分析框架的探索[J].社会学研究,2001(1).
[18] 胡荣,叶丽玉.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问题(专题讨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5).
[19] 朱晓辉.中国消费者奢侈品消费动机的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7).
[20] 李莉.教育对社会分层流动的影响——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J].现代教育科学,2007(2)
[21] Blau P M,Duncan O D.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67,33(2).
[22] 陈彬莉.教育:地位生产机制,还是再生产机制——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理论述评[J].社会科学辑刊,2007(2).
[23] 张学敏.教育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4] 夏建中,張达.我国城市白领群体生活方式的社会学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03(5).
[25] 陈卓.桥梁与屏障:当今中国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9(6).
[26] 陈卓.教育场域中的文化资本与社会分层[J].上海教育科研,2013(9).
(责任编辑 涂 艳)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consumption attitude is one of the non-monetary benefits of schooling and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expanding consumer demand.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10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finds that the education level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eoples positive brand consumption attitude,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o connect the two variables above.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al level on the attitude of brand consumption has obvious cumulative effects, which only exists in groups who are above the high school education level. This provides us with new clues for expanding the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with the supply of policies based on school educ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 level;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brand consumption attitude